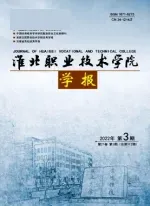关于《涅槃无名论》研究的一些问题之我见
张兆勇,曹二林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文学与语言研究·
关于《涅槃无名论》研究的一些问题之我见
张兆勇1,曹二林2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关于《涅槃无名论》的真伪问题,现代以来,汤用彤、石峻二先生所持的“伪著”观点影响很大。联系《肇论》中其它几篇及《维摩经肇注》中僧肇的有关论述对汤、石二先生经常用以为证据的几点提出质疑,以就教于学术界。
真伪;学术;佛学进程
今天常见的《肇论》通行本有三个:一是唐元康《肇论疏》三卷;一是宋本《肇论中吴集解》;再一是元文才《肇论新疏》。其中的编目依次是《宗本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答刘遗民书》、《涅槃无名论》等。上述篇目除《宗本义》外,均见于南朝宋明帝时人陆澄撰《法论·目录》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今本《肇论》中篇目散见在《法论·目录》的不同类别中,却并无《肇论》之名;(二)《涅槃无名论》一篇于篇末附《奏秦王表》目次,这是最早记载有僧肇著作的目录。此后《涅槃无名论》一篇被梁慧皎《高僧传·僧肇传》所节引,并记述了本记的写作契机,同时也节引了《奏秦王表》文。至陈时小招提寺僧慧达《肇论疏》序里提到了《宗本义》一文,亦在《涅槃无名论》前加上《表上秦主姚兴》一文。据石峻先生说法慧达《肇论疏》的篇目次第仍不同于唐以后《肇论》的篇目次第,故今天通行本的篇目和次序只可看成是陈以后迟至是唐人才有的定本。
以上是我们简明论及《肇论》之书形成的大致情况。
上述《肇论》中的这些篇目,其中的《宗本义》与《涅槃无名论》被近代的学者怀疑是伪作。《宗本义》一文我们在本文里姑且不论。关于《涅槃无名论》的真伪,汤用彤先生以为《涅槃无名论》被最早怀疑为非僧肇所作出自唐人道宣《大唐·内典录》。该书云:“涅槃无名论九折十演论,无名子,今有其论云是肇作,然词力浮薄,寄名无有。”但汤氏的旧友吕徵先生则以为《内典录》原文“无名子”以下一段是批评另一种书名为《无名子》的,与《涅槃无名论》无涉。吕氏的这个结论在学术界也很有影响,据他的结论,最早怀疑《涅槃无名论》为伪的帽子不能加在盖道宣的头上。
现代以来,持《涅槃无名论》一文为伪作者主要是汤用彤、石峻二先生。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提出了一些证据主要见于《竺道生和涅槃学》一文[1]以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第十六章。又,石峻先生在汤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内容分析,分别在1944年发表《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一文[2]295及近年发表《〈肇论〉思想研究》[3]等证明《涅槃无名论》为伪作。
但我们细读石氏的近作,以为他的观点略有缓和,其云:“总之,若果肯定《涅槃无名论》为僧肇所作,必须将这样一些思想上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的原则系统而深入地作出合理的说明”,此种结论较他在四十年代的结论有了细微的差别。
以下,我们想就汤、石二先生关于证《涅槃无名论》为伪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责成几个方面,通过研读《肇论》①及《维摩经》[4]肇注,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涅槃无名论》的写作与《上奏秦王表》
分三个问题看:
(1)关于《涅槃无名论》一文的写作时间,今天可资参考的材料有二:一是《上秦王姚兴表》,再者就是慧皎《高僧传·僧肇本传》。
其《上秦王姚兴表》有云:“什公门下,十有余载……不幸什公去世”。
其《高僧传·本传》云:“及什亡之后,追悼永往,翘思弥厉,乃著《涅槃无名论》”。
据僧肇《鸠摩罗什法师诔》云:“什以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死于大寺”。癸丑乃秦弘始十五年,亦即晋义熙九年。又,《高僧传·本传》载,肇死于义熙十年,故《涅槃无名论》只能作于义熙九年至十年这一年间。汤用彤先生以为从《涅槃无名论》的文章看,似写作远于什公之卒,我以为非是,我们可以从《维摩经注》里检出肇公不止一次地申述涅槃乃超越生死,可能他以为作此文专言生死最表哀悼之情。故师父刚圆寂写此文在情理之中。又,肇公死时年仅三十有一,如不误,也可说明他已视死以坦然,体现在文中则是虽悲而文理清也。
(2)关于写作《涅槃无名论》一文的目的。
《上秦王表》继续说:“殿下圣德不孤,独与什公神契……一日遇蒙答安城侯姚嵩书……然圣旨渊玄,理微言约,可以匠彼先进,拯拨高士。惧言题之流,或未尽上意……辄作涅槃无名论,论有九折十演,博采众经,证成喻,以仰述陛下无名之致。”
又,《高僧传·本传》则云:
“什公辞世,肇悲怯不已。乃作《涅槃无名论》……《论》成之后,上表于姚兴……”
上面两段文字略有不同,但不妨我们推测肇公写作此文的目的可能关乎的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对什公去世之哀思;二是感于姚秦主能妙契什公之神思,文中提出涅槃无名,既能仰述圣意,又能发挥哀悼之悲情也。
(3)关于《奏秦王表》里征引秦王姚兴《答安城侯姚嵩》的书信。
《奏秦王表》里征引秦王姚兴《答安城侯姚嵩》的书信共有两段。
其第一段云:“问无为宗极,何者?夫众生所以久流转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若欲止于心,即无复有生死,既无生死,潜神玄默,与虚空合其余德,是名涅槃矣。俊可容有名于其间哉!”
概括本段秦王姚兴之意,所谓涅槃即是无名,无名即是无生死之分辨,而这种分辨乃是众生著欲之结果。故涅槃的获得即是超越生死分辨达于“与虚空合其德”。这一点是与僧肇《涅槃无名论·开宗第一》里“无为者,取于虚无寂寞绝于有为”的境界是一致的,并且这也是僧肇的一贯主张,如《维摩经·弟子品》肇注有云:“涅槃无生死、寒暑饥渴之患”,又“涅槃坏五阴和合”等。由此看来,就这一点而言,僧肇是真的赞同姚兴的。
问题出在下面,《上秦王表》所引《答安城侯姚嵩》书信中的另一段云:“诸家通第一义谛,皆云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太甚径庭,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石峻先生以为姚秦主的这一观点也为僧肇所赞同,并以此作为证明《涅槃无名论》为伪作的理由。
我们以为石峻的这一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姚秦主的这一观点并不被僧肇所接受,尽管肇公读之叹曰:“实如明诏”。我们不难发现肇公所谓圣人是“与道游者”,其云:“若无圣人,谁与道游”。这已经不同于姚秦主之谓圣人即是“知无者”的概念。查姚秦主书信中的“知无者谁”议论,被现代佛学者吕徵先生《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概括成是他对“涅槃”的一个观点,即涅槃是有得者。
细读《涅槃无名论》中《核体》一节,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节正好是对持涅槃当是有得者论点的充分展示,而在下一节《位体》中肇公所破除的正是此论点。故不能误把姚秦主的观点看成是肇公的观点。关于此点,吕徵先生亦指出:“姚秦主认为涅槃应该有得者,如果一切都空,那么能得者是谁呢?肇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实际上如果理解了涅槃真义就不会产生这些分别了。(《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依般若的观点来看,“涅槃是有得者”之观点,其误有二:(1)对主体割宰以求之,二分于主体;(2)把涅槃说成是独立的实体。
姚秦主关于“涅槃”的这一看法,曾不断为罗什、肇公师徒所批评。《广弘明集》卷十八载罗什公文《答后秦主姚兴书》即如此,试录之如下:
佛说色阴,三世和合,总明为色,五阴皆尔……又云若无过去业,则无之途极……固知不应无过去,若无过去未来,则非通理,经法所不许;又十二因缘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过去,未来,则与此法相违。所以者何,如有谷子,地水时节,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则无所待有,若先有则不名从缘生,又若先有,则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无,有无之说,唯时所宜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本)
这里什公是站在大乘中观的立场以指出姚兴“通三世”论的错误在于执著于实相(详见《广弘明集》卷十八)。作为什公的弟子僧肇则更指出涅槃是般若智的正观结果,“不可以有无得之”。姚兴之论,乃是“舍有入无,因以名之”,是所谓“采微言於听表,拔玄根於虚壤。”
由上看来,肇公并不完全赞同姚兴的观点。我们以为肇公之作《涅槃无名论》不可谓与姚秦主之《答安成侯》书无关。但肇公之意实在发明“无名”之说,而又欲杜绝对“无名”的谬误之解也,此所谓“曲辨涅槃无名之体,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谈”是也。
二、关于“真空”与“妙有”转换问题与肇公的涅槃学
自汤用彤先生以来,佛学史论家一般都认为时在晋宋之际,中国佛学界完成了一风气的转换,即是从“真空”向“妙有”转换,这是对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换的理论表述。
试从汤氏的论著《中国佛史零篇》中摘录一些表述:“般若涅槃经虽非一,理无二理(《涅槃》北本卷八,卷十四均言涅槃源出般若),般若破执相,涅槃扫除四倒,般若之遮诠即所以表涅槃之真际,明乎般若实相义者,始可与言涅槃佛性义。”又,“般若主扫相显体,涅槃乃本性之学。”又,“扫相所以显体,忘相乃所以表性。言象纷纭,体性不二,方法虽异,一如是同。(生公《法华疏》)真如法性妙一无相,于宇宙曰实相,于佛曰法身,于众生曰佛性,实相也,法身也,佛性也,导真不二,绝言超象。”
按汤氏议论虽精,但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涅槃之学乃是本体之学是沿着般若扫相之路继续深究玄言之本体,并且把此看成是从“真空”向“妙有”的本义,学术界于此误会至深。
石峻先生《〈肇论〉思想研究》论云:“(僧肇)无疑是我国佛家般若空宗的一位杰出代表,而《上秦王表》中则自称‘在什公门下,十有余载,虽众经殊,胜趣非一,然涅槃一义,常以听习为先’。这个话是否属实可靠,我认为就很值得商榷……他是当时持经“三论”的学者,曾为《百论》作序……(所研习的)《维摩经》也是属于大乘‘空宗’系统,那么本轮这样在突出‘有宗’涅槃学,总觉得语气之间,似乎与客观事实不符。由于僧肇早死(公元144年),很难说他已适应我国佛学思潮发展的趋势,即自主张‘真空’转入提倡‘妙有’。”
该文中石峻先生又说:“南北朝时期的佛学理论不得不转变方向,即所谓从‘真空’进入‘妙有’,于是涅槃佛性的学说成为我国佛学理论的中心。”显然,上述石氏的议论是建立在汤先生结论的基础上的,但我们细读《肇论》各篇及其《维摩经注》之后觉得其实这里问题还有很多。比如(1)《肇论》对涅槃的研究并不能用后来的“妙有”佛性义来概括;(2)《肇论》之中,从般若到涅槃亦不能用真空向妙有的转换来概括;(3)《肇论》中的涅槃义是肇论自身理论的产物与后来的涅槃佛性的谈论不是一回事。我认为上述几点是读《涅槃无名论》时必须搞清的。
首先,我们能从《维摩经注》中摘要出肇公直接谈论涅槃的地方有二十六处之多,且经分析,我们以为与《肇论》诸篇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或言有互相发明之妙,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没有理由说肇公不关心涅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从佛性的角度来理解肇公所言的“涅槃”,我们以为肇公之研究涅槃是他哲学的逻辑发展,亦即般若之学的逻辑发展。
若从哲学命题产生的角度看,多在由于般若学的兴起,当时的知识界欲用一种新的观念来取代玄学对世界的观念。般若的任务即是识破诸法的实相,更准确一点实际上就是在万法上廓清玄言观念的分辨,从而取代玄言的寄言出意。《肇论》建言般若无知,以真俗范畴取代了玄言的有无范畴,又以不迁取代了迁化观念,终于以一种新的观念——“般若”的建立而扫清玄言之相。
中华之学术,亘古以来就有一个特点,即往往以当下的人生困惑引发对世界本体之探讨,由此展开了一种哲学思潮的隆盛。又,任何一种哲学思潮都是以最终对人格理想的关怀、建立而告终。以上这个特点在以人的觉醒为背景的魏晋时代的哲学上体现的尤为显著。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般若学以其所建立的“般若”观念,完成了对玄言封疆的廓清,从而提供了导人识破诸法实相的本领。《肇论》之中把识破诸法实相的人称为圣人,毫无疑问进一步描述一下“圣人”其精神状态,当是般若学者的应有之意,亦可以说是般若学的逻辑必然结果。
般若学的这一逻辑轨迹,从哲学的进程来说即是指士人从对客体的认识转而表现出对认识客体的主体的关怀。我们认为《肇论》把对主体关怀的任务集中在对“涅槃”的讨论上。在讨论中,肇公持论以为涅槃的境界即是了悟般若智慧的境界,故建言无名以表般若的寂照特征,并以此建立对涅槃意义的阐释。如《涅槃无名论·开宗第一》云:“夫涅槃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又,“本之有境,则五阴永灭;推之无乡,而幽灵不竭。幽灵不竭,则抱一湛然,五阴永灭则万累都捐。”
总而言之,肇公是以对般若寂照的把握来作为对涅槃真相理解的途径的,更明确地说肇公把了悟般若寂照的人称之为圣人,而涅槃则是作为对了悟般若寂照的圣人之人格理想阐释的。
我们认为晋宋间涅槃学的研究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以涅槃来把握般若智慧的境界;第二,则是以此为切入口展开对佛性的探讨。肇公之论可谓是第一阶段,不能笼统用“妙有”之说加以概括,准确地说,“妙有”之说是从佛性的角度谈众生达于涅槃之可能性的,而就这一点而言,道生之说足以当之。石峻先生以为肇公关注涅槃即等同于关注“妙有”之说,实际上是没能分清晋宋之间涅槃研究仍有阶段次第的区别。我们以为“妙有”之说仅代表涅槃佛性论研究的这一阶段,并没能笼罩所有涅槃之论。相反,由于《涅槃无名论》里没有涅槃佛性的表述恰恰说明《涅槃无名论》著作之真实性,因为它的讨论范围没有涉及晋宋易代之时才形成热潮的涅槃佛性问题。
三、关于“顿”、“渐”问题辨
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部分第十六章有云:“《无名论》十演中反驳之顿悟,显为生公说。而九折中所斥之渐说,则为支公七住顿悟说,是作者宗旨赞成七住说和呵弹大顿悟,据今所知,生公以前,无持大顿者,生公立说想在江南,且亦远在肇死之后”。
汤氏此说几为证明《涅槃无名论》为伪作的不易之论。但我们细读《涅槃无名论》的《难差》到《明渐》这几节,觉得仍有值得深思、推敲之处。其《诘渐》中持顿者得中心观点是“无为大道,平等不二。即白无二,则不容心异。不体则已,体应穷微,而曰体而未尽,是所未悟也。”但是我们从《辨差》、《明渐》中看出,所谓“无为大道,平等不二”的观点,肇公所持无名论者并不曾反对。如其《辨差》第九云:“然究竟之道,理无差也。”又,《明渐》第十三云:“无为不二,则已然矣。”又,《维摩经·佛国品》肇注云:“所因虽异,然其入佛慧一也。”又,《观众生品注》:“万法虽殊,无非解脱相。”可见,所谓“无为不二”之说,肇公亦持之。《涅槃无名论》一文怍公建言无名,究其本义则是于涅槃默其一切分辨而显无为寂灭相。亦“无为不二”之义。
总之,无论《肇论》还是《维摩经注》,肇公之论并不曾持理于分化,渐次悟之,他始终把“悟”看成是圣人、至人才能具有的境界和智力,其云:“至人无心,无心则无封,无封则无疆,封疆既无,则其照无涯,其智无涯,则所照无际,故能一念而知一切法。”而一般的人,心存惑念而有疆,如欲达“一念知一切法”的境界,只有渐修以损之又损之,从众生到圣人,可见肇公之所言渐不是就悟而言,而是就从众生到达于圣人这一段来看的,从十地上看,是指七地之内的修行。
不仅如此,肇公看来,七地之后虽“心智寂灭”但仍不能叫悟,仅得无生忍而已。自慧达注以来,世人以为肇公持七地悟,即所谓小顿悟,实乃是误会之深。
从《维摩经注》中我们知道,肇公虽以为七住以上得无生信。虽则如此,仍有差别。亦即肇公又以无生忍与无生二个层递的境界区别之。无生之终端才圆融般若之智,所谓智力具足,于法自在,常在闲地,此与无生忍相对。无生忍其特点则是智力犹弱,大觉未成。可见,肇公之所谓“大觉始成”,“一念知一切法”并不包括十地之内的渐修,但渐修则是大觉得必要条件。
由此看来,就理本无差这个意义上来说,肇公之于道生其观点是一样的,肇公之所谓“十地无生,大觉始成”亦同于道生之“大顿”。这正好说明他们同沐于什公门下的结果。
笔者以为肇公与道生的区别在于肇公是从般若的立场本着扫相目的以强调渐的,而道生则是涅槃佛性问题的强调者。
盖众生之于涅槃问题从肇公到道生可以概括成两个阶段:(1)是众生如何达于涅槃;(2)众生有无涅槃的可能性。肇公属前一阶段,道生属于后一阶段。
汤用彤先生以为《难差》以下六章“反复陈述,只陈理本无差而差则在人之义,”这正好表明肇公的般若学的立场,即探讨众生如何达于涅槃。所谓“差别在人”的问题,从《维摩经》肇注及《明渐》里,我们不难发现,肇公强调“舍”“尽”“损”“造”,而并不强调“悟”,可以证明肇公无意去讨论“悟”的特征。肇公言“顿”亦往往与“尽”“舍”联系起来,如《维摩经注》卷五:“群生封累深厚,不可顿舍,故阶级渐遣,以至无遣。”又,《明渐》:“结是重惑,而可谓顿尽,亦所未喻。”又,“况乎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其道无涯,欲之顿尽耶。”
可见,肇公之关怀确实是扫众生之相,以其认为众生心存惑念而有疆,故必须渐修以损之又损之,这是众生达于涅槃的首要条件和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生公一生也不忘言渐以扫众生之惑:其注《法华》云:“倾以渐渐变耶?所以尔者欲表理不可阶顿,必要研粗以至精,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损矣。”[5]又云“夫圣人设教,言必有渐,悟必有阶。”这说明道生若回到肇公的问题上,他们的意思仍是一致的。
道生后往江南大倡顿悟之说。我们推测主要是当时的学风已经转移,即从“众生如何达于涅槃”的问题转移到“众生有无涅槃的可能”问题上,亦即涅槃佛性问题上,道生以佛性与生死对,顿悟之说被突出出来,当然这已经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
我们想要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顿悟”说所依据的理论诸如“无为无二”“理不可分”“一念知一切法”“大觉始成”等等不一定要到晋宋易代之时涅槃佛性的讨论形成热潮时才有。相反《涅槃无名论》讨论之中没有涉及佛性问题,恰说明它的成文在涅槃佛性讨论的热潮到来之前,此亦是其不伪的证据。
四、关于《涅槃无名论·动寂》之“动寂”与《物不迁论》的“动静未始异”问题
据《涅槃无名论·动寂》一节,持“有名”论者引经以提出以下的问题:人通过修行而如涅槃无为境后,达到所谓“体绝阴入,心智寂灭”境界,如此即不需“进修三位”。“有名”论者以为“进修三位”是有为法,需要判断、取舍、损益,从而滋生分辨之心。
关于入无为境之后的“体绝阴入,心智寂灭”境界,肇公亦的确持之。在《维摩经佛国品注》中肇公引经句注云:“既得法身,入无为境,心不可以智求,形不可以象取,故曰无量,六往以下名有量。”又《维摩经观众生品》肇注云:“七住得无生忍之后,所行万行,皆无相无缘,与无生同体。无生同体,无分别也。真慈无缘,无复心相,心相既无,则泊然永寂。”
然肇公虽言住于涅槃,其特征就是寂灭。但他同时又指出:严格地划分涅槃而卑于生死,则是小乘之障。其《维摩经·弟子品》注云:“小乘以三界炽燃,故灭之以求无为……大乘观法,本自不然……。”又其《观众生品》注云:“二乘虽无结慢,然卑生死,尊涅槃,犹有相似慢结慢者。”
故此,肇公并没有说心智寂灭后犹绝对不动。肇公之意在于“现於涅槃而不断生死”,并以此作为“解缚而达于涅槃者”的应有姿态。
在《涅槃无名论》,肇公进一步把《维摩经注》的这一思想概括成“无为而无所不为”。亦即“无为故虽动而常寂;无所不为,故虽寂而常动”。此所谓的“寂”乃是心寂于灵照,此所谓“动”是以涅槃之寂心反于尘俗也。以此肇公反对那种截然区分尘俗与太虚的观点而采取中观之般若观,此所谓“不知众庶之真,即太虚是也。”
石峻先生认为《涅槃无名论》非肇公所作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是以为《动寂》一节与《物不迁论》中“动静未始异”理论相矛盾,具体地说,即是《动寂》里的“动寂”与“物不迁”中的“动静”观不一样。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动寂》一节里用的是动寂概念,而《物不迁论》用的是“动静”概念。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的不同。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把《肇论》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就不难发现其实它们所要讨论的亦不是一个命题。《物不迁论》是致力以静来揭示万法的生灭相,而《涅槃无名论》中的“动寂”概念则旨在揭示众生经修持而至涅槃境界所应有的姿态。一个旨在导人识万法之真相;一个则是提供对主体的关怀。二个范畴,严格意义上讲,不具有可比性。
在《维摩经》中记载了一则关于获得无生法忍的人乞食的掌故。据载维摩经批评那种只向穷人行乞的观点,以为他们有分辨之心。关于此,肇公注论云:“不食即涅槃法也,涅槃无生死寒暑饥渴之患,其道平等,岂容分辨?应以平常心而行乞,使因果不殊。”
这就是说,行乞而为平常之众生,此所谓动者。而以平常心无分辨,此又是所谓寂者。关于此《动寂》章释云:“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即其事也”。可见《动寂》之观点旨在提供关于圣人涅槃境界的阐释,与《物不迁论》旨在破诸法的迁逝相不存在有冲突,故不得以而视《涅槃无名论》为伪也。
注释:
①本文所用《肇论》原文资料均据金陵刻经处本元文才《肇论新疏》,不一一注明。
[1]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张曼涛.三论典籍研究:三论宗专集之二[C].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六十八.
[3]石峻.《肇论》思想研究[G]//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注维摩诘所说经[M].僧肇,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
[5]竺道生.妙法莲华经疏[M].续藏经:第23套:第4册.
B942.1
A
1671-8275(2011)02-0016-04
2011-04-06
1.张兆勇(1965-),男,安徽五河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2.曹二林(1988-),女,安徽宿州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批评。
张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