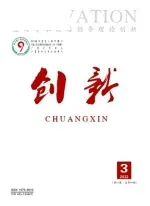浅析马克思的平等观
李书巧
浅析马克思的平等观
李书巧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平等是仅仅依据“人”这种身份的平等。马克思的平等观体现了彻底的人本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政治价值理想,为我们提供了和谐社会中“平等”所应追求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目标。
马克思;平等观;人本主义;价值理想
自人类开始思考政治现象以来,“平等”就成为了思想家们广泛关注的对象,然而,对平等的看法却众说纷纭。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各自立场出发,往往得出很不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可以说,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人们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那时每个人都将受到真正平等的对待,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不会考虑他们地位的尊卑、财富的多少、智力的高低和劳动量的大小等诸多外在因素。
一、马克思的平等观的基本内涵
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高举“平等、自由”的口号,认为平等是人类的一种天赋权利。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观”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从分配消费品的角度,指出真正的平等不是“权利”的平等,而是按“人”的需要来进行分配的平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所存在的平等,指出它仍然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权。在初级阶段,虽然生产资料已归全社会共同所有,不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但是“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因此,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304显然,这里每个人除了向社会提供自己的劳动以外,不能提供别的东西;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消费资料的分配只以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为标准,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人们之间的平等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平等,除了劳动引起的不平等之外再没有别的引起不平等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资本、地位、出身等在这里统统都不起作用了。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304-305
可见,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有着不同能力与需要——的人身上,因此以劳动为惟一尺度的平等权利虽然是现实条件下最为完善的一种权利,但是它还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因为它是以劳动量而不是以“人”的需要为标准来进行分配,这样就会导致不同劳动能力的人获得不相等的物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使在有着相同劳动能力的人们中间也会因为需要的不同而产生满足程度的不同,如果再考虑到每个劳动者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那么这种基于“劳动”之上的“平等权利”就会带来更多的现实的不平等。可见,它不能同等地满足人们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需要,它不能同等地体现每个劳动者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在马克思看来,平等的真正要义在于给每个人以同等的作为“人”所应享受到的待遇,平等应当是人们仅仅依据“人”这种身份而获得同等满足和尊重的“权利”。这是一种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平等,它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无条件的要求,它要求人类个体作为一个人而普遍得到社会实现,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使他们个人的人格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
同时,平等也不是像有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实行的那样,整齐划一地分配同种同量的物品,而是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进行分配。这种真正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实现,那时“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05-306
二、马克思的平等观体现了彻底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提出了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其平等观正是以此理论体系为基础,以人类的最终解放为视角,以每个人充分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超越了狭隘的阶级局限,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终极人文关怀,实现了彻底的“人本主义”。
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天生是不平等的”,生来就分为奴隶和自由人。在自由人之中,人们又因为财富、地位、出身和品德的不同而有高低贵贱之分,卑微的人天生要受高贵的人的统治。每个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享有与其对城邦所作贡献相称的政治权利,相等的人有着相等的政治权利,不相等的人有着不相等的政治权利,这即是“比值平等”的原则,也是“平等”的真正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就如同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所存在的秩序一样“自然”。这里奴隶天生就是自由人过城邦生活的工具,没有自身的价值。自由人也一样要受到一小部分人的统治,籍以实现城邦的目的。可见,亚里士多德考虑“平等”问题不是以“人”为出发点,他考虑更多的是城邦。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平等”问题被置诸脑后。在启蒙运动中,“人本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人们考虑许多政治问题皆以此为出发点。大多数思想家都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强调个人的天赋权利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政府或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种种天赋权利,比如自由、财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他们坚持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决定公共事务。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但理论上虽如此,现实生活中却有种种资格限制,比如财产、性别,种族等,使这种平等的权利只能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中。而且即使到了当代,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比如诺齐克等,都还认为只有政治权利的平等才是合乎正义的,任何为了实现经济或社会的平等而用政治手段来进行调整和干预的政策行为都是不公平的,都是不正义的,都会侵犯到个人的自由。他们认为人们在经济上从来都不是平等的,而是不平等的。
可见,大多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积极捍卫的平等不过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虽然已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极不充分的平等,更不用说建立在人们事实不平等基础上的政治平等又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这里进入思想家视野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幸福、自由、平等、权利、需要,所谓“人本主义”只是一种极不彻底、极不完全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到人的彻底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
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普遍认为“马克思本人正是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开创者”,[3]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人本主义。说它是彻底的,是因为它超越了一切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马克思的平等观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没有私有财产,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对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需要什么、需要多少都能够得到满足。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没有因阶级差别和个人能力的不同所导致的贫富悬殊。
总之,消除能够引起任何不平等(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的一切条件和动机,就再也没有产生不平等的因素。每个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与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没有谁享有多于或少于另一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平等、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每个人的各种不同的需要都在较高层次上得到了同等程度的满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处于完全平等和谐的状态,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人之所以为人所特有的各种需要(比如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都受到了同等充分的关注,每个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
可见,马克思的平等观深深地植根于其“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其根本目标和终极理想是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自始至终所深切关怀的是整个人类。“人”是马克思思考一切问题包括平等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是平等,还是自由,都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就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
三、马克思的平等观:科学的政治价值理想
在社会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入低潮之后,马克思的这种“平等”思想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更是强化了对这种看法的认同。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失望和对西方发达国家繁荣景象的渴望使人们转而得出结论,马克思式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永远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起点平等”才是现实的,也是永恒的,人类追求政治发展的模式已经终结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4]中。马克思和他的这些思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成了打趣、讽刺和怀旧的对象,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如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了,我们需要抛弃马克思,寻找新的更为现实的意识形态支撑。笔者认为这样对待马克思及其思想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
马克思的平等思想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进行反思的产物。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虽然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但它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更为严重。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更为残酷、更为彻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繁荣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广大的劳动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温饱问题尚难以解决,更不用说去享有所谓与上流社会的权贵“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所谓平等只不过是劳动者“平等”地受资本家的剥削。
正是基于对这种黑暗现实的深切感受,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科学分析,揭开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示了阶级压迫和阶级不平等的根源,揭露了资产阶级平等的虚伪性,道出了平等的真正含义,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将处于真正平等的地位并获得人的彻底解放。
的确,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平等”的美好政治价值理想,但理想并不因其美好而失去科学性。理想之所以是理想,而不是空想,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它是科学的,因为它以科学的方法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工具,并以大量的客观事实为理论依据。社会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的统一,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根本特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有的人也许反对马克思的思想,但其潜在的思维方式却不知不觉地采取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的这种科学的政治价值理想同时又有着自己实现的具体条件,马克思本人从来不认为可以为了实现所谓理想而超越具体的现实。
实践表明,对马克思平等思想的误解往往是由于将该思想与其赖以实现的具体前提相分离所造成的。这些前提说到底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了,从而阶级统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存在了;商品、货币、市场和交换消失了,产品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即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全面的发展;人、自然、社会三者处于和谐之中,个人与社会实现高度融合和统一;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因此这种平等不是一种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总之,如同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社会乃至后全球化社会,马克思设想的平等亦是后现代社会乃至后全球化社会中的平等。
可见,与其说马克思的平等思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平等的理想蓝图,毋宁说它为我们提供了和谐社会中“平等”所应追求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目标。这样,长期以来关于是应该“起点平等”还是“结果平等”的各种政治思想在这种有着博大胸怀的政治哲学面前黯然失色。
也许在很长甚至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这种关于“平等”的政治理想不会实现,但它却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没有高尚远大的政治理想,现实政治生活便失去了意义。一种思想之所以重要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可实现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类的启迪。而且,许多迹象表明,马克思的许多思想(包括平等思想)正在成为渗透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信仰里的价值理想。在马克思的这种有着诸多合理内核的思想的压力面前,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改革,逐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类为获得“平等”的努力也永不停歇,人类对“平等”的认识也与时俱进,但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种体现了人的彻底解放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将是和谐社会中政治发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理想,我们每前进一步,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迈进。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3]王南湜.范式转换: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人类学——近五十年中国主流哲学的演变及其逻辑 [J].南开大学学报,2000,(6).
[4][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A81
A
1673-8616(2011)05-0028-04
2011-04-11
李书巧,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1620)。
潘丽清 实习编辑:杨延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