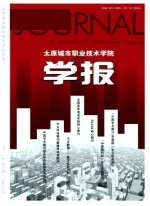浅论绘画的应物象形
翟翌辉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浅论绘画的应物象形
翟翌辉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在中国古代美术评论实践的过程中,历代画论十分丰富,大量杰出的美术作品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国美术体系。中国古代美术中对物的理解是取其似与不似之间,作为表意尽意的手段。其次是中国早期象形符号的发展,对线的表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者中国画线对形的运用,对整体塑造关系的表达,在绘画的形式上概括为:构图、章法、布局等等。“六法”的提出,更是对后来绘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本文从“应物象形”一法,做简要论述。
中国画;含蓄;简单
“应物象形”理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的“六法”论中即已提出。总括起来“六法”阐明了绘画的功能和艺术标准,是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上,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应物象形”就是说随着物体的变通而规定形象,也就是写实的意思,所谓“写实”,当然是指“写”形的真实面貌。中国画的物,中国画的象,中国画的形是与品评作品高尚、优劣之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整体的。中国画形的理论表达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美学意义。
谢赫的“六法”作为千百年来中国绘画鉴赏上唯一的标准,关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各朝各代的画家各有不同。谢赫自己在《古画品录》中说:“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附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一、物
“应物”这两个字出现的很早,大约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对应物的理解在这里要加以全面的悟。“应物”包含着中国人对事物的应和、应当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待事物所采取的方式。中华民族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朴实的。中国的这个“物”既属于客观存在的对象,又是艺术家主观感受的对象,艺术家表现对象时在所表达的对象之中,存在两种物象。其一是客观存在的物象,即中国的画家是以客观存在的物为原形而由艺术家将其升华重塑的,它与客观物象具有很高的似真性,以艺术家特有的艺术观察力和捕捉力共同作用而取得的。其二是主观情感物象,即特定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艺术形象是艺术家主观情感积极能动外化的结晶物。此物象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感情激扬时创作的。描绘这个物象第一品乃陆探微是也。
中国画中的物,为物至简单,为物至明确。中国画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与语言相当的。语言者无形之图画,图画者无声之语言。对物用作艺术语言的表达对象起到类似语言的表情达意的作用。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语言是一种精神劳动,那么绘画就是一种体力劳动,可见绘画语言在理解层面上就是一种超越了体力和精神的纯正的艺术活动。文学语言是由加工提炼的人民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组成的。美术语言是由颜料、体积、面积、色彩、线条等材料因素组成的。中国画的艺术语言多是借物象形,用物拟人之做,发挥出了作为这种特殊艺术语言的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宋代的画院在招收画人的时候,拟的题目,就是要借这个物,用这个物让科举画人表达出他们的所想所感,从而选拔英才。“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神色,惧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宋史·选举志》
二、象形
(一)“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
“象形”是谢赫在表达此法,要让画家对待物象时,通过自己内心的主观感受,能动地“应物”,通过轻灵的心境,自然而然地图绘。描绘物形更是绘事之初的主要任务,唐韩赣最工写生,韩赣的《牧马图》画黑白二马在奚官系下缓缓徐行,二马的骨肉停匀,体态圆肥,奚官威武有力,深目虬须,两眼炯炯有神,带有游牧民族的面貌特征。整幅画勾染都极其细腻,体现了韩赣高超的写实功力。中国绘画的表面,虽不外为描写外形,但要有超越物形的感情参于其间。宗炳以“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画山水序》中加以说明。在六法中把“象形”之法摆在第三位,意在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家已经相当深刻地把握了艺术与现实,外在与内在精神的关系。因此“应物象形”的位置的确很恰当。
“象形”这个词谢赫用得太绝妙了,它概括了中国诸家的文化信息。魏国时期王弼的《四象形则大象畅》曰“: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王弼《老子指略》)魏晋时期,那股从汉代规定儒家为一尊的正教伦理风气带着强大的惯性而对艺术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老子关于“道”的论述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是以其作为宇宙之体的本体或本源,是无形、抽象、虚无,因而与自然万物可见之“象”截然对立的话,那么,到玄学初起,王弼论道就已经把“无”与“有”联系论之了。同时随着绘画艺术的愈趋精密,这种重精神而不放弃对形的描绘的现象,在魏晋六朝时期甚至出现了对自然造化的深入细致地的观察及精确描绘的倾向。如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中那种严格依据自然形色所作的类似西方油画式的设计,宗炳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及他的带有透视学意味的表现空间距离的研究,乃至谢赫的“应物象形”、“随类附彩”等标准的确立等等,都说明了这种写实性倾向。
(二)中国早期艺术精神中那种象征、表现的性质,在文献上最早出现于《尚书》、《周易》上的记载,十分明确地自觉地说明了形象的象征性质:夏商铸鼎等。到后来就演化为儒家“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的道区别,也演化为道家“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庄子·天道》)再者中国早期艺术精神中那种象征、表现的性质在中国古代先民美术文化中的大汶口文化的古陶器上刻的图形符号、仰韶文化中刻图画,如彩陶盆上的鱼纹、鸟纹、动物纹,这些纹饰都是由具象成为抽象并图案化的。
就中国画的形而言,绘制中国画的作者,是要达到形神兼备的能力。故绘画所以传写自然,写生是绘画的标准,这一点,古今都是认同的,描写物象,不得不从模仿入手。例如在元四家尤其是王蒙的作品中,决不是一种醉后的挥写状态!假若没有一种精心的构思,没有一种严谨的笔墨表现,不会有如《富春山居图》、《深林叠嶂图》那样的精品。从顾恺之的《女使箴图》到阎立本的《步辇图》,从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均体现了画家对形的准确描绘。作为艺术作品,“构成”也是其有机的架构要素,一件具体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将用塑造艺术形象的艺术语言有序地、有价值和意义地设计、编排而组成“有意味”的乐章,那么,其做出的所谓作品,也是没有骨格,没有灵魂的任意堆砌。绘画的最终目的是传神。
三、中国画线对形的运用
(一)中国画是书法同源的绘画,自有文字以来,书法和绘画的关系就是形影不离的兄弟关系。前人都有定论。赵承旨自题《枯木竹石画卷》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发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文字与绘画在原始状态都是为了说明某些事物,像结绳记事之类就是为了避免某些事物。而象形字是以最简洁的绘画形式去完成文字的功能,在文字意识的朦胧状态下,书与画是联为一体的,其目的也是一致的。也有人说绘画是从象形字中分化出来的,元代朱德润在《书画同源》中说:“盖字书者,吾儒六艺之一,事而画则字书之一变也。”书画产生之本源说法虽然有不同的争议,但还是达到了共识,书画同源之处是在于亦书亦画的原始意象符号。王羲之的《兰亭序》对后世影响极大,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章法、布白,笔划之牵引皆精妙无比,字形飘洒,像一首抑扬顿挫的乐曲,又似一幅恬静的山水画。透过书法见其风度和气质,可见闲适飘逸的形象。中国画的笔墨差不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唐张彦远《运墨而五色具》中说:“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绿,凤不待五色而卒,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毛笔对书写过程中的动作的变化、力量的轻重有高度敏感性,哪怕是一点点动作的不同和力量的微妙变化,落在纸上的迹象便有不同。对书法的影响极为重要,他使书写者在用笔的快慢节奏、线条的粗细变化、墨象的枯湿浓淡等方面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由此形成了书法的“笔意”。对于书法来说一经画出就成了客观意义上的线条,这根线条是笔者一次性完成的,书法的创作性上具有不可重复性。相对应的,在中国画的绘制过程当中,“线”的妙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线是中国画术上所特有的利器。例如唐朝时期的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精力、充沛的情感、娴熟的技巧、创造的气势宏伟、感情奔放的宗教壁画中人物形象,充满了活力。为了强调笔墨线条的特殊功能,适当地压缩色彩在画面上的比重,往往“于焦墨之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线条在绘画作品中,之所以具有审美的价值,首先是它能够表达客观物象一定真实的造型能力,纯粹的不表现任何物象的线,在绘画作品中是不具有审美意义的。宗炳提出“以形写形”,谢赫提出“应物象形”,就是要求绘画的形象创造,要以客观存在的物象为依据,并表现出它一定的自然真实。例如从战国帛画中,长沙马王堆的一、三号墓帛画就是借助主人公升仙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此幅帛画在形象塑造方面与主人甚为相似,显示了汉代肖像画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画家的形象创造,逐步在摆脱作为器物装饰的那种图案化的造型,努力地追求他所描绘的对象的自然真实感,尤其是人物上。
总之,中国的绘画,在六朝以前全是羁绊的艺术。至六朝逐渐摆脱了束缚,发生以美为美的审美风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思想观念的活跃,美术创作题材范围的扩大,以文学作品为题材的绘画创作日趋旺盛;在艺术领域里,随着美术实践的深入,人们对美术的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绘画理论著作开始出现。那么中国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有其独特的精神面貌,所呈现的是对客观具体事物的塑造。“应物象形”一法不仅在当时,也给我国以后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开创了一个精密而又具有普遍艺术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国画的线和形是相辅相成互为整体。脱离了线的形的中国画,就好像失去了载体;抛弃了对形的表达,线也就无所寄托,无所依存。精细的线条给形浇筑了无限的生命力,而精确的造型又为线条的挥洒构筑了一道和谐的屏障,使得线条有弛有缩,运用自如。“应物象形”一法与第一位的“气韵生动”相辅相成。谢赫的“应物象形”,是要通过这个固有的形,传达出作者的气韵,这个结论汇聚了历代画家的大智大慧,让画家自然地表现,自然地创造。最后引用一句话作为此文的结尾:“真正的艺术是历久弥新的,因为这种艺术对每一时代的人都有感染力。”
[1]傅雷.傅雷经典作品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3]梁玖.艺术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5]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
[6][德]威廉·冯特·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薄松年.中国美术史教程[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J2
A
1673-0046(2011)05-01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