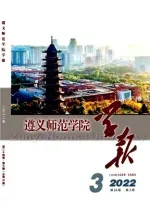王学主体性之我见
牟永生
(苏州科技大学政治系,江苏苏州215009)
近几年来,随着现代性与全球化思潮,在一片“重写中国思想史”的呼声中,再读王阳明,新究心学价值观,无疑是这股“重写”、“重评”思潮的重要方面。然而,统观学界对于王学的哲学倾向之界定,笔者发见,所谓“重读心学”,无非还是长期以来视“心学价值观为主观价值观”的重新发掘与论证,始终未能超越这一传统研究中似乎不是学术定论的学术定论。因此,摒弃王学的主观性之根固定位,确立王学的主体性之全新理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读和再评王学。
一、一字之别:定位王学之基础
走进传统不易,走出传统更为困难。重评王学的哲学倾向,确立王学的主体性,不仅要对王学的生成、流变及其主要内容给予总体观照,对学界关于该问题的大量诠释与引申进行剖析、比较和鉴别,而且还须首先作出一项理论预制:厘析“主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异同。正所谓孔夫子所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与流行的定位──王学的主观性相比,行将确立的全新理念──王学的主体性,只是以“体”代“观”,以致二者之间仅有一字之别。中文表达之丰富性与精确性并存,恐怕是世界语言中数一数二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这样近乎咬文嚼字的一字之差,却足以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实、科学地揭示和概括王学的基本哲学倾向,从而,真正克服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仅仅运用现代哲学的“板块”模式对王阳明哲学中丰富的价值思想进行条块分割,作出近乎非此即彼的理论定位之片面性。
然而,对于“主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巨硕差异,人们远未达成共见,而是见仁见智:或认为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无须过多强调;或坚执这种差别微不足道,没有必要加以细究。因此,探察二者之间的区别比起考究它们的联系,尤具现实价值,至少在本文的主题视角内是如此。
大凡价值观均意味着人们对于价值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一贯态度。而价值问题不过是在学理上对价值的历史发生、价值的本质特征、价值的主客体、价值的结构序列、价值的评价标准、价值的活动取向和价值的创造享用等意义世界中最普遍、最一般现象的涵摄。这样的价值观,不仅每个时代具有,各个群体、阶级、社会具有,就是现实的每个人也少不掉。价值观以人的存在为落脚点,人的活动又以其价值观为“发生器”。
一切价值皆是对于人的价值,所有人均为价值活动中的人,价值与人之间相伴而生,又影形合一。长期以来,不少论者所以怀疑,并企图剥离价值问题的客观实在性,深层次原因即在于,它误读了价值与人之间的这一客观辩证法,从而把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简单地等同于“无需人的参介性”,把价值的“主体性”简单地等同为“主观性”。
能否以人的活动的参介性──或者以某一问题对人的活动之依赖性──来否定该问题的客观实在性,列宁对此早就作过明确回答:“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1]P331-332其实,倘若可以凭借人的活动之参介性为由,加以否认并拒斥价值问题的客观实在性,那么也未尝不可以把它推而广之:势必否定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普遍性和客观性。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永远都是无法撇开人类活动参与的历史。
主体性一般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特殊本性,而人无疑是肉体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主观性则仅仅是人的思维与意识特性。对于二者,尽管我们过去作了一定程度的区分,认为主体性是人处于特定认识活动、价值活动的目的地位,主观性则是人对认识客体、价值事实的观念把握,但有些地方也曾出现过明显的失误:1972年首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就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误译成“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好在1995年的新版本作了更正,译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P16
二、心物之辨:王学主体性之秘密
人与世界的关系始终是困扰现代哲学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当代西方智者为此殚精竭虑,颇费心力。但在中国先哲那里,通过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智慧积淀,似乎早已触及并部分地揭开了解答这一重大课题的基本思路,这就是天人和合,心物不二。
人与世界的关系固然有其本体论、知识论层面,但同时也蕴藏着价值论。王学就是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契机,高扬陆九渊“心即理”的价值理念,在熔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于一炉的哲学体系里,对心与物、理与气、道与器、性与情、知与行、一与多、变与化、太极与阴阳、天理与人欲等理学思潮中这些主要问题的价值审视。“心物之辨”作为心学家、道学家与气学家之间一直论争不休的问题,不仅是学界再现王学思维轨迹的逻辑起点,更是我们体悟王学的主体性之根本秘密。
对于心物之辨,王阳明最集中、最简明的表述莫过于此:“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天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之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卷4《与王纯甫》)[3]在王阳明的价值观中,“心”与其说是指知觉意识活动,毋宁是指“心体”或“心之本体”,也就是对应于从孟子到陆九渊的“本心”范畴。通过这一置换,王学中的“心”就不再是事实现象化为意识层面后所提炼出来的纯粹经验的自我,倒是转变为价值活动中活生生的具有优先权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物”、“事”、“理”、“义”、“善”均“非在事物之有定所”,可以无需任何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参介而独立凸现,恰恰相反,这些价值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一个环节,都唯有被纳入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优先存在的价值公理模式,方能具有价值意义。
价值既非物质实体,也非本质属性,更非主观感觉,而是事实世界与人之间一种特殊关系──事实世界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和完善。由于事实世界不过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统摄,因此价值分别表现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一切合乎规律性的现象、事物和行为对人的本质之确证、提升和完善。无论以自然界为价值载体,还是以人类社会或思维自身为价值对象,全部价值的落脚点都毫无例外是对于人的价值。脱离人探察价值,无异于缘木求鱼。“‘人的实在’是价值来到世界上的原因。”对于价值与人之间这种须臾不可离性,王阳明也算是深谙其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卷1《传习录》上)[3]
价值这种关系性存在表明,它既无法单纯地存在于事物这一极,也不可能仅仅衍生于主体身上,而是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或主体客体化,或客体主体化──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价值现象──诚如中国第一个价值哲学家张东荪所言──“好像矾纸浸在米汤中便变为红色。这个红色就是所谓关系质。关系连在一起以后才能出现。关系一断,这个质便消灭了。主观与客观相遇,其所见的东西,正和矾纸与米汤相遇一样。换句话说,这种特性在主观方面看来好像是属于主观的,而其实只是主客相遇的一种自然结果。”[4]P8价值这种关系性同时表明,一旦脱离价值主体或评价主体,价值也就同时失去其存在依据。也就是说,价值的发生既有赖于价值客体或评价客体,又依赖于价值主体或评价主体,还取决于价值主体或评价主体与价值客体或评价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诚然,能否确立王学的主体性还要取决于论者如何阐释王氏的心物之辨。阐释不同,结论迥异。对于王氏而言,心物之辨并非一定就是针对外在的客观实在性与主体人之间在历史发生问题上的先后关系的,很可能是着眼于价值活动或评价活动的两极:一极是价值主体或评价主体,一极是价值客体或评价客体。因而,“心外无物(事、理、义、善)”说本来与那种视个体意识之外什么都是“无”的思想不相干,至少对于一个儒家的著名学者来说,他绝不会认为父母在逻辑上后于我的意识而存在,也不可能认为我的“意之所在”不在父母时,父母便不存在。王学这一命题不是本体论上的,也不是知识论上的,而应该是价值论或评价论上的。要不然,这一命题就将永远成为众矢之的。正如学界所见:“如果说他不能完满回答关于外界事物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本来不是面对这一问题的。”
三、知行之合:王学主体性之关键
不管知行之合是不是王学的“立言宗旨”,但它作为王学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层面,则是学界比较公认的。如果从心物之辨我们已窥探到王学的主体性之根本秘密,那么再透视其知行之合,我们则可以进一步体察出王学的主体性之理论关键。
与大多数儒者一样,王阳明的知行观也是立论于道德价值修养和践履工夫的,而非一般知识论上的知与行。因此,他一方面坚执道德价值的认知与道德价值践行的完全同步性,甚至简直就是合二为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妄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卷6《答友人问》)[3]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道德价值的认知无疑具有优先地位,它需要经由确立道德价值的情感意志──这是必要条件──方能使二者水乳交融,契合互补。这种交融和契合当然不是制作“拼盘”,也不是不分轻重缓急和主次贵贱的绝对同一,而是凭借“知”范畴的外延拓展来实现的。也即,“知”是强调主体的情感意志对道德价值的理性自觉,它不仅要求主体的情感意志对道德价值的绝对敬畏和无条件系守,而且主体必须时时刻刻克除其思虑中的邪念、“妄想”。主体这一番自我清查、自我根绝“妄行”于意念萌动之初的工夫,已不失为“行”了,所以知行合一。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卷3《传习录》下)[3]一念发动处哪怕存有一丝妄欲也不曾放过,即是他所一贯倡守的真实切己工夫。一丝向恶之念与不好善之念皆为念之不善,当革除。但问题在于,既然一念上之不善并未成“行”,并未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害,那又何必这么认真呢?看来,王氏连人们内心世界的邪念都不想放过。其实说他小题大作,他还是不算小题大作。他始终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既然难,就得从小事抓起,从一般人极易忽视的地方抓起,以“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卷2《答陆原静书》)。[3]显见,他的知行之合的知与行都是要达到知善与欲行善的契合,唯有此才算真正和合为一,也才算真正实行了“知即是行”的价值活动。
对此,王门弟子不是一开始就津津乐道的,而是经历了从质疑、发问、受答、到确信等几个环节与过程。从先生对其弟子的解答中便知,王学中的“知”并非普通之知,倒是一种真切之知。真知者必然会把他所认知的价值观念付诸价值活动,不会出现知而不行的问题。倘若出现知而不行,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达到“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卷2《答顾东桥书》)。[3]可见,“晓得当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价值主体就不是知而不行,而只能算是“未知”。因此,在王学中,知行之合同时意味着言善从心始,言行一致,随时随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弘扬道德价值的主体性精神。
既然“知”乃是一种“真知”、“良知”,那么《大学》的第二条目“致知”便是“致良知”。在王学看来,“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作为王阳明立言宗旨的又一神圣价值理念,无疑是对“亚圣”孟子“良知”、“良能”说的空前系守与阐发。“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卷1《传习录》上)[3]这种人人所固有的良知,就是每个价值主体从事一切活动的内在道德法庭,它发挥着对意念活动的导向、监控、评判和制裁的特殊功用。“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卷3《传习录》下)[3]良知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明善明恶”,还表现为“善善恶恶”,敦促和昭示人们“善”所是,而“恶”所非。它既是一种价值理性,又是一种价值情感,既是一种价值认知,又一种价值实践,是二者的有机弥合。
从价值的两极(善恶)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命题,更加鲜明地体现了王学的主体价值之取向性。这一命题的真义是:一念发动处有“妄想”便是行恶,而一念发动处有“善意”则不一定就等于行善。因此,光有善的意念或对善的认知,还不算是知善、行善,只有把善的意念落实为为善的行动,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德事实,从而确证、•提升和完善了人的本质力量,才是真正的知善、行善。而价值主体并非一定有明显的恶行才是行恶,只要有“妄念”就是行恶了。同一个价值观命题,在不同的价值域中扮演着几乎是“二律背反”的价值角色,而且共同地凸现了王学的“立言宗旨”,这不能不是王学的主体性精神之魅力所在。
[1] 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王阳明.阳明全书[M].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1927.
[4] 张东荪.价值哲学[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