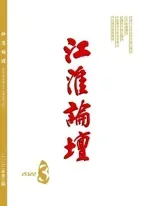论柳宗元“天论”思想的时代意义与理论影响*
朱 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北京 100872)
论柳宗元“天论”思想的时代意义与理论影响*
朱 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北京 100872)
柳宗元对“天”这一范畴的重拾、对“性与天道”问题的复归,推动了哲学思潮由有无、本末等辩题向儒家义理和心性之学的转换。柳宗元的“元气自动”论与“势”、“道”观念和《天爵论》影响、启发了宋明气本论哲学、“理”的观念以及“天命/气质之性”关系论。
柳宗元;天论;时代意义;理论影响
如果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场以反地心说为基点,进而向古希腊罗马自然人性论回归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史上,同样存在着一场以反对神学之天为途径、重拾先秦人性论地位的复兴运动,即古文运动。表面上看来,古文运动似乎只解决文体问题,即反思六朝以来辞藻堆砌的骈体写作,提倡恢复汉以前的朴质文体,但其实际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正如范文澜先生所指出的,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提倡古文,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度衰弱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1]
先秦时代,“性与天道”被视为最不可讳言的哲学问题,后来经由孟子、荀子及两汉诸儒,天人关系、人性问题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议题。然而此后,随着汉末谶纬神学、魏晋玄学以及佛学的兴起,本末、体用、有无、般若等问题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中唐时期,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努力下,天道与人性问题的讨论得以重新回归中心地位。
韩愈作“天之说”与《原性》,柳宗元作《天说》、《天对》、《天爵论》、《答刘禹锡 <天论 >书》,刘禹锡作《天论》以回应和重新阐发儒家天论思想及人性论。韩、柳、刘都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统一性原理[2]533,他们通过对当时天人关系的讨论,把人们对天命观的怀疑和否定引向对汉以来整个儒家经学传统的怀疑和否定[2]534。
然而就“天论”这一问题的讨论而言,韩愈贡献不大,柳宗元、刘禹锡以批判韩愈的意志之天入手,成为这场讨论的核心。就柳、刘二人之间而言,柳宗元的天论思想直接启迪了刘禹锡(1),在中唐“天论”的讨论过程中,柳宗元起着上承韩愈、下启刘禹锡的作用。
柳宗元在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时指出: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吏,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柳宗元集·贞符》)
柳宗元不满意汉代的训诂经学,以为“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其非人”(《柳宗元集·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对于汉以后的儒学发展,他更不屑一顾: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去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胡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柳宗元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因而柳宗元认为,从汉代的儒学大家到唐代的学者,都未能掌握儒学的基本精神使儒学发扬光大,反而使之误入歧途。
鉴于此,柳宗元在屈原问天的千百年后,作《天对》以答《天问》,重拾对“天”这一范畴的讨论。柳宗元天论思想当不仅被视作对先秦至汉唐天论思想的一次系统总结,也是一次恢复儒家传统精神的尝试。他对两汉以来神学之天的否定,影射着中唐儒学史上对先秦性与天道问题的复归。这一主题的重新置换,扭转了当时的哲学发展思潮,为此后宋明理学家对天道与人性问题的探讨打下了基础。
一、“元气自动”论与宋明气本论哲学
“气”这一范畴,在理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朱熹称赞道: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人未经说到,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张子正蒙·诚明》朱熹注)“气”这一范畴与“理”一道,成为构建整个理学系统的中枢,为理学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模式作出了说明。
严格地讲,宇宙论和本体论并不是一回事。本体论讲世界本原、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宇宙论则讲宇宙自然的生成和发展问题。[4]1那么以此来划分,就儒家天论思想系统而言,先秦出现了自然宇宙论(如荀子)、心性本体论(如孟子)的初步模式;两汉的天人神学系统基本上属于宇宙论;魏晋的有无本末自然之辩属于本体论;隋唐则是过渡期;理学是二者的结合,理学家建立了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就理与气而言,理是本,它是个洁净空阔的世界,可以独立地存在于本体世界。但是“理”要生万物、发育流行,就必须依赖气,因而“气”是理从逻辑本体走向生成本体的桥梁。就连接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而言,“气”具有比“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以宇宙论和本体论为发展模式的儒学史阶段划分,同样也适合于“气”这一范畴的发展阶段划分。就气源论哲学这一脉而言,先秦两汉(荀子、王充)多为宇宙自然之气,魏晋为本体之气(杨泉)。到了柳宗元这里,他将自然与本体相结合,在王充、杨泉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气的聚散、氤氲等运动形式是元气自身的运动,为宋明元气本体论哲学创造了条件。[5]155
柳宗元的元气自动理论对气本论哲学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张载对气的论说里一窥端倪,这主要表现在:
(一)天、地、人三才的结构上
柳宗元《天说》:“彼而上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张载《正蒙·乾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二)皆以元气为本
柳宗元《天对》:“庬昧革化,惟元气存。”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天惟运动一气。”
(三)关于参两关系
柳宗元《天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张载《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
不难看出,张载的气论较柳宗元的要具体、系统且富有伦理意味,这也是理学较之于儒学此前诸种形态的优势所在。
二、柳氏“势”、“道”观念与宋明“理”的观念
自隋至中唐,众多儒者自觉到了儒学中衰之势,进而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如王通、吕才、刘知几及稍后的李华、李筌等。(2)这一批判潮流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儒生们试图恢复儒家地位所做的一次努力。但是,在否定和抛弃一种旧的思想形态的同时,必须着手建立能够取而代之的新思想学说。这个思想的核心,由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朦胧地提了出来,那就是“理”、“势”、“数”和“道”,[7]16因此,隋唐儒学的变化趋向之一,就是用“理”和“道”的观念来代替天人感应论的“天”和“命”。经柳宗元和刘禹锡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天人关系争论便大体上告一段落。以后的争论,更多的是理气,宋初诞生的理学,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行的。
柳宗元在清理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的时候,比较自觉地运用了“势”这一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终极力量,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贞符》)“德绍者嗣,道怠者夺”,道与德对于社会国家的变迁起着绝对权威的作用。
此后,王夫之、魏源对“理”、“势”关系也多有发挥。王夫之认为势与理不可分,“得理,则自然成势”,“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船山全书·读四书大全说》卷九)。魏源论及势道关系时指出: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
三、柳氏新天爵论(3)与宋明的“天命”理论
《天爵论》一文在《柳宗元集》里是显得有些突兀的。综观《柳宗元集》,关于“元气”自动思想、“天人不相预”思想及顺“势”的历史观显然是其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此外,涉及佛教、佛学、佛寺及僧侣往来的函信占《全集》的十分之一左右,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整部《全集》里面,《天爵论》一文似乎偏离主旨。其实不然,如果将《天爵论》放在整个中唐时期社会思潮中去考量,我们不难体会出这也应是柳宗元回应当时儒林三辩(4)的一部分。
如果说《天对》是柳宗元就天人之辩对屈原的历史性回应的话,那么《天爵论》则是柳宗元对孟子“天爵”理论的一次再发挥。《天爵论》指出“气”分为“刚健之气”和“纯粹之气”,禀受的“刚健之气”、“纯粹之气”多则为贤人,少则为愚凡,“其各合乎气者也”。“刚健之气”表现在人的生命中即为“志”,具有这种品质的人,“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纯粹之气”表现在人的生命中即为“明”,具有这种品质的人,“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志”,相当于“意志”;“明”,相当于“领悟”。兼具这两种能力,那么仁义忠信这四种美德就可以显微卓著了。“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柳宗元的天赋说与气禀说,与韩愈、李翱的性情说一道,为宋儒的心性论做了铺垫。[2]552
儒家天论系统的建构,始于战国后期,两汉时初见功效,董仲舒所建立的天论系统是第一个被官方肯定的儒学形态。魏晋时代,玄思盛行,名教自然之辩成为玄谈的主要论题之一,或以为名教本于自然(王弼),或以为名教即是自然(郭象),其根本旨向仍在于追寻纲常名教的自然本原,与儒家言天道以发明人事的思路究根上是一致的,但这种引老、庄、易三玄为根据的思潮,客观上淡化了儒学以纲常名教为中心的原则,动摇了名教的地位,尤其在面对佛学长于思辨的宇宙论体系时,儒学未免相形见拙。儒家地位的下降,儒家伦理纲常败坏的“中衰”(5)局面,自两汉后,从魏晋一直持续到隋唐。韩愈、李翱虽主张明道统、辟佛老,但因未建立系统的宇宙论,终显理论不足。柳宗元继承荀子天道自然、王充元气自然、杨泉元气本体的思想,并重视吸收佛老的哲理(6),试图以元气自动论为儒学的伦理学提供宇宙论根据,为宋明时期思辨化、伦理化、哲理化儒学宇宙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从战国、两汉、魏晋到隋唐的儒学发展史,同样也是儒家学者逐步为儒家伦理学说建立宇宙论基础的历史。当儒者为儒学建立起系统的宇宙论时(如两汉、宋明),儒学便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或文化主流;当宇宙论基础不够系统完善、儒学理论思辨思维水平较低时(如魏晋隋唐),儒学就只能相应地处于中衰或旁落时期。可见,构建一个完善健全的宇宙论系统,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究其原因,在于宇宙本体论乃是儒家伦理与道德的形上根据[10]64。
柳宗元以元气自动论为一贯的天论体系,就儒家天论思想史而言,上承先秦、两汉、魏晋三代,结束了长期的天人之争;以气为言说工具,弥补了天论思想系统中所潜存的先天不足,并予宋明气本论哲学以新的启发。就儒学发展史而言,柳宗元所在的中唐,是中国儒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儒学在经学时代之后漫长的徘徊低落期,在此开始呈现否极泰来的征兆:以韩、柳、刘、李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适时兴起,三辩问题对先秦性与人道问题的复归,同样也标志着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新的起航,推动了宋明时期儒学形上学时代的到来。
注释:
(1)从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到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从柳氏的“元气自动”到刘禹锡“无形非空,无形即为无常形”的思想,从柳宗元论“势”到刘禹锡进而论“理”、“数”、“势”,均不难发现柳宗元对刘禹锡的思想影响。
(2)张岂之先生主编的《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对此多有论述,因而在此不展开叙述。
(3)名为“新天爵论”,是为了区别于孟子的“天爵”论。
(4)天人关系辩、性情关系辩、三教关系辩。
(5)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将儒学在两汉经学后的时期,称为“中衰时期”。
(6)柳宗元与韩愈不同,他并不排斥佛教,主张统合儒释。《送僧浩初序》道:“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
[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吴文治,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宋]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7]张岂之.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明]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9][清]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彭永捷.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B241.9
A
1001-862X(2011)06-0065-004
耶鲁大学麦克米伦(Macmillan Center)中心“全球正义”项目(Global Justice Program)
朱璐(1984-),女,江西上饶人,中国人民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先秦儒学、儒家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