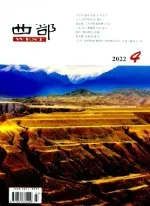枫木村的爆炸声
文/杨国峰
夜已深沉,晚秋的过山风刮过山坳,撩弄起一路响声,在雪峰山余脉雪峰界山脚下的枫木寨,闻不见鸡啼狗咬,此刻已归于平静。可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之夜,从村民钱老贵家中传出一声骤响,继而有人惊呼:钱老贵跳楼了!
钱老贵的家门前,蚁囤蜂涌,陆续骤拢一些看热闹的村民。
只见钱老贵的妻子郑青岚一丝不挂,被反捆着双手,瘫倒在中堂楼上,一张脸寡白,身子痉挛着,下身血糊糊的,已昏厥过去。
村民私下议论:这幕戏是迟早都要上演的。
失踪两年的小女猝然归来
那是个让人惊喜的日子,当失踪了两年的胡菊猝然归来,胡岩滩夫妇又惊又喜,抱着女儿哭作一团。他们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杳无音讯的女儿竟突然站在了他们面前。
胡岩滩生有两男一女,两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分家另过,只有17岁的小女胡菊待字闺中,厮守在父母身旁。胡菊长得水灵俊俏,鲜嫩亮丽,人见人爱,是枫木寨的一枝花。只是胡菊读书不长进,勉强读完初中死不愿再读下去,整日呆在家里消磨时光。胡菊被父母宠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蜗居家中煮煮饭,喂喂鸡鸭,闲余时间看看电视。父母也不靠她寻钱找米盘家养口,就任她在家闲着磨蹭岁月,现在的父母对儿女都宠爱有加,所以也不逼着胡菊打工挣钱。
那一日,胡菊突然对父母说,她要同本村的钱小燕外出打工,长年缩在家里终不是办法,腻透了。那些年外出打工的人并不多,尤其是女孩子打工的更少,大多数人还是呆在山沟里死守着几亩薄钱过日子。胡菊要外出打工,父母心里就毛了。开始坚决不同意,一个弱女子出外挣钱,钱来得辛苦,父母心痛;钱来得容易,父母又多一份担心——女孩子的钱来得容易总不是好事。但经不住胡菊的软缠硬磨,只好放行。
钱小燕是村里钱老贵的二闺女,比胡菊大三岁,本来是个性格内敛,不好张扬甚至有点木讷的姑娘,从来不思谋外出打工挣钱,在家挨着父母规规矩矩过日子,16岁那年却吵闹着要只身外出闯荡。父母当然不放行,说要打工也要有熟人作伴,形单影只远走他乡,父母不放心。钱小燕出奇的倔强,她竟趁着夜色离家出走。钱小燕一走,既不给家里打个电话,也不写一封信,就这么悄然地在枫木寨消失了。家里人只以为钱小燕被人拐卖了。两年后钱小燕突然与家人取得联系,并大把大把往家里寄钱,好像一夜之间钱小燕在哪里打开了一座金窖,发了大财。村里人私下窃议,钱小燕已蜕化成花枝招展、风情万种的卖身卖笑的坏女人,这几年出入花街柳巷,赚的是“松活钱”。一次钱老贵病重,钱小燕日夜兼程赶回家中,甩给家中五万块钱,惊得村里人眼睛鼓起牛卵子大,那时的人能亲眼见到五万块大钞无异于见到了一座金山。钱小燕还留下话,如果治病的钱还不够,再打电话给她,钱对她来说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怎么才能把父亲的病治好,那口气好像张嘴就能吞下一头大水牯。为了赶时间,钱小燕第二天便搭车到桂林,坐飞机直飞广州。那时枫木寨坐过火车的人都没有几个,坐飞机更是村里的奇闻,看钱小燕那神态,不知攒了多少钱,如果靠打工挣钱,能有那么财大气粗的派头?
胡菊随钱小燕走了,也像胡菊当年出走的那样,这一走就断了音讯,家里人竟不知胡菊是死是活,只苦苦地盼着胡菊的消息。但胡菊不像钱小燕当年那样两年后大把大把地往家里寄钱,而是两年后突然神情落魄地回了家。
父母急着追问胡菊这两年去了哪里,在外面干了些啥。胡菊只是摇头避而不答,一脸的愁容浓得化不开。父母就犯疑,难道女儿在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不好启齿?或者遭人欺负受人威胁不敢说出来。胡菊越不肯吱声就越证明心中有鬼,越激起了父母心中的疑窦。胡菊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胡岩滩火起,捋个拳头要揍人。胡菊不避不躲显得很坦然,她终于说话了,你们打吧,让你们打够了出了气我再离开这个家,我千不该出门闯荡,万不该再回到家里,死在外面倒自在省心,这世界孤魂野鬼多的是,我活够了!父母掂出了胡菊话中有话,立马就蔫了,既不敢“审”又不敢打。
“女婿”千里寻上门
胡菊整日郁郁寡欢,神情恹恹的,一张脸蜡黄寡瘦,那样子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常常是一个人躲在房里暗自垂泪。父母不敢过问,只是精心地把伙食搞好调养胡菊的身子。可是胡菊日渐形销骨立,并没有康复的迹象,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母亲陪同胡菊到医院检查,医生问胡菊母亲,胡菊是否已经嫁人了,胡菊曾经打过胎,现在肚里还怀着孩子。怀孕?这无异于当头一捧,狠狠地击在母亲的心头。母亲一阵晕眩,她恼怒地盯着胡菊,竟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在枫木寨出了未婚先孕的丑事,该女子必定被划归破鞋烂货之类,是谁都瞧不起的,这样父母也会感到蒙羞受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终的结局是像倒垃圾一样把女儿扔出去,匆匆出嫁。母亲又气又恼,扬起巴掌狠狠地打在胡菊脸上。死不要脸,你一个黄花闺女,怎么可以胡乱在外面做猪狗事?你是在往父母的脸上抹屎撒尿呀!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我打死你,就当没生养你这么一个女儿!胡菊哭着说,我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我早就不想活在这世界上,死了一了百了,娘,你干脆拿刀来把我杀了!胡菊说到一个“死”字,母亲心里软了下来,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坨肉,是好是丑就这么一个女儿,只好打碎门牙肚里咽,再不敢大喊大叫了,反过来好言安慰女儿。
父母已猜测到胡菊这两年出门在外肯定遭遇不幸,这个孽是钱小燕种下的,于是气鼓鼓地要上钱家论理。胡菊就“咚”地跪下了,哀求父母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如果父母一定要上钱家闹,她马上就去死!父母压住火气,暂时不上钱家闹事,待日后再择机追根究底,他们绝不会放过钱小燕,硬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家里出了丑闻,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趁早把胡菊打发出去,这才是上策。只要胡菊嫁了人,也就雷打柱子挡,家花野花也就有了主。于是父母四处张罗放信给胡菊找婆家,哪个男人想要,是聋子是哑巴,是跛子是瘸子只管招手娶去。
月亮田村有位姓固的民办老师,前年死了老婆,身边有个两岁的女儿,正在饥渴的寻找老婆,经人牵线,就拎了彩礼寻踪觅迹来到胡家提亲。一方是结婚生子的二路货,一方是未婚失身的残花败柳,也算般配。经人撮合,事情也就一拍即合。双方议定,国庆节结婚了事。
时间捱到了9月中旬,却事有变故。那天胡家突然来了一位瘦若猴精的男人。“猴精”自报家门说他叫宋民欢,是从江苏南充来找老婆胡菊的。“猴精”一进家门就冲着胡菊父母呼爹叫妈,叫得忒甜。胡菊父母搞懵了,女儿从来就没说过自己已经嫁人,况且说定国庆节与固老师完婚,现在节外生枝突然冒出一个“猴精”女婿?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了。父母追问胡菊是怎么回事,胡菊阴着脸说,我不认识他!于是胡岩滩的两个儿子把住大门,不让“猴精”进屋。胡菊的二哥胡魁扬起锄头,冲着“猴精”吼,哪里来的疯子,你是拎着臭猪头上香,找错庙门了吧?再闹老子一锄头挖了你!“猴精”孤立无助,寡不敌众,不敢恋战,只得节节败退,边后退边扯着嗓子嚷,胡菊,你跟我回去,你好狠心呀,你腹中有我们的血脉,怎么把肚里的孩子给弄了!你……
母女的鲜血染红刀刃
“猴精”走后,一家人围住胡菊问根由,胡菊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父亲猜度胡菊心中可能受了莫大的委屈,逼急了保不准会逼出问题来,于是使眼色相互提醒,一家人装聋作哑不再追问胡菊。现在最要紧的仍是赶快把胡菊嫁出去,只要固老师把胡菊领走,事情就一了百了,于是便加快了操办婚事的步伐。
时隔五天,“猴精”再次上门纠缠。“猴精”说他是花了25000元钱从人贩子手中买下胡菊,要么带走胡菊,要么赔偿钱财,如果人财两空就死在胡家门前。胡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家人都搞懵了。于是胡岩滩星夜赶到月亮田村同固老师商量对策。固老师说他凑10000元,余下的钱由胡家自己筹措,“猴精”拿到了钱,耍赖就没有理由,自然会走的。
胡岩滩从月亮田村返回村里对“猴精”说,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取款,我们不会赖帐,钱一文不少会退还给你,但胡菊绝不会跟你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猴精”扔下一句话:七天以后我再来,到时是红是白自见分晓!便悻悻地走了。
固老师如数送来10000元,胡家也筹足15000元,至此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七天以后“猴精”如约来到胡家,这回他脸色铁青,神态异常,眼神怪怪的。他食言不要钱却要带胡菊走,生生死死要和胡菊在一起。胡家已经凑够25000元,底气就足了,当然容不得“猴精”胡搅蛮缠,把25000元硬甩给他,一拨人推推搡搡撵“猴精”走。“猴精”赖着不走,冲过去要去拉胡菊。胡菊母亲持了把火钳隔在中间,边挥舞边骂,火钳几次差点碰到“猴精”的脑门。胡菊的两位哥哥也是绾衣捋袖直逼“猴精”,骂骂咧咧逼赶“猴精”。 “猴精”干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走,胡菊大哥抓住“猴精”衣领,下蛮劲往外拖,胡菊二哥更是牛气冲天,用脚狠劲踢“猴精”的屁股,胡菊二哥在前面拉扯,大哥在后面撵赶,事到如今,“猴精”不想走也得走。
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猴精”人地两生,寡不敌众,只得起身磨磨蹭蹭往后退。他不甘心,仍绝望地喊,胡菊,难道你的心肠就这么硬,你到我家的那些日子我没有亏待你呀!我把心都掏给你了!请你跟我走!跟我走!我给你跪下了!“猴精”咚地跽跪下去。胡菊脸色苍白,嘴唇剧烈痉挛着,我不认识你,你……你走!胡菊二哥走过去,叭地给了“猴精”一耳光,你害得胡菊好苦,你再吼叫老子一刀杀了你!钱如数给你了,咱们两清了,你还闹什么?滚吧!“猴精”绝望了。
“猴精”傻愣了好一会儿,突然他霍地站了起来,飞快地跑进屋里——他一进屋时就发现屋壁刀销里插了一把亮闪闪的剥牛刀。平时胡岩滩做一点杀牛贩肉的生意,这刀是胡岩滩前些日子从集市上买回来的一把崭新的剥牛刀,他磨了一个早晨才把刀锋磨锋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溅血祭刀的竟是自己的老婆和女儿。
其时“猴精”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丧失了理智,变成一头发怒的雄狮。他持着剥牛刀直逼胡菊,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活着不肯跟我走,就是死尸我也要把你拖走!说着挥刀就刺。胡菊母亲不顾生死地护住女儿,一窜身横在胡菊面前。“猴精”瞪着充血的眼睛,朝胡菊母亲劈胸一刀捅去,胡母身子一颤,当即倒地。“猴精”抽出滴血的剥牛刀,继续追杀胡菊。
胡菊夺路逃命,从家里跑到屋门前的公路上,公路前方是一个农贸集市,但这天不逢赶集,集市上没有几个人,她一边跑一边惊呼:“杀人了,救命呀!”。
公路两边是密集的民宅,民宅中巷子纵横交错,如果任意往一侧跑,“猴精”不熟悉地形地貌,匿藏容易追寻难,“猴精”不一定追杀得上。可是胡菊错误地估计,公路正前方两侧有一长溜肉案,有七八位五大三粗的汉子在卖肉,只要其中一位屠夫出面制止“猴精”的杀戮,自己就会死里逃生。可是面对杀红了眼的暴徒,手持屠刀的屠夫惊骇得不敢动弹。毕竟生死就在一瞬间,谁也不敢上前阻拦“猴精”行凶施暴。“猴精”几步冲上去,抓住胡菊的衣领,朝胡菊背后猛捅一刀,胡菊惨叫一声扑地而倒。“猴精”复一刀刺向胡菊的脖颈,胡菊当即气绝身亡。
就在“猴精”持刀逞凶的刹那间,胡菊的两位哥哥本能地感到赤手空拳要制伏歹徒,不但难救下母亲和妹妹,自己也面临着被杀死杀伤的危险。可是待他们一个手持扁担,一个手握锄头追截“猴精”时,一场凶杀最终以母女丧命黄泉宣告结束。
宋民欢杀人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后被判极刑,那是后话。
债各有主,债主是谁
胡家在清理胡菊的遗物时,发现胡菊在日记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恨钱小燕,是她把我骗到江苏的南充卖了……钱小燕恨我家,她说她16岁时被我二哥强暴了,她要报复我家……
胡岩滩马上“提审”胡魁,胡魁供认不讳,胡岩滩一拳朝胡魁打去……
至此,事情总算有了些头绪。无疑钱小燕是受害者,她16岁那年同胡魁在偏僻的山冲里放牛,被一身蛮肉的胡魁强暴了。她碍于面子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求助于法律达到维护自己尊严惩罚罪犯的目的,而是采取一种极端的报复行为迁怒于胡菊,她以打工的名义把胡菊骗到江苏以25000元卖给了家里寡穷且老实本份的宋民欢以解心头之恨,她不是为了钱财,完全是为了报复胡家。胡菊几次逃跑,几次被宋家抓回,每逃跑一次即被宋民欢暴打一次。她想自杀,但几次自杀未遂,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几经磨难她终于逃回了家中。胡菊生前曾想把钱小燕推上公堂,但又怕牵出二哥强奸钱小燕的丑事,否则进大牢的不止一个钱小燕,还要搭上胡家的二公子。思前想后,权衡再三,为了顾全二哥,胡菊选择了隐忍,把怨恨埋在心底独吞苦果。如果她不留下这段日记,胡菊注定是一个屈死的冤魂。
丧妻失女,胡岩滩悲恸得疯疯傻傻,他一口咬定是钱家害得他家破人亡,于是隔三差五手持一把剥牛刀闹上钱家讨还血债。当然他闭口不提胡魁强奸了钱小燕的事,钱小燕不在家,自然是“死口”无对。
胡岩滩起着泼妇骂街的架式,钱家人只好硬撑着一张笑脸对付他。钱老贵老实巴交,嘴笨舌拙,根本不敢应战,枪林弹雨让嘴尖舌巧的妻子郑青岚一人顶着。
这郑青岚四十有五,虽韶华已逝,但风韵犹存。她虽身居偏僻寂寥的乡下,平日里却勤修边幅,看重梳妆打扮,那身段那模样,乍一看还有几分姿色,虽少了勾魂摄魄魅力,也能勾起男人的许多遐想。每次胡岩滩吵上门,郑青岚不敢怠慢,先是好言好语相劝,后是好酒好肉相待,如此对付胡岩滩,胡岩滩也就没理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说起郑青岚和胡岩滩,两人还有一段情感渊源。搞集体时,两人都在村里当民兵,那时民兵为了备战,春秋两季都搞拉练。那时郑青岚和胡岩滩沉浸在热恋中,两人自然是形影相随,相互提携。哪想到民兵营长也暗恋着郑青岚,总是找机会与郑青岚接近。利用拉练的机会,民兵营长有意把郑青岚分到自己这个小组,胡岩滩分到了另外一个小组。在大山里郑青岚被民兵营长强奸了,营长被撤职查办,可郑青岚也觉得无脸见人,对不起胡岩滩最终嫁给了三十好几,老实笨拙的表哥钱老贵。
那天傍晚胡岩滩又是骂骂咧咧闹上钱家,钱老贵闻讯龟着头从边门溜走,避免与胡岩滩正面冲撞。其时郑青岚正好从山上劳作回来,关在茶堂里洗澡。那时乡下住房拥挤,一般的家庭都没有专辟的浴室,要洗澡要么借助灶屋,要么就在茶堂里洗。闻讯胡岩滩闹上门,只得赤裸着身子龟在茶堂里把门死紧的闩住默不透气。见钱家没有任何动静,胡岩滩就火了,破口大骂起来,见关着门没有人迎接自己,索性一脚把门踢开了。郑青岚想不到胡岩滩会来这一手,顿时骇得僵成一尊木雕,本能地护住赤裸的身子,蹲下身子抱住胸脯缩作一团。眼前这一幕让胡岩滩目瞪口呆,他没想到郑青岚关在茶堂里洗澡,更没想到她一丝不挂的胴体全被他看到。他的脑海中一阵晃悠,倏地回放着当年与郑青岚相爱的情景,他像喝多了酒,竟晕晕乎乎向郑青岚一步一步靠近……
以后胡岩滩照样去钱家,只不过不再像以前那样吊着嗓子大吵大闹,而是同郑青岚暗中苟合。
血债变成风流债
钱老贵相貌丑陋,且比郑青岚整整大了10岁,郑青岚骨子里根本瞅不起钱老贵。郑青岚对自己的婚姻一直不满意,但生米已煮成熟饭,自己已经为妻为母,也就只好认命。她心如止水,与钱老贵貌合神离,钱老贵受尽了她的白眼和冷落。她曾思谋过同钱老贵散伙,但是想到膝下的儿女,还有舆论的双重压力,便冷却了离婚的勇气,也就只好凑合着把日子过下去。她与钱老贵分床另枕快十年了,彼此感情已降到了冰点,婚姻只剩下一具空壳。现在胡岩滩插足钱家,上演着鸠占鹊巢的闹剧,他们落雨栽花记旧情,竟不顾伦理道德,彼此暗中来往甚密,闹得枫木寨沸沸扬扬,街头巷尾都在窃议胡岩滩与郑青岚的风流韵事。郑青岚豁出去了,全然不顾那些流言蜚语,理由是当年自己与钱老贵是错配鸳鸯,胡岩滩比钱老贵强一万倍。
胡岩滩和郑青岚暗中厮混,在村民看来是心知肚明的事,却把钱老贵给瞒过了。钱老贵自惭形秽,感到自己同郑青岚不匹配,就缺了做男人的底气。郑青岚疏远自己冷落自己,他并不在乎,事实他的心早已麻木。他移情别恋爱上了“修长城”,常常深更半夜在外打麻将,这在客观上为郑青岚和胡岩滩提供了暗中苟合的条件,以致钱老贵压根儿就意识不到后院已经失火。
钱老贵同郑青岚生养了两男一女,女儿钱小燕出走后只往家里寄钱却不回家。大儿子成家立业后在外打工,二儿子尚未婚配,长年在外做生意,很少回家。二儿子盖了一栋新瓦房,一直闲着没人住,却成了郑青岚与胡岩滩偷欢的安全岛。
一次二儿子带了未婚妻覃小娥回家,因生意上的事二儿子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临出门时他把覃小娥安排在那栋新瓦房的楼上住宿,他担心覃小娥新来乍到晚上胆小害怕,特意吩咐母亲晚上要和覃小娥作伴。
晚上郑青岚把覃小娥安排到新瓦房楼上歇着,她说有事出去一下,呆会再来陪覃小娥睡觉。郑青岚半夜未归,覃小娥就半夜不合眼,翻来覆去睡不踏实。不知什么时候,迷糊中听到隔壁房间里有窣窸声,不知是鬼还是贼,心里不免发怵,最后索性持个手电朝隔壁房间一照,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就被手电光网住……
后来覃小娥把那天晚上“闹鬼”的事告诉了二儿子,二儿子又把原话告诉了父亲钱老贵。钱老贵就憋了一口气一巴掌朝郑青岚脸上扇去。他娘的,背着老子偷人养汉,你破靯烂货!死不要脸!郑青岚竟毫无愧色,干脆撕破了脸皮吼起来,你钱老贵算个什么角色,人没几拃高,要头没头要脸没脸,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有什么能耐?晚上一杆破枪也是三打两不响,跟着你过了几十年清心寡欲的日子,腻透了!我们欠了胡家两条人命怎么还?你再闹,胡岩滩头一个就一刀杀了你!你吼吧,你闹吧,我还巴不得闹个鸡飞蛋打,妻离子散呢,大不了这个家散了各过各的!钱老贵立马就哑了,龟着头不再吱声。不过此后胡岩滩和郑青岚不再在家里乱搞,二儿子发了话,以后谁再敢在新瓦房里偷人养汉,是人是鬼都一刀给砍了!到时别怪他六亲不认。
深夜爆炸声
胡岩滩和郑青岚不敢明目张胆的乱来,并不等于彼此收心不再交媾野合,钱老贵知道胡岩滩和郑青岚还藕断丝连,只是没被自己撞见罢了,也就装聋卖傻一直忍着由着胡岩滩和郑青岚乱搞。
近些时风传钱氏祖坟地闹鬼,传得活灵活现。知情人嗤笑:那是野鬼、风流鬼、短命鬼。后来“鬼”终于现形了——胡岩滩和郑青岚躲在坟地里干野事玩快活,被钱氏族人设下埋伏生擒活捉了。钱氏族人动怒了,祖宗坟地出现了鸾颠凤倒的丑闻,这可是有辱祖宗,殃及子孙的大事,非要从重处罚这对狗男女不可,于是族人手持柴刀、木棒、锄头闹上钱家,如果钱老贵不出来坐镇处理此事,钱氏族人就要杀人放火。
钱老贵沉迷于牌桌打麻将,什么都不做,每天只回家吃三顿饭,以此来消愁解闷,麻醉自己。他知道管不住郑青岚,也知道她偷汉子,眼不见心不烦,他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一个傻子。没想到郑青岚和胡岩滩躲到祖宗坟地里乱搞激怒了族人,把自己推向前台。他只得双手抱拳向族人打躬作揖,请大家息怒,答应这事由他来处理,族人才陆续散去。
是夜,钱老贵把郑青岚“押”到自家的楼上,此刻的钱老贵比平日多了一些威风,他硬着头皮要做一回男子汉。他剥了郑青岚的衣服,把郑青岚双手绑在背后,并威严地命令郑青岚跪下。钱老贵无奈地绕着郑青岚兜圈子,嘴里嗞嗞地吸着烟,脸上漾着一种无可名状的表情。他终于停止了兜圈子,突然飞起一脚朝郑青岚的下身踢去,郑青岚一声惨叫,歪在楼板上痛得打滚。钱老贵扑过去,两胯骑在郑青岚身上,使她动弹不得,只得瘫在楼板上低声的哀嚎。突然,钱老贵从兜里掏出一个拇指大的纸炮,死劲塞进郑青岚的下身,怒骂道:臭婊子,我让你搞,我让你快活!他摁亮打火机,将纸炮的引捻点燃。
随着一声闷响,一声惨叫,钱老贵纵身从楼上跳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