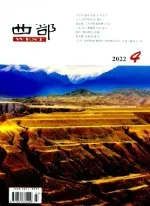跨文体观鸟笔记
戴江南
跨文体观鸟笔记
戴江南
野鸭的角逐
早晨的天空开始是简单明了的,一派湛蓝,澄明透彻,没过一会儿,从看不见的地方游过来丝丝缕缕又轻又软的云,消解了湛蓝的深度,使天空变得微蓝,然后是粉蓝。
越野车在一片荒漠沙石地上歪歪扭扭地弹跳。在野外,不能离鸟儿太近,它们老远就会被吓跑,鸟儿跑了,我们不就白来了吗?
我端起望远镜先整体搜寻一番,像做贼心虚的人那样,偷偷摸摸,轻手轻脚朝前走。我经常会为此感到呼吸紧张。鸟儿的身姿就像一个蒙太奇镜头,从小到大,落入我的眼中。起初,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湖面是一片茫然的灰白,上面落着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我心里直嘀咕:“到底是什么小东西,会有那么多?”慢腾腾靠近,湖面清晰起来,上面依然覆盖着广袤的冰雪,靠近湖岸冰雪消融了一点,露出一片开阔的水域。
太阳光洒在蓝色冰面上,好像一层碎金子覆盖湖面,波光粼粼,闪烁不定。细细一看,原来那密布湖面的水鸟,正是最先到达的野鸭。每一年,它们都以极其壮观的景象宣布春天的到来,好像它们和这湖有一个诺言,而野鸭以坚定的信心如期到达,从没有迟到过。想到这一点,我为它们的守信和勇气感到惊讶。是啊,它们看起来是那样的普普通通,貌不惊人。
一大群野鸭挤在一起,闹哄哄地玩耍戏水。五只针尾鸭,笔直地站在冰面,留下一排肥乎乎的影子。一种高而粗哑的鸣声,就像有谁在敲破铜烂铁,故意捣乱,吵得人难以忍受,恨不得捂住耳朵赶紧逃掉。
唱出破锣般歌声的是雄针尾鸭,它们一刻不停地向雌鸭卖弄歌喉,吸引伴侣,也不知自己的嗓音实在难听。我真想跑上去提醒提醒:“喂,各位,能不能唱个好听的情歌?”一只雄鸭太过分了,也不遮遮掩掩,假装含蓄一点,一下蹦得老高老高,向它的意中情人冲过去,哪料心太急,还没飞到雌鸭身边,那胖乎乎圆滚滚的身子,扑通一下,倒栽进水里了,溅起一大片浪花,出尽了洋相。它那笨头笨脑的样子,让我捧腹大笑。
赤嘴潜鸭把胖屁股朝天撅起来,一头扎进去,找吃的去了。这种鸟儿的头看起来很好笑,红色艳丽的冠状,毛乎乎的,当它们的身体躲进水里,湖面上就露出圆圆的脑袋,一颗又一颗,像一朵朵雨后的蘑菇,从水里长出来,轻轻地飘啊飘,真有趣。
我想给赤麻鸭拍一张近照,便贼头贼脑猫腰朝一个角落走过去。赤麻鸭太机警了,有两只好像是专给大伙放哨的,赶紧发出紧促的信号:“嘟嘟——嘟嘟嘟。注意啊,有人来了。”听到警戒声,它们扇动翅膀,发出呼天喊地的惊叫,但也只是干打雷不下雨,示威抗议罢了,并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还看到另几只水鸟,赛跑一样争先恐后齐齐朝前冲,唯恐自己落后。它们是秋沙鸭,太过袒露,丝毫也不遮掩对爱情的饥渴。在冰面上奔跑的都是雄鸟,正向雌鸟求爱呢!那些雄鸟追逐着雌鸟,在冰面上跌跌绊绊,摇头晃脑,四处乱撞。雄鸟的头一点一点,脖子一伸一伸,点头哈腰的,围着雌鸟转来转去,一副急慌慌的样子。雄鸟发出呱呱呱的啸音,雌鸟对跑来的雄鸟发出一连串低沉含蓄的鸣叫!哦,它在鼓舞雄鸟的斗志。雄鸟受到鼓励,跑得更欢了,还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
雄鸟的颜色看起来要艳丽得多,也比雌鸟更漂亮。这些野鸭在湖面展开各种表演——在水上翻跟头,扎猛子,上去,下来,发出奇奇怪怪的求爱声。不同的响声混合在一起,热烈而高亢,就好像突然从某个遥远神秘的世界传来持久的乱弹吉它声,这是一曲春天的爱情交响乐。眼下正是鸟儿们的求偶期,尽管湖面上还结着冰,可几乎所有的鸟儿都已开始了爱情的角逐,一派闹哄哄的景象。天上地下,每一片角落,每一个缝隙都弥漫着浓郁而热烈的情欲。
我的记录如下:
野鸭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有十多个种类,它们是赤麻鸭、针尾鸭、绿头鸭、白眉鸭、赤嘴潜鸭、凤头潜鸭、秋沙鸭、眼潜鸭等。这一片水域,有几千只野鸭。
天空还飞过另一些鸟儿,它们的大名是:白脊鸟令鸟、鱼鸥、鸬鹚、灰雁、紫赤椋鸟、猎隼、燕隼、戴胜……
有五种鸟儿我不认识,叫不出名字。
众多的鸟
上午,明晃晃的太阳照得到处暖洋洋的,空气中散发着潮湿而温热的气味。我四处溜达一通,坐在湖边一个铺满厚草的缓坡上,看着远处发呆,胡乱做了一点记录。毛毛糙糙画了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我画得很糟糕,根本算不上是画,只不过几根简单的线条罢了,一个圈代表鸟头,两个叉代表鸟脚,也只有我知道那是什么。在野地里,我通常都很懒,只想着玩,东游西逛,后来我连记录都懒得做了,干脆脱下草绿色外衣垫在头底下,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嘀哩——嘀哩”一种尖厉的口哨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懒得理它,仰面躺着听它瞎叫。这鸟的叫声实在动听,好像一个儿童吹着响亮的哨子跑过来,在我跟前吹啊吹的。哨子声从我头顶一闪而过,我看到它穿了两只红色的小鞋。我想起来了,能吹出“嘀哩——嘀哩”这种哨子音的,一定是红脚鹬。
这只红脚小鸟太顽皮了,吵醒我,它却跑了。我睡了多久呢?一个小时,或者只有几分钟?在荒野里是没有时间的。我早就习惯于此了。有人这样说,戴江南啊,这个浪荡的家伙。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经常搞不清我是在城里还是在荒野。
大片玫瑰色的云停在头顶,越压越低,感觉伸一伸手就可以摘下一片。云倒挂着,看起来好像和天空没多大关系,不依不靠地悬在半空。一个冰冷的小点冷不丁打在嘴上,我朝天空望去,寻找它的来路,以为是哪一只讨厌的鸟飞过头顶时拉了一粒让人恶心的屎。正咕咕哝哝骂它呢,啪,又一个冰冷的小点掉下来,接着是几滴,才发现原来错怪了鸟儿,是玫瑰色的云带来的一片太阳雨。仔细一看,别的地方都没下,就我头顶有云罩住的一小片天稀稀拉拉落下一阵雨。
我站起来伸个懒腰,溜达到一个布满石块的山坡上。那里的草长出来一大片,又短又密,毛茸茸的。
一只黑顶麻雀,刚才还像一枚钉子钉在蓝天上,趁我跑神的一小会儿功夫,就不见了。我的眼睛在天上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咦,小黑点呢?藏到云中小岛上了吗?”我有些纳闷,一低头,它竟悄无声息地落在一棵高高的草尖上,轻轻晃动。它微弱的鸣叫实在是对我疏忽的嘲讽。可是,可是,它是什么时候从天空跑掉的呢?我的眼睛好像从没有离开过那个小黑点啊!我仔细盘查回想,想起来了,我被头顶的纯蓝刺中时,紧闭了一下眼,它肯定就是那瞬间箭一样跑掉的,可那动作也快得有点玄乎吧!
它一边在草尖上荡秋千,一边拿一双小豆豆眼紧盯着我左看右看,眼珠子飞速眨一下,又眨一下。它的眼睛太像两颗小绿豆了,在三角形的毛糙脸上滚动。我也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头伸到它面前扮鬼脸,朝它呲牙咧嘴,想吓唬吓唬它。可这都不奏效,一点儿也没影响它玩乐的行为,它甚至荡得更欢了,有意要耍我,草茎都要被它疯狂的摇摆折断了。直到玩够了,它才嗖地一下,像个玻璃球从草茎上高高一弹,向空中弹去,离地几十米还反弹了几下。就在它侧身晃悠时,才露出白色的腹部。它好像是一朵蒲公英在蓝雾中晃晃悠悠,被风刮走了。
本以为它一去不返,谁知,它猛一个急转身,朝我的方向迅疾扎下来,几乎要撞到我的脸上,我尖叫一声赶紧闭眼。等了一会儿没声息了,再睁眼,它又到半空中了,钉在一处,好像空中有一个小树桩任它停落。它长久自由地抖动两个翅膀,像风车一样旋转,没多久动作慢了下来,有时静止,有时翻转,有时低头,有时仰脸,“唧唧,唧唧”地欢叫着。
它把俏皮的小身子映在蓝幕上。这个长相不出众的小坏蛋,刚刚调戏了我,大概过意不去,想讨我欢心,给我跳起独舞来。在粉色的霞光里,在一个无边无际的舞台上,它能想出这样的独创,也是个天才呢。好一个小精灵,我受宠若惊。
春天的鸟儿汇集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乐队,没有白天和黑夜。鸟儿在春天很少睡觉,它们唱一阵儿,打一会儿盹,醒来再唱一阵儿。
我有些羡慕鸟儿,它们好像任何时候都充满欢乐,它们不停地唱歌,做运动,不知疲倦,对这个世界永怀乐观。
大天鹅
整个天空是一种深而透明的蓝,可临出门时,刮过来一阵风,云就莫名其妙出现了,洒在天上。它们几乎大小一样,形状也差不多,又轻又薄,好像一张无限大的民间蜡染过的印花土布罩在头顶。我惊讶的是,云朵怎么分布得那么均匀,并且白得不可思议,看久了,眼睛会被那耀眼的白刺痛,流出泪。
眼睛离开天空好一会儿,才从眩晕的印花布里适应过来。
刚接近湖面,突然,高而远的天空传来一种号声,号声一会儿高亢,一会儿低沉,最后汇在一起就成为一种令人震惊的喇叭声,听起来格外嘹亮,像一种突如其来的爆破。我循着声音仰面朝天,遥远的天空移过来一条白线,在柔软微蓝的画布上飘啊飘,起初,只能看到一些白色的亮点,它们光滑、柔软,像一条锦缎在空中起伏抖动,很快,白线变成一排列队。看清楚啦,这正是我恭候已久的大天鹅,它们终于大驾光临了。似乎是故意向我炫耀,这支列队不停地变换着队形,一字形,人字形,翻飞自如,后来,它们的翅膀一动不动,滑翔着出现在冰的一侧,掠过了天空。它们以嘹亮的鸣叫,向草原,河流,湖泊宣布春的信息,这架势震撼了整个大地,整个湖面。
看得我瞠目结舌。
这个大体型的鸟,被人称为“鸟中美神”。你看,它们全身洁白,停在冰面时,就像一团一团呆立的雪孩儿。一只雄天鹅紧紧跟随雌天鹅,高高地昂着头,轻轻地朝前游弋。停了几秒,一起梳洗柔软的羽毛。这一对天鹅简直目中无人,大大方方将富有弹性的脖子弯曲,扭动,卷缩,在阔大浩荡的舞台上表演一种自由体操,高雅,流畅。偶然会看到,它们把脖子平平伸开,几乎同它们的身体一般长。这优美的一幕让我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明摆着,它们知道自己的美,并对自己的美充满了骄傲。和它们一比,我觉得我先前看到的那些小里小气、缩头缩脑、毛色灰暗的鸟儿太平庸了。大天鹅的绝美,对于这样的鸟儿显得很不公平。
那一边,它们不成规则,在河面上散开一大片,有的聚大群,有的成双,有的落单。阳光从微蓝的空中撕开一条口子,投射在灰色的河水上,投射在一大片游动或者静止的白色身体上。
可能接到某个号令,先前宁静的河面开始喧哗,水面起伏动荡,波纹一圈一圈向远处荡漾。它们的身体借助波浪的力量,也一起一伏,好像坐着一只只小船,向前划动,朝河中央划过来,“咯够——咯够——”,边游边快乐地吹哨子。它们做着相同的动作,低下头,洁白的脖子朝前伸直,啄东西吃。
它们吃什么呢?
河面上漂浮着一片一片掰碎的面包。面对美食,它们没有吵吵闹闹,没有争抢。不用担心谁会多吃,谁会吃不上,好像食物永远放在这里,谁都可以自由自在、随时随地地吃。
我感到惊讶。这么多的同类,有限的几片面包,它们竟如此从容、优雅。看来,它们一贯的美名——优雅、高贵,是经得起美食的诱惑的,是名副其实的。我心中更增加了对它们的喜爱和尊敬。
河面安静下来。
两只天鹅面对面,朝天空把脖子伸,再伸,直到完全拉直。尖尖的黄嘴贴着黄嘴,当众勇敢地接吻,嘴巴里发出低低的呢喃。
另两只天鹅,昂头挺胸,并肩游弋,双脚朝后翘出水面。游了没几米,可能感到腻味,变换花样,双双竖起身体,“哗啦——”翅膀同时打开,一下一下扇动起来,那大大的白翅膀,在水面掀起一阵风,显得优美有力,如超大的白扇子,看的人都发呆了。
一只天鹅不愿凑热闹,在离群很远的地方独自玩耍,游过来游过去,看起来有些无聊。它游一阵,扭头朝后看一看,不知道在看什么,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动作。后来,它把头朝后拧啊拧,拧成一个麻花状,啄身上的水珠玩,玩了十几分钟,大叫一声,飞到半空中,优美地旋转了三圈,又回到水面。这是一个爱独处的家伙,也许,它正处在懵懵懂懂的年龄,还不知道爱情的美妙。它正在长大中。
五只天鹅排成一支纵线队伍,在水面平静地朝前划游,不紧不慢,平和舒缓。它们悠闲地、静悄悄地游,好似在水面弹奏一曲舒缓动听的钢琴曲,自如娴静,舒展平和。它们的身后,留下一条细细长长的黑色水线,光在水线上一闪一闪的。
一只海鸥大声地唱着歌,从五只天鹅头顶飞过,慢慢地降低,降低,在低空盘旋,好像对下面的天鹅说:“你们好!干吗装得一本正经?”
五只天鹅,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行我素,海鸥讨了个没趣儿,嘴里嘟嘟囔囔着,飞走了,向空中一片小岛飞去。它以为那真是小岛,可还没等它飞到,瞧,小岛散开了,分成三块,越来越薄,薄得像一层纱,最后完全融化了。
海鸥闷着头飞,快到跟前,一抬头,小岛不见了。真奇怪呀!它碰了一鼻子灰,很没趣地又飞回来,失魂落魄地落到水面上。
五只天鹅偷偷地笑了。
猛禽
我也很留意空中的猛禽。猛禽的脚步总是紧紧跟随众多的鸟儿。但它们喜欢落在岩石上,藏在崖壁上,伺机偷袭某一只落单的鸟,美餐一顿。果然,我看到一只鹰,突然从不明处跃起,它那尖利的啸叫乍然响起,它凌空遨翔掠过高空,黑色的巨大的剪影在河面上晃动,很快,芦苇跟着晃动,似乎,近处的山峰也跟着晃动。我觉得自己也晃动起来。
鹰一来,所有的鸟一哄而起,高声鸣叫,似乎空气里也充满了它们的歌声。有的是尖叫,有的细声细气,也有的是一种颤音,当它们合在一起时,就变成一个大合奏,无拘无束,遁入云霄。
一会儿猫腰,一会儿匍匐前进,搞得我浑身发麻。就在我站起来疏松筋骨时,我看到一只猛禽朝空地上的一棵枯树飞过去,它盘旋一圈,落在一个大树杈上,树上有个大大的巢。那是谁的巢呢?它块头很大,差不多有成熟的向日葵圆盘那么大,停落时那双敏锐的眼睛和耳朵四处搜索嗅闻。好一个精明机警的家伙。它坚硬的嘴向下弯曲,翅膀有力地四下击打,锋利的爪子攀住树干,那爪子可是它捕食的好家当。
猛禽的种类在新疆非常多,有五十多种。它们被称为“天空王者”。所有的猛禽都是国家一级或二级保护动物,享受特殊待遇。
那是河谷边的一棵胡杨树,猛禽的巢就高高挂在上面。那只猛禽飞进去再也没出来,坐在巢里,安安静静孵蛋呢。一只小兽偷偷摸摸地朝那个巢爬过去。我搞不清那是什么兽,麻灰色,小耳朵,圆咕隆咚的,爬起来很费劲。它爬到洞口,往里瞧了瞧。天哪,它要偷吃鸟蛋。它真不害臊,也不知天高地厚,很有可能它压根儿没看到猛禽飞进去啦。我等着看一场好戏呢。巢里的猛禽妈妈早有防备,探出身子,用它那铁臂一样的翅膀朝前一扑打,小兽朝树干后一闪,打了个趔趄,差点儿一头栽下去,慌不择路溜之大吉。
沼泽地上的雪都融化了,在草墩和草墩之间,还残留着一汪一汪的水。我扒开草墩,里面藏着一些银白色的小穗儿,在光滑的绿茎上轻轻摇曳。我猜这是去年还没来得及飞掉的种子,仔细一看,又不完全像,因为它们看起来是新鲜的,干干净净,没有浊泥的污染。我采下一株小穗儿,把表面的绒毛拨开,谜底露出来了。你怎能相信?那是一株花,它躲藏在丝一般的白毛绒中,露出金黄的雄蕊。这花是不是同类当中第一个传达春天的喜讯的?幸亏有那绒毛的庇护,因为春天的夜晚还是让人感到一丝寒冷的。
傍晚,我返回时,在河谷边的崖壁上看到一个十分壮观惊人的景象:整个一面岩壁,足足有三十几米长,被一种鸟儿筑了巢。我惊讶得连声尖叫:“天哪,天哪,太神奇了!”鸟儿们把河岸搞得窟窿密布,像个筛子,不过在我看来,那更像一个鸟儿的村庄,一户挨着一户,窗户贴着窗户,密密麻麻。后来我从书上得知,那是燕子的村庄。燕子们喜欢在陡峭的河岸上凿无数的小洞。
克兰河边花花公子
我在克兰河边住过几天,每天早晨在大树上做窝的攀雀把我从睡境中吵醒。它们起得太早了,忙忙碌碌做窝,喂食小鸟。和那些勤劳的攀雀比,我觉得自己太悠闲,好像荒废了一些时日,心里不免有些羞愧。
河谷两岸山势陡峭,悬石断崖,白桦、柳树、青杨、云杉混交生长,形成一个天然的原始森林。
沿河一直往前走,不知不觉陷入林中,里面灌木丛生,野蔷薇、野山楂、毛柳,比着个儿往上蹿,底下布满鹅卵石。河水跳过斑斓的鹅卵石,淙淙流淌。
岸边长着高高的芦苇,小蝌蚪在浓密的绿苔藓上扭来扭去。河边石子一溜儿圆,好像从一个模具中漏下来的。我觉得很奇怪。
草很深很密,大多是禾本科。浓浓的草香味沁人心脾。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虫子,受了惊动,四处跳跃,鸣叫,奏起乱糟糟的大合唱。这大概是我所听到的最没有腔调的合唱了。
我们分了工,同伴架望远镜和摄像机,守住旧巢,记录这几窝攀雀的详细行踪——看攀雀在设定的时间内,飞进去几次给鸟宝宝喂食,又飞出来几次,以及它们的伴侣的情况等等。总之,把攀雀这一整天的生活一个不漏给照下来(攀雀是否知道有人在跟踪、探秘?)。
我过河到远处找新巢。找鸟巢太有趣了。碧草齐腰高,浓密幽深,随风送波,走过去沙沙沙地响。我吹着乱七八糟的口哨在草里闲逛。蓝、紫、白各色花都比着劲儿朝上长,它们在草的遮蔽中闪一下,消失,又闪一下。那种美好可爱的模样,让人怦然心动。那黛色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细细回旋叮叮咚咚的溪流,合成一个不可言说沁人心脾的圣境。我干脆仰面朝天,在深草里睡了一大觉。我睡觉时,大树罩住了强光,草把我藏得严严实实,谁也看不见,除非打我头顶飞过的几只鸟儿,我的每一寸体肤都触及这清香的植物,这潮湿的泥土,这红红绿绿的花朵。
总共找到八个新巢。我坐在小板凳上,仰头盯住一个巢。呀,一个茶壶状的鸟巢高高挂在杨树枝头,在风中晃啊晃的,就像一个婴儿的小摇篮。我心想,鸟宝宝睡在里面一定很舒服。久久地看,我知道了攀雀的一些生活秘密。
眼前这只攀雀可真小,是小鸟中的小鸟,只有乒乓球大小。鸟蛋跟豆豆糖一样大,白色,透明。别看它小,孵育率却很高,一只攀雀可以连续下七八个蛋,一天下一个,就像一个下蛋机器,这在鸟类中是罕见的。
我捡来一个废弃的旧巢,仔细揣摩它的形状和材料。这巢很漂亮,它们先用两根树杈弯成一个半圆形,再衔来柳絮、羽毛,一点一点地添加,做成一个花篮。这是鸟巢的主体。鸟宝宝就躺卧在这个花篮里啦!它们可真仔细,一点儿也不能将就,不像有些懒惰的鸟,把巢建得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泥巴一糊就行了。攀雀可不愿这样,它们似乎接近完美,还要给花篮做一个朝下的壶嘴——这是鸟儿的进出口。整个鸟巢看起来就是一个圆圆的茶壶。可见攀雀是才高八斗的建筑师。壶嘴口儿很小,鸟儿从远方飞回来,唰,就射进去,好像一颗子弹,瞄得准,射得快。我站在板凳上,晃晃悠悠看那个壶嘴,心里直嘀咕:“这么小的壶眼,攀雀如何瞄得那么准,又以极快的速度射进去的呢?”真是不可思议。
那边,一只雄鸟正在做巢,雌鸟蹲在一边,慢腾腾地梳理羽毛,让人觉得很可笑。巢建得差不多啦,雌鸟飞进去叽叽喳喳,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见。雄鸟一连做好了几个巢,吸引雌鸟。巢由雌鸟儿挑选,看中了,就开始坐窝孵育,看不上的,就丢掉。最厉害的一只雄攀雀,我数了数,几天来它一连建了八个窝——可能想同时吸引八个情侣,但正在孵育的也就二三个,其余是空巢,被放弃了。
攀雀的行为很诡秘,爱情复杂多变,是典型的花花公子。它们和天鹅的爱情观形成强烈的反差。只有极少数攀雀是一夫一妻,有的一夫多妻,有的一妻多夫,婚姻关系笃定的似乎不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一次我刚走到有巢悬挂的大树底下,“哗啦”一声,母鸟从树上飞下来,挡住了我的去路。见我不停步,它身子一横,躺到地下装死。我假装追它,它扭头边跑边在草里打滚,接着,竟然装出一瘸一拐受伤的模样,以此蒙蔽我。它用这些伪装战术想把我引开,保护它的小鸟,我常见鸟儿这种装腔作势的伎俩,可每次都逗得我直乐。
我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也没见到一只幼鸟飞出窝,只看到它们把嫩黄的嘴巴从洞口伸出来,尖尖嘴一张一合,“嗷——嗷”,一个劲儿地叫唤,向妈妈要吃的。它们不知道妈妈冒了多大的危险,还要想尽聪明的点子,对付外面这几个探头探脑的家伙。一个鸟巢里往往有七八个鸟宝宝,这样一来,分配给每只小鸟的食物就很少了,我看到鸟妈妈不停地飞出去找食物。
有一些巢里没有鸟,是个空巢,它们被遗弃了。断定有没有鸟的方法,是看柳树枝是不是在晃动。一般来说,只要有鸟儿,那巢就会像摇篮一样摇啊摇。有一只巢晃动的幅度很大,像个秋千在荡,我感到纳闷,站在板凳上左右环顾才发现,这是大鸟在翻身,哺育婴孩,巢里动静当然就很大了。
“嗖——”我看到一只攀雀子弹一样射出来,嘴上叼着个小白点。它在干吗?原来,它们不停地飞进飞出,除了叼来食物喂给鸟宝宝,还不断从巢里叼出粪便。攀雀很爱干净,从不让小鸟儿拉的屎留在巢里,污染家居环境。它们的粪便很袖珍,像个白色的小米粒。攀雀飞出时我看到,它们个个有一副熊猫眼,戴了一副天然的黑墨镜,雄的眼罩大,雌的眼罩小。雄攀雀的眼罩就好像英雄佐罗的蒙面罩,很滑稽。
一个黑黑瘦瘦歪戴帽子的牧民赶着一群羊经过,我问他见过攀雀吗,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迟疑地摇了几下头。我拿出样本给他看,他惊讶地甩动羊鞭大喊大叫:“灵雀,灵雀!”吓了我一大跳。看来,当地人管这个鸟叫灵雀,可能因灵敏而得名吧。
我家屋前的小鸟
四月的光洒遍每一个角落,我坐在院子褪了色的小方桌前,享受每一寸光的照耀。
院落里野草可劲地长,荨麻草更是疯了似的,长得有一人高了。许多小鸟对荨麻草情有独钟,站在草尖上晃啊晃的,我呆呆地看它们玩,好像荡秋千的不是鸟儿,而是我自己,我变小了,变轻了,成了一只小鸟,和它们一起在那里荡。
最喜欢站在荨麻草上的是一群小麻雀,“哗啦——”一个黑影子从天空一闪,黑压压落下一大群,并不久留,好像不是为了叼草籽吃,只为了经过荨麻草时,在草尖点一下,逗留一会儿,也不知它们到底图个啥。更多的时候,它们排成一排,站在泥墙上,东张西望,蹦蹦跳跳,唧唧喳喳,极其活跃。偶尔,它们也会安静下来,闭着眼,打盹,晒太阳。
有一种鸟是我的常客,它们有一掌长,小头,长身子,灰背,白腹,脖子上戴一个黑项圈。它们总是冷不丁飞过,落在院子里,迈着碎而快的步子,朝前走,尾巴又细又长。每当它们迈步子时,尾巴也跟着一点一点的,尾巴尖触着地面。有一次,我看到它捉了一只白色的小虫子,在地上一磕一磕,“咚咚——咚咚——”发出一种很古怪的磕碰声。我以为它啄地下的小石子呢,觉得很怪,低头仔细一看,它锲而不舍地啄啊啄,终于将那个可怜的虫子吞进去了。又一次,它一直在我身后踱步,可我并不知道,直到我转身时,它才惊叫一声,慌慌张张飞走了。我后悔得要命,早知道它跟在我身后,我就让这个跟屁虫自由自在地安心漫步。
遍地的荨麻草,细而高的狗尾巴草,低矮碧绿的兔耳草,它们一起在风的奏乐中翩翩起舞。
变天了,铅色的阴云布满天空,森林间拉起紫色烟雾,后来这纱帐又绕过岩石,绕过峡谷,轻柔缥缈。“滴滴滴”草丛里传来几声婉转的鸟鸣。我循着声音悄悄爬过去,一只鸟儿正在草丛间欢快地觅食。它身子敏捷,迅速地从一棵小草尖上,跃到另一棵小树上,它攀住的一个枝丫,摇啊摇的。它的动作轻盈又迅疾,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
抬头的一刹那,它的头颈和腹部两大片金黄的绒毛,闯入我的眼睛,非常耀眼。
多美的一只鸟儿,它的毛色和花纹让我两眼发光。它披黑白相间的花衣,尾部别一把小刀,约一指长。我对着鸟谱认出来了,这个鸟中佼佼者被人们称为“草原一枝花”——黄头脊鸟令鸟,因长相出众而大名鼎鼎。
有三只,它们相隔约一米,跳跳停停,在歌声中觅食。它们看起来相当自信,这种自信也许缘于它们美丽的身姿和鲜艳的羽毛。在见到它们的一刹那,我有些冲动,想给三个家伙画一张素描图,但我绘画的水平太差了,画了几张都不成样子,看起来有些败坏它们的形象,只好作罢。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它的模样已经装在我的心里了。
另一次我弯腰吃力地在山路上走,气喘吁吁。
山路盘旋而上,沿途布满了大大小小黑色白色褐色的石块。山路右侧,是一条河流,高声欢唱,一路陪伴着我。河床一会儿宽,一会儿窄,河中巨石突兀,浪花翻滚,轰轰作响,气势惊人。有一处,宽银幕样的瀑布从天空垂挂下来,一个银色的链子将天上人间合为一体。
一只黄脊鸟令鸟在这个通天梯上点水玩耍。它敛起翅膀,飞速地点一下,再点一下,小水花随着它的小圆身子跳跃着。它实在太顽皮了。我有点替它担心,怕它被那巨浪般的瀑布吞掉了。我欣赏它玩耍的模样,看了好几分钟,才明白,是多余的担心。它的小身体灵巧又机警,它天生就是戏水的大玩家。我的心也就放下了,悄悄地乐,还为它鼓掌,但不知它是否看到了。
隔了两天,我正在太阳底下洗脸,“唧唧——唧唧——”河边林子里有鸟儿乱叫,我赶紧绕到屋后。天哪,一个高高的独枝上,一只鸟儿正在高歌,小小的身体,腹部是一片麦穗般的金黄。它在晨练吗?它的心情看起来好极了,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来回折腾,好像故意表演给我这唯一的观众看。我忍不住大叫一声:“黄脊鸟令鸟!”呵呵,我的呼叫声把鸟儿吓了一大跳!小家伙愣了一下,跳了一个蹦子,很快又平静了,有些嘲讽地盯住我看了一阵子。我为自己终于记住了某几种鸟的芳名自鸣得意。说起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常背鸟谱,记它们的模样,可一旦这个鸟突然光临,我就傻了眼,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一次,可不一样。
责编: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