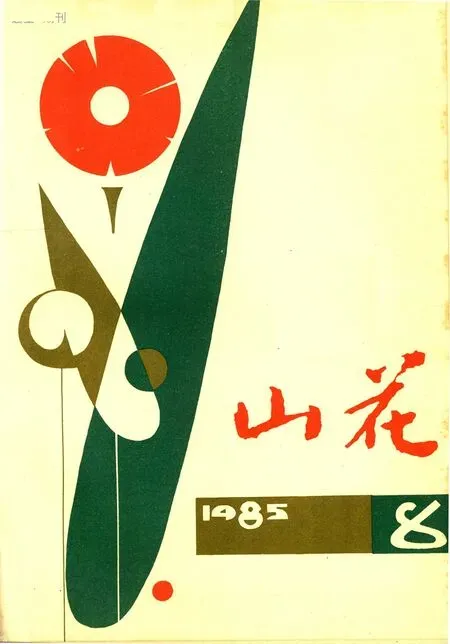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命运意识
王艳平
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命运意识
王艳平
人类从诞生之初,就希望能够自主决定生存形态,但却最终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存总是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为了自己的追求与向往,人们也不断作出努力和抗争,但一次次抗争的结局总归于失败,于是人们就臆想冥冥中可能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命运,于是这也就成为人们对自己身不由己的生存状态最好的借口。从《论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到《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者,命也”,以及我们经常提到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可以看出命运观念深入人心。古今中外很多哲学家、文学家也阐述过对命运的理解。作为我们最先认识的台湾作家白先勇在他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也通过他所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凸显了他对命运的理解,表现了其浓厚的命运意识。
《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由14个短篇小说构成,其中人物几乎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各阶层:有“大”人物,如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有“中”人物,《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有“小”人物——下层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这些人物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从他们身上,我们不难找到共同点:他们都在受命运这只巨手的无情拨弄,由于命运,他们倍感生存的无奈、凄惨和苍凉,而且在命运的神力作用下,他们都身不由己地归于这样或那样的“毁灭”。
白先勇对“命运”的阐述,从他的《台北人》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中可见一斑。小说刻画了一个“总也不老”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从上海到台北,不管时空如何变换,尹雪艳却是凝固不动的,她“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她的均衡”,然而她却“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围绕着尹雪艳身边的男子都难逃劫数:王贵生犯下了官商勾搭的重罪,被枪毙正法;洪处长在娶尹雪艳后一年丢官,两年破产,空空如也;年轻有为的徐壮图死于非命。白先勇在小说中把尹雪艳形容为“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颜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冰雪化成的精灵”。尹雪艳既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白先勇赋予她一种神性,好像在用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众人,将众人都“拘到面前来”,然后“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目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叱咤风云的,曾风华旷世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尹雪艳就如一个命运之神在毫不留情地拨弄着众生,肆意张扬地摆布着人类。
第二篇《一把青》中的朱青的人生遭遇进一步让我们感受到命运的强大,人的渺小和软弱。在南京时的朱青还是一个金陵女中的学生,清纯、羞赧、专情,“面皮还泛着些清白。可是她的眉眼间却蕴涵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被拿走了心的郭轸把飞机开到了她的学校上空,受了处分,她因此被开除,等到新婚宴尔,命运却又把郭轸给带走了,于是翘首以待,盼望和郭轸的重逢,但这次命运却永远带走了她的幸福。平凡而又普通的愿望,一次次被夺去,艰难的努力一次次被摧毁,人在命运面前显得渺小而又软弱,命运表现为一种无常感,一种孽缘。
他最精致完美的杰作《游园惊梦》中看不到人物对命运的抗争,但却在前尘往事的感时伤怀中揭示出人的“命运”的失落和轮回。《游园惊梦》主人公蓝田玉原是南京秦淮河畔得月台名伶,擅长昆曲,尤长于名段《游园惊梦》,被钱鹏志大将军看上并娶为填房,享尽了荣华富贵。钱将军虽然对待蓝田玉有如女儿,百般珍爱,但由于两人年龄悬殊,使她事实上是在一种生命的死亡状态下享受这种外在物质形态的荣华富贵。钱夫人与钱将军的参谋郑彦青陷入情网,并与之灵肉结合,但她的嫡亲妹妹月月红,在一次宴会上,夺走了姐姐的情人,钱夫人因伤心而哑了嗓子。钱将军去世后,当年的蓝田玉在经历了将军夫人的显赫之后又成为一介平民,她的一切辉煌早已成为过去,一人独居冷清的台南,孤独黯然地消磨自己的岁月。而昔日的桂枝香在被妹妹踹脚和做偏房等坎坷之后,终于扶了正,丈夫也做大了官,故事就以蓝田玉接受昔日姐妹、今为窦瑞生夫人桂枝香之约赴宴时,追忆前尘往事和宴会这一现实场景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两条线索交错展开。
小说中的钱夫人,这位曾经是繁华热闹的“舞台”上的主角人物,如今却只是站在舞台一旁的一位“看客”,众人的精彩出场一次又一次勾起她对往事的伤心回忆。钱夫人一生的经历其实早已被流逝的时间和不可更改的命运所操纵,曾经的荣华富贵终将谢幕,最后只留下些许残存的记忆,偶尔在别人的晚宴中被唤起,今昔对比的落寞、物是人非的苍凉是时光流逝和命运流转的必然结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钱夫人命运的失落,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这种失落不仅在钱夫人身上出现,在不同的人和事上不断地重复出现,呈现出一种轮回。小说开头,钱夫人到达窦公馆时,“一踏上露天,一阵桂花的浓香便侵袭过来了”。原来享受着荣华富贵的是钱夫人,而今日享受着极端荣华富贵的是窦夫人,而这桂花的浓香发自露台,露又能维持多久,未来的桂枝香又何尝不会成为今日的钱夫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白先勇命运意识的核心:“命运不但是人把握不住的,而且似乎也总是悲剧性的”。[1]
《岁除》中赖鸣升面对现实失败时,企图以过去的辉煌回忆抵消和抗拒,从他这种努力的无奈和可悲本身,我们可以看出人在现实命运面前的渺小卑微,人的命运的不可抗拒,以及人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努力抗争的最终失败;《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的选择表现了她对现实命运的无奈臣服和黯然皈依;《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王雄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也最终失败;《思旧赋》中,我们看不到与命运进行的抗争和搏斗,弥漫全篇的是哀感凄凉,是无奈的沧桑,而在此背后蕴涵的是对强大命运的顺从与感叹;《孤恋花》、《冬夜》则显示了命运对人的捉弄和摆布;《花桥荣记》中一系列人物的遭遇向人们展示命运的不可违逆和人们不甘心顺从却不得不顺从的悲剧,还有《一捧雪》、《国葬》等无不向我们展示命运的强大和不可抗拒。
从《台北人》中人物命运的最终结局,我们可以看出白先勇命运意识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一种无常感、一种冤孽。所有人都在命运的摆布中,每个人都难逃命运的罗网。而其作品中演绎的人物命运的基本模式则如《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一句所宣告的:无论是谁,无论是抗争还是服从,其最终的结局都归于失败。
命运观念的拥有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西方在希腊时期就开始探讨命运问题,命运观作为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在各个民族、各个历史阶段普遍存在,也影响着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生命态度和心理结构。人类把自己从动物当中提升出来,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已经发现一旦面对自然,产生一种想要征服自然的意识时,就会同时产生另外一种意识,即在和自然斗争中,他发现自己还有一个敌人——他自己。“人非常可悲地意识到,自己在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不只是面对着自然界对自己的控制,而且有一种神秘的自己根本无法掌握的力量在支配着自己,自己在一条自认为平坦的大道上往前走的时候,却忽然跌入了陷阱;本来想向东,结果走到西边去了。这种神秘的自己不可知的、令人感到恐怖的力量就叫做‘命运’”。[2]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分别以他们的作品显示了各自的命运观。希腊人观念中,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知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命运观也在变化。埃斯库罗斯把命运看做具体的神物,主人公相信命运,认为命运支配一切,包括神;索福克勒斯则不把命运看做具体神物,而认为它是一种超乎人类之外的抽象观念,虽然不可抗拒,但其正义性、合理性确是可以怀疑的;欧里庇得斯却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行动。白先勇的命运意识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对希腊文学中的命运观念有着很深的渊源。而其命运意识的核心内涵“无常感”却缘于佛教中的“诸行无常”,即“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变化不已,没有常驻不变的。人生无常,因此,一切皆苦”。[3]而白先勇的“无常感”主要是指人生的种种变故和转化是没有前因的,难以预料和控制的,人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和转化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无助和渺小,任其摆布而无法制止。而“孽”,白先勇对它的解释是“孽缘、孽根,我想人性里面生来不可理喻的一些东西,姑且称为‘孽’”。[4]这种命运观又带着中国文化的特质。在《访问白先勇》中,白先勇也提到“个人宗教感情相当复杂”。[5]“差点信了天主教,其后虽然没有入教”,[6]但天主教给他很大的启发。到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宗教情感是佛教的”。[7]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深。而他之所以“喜欢《红楼梦》,与其中的佛、道哲学很有关系”,[8]“《游园惊梦》,也充满了佛道的感情和思想,在传统文化里头,佛道与儒家是一而二,二而一,一体的两面”,[9]其实儒、道、佛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与生俱来、无法分清的,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宗教中,儒释道三者早已融会贯通,难分彼此。佛教的大慈大悲和儒家的仁政思想结合在一起;佛教的色空观念和道家的人生无常以及儒家的消极避世纠缠不清。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人生认识及文学表现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儒的现世实用精神和道德虚无飘渺的奇幻想象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文学存在的基本意义和基本形态,而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和中国固有传统融合交织并中国化后,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带来了更为深刻的思想蕴涵乃至艺术结构。古代文人在现世环境中受到挫折和打击时,就会追求一种思想能够为他们人生的不断失败提供合理的令人能认同并接受的阐释,佛教理论中的“轮回”、“无常”等使他们从中寻找到了环视自己人生失败和精神苦闷的通道。因此佛教的渗入是中国文学在厚实的内容和绮丽的表现外,还带上了一种人生的参悟和东方式的智慧,这种对人生和世界的东方式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对之吸收、改造同时,也对之进行了强化,使之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特有精髓。而对于像白先勇这样一个自小对世界和人生有着敏锐“无常”感受的作家来说,中国文学传统的这种精神对他必然会有深刻影响。他提及《红楼梦》说“这本小说还有一种超越性,就是写佛家和道家思想,写人生变幻无常,这种思想,由古至今,都可以引起人的共鸣”。[10]他还十分欣赏《三国演义》的题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佛教情怀已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
白先勇的命运意识表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和渺小,人们抗争命运的无力,但对这些失败的人们,白先勇却表现出基督教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感。白先勇是一个回民,恪守伊斯兰教的一切礼俗,但思想上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西方的这种宗教精神,其实这种精神并不为西方独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这种精神的体现,如中国儒家学说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就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精神,由此可以看出白先勇命运意识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承继和融合。
注释:
[1]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2]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3]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4]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5][6][7][8][9]白先勇:第六只手指·访问白先勇,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542页。
[10]白先勇:第六只手指·文学的主题及其表现,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王艳平,女,鹤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