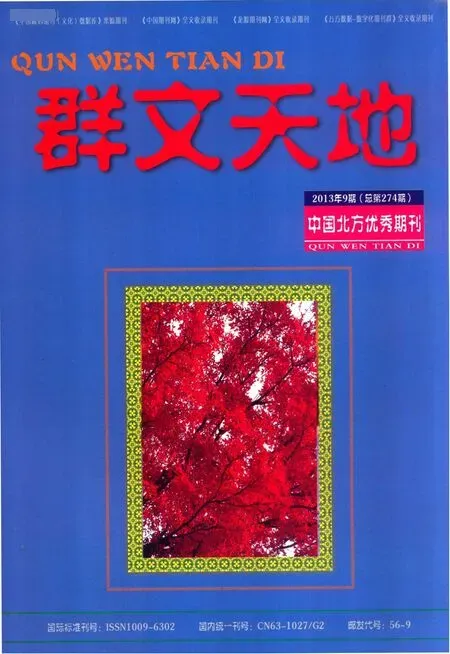左宗棠与西宁
靳育德
左宗棠被誉为清季“中兴名臣”,过去,人们就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事,指责较多,但他用兵新疆,反击阿古柏入侵,被认为“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与张骞、班超并驾齐驱。无张、班二人,无中国之西域;无左宗棠,中华之新疆今落谁人之掌,未可知矣!”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左宗棠,字季高,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左家塅。幼时家境贫寒,拿他自己的话说:“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二十多岁时,虽因家贫依居妻家,以教书、种田为生,却书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张挂在门厅。夫人周怡端曾以“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的诗句来安慰他。公元1851年1月,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举事,这时的左宗棠已到不惑之年,才受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参赞军务,真可说是“大器晚成”。之后,受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起,将建国十三年、略地十一省的太平军结束在嘉应州的黄沙嶂,因而官封一等恪靖伯。
西北边疆本来是清王朝的军事要区,由于东南战事连年,陕甘兵卒抽调出征,地方驻守兵力严重不足,粮饷短缺,加之爆发了以白彦虎为首的农民起义,“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各省自顾不暇。就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同治三年,喀什噶尔境外的小国浩罕有一个名叫阿古柏的竟趁新疆边境空虚,聚众从安集延窜入新疆,攻陷了南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占据了天山南路,并自称“毕条勒特汗”,进而入侵天山北路,意欲夺取伊犁河谷。至此,南至和阗以南,北至玛纳斯、呼图壁,东到吐鲁番、诺羌,西至边境的一大块国土,竟沦入阿古柏统治之下。阿古柏在占领区开征地税、要求人们按安集延“光顶圆领”的习俗,改变服装。陕甘烽火连天,国势危如累卵,俄军也乘机寻找借口,侵占北疆伊犁河谷。新疆眼看不保,朝廷内又有“海防”、“塞防”之争,当时竟有人认为新疆“地处僻远,师行困难,内地经十多年战乱,元气大伤,筹款不易,暂以度外置之。”左宗棠力陈:“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同治五年十一月,在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间,调任陕甘总督。同治六年二月,左宗棠督军从汉口出发北上,分三路入陕,力挽西北危局。就像他在《书牍》中曾说:“欲图数十百年之安,不争一时战胜攻取之利”,经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战,平定了陕甘,在“新复之地,发牛种赈粮”,尽力做好善后恢复工作,为集中军力进疆解除了后顾之忧。并命自泾州至玉门夹道种柳,使之“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左公柳”。六年后的光绪五年,杨昌濬应左宗棠之约西行,沿途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触景生情,曾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进疆路途遥远,粮糈运输困难,加之清军所控地盘只有经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到济木萨和塔尔巴哈台这狭长一线,其余地方都在阿古柏控制之下。清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驻节肃州(今酒泉),督办军务。他采取缓进速战的方略,决定首夺乌鲁木齐。六月二十九日,刘锦棠率军攻取乌城,随后在金顺和伊犁将军荣全的配合下,三军会攻,到九月二十一日收复新疆北路。
阿古柏失去乌鲁木齐后,集中兵力坐镇托克逊。为把住南疆大门吐鲁番,召集余部死守达坂城。为彻底消灭阿古柏入侵者,左宗棠迅即调兵出关增援,光绪三年三月初一,刘锦棠进军达坂城,张曜从哈密西进屯盐池,徐占彪率军出巴里坤。初七日,克达坂城;同日,张徐两军攻占七克縢木;十三日,会师吐鲁番,“乘敌不备,歼尽守城贼寇”,星夜兼程,攻取托克逊。大兵压境,风声鹤唳,阿古柏在喀喇沙尔授命爱伊德尔呼里代表自己,表示愿献南疆八城乞降。乞降之事未果,四月初十,阿古柏逃往库尔勒服毒自杀。刘锦棠等挥军越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分兵两路,攻取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和阗。至此,南疆八城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新疆南北两路收复后,只剩伊犁尚在俄罗斯占领之下。当年俄军初入伊犁,曾声明:“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收复后,俄方却毫无归还之意。光绪六年正月,清政府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与俄方磋商收回伊犁;四月,左宗棠不顾年已六十九岁的高龄,车载着棺材,率军离肃州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五月,驻军哈密城西凤凰台,并决定兵分三路,进驻库尔克拉乌苏、精河,做好了收复伊犁的军事准备。正是“文有曾纪泽折冲之才,武有左宗棠干城之勇”,清政府才以偿还俄罗斯九百万卢布“代管费”的代价,收回了伊犁。这是晚清外交史上仅有的一次胜利,正如左宗棠死后,有人在挽联中所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左宗棠死后,清廷谥‘文襄’)”。
早在同治十一年九月,正当平定西宁的战事进行时,左宗棠就在安定(今定西)大营命三品衔刘锦棠戡定湟中后,“凡乱前所毁学校、书院、义塾等,均需第次重建”;冬,左宗棠知道西宁自经“河湟事变”后水利失修,田园荒芜,曾命西宁各厅县详细调查境内荒废渠道,准备敷料,以待来年春实施兴修。据《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介绍,在他的关注下,“修复了府城(西宁府)西阴山崩裂时压坏的渠道约一里许,创修碾伯(碾伯时属西宁府管辖)栖鸾堡一带沟渠二十公里。至于小峡外曹家堡一带,兵燹而后,烟户萧条,渠道虽废,就没有人力修复。”进军新疆期间,虽南北疆烽火连天,但左宗棠认为,没有河西走廊,不能保新疆,也不易保陕甘;没有宁灵(指宁夏)和河湟,也不能保新疆。所以在新疆用兵时,为防御敌兵溃散时窜向敦煌,进入青海,做了积极的防范准备。
西北大局平定后,青海办事大臣豫师在西宁小峡口南北两岸各修建一关,作为平乱后的一组纪念建筑物,伫立在西宁东的军事要地上。两关修建工程竣工后,豫师特派专人去左宗棠处请求写篇《记》,以记其事,他不辞辛劳,欣然命笔,写下了已收入《西宁府续志》中的《西宁小峡河新筑南北两关记》。左宗棠在《记》中说:“西宁城东,悬崖陡壁,对立千仞,湟水中流,霆惊箭激,山径狭隘,……守者得此,以一当十;攻者逾此而入,则西宁不可复守。……光绪三年,青海办事大臣豫师公于河南北筑两关扼之,屹然相向,形势险固。南关曰武定之关,志兵威也;北关曰德安之关,饬吏治也。”清末西宁诗人张思宪曾以《石峡清风》为题,写下了有名的一首七绝诗:“石峡新修武定关,东西流水南北山;行人莫嫌征尘污,两袖清风自往还。”我们可以想象,小峡两峰高耸,苍崖苔染;关楼屹立,一水中流。是一幅多么雄浑的边塞图啊!上世纪20年代初,陇上名士周子扬经过小峡时,见到“两岸有关,北完南圯,路左有左文襄所撰《创修南北二关碑记》。今‘德安’独存,而‘武定’半圯,岂乙未再变时所毁耶?”
可惜九十年后,这里不要说“半圯”的武定关痕迹无存,就连德安关也灰飞烟灭,更不要说左文襄公所撰《创修南北二关碑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