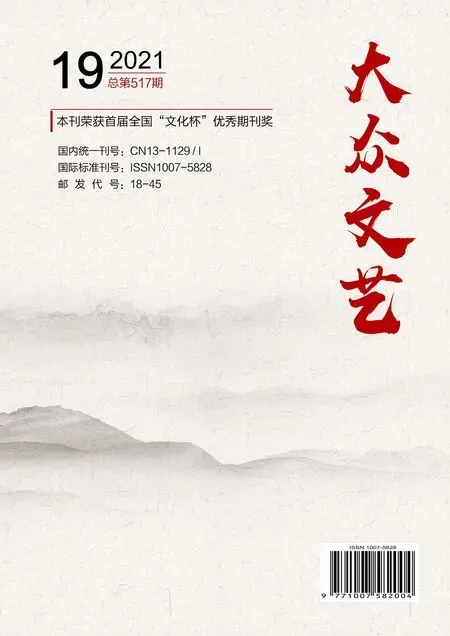现代的古典意象:张爱玲的“月亮”
李爱红 (山东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在中国文化里,月亮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同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朗朗明月从古至今绵延流转了中国文人广阔的心灵空间,它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体验,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1中国古典诗词善于把世事的忧患、人生的缺憾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审美化和诗意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意象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张爱玲在作品中,频频使用月亮意象来摹写人物、描绘景色、表情达意,并寄托对人生的感悟与体认。这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的:“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道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2
一、冷月无声
张爱玲小说的基调是“苍凉”,与此相适应,她喜欢写一些冷色调:蓝色、青色、灰色、白色是她常用的色调,月亮意象自然被这些色调来修饰成冷月。面对人性真实而残酷地暴露,张爱玲依然能够平静而不失锋利,只因她不是前世之石,而是冷月无声。
在《倾城之恋》中,作者写离婚后的白流苏在娘家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最终为了抓住“财富”这棵最后的稻草,走上了大多数人会选择的一条庸俗之路:为了生存,白流苏远赴香江,博取情场高手范柳原的爱情。两人在浅水湾饭店展开了关于爱情的真真假假的斗法和试验,在真实与虚幻的斑驳光影中,她对人生的悲凉有了越来越深刻的切肤体验。在这篇小说中三次写到月光,有泛着寒光,如霜的冷月:“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楞。” 有的是借着冰冷的月亮营造苍凉意境,平添人物的孤独凄凉之感:“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心寒,拔转身走到梳妆台前。十一月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回到了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
这里的描述的月光,就是白流苏眼中那不复柔和不复温馨的月亮。这是因为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并没有真爱,只是急于抓住实实在在的物质,被迫冒险用冰冷的奢华在填补内心的空虚与绝望。于流苏而言,她的婚姻如同长期卖淫,范柳原给予她的这个刻薄无情的断言因真实而惊人。这让我们想到弗洛伊德在1908年说过的:“大多数的婚姻的结局是精神上的失望和生理上的剥夺。”又说:“要消受得起婚姻的折磨,一个女子必须特别健康才行。”3流苏的悲剧是用世俗表象掩盖了悲凉感的悲剧,所以她要比大多数人更不幸。且看张爱玲写她眼中月亮时用的字眼:“光冷”、“霜花”、“银鳞”,还用了绿、银、白等冷色调烘托出悲凉的气氛,这就把白流苏心中那冰冷的感觉外在化、具体化、物化了。另外,作者还用“模糊”的月亮来预示她暗淡的人生前景。这里,模糊的冷月既明示与流露出白流苏的孤寂无依和凄凉悲惨的身世之慨和人生命运,又折射出深蕴其中的无限苍凉的意味。香港陷落的战火,成全了一场无奈的恋情。伴着一弯冷月,笑吟吟的白流苏在万盏灯火的夜晚,听一曲苍凉的歌。这样的爱情是倾城之恋,但又是可悲的,辛酸的浪漫而已。原来在相爱之外有许多东西在主宰着爱情,反倒显得相爱是不足为道的。
再看《多少恨》里一个用月亮作比的譬喻:“她不能够多留他一会儿在这月洞门里。那镜子不久就要如月亮里一般的荒凉了。” 这里冰冷的镜子被比喻成月亮,月光的冷辉与镜子的冷光,让人顿感寒凉。张爱玲对月亮的眷恋之情,我们可以透过人物的眼与心深刻明了。她时刻准备着让笔下的人物与月亮有情感交流与共鸣,月亮也随时随地可以映衬人物的心境。这是个非常特别的比喻构成,用荒凉的月亮为喻体,而它所喻的本体是被爱情的喻体镜子。映在镜子里的那对爱而不得的恋人因爱情的中断,空对着一片荒凉了。
二、缺月挂疏桐
在古典诗词中,月亮常常象征着温馨和美的家园。在古代,不论是女系氏族期还是男权主宰一切时,女性与家都是幸福温馨的代名词,是可以给人呵护关爱的避风港。人们在外遭受挫折、身心疲惫之时,总能在家中得到安慰,获得精神慰藉。而月亮的隐性特征赋予它同样的静谧、温馨、祥和,成为古人心中的精神家园。因此,古代诗人常常望月思乡,借月抒怀。然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缺月便是家园缺失,心灵无归宿的写照。张爱玲从一首首思乡怀人的咏月诗中读出了月亮的这一美好象征,而反其意用之,塑造了经典的缺月意象。
在《金锁记》中,长安所出生的家庭,尤其是有七巧这样的母亲,就注定了她悲剧的命运。小说中,张爱玲用了缺月意象渲染她决定退学后的悲哀心理:
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
这就是长安眼中的月亮,有一种虚无缥缈,无法确定的意味,但又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凄凉晦暗的诗意。“缺月”这个意象是长安的象征。长安的命运亦如她眼中的那残缺的月亮,有如此多的残缺,让人唏嘘不已,却又是生来注定,无法改变的。她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一个悲剧;因为有七巧这样一位心理扭曲变态的母亲,注定要有一个残缺甚至完全被毁灭的人生,所以长安本身就是一种牺牲,而且最可悲的是这是一种模糊的牺牲,长安自出生起就注定要陷入这种不清醒的模糊悲剧中。正如天上模糊的缺月,长安自身也是模糊的,平庸的姿色,平淡的举止,都增添了她的模糊性。长安自身的性格也是模糊的,她的退让和牺牲也还是模糊的。长安的月亮于是就具有某种模棱两可的诗意,说不清道不明,没有人教她应怎样做,她只是下意识地觉得应该是这样,惟有这样,这种模糊的意识,已经足以督促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下定一个模糊的决心。长安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牺牲就像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其实这种手势只是她唯一的自卫武器而已,衬着墨灰的天和几点星,再美丽、再苍凉的手势也会变得模糊,仍旧还是一种徒劳。以悲景写悲情,原本悲衰的内容却用欢快的形式表达,越发凸显了景之悲、情之悲、人之悲。
“缺月”本有两种:一种正在走向圆满的新月,它是带着希望与激情,临空普照,让人翘首,让人雀跃;一种是由圆满而陷入偏缺,它必定要经历残毁甚至沦丧。长安眼中的缺月当然是后一种。因为七巧依旧继续“迫害”着自己的女儿,她让生病的长安吸食鸦片,直到完全葬送了长安原本可以幸福美满的婚姻。就因为她自己身处不幸,容不得别人包括自己的女儿可到幸福,极尽恶意中伤之能事,千方百计破坏了长安和童世舫的幸福。长安的悲剧完全是七巧一手蓄意造成的,可以断言七巧在一日,长安的不幸就存一日。月亮便是这个苍凉悲剧的见证。只是那月永远不会再圆。
三、依依残月下帘钩
“孤月停空欲别时”,孤月是象征孤独失意的意象。曾引发了我们诸多美妙的遐想的 “嫦娥奔月”神话,蕴含着此类文化意蕴。孤悬浩瀚天空的月亮,流淌着无尽的清冷月辉,正是嫦娥孤独寂寞、惆帐凄苦的情感流露。在古典诗词中,我们常常看到失意、彷徨的古代文人,总是引月为知己,借月抒怀,寻求寄托,释放郁结。蚀月、残月的孤凄意味尤为浓重。张爱玲就擅于在小说中用残月的意象写男女恋情的崎岖坎坷。
“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 这是张爱玲在她的早期作品《霸王别姬》中对虞姬的心理活动的摹刻。在中国男权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女性始终是男性的附庸,男性是日,女性是月,再辉明的月光也是来自日光,再迷人的月色也有 “被蚀”的最终结局。张爱玲早在少女时代就明白无论项羽能不能做成皇帝,虞姬最终都无法逃脱“被蚀”的命运。这里,虞姬的“阴暗、忧愁、郁结、发狂”不仅是个人,同时也是无数中国女性可以预见的处境与心态。
《半生缘》是张爱玲小说中描写两性关系最温暖的一部。其中有着难得一见的纯挚爱情。在这部小说中,月亮一直紧随小说主角世钧和曼桢,丝丝入扣地映照着这对恋人的微妙心理,自如、自然地勾勒出故事的变化,并恰到好处地渲染着规定的情境。两人初恋时月亮是“像一颗白净的莲子似的”凸月——彼此心照不宣,心灵相通,毋需太多言语,即可感到对方的款款深情。等到定情之际则是“特别有人间味”的“黄色的大月亮”,显然,这是成熟、圆满爱情的象征。彼此心意的明朗化,各自心中如黄色满月般敞亮明净。后来,当曼桢被姐姐设计、幽禁,世钧寻其不得,最终两人失之交臂,咫尺天涯。这时,两人同时看到的了“一钩淡金色的蛾眉月”——爱情的美丽被曼璐的阴谋慢慢蚀掉,温情一点点荡去,逝去,只剩下那弯残月样的一丝记忆。这弯残月是眼前之景,更是心中所想,曼桢与世钧始终对他们之间的真挚爱情留有一丝丝希望,然而事与愿违,这一钩细月,最终还是化作了两人心中关于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的一抹幻影,是一点点的痴,一缕缕的怨。斗转星移,蛾眉月可以变回满月,但曼桢和世钧却再也“回不去了”,他们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那钩蛾眉月下,注定了这是段擦肩而过的爱情,让人茫然,无望。
月亮是张爱玲的品性,是她文章的格调,也是她古典气质心性的书写偏好。月亮情结显示出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她钟情于逝去的年代与那个年代的文化:喜欢穿清装,常把小说背景置于旧时代的大家族,擅于演绎男女婚恋这个经典主题……在月亮意象的使用中她更是始终秉承着中国古典诗词将人生缺憾、世事忧患诗意化、审美化地呈现为艺术的传统,由此传达出一种地道的古典韵味。
逄增玉先生曾说过:“张爱玲所具有和表现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时间观与历史观,而回避和舍弃了现代性的进化时间观与历史观。时间和历史既然是苍凉循环的,那么,在时间和历史的大舞台上所上演的种种人生故事、人生命运,自然也就是苍凉循环而非‘进化’的。”4——即使在有着所谓的优雅与趣味的文明社会里,人生的真谛依旧没变。张爱玲深谙此理,将古典诗词中月之魂与自己作品的人物命运巧妙的融合为一体,用月亮意象把普通人无奈悲凉的人生,日常琐碎的生活中散发出的命运的压迫感和无以名状的空虚、压抑、荒诞、对生命与命运的困惑与绝望,描摹得透彻而尽致。
注释:
1.傅道彬.《晚唐钟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2.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评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3.霭理士.《性心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5页.
4.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评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刘锋杰.薛雯.黄玉蓉.张爱玲的意象世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李欧梵等.重读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5]胡亭亭.张爱玲的世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