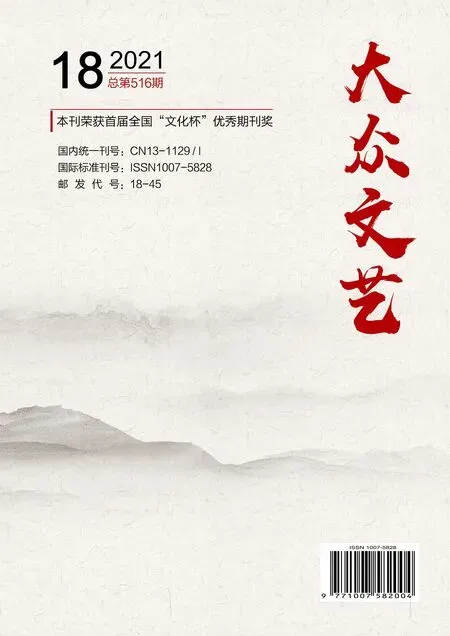初唐四杰诗歌中的盛世先声
韩 宁 (韩国大田培材大学中国学部)
唐代的盛世,无疑应该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的盛唐时期。盛唐诗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风貌,积极进取的心态,以及渴望功业的英雄气概,皆为盛世之声的反映。然而,盛世之先声却是最先从初唐诗人的诗歌中呐喊出来的。
四杰王、杨、卢、骆是初唐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诗歌创作唱响了盛世先声。四杰都是少年才子,卢照邻十岁便能诵记《苍》《雅》及经史;骆宾王七岁作《咏鹅》;王勃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写出《指瑕》十卷;杨炯十二岁举神童,授校书郎。不过天才似乎总被天妒,四杰的人生经历了诸多挫折磨难,王勃渡海,堕水而卒;卢照邻因不堪忍受病痛,自投颍水而死;骆宾王随叛军叛乱,兵败,不知所终;惟有杨炯算是善终,但亦终生不得志。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未磨平他们身上的棱角,反而让他们锋芒毕露。
四杰才高文华,冠绝一时,但他们又有着恃才傲物、浮躁浅露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加上蒸蒸日上的国力,催生了强烈的功名心。在四杰的一些文章中,屡屡急切的表达自己的求名求显之意。如骆宾王所作《自叙状》本是婉转推辞李元庆的垂青提携,他自叙“进不能谈社稷之务,立事寰中;退不能扫丞相之门,买名天下”,表面上是自谦,实际上是不屑,他本是要“立事买名”“谈社稷之务”“扫丞相之门”的,而区区李元庆的提携怎能屈就?①
强烈的功名心,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推陈出新,显才扬名。唐太宗作《帝京篇》十首,骆宾王亦作同名诗一篇。且骆作在结构、立意上明显模拟太宗诗,但又在篇幅、句式等方面刻意表现出不同。太宗作《帝京篇》,因其帝王的身份,此作蜚声内外。骆宾王作同题歌诗,本身就比较引人注目。而他在刻意模拟之外,又有所区别,似乎有相较略胜一筹的私心。事实证明,骆宾王用《帝京篇》扬名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旧唐书》本传载:“(骆宾王)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②
卢照邻“放旷诗酒”③,骆宾王“落魄无行”④,王勃、杨炯“恃才傲物”,一个杀人犯法,一个执法苛酷。⑤张扬无行的背后是他们自信、自负的个性,这样的自信是才华横溢难以抵挡的自信,这样的自负是志向高远肩负理想的自负,以这样的自信自负而创作的诗歌定然具有开阔的意境,具有大丈夫的气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把离别说得如此风轻云淡,不是不伤感,而是小小的离别怎能堪比心中的理想,离别后,放眼前路,那是更为豪迈的事业。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不同以往的激情振奋的道路,投笔从戎之后,那就是轰轰烈烈的人生。这是多么高涨的热情,多么崭新的面貌。
其时,流行于诗坛的是宫体诗和上官体,宫体诗和上官体的雕琢精致,细腻典雅,无疑熟练了诗歌的技巧,但是,仅仅有这样的技巧还远不能迎接一个盛世诗歌高潮的到来,盛世之音还需要风骨和气势。四杰的诗歌粗犷豪迈,充满了对人生和理想的自信,极具个性色彩,而这才是盛世诗歌的灵魂和精髓。
由于过着“承平日久”的生活,盛唐诗人已把盛世情怀融入骨子里,因此其诗歌自然流淌着盛唐之音。而初唐诗人在不期然间就要迎接一个盛世的到来,欣喜中亦有疑惧,所以他们所受到的冲击显得更猛烈些。
唐太宗励精图治,施展雄才大略,抵外患,治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帝王贵族在生活上日益奢侈,修池苑,盖宫殿,歌舞畋猎,祭祀求仙。这种繁盛是否只是昙花一现,怎样才能让这样的繁荣持久,经历其中的初唐诗人们不得不去思索,带着这种思索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表达了“盛中忧衰”的情感。“盛中忧衰”情感在初唐长篇诗歌中最为突出,如王勃的《临高台》《采莲曲》、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从军中行路难》、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峤的《汾阴行》等。其中,四杰创作的长篇诗歌数量是最多的。长篇诗歌多描写帝京壮丽、皇室豪奢,多方铺叙,尽数描摹,清人毛先舒《诗辨坻》云:“初唐如《帝京》、《畴昔》、《长安》、《汾阴》等作,非巨匠不办。非徒博丽,即气概充硕,无纪省之养者,一鸣即走。唐人无赋,此词可以上敌班、张。”⑥简直把初唐长篇诗歌视作汉赋的替代品。汉武帝建立了一个政治空前统一、国力空前强盛的封建大帝国,但在一片升平中又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盛中含衰”的社会现实,既为赋家提供了铺陈描写对象,也触发赋家形成“既美且刺”的主题思想。初唐长篇诗歌与汉赋的相似,表面上看来是篇幅,实则是其背后的产生原因。
如果仅具备阔大的题材,即使敷衍成篇,尚难震撼人心。初唐长篇诗歌,相应于其阔大的题材,增加了沉重的历史感和浓重的生命意识。如卢照邻作《行路难》,首句“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把视角投向长安城,后继之以全诗近半篇幅铺叙长安城的繁华壮丽。而以“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一句陡转直下,用今昔对比发出“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的感叹。如王勃的《临高台》,与卢作《行路难》篇幅相当,亦以大半笔墨描绘长安城的壮丽豪奢,以及城内享乐放荡的生活,篇终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收结,似在告诫人们,繁华终将逝去,一切皆成沧桑,表达了作者沉重的历史感。
与沧桑沉重的历史感相对应,又表达了空前的生命意识。可以说,生命意识一直贯穿于古代诗歌发展的始终,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陆机《驾言出北阙行》:“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间,戚戚如履冰。”而对生命意识的表达在初唐长篇诗歌中格外密集,卢照邻《行路难》中“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始终,倏忽须臾难久持。”骆宾王《帝京篇》中“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李峤《汾阴行》中“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诗人们通过对生命、对人生的思索和领悟,感叹生命的短暂,功名富贵的转换。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一文评论卢照邻和骆宾王时总结道:“从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扩充到卢骆二人洋洋洒洒的巨篇,这也是宫体诗的一个剧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情感。”⑦这里的情感,更确切的说,是真情,是激情。只有势不可挡的激情才能支撑起洋洋千言的长篇钜制,激情使得诗歌有了延展的冲力,激情使得诗歌浑融完整。四杰的人生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激情,他们用激情撑起千百言篇幅诗歌。一扫宫体诗纠缠于男女之间的柔情,把玩于女人器物的矫情,以及上官体用精致典雅掩盖的虚情,高歌着盛世先声,静候着一个诗歌高潮的到来。
注释:
①《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七,第199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第500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第14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见《旧唐书•文苑传》卷一百九十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见《旧唐书•文苑传》卷一百九十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唐才子传》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⑥ 清毛先舒《诗辨坻》卷四,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⑦闻一多《唐诗杂论》,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