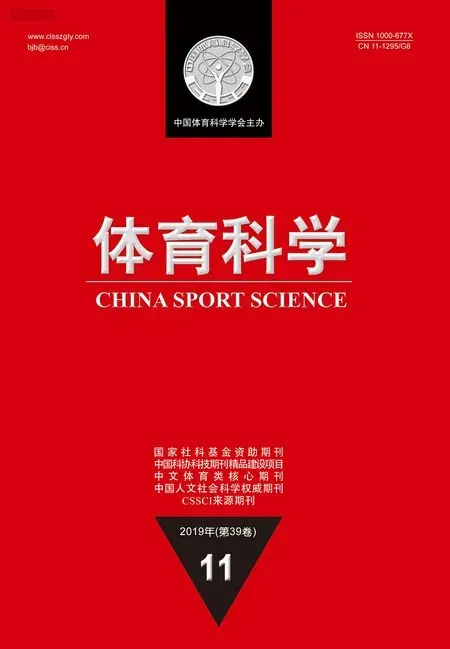全球体育法引论
谭小勇,姜 熙
全球体育法引论
谭小勇,姜 熙
传统的法律理论主要是围绕国家法而展开的。主权国家制定的国家法和国家政府间形成的国际法是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当世界迎来全球化时代后,在全球层面产生了一种新的法秩序——“全球法”。这种法秩序突破了国家与法之间那种传统意义上固有的联系性。然而,这种突破了传统法律理论的法秩序在缺乏新的理论阐释的情况下举步维艰。对于全球法的论证,以往的研究都是以“Lex Mercatoria”作为例证进行研究。随着体育全球化成为一种客观事实,体育法治全球化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全球法类型——“全球体育法”。主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首先按照“万民法”——“国际法”——“跨国法”——“全球法”的历史发展脉络考察了“全球法”的出现,并阐述了“全球法”的基本形态和范例;其次,分析了“全球体育法”产生的可能性。第三,对论证“全球体育法”合法性的方法进行了考察,并最终采用 Gunther Teubner论证“Lex Mercatoria”的方法来论证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最后对“全球体育法”的形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旨在为“全球法”的研究引入“全球体育法”这一新的例证,并为开启“全球体育法”领域的研究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
全球化;全球法;体育;全球体育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政治、文化、法律、教育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法律全球化的论题也开始得到研究者们热衷的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个别法领域(如商事法、体育法)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是否会促使一种突破现有法律二元论的第三种法律秩序①米歇尔.维拉利认为人们对法律的主要看法是二元论的,主要是指存在两种法律体系,一种是国家或国内法,一种是国际法。然而这种分类方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不管是国家法律还是国际法律都是由国家创造的,只是国际法的任务是规范与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法”出现呢?由此,关于“全球法”的研究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但由于受制于传统法律理论的局限,关于“全球法”这一新的法秩序存在许多争论,甚至有学者对“全球法”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导致这种“全球法”秩序在缺乏新的理论阐释的情况下举步维艰,学者们对全球法展开研究时往往很难找到让人信服的论据。对于“全球法”的论证,以往的研究主要以“Lex Mercatoria”作为例证进行研究。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体育全球化也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①体育全球化的特征也开始显现。体育的全球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全球性体育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其次,全球性体育赛事开展的常态化,这些全球性赛事既有由政府机构承办的奥运会等赛事,也有由商业机构运作的商业性赛事;第三,体育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也是体育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参见Wagner,E.A.Sport in Asia and Africa:Americanization or mundialisation?[J].Sociology of Sport J,1990,7:399-402.姜熙.体育全球化中中华武术的生存危机和发展抉择[J].体育学刊,2009,(10):16.。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法也以一种完全的法律身份得以迅速的发展。在法律全球化和体育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体育法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发展的问题,一些学者根据体育全球化的现象和法律全球化的概念以及体育的全球法治提出了“全球体育法”(Global Sport Law)的概念。在“全球法”研究领域,即使是“Lex Mercatoria”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全球体育法”概念的出现是否能够为“全球法”理论的发展添砖加瓦?“全球体育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特征是什么?本研究就是在此背景下,以“全球法”的出现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探索“全球体育法”何以可能,对“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并研究“全球体育法”的主要特征。
1 “全球法”(Global Law)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法”(Global Law)的研究成为当前法律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正如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 Harold J·Berman认为:“20世纪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带入一个或多或少频繁相连的关系中,一个世界社会正在形成”[10]。既然一个世界社会正在形成,那么,一个世界法体系是否正在出现呢?早在20世纪70年代,法社会学家 Niklas Luhmann就提出一个世界社会的概念,即“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而且,他早已在全球社会层面预见了法的全球化。
1.1 从“万民法”、“国际法”、“跨国法”到“全球法”
Harold J·Berman认为,“全球法”概念的出现应该涵盖了Jeremy Bentham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和Philip C.Jessup的“跨国法”(Transnational Law)[10]。为此,我们就有必要从“万民法”、“国际法”、“跨国法”来考察“全球法”的出现。
“万民法”(ius gentium)这一概念是从罗马法而来,它是罗马法中与“市民法”相对的概念。“市民法”就是规范罗马城邦市民共同体秩序的法律,被称为“城邦自己的法”(ius proprium civium Romanorum)。“万民法”被定义为:“自然理由在所有人当中制定的法”(ius quod naturalis ratio inter omnes hominess contituit)[8]。因此,“万民法”是“在所有民族中得到遵从”。这种理论概念有时被用来表达某些制度功能的普遍性,从更准确的具体含义上讲,他针对的是那个在历史上适用于罗马人与异邦人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人们在谈到万民法概念时一般认为其有双重含义。一个是理论上的含义,它的根据是存在一种所有民族共有的法,并且认为,自然理由是这种普遍性的基础;另外一个是现实的含义,它指的是产生于罗马人与异邦人之间关系的罗马法体系。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 Grotius继续维持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区别。而他所称的万民法,是指其拘束力来自所有国家或许多国家的意志的法律,因而,他指的是万国法,已不算是原来意义上的万民法。但是,由于它不能完全表达国家间的法律意义,Harold J·Berman在An IntroductiontothePrinciplesofMoralsandLegislation一书中,根据“国内法”提出了“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论述[12]。由于 Harold J·Berman的国际法概念更能表达国际法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这一实质,使国际法这一名称得到了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关于国际法的定义存在很多说法,如《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将其定义为:“各国认为在他们彼此交往中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和条约规则的总体”[4];《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下的定义却是:“国际法是对国家在他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7]。惠顿在他的《国际法原理》之中称:“国际法可以界定为包括那些存在于独立国家间的从社会本质推动而来的符合正义的理性的行为规则”。Kornelius van Bynkershoek认为,“国际法是由国际习惯和条约表现出来的各国的共同同意”。[2]虽然,学者们的定义有所差异,但是,所表示的实质却趋于一致,即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应当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王铁崖先生认为,“把国际法看作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就够了”[6]。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世界秩序有了新的变化,有的学者提出以新的法律适用新的世界秩序。从而出现了跨国法学派,其中20世纪中叶的 Philip C.Jessup就认为,国际法的概念具有误导性,它仅仅关注的是一国与他国的关系,所以,他提出了“跨国法”的概念。认为“跨国法”是规定和调整一切跨越国境活动(包括政府间行为,也包括商事主体的交易行为)的法律规范,“跨国法”中不仅包括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而且,还包括国内法中的其他公法和私法[17]。然而,Philip C.Jessup的“跨国法”还是停留在主权民族国家的层面,仍将主权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参照点,没有超越出国际法同样涉及主权国家相互关系规则的界限。为了适用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社会,一些学者提出,应该采用以突破主权国家层面上升到全球层面的“全球法”来对全球事务进行管理。
1.2 “全球法”的形态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全球法律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可以说对于“全球法”的研究大大拓宽了法律思维的范围和更新了法律分析的维度。对于“全球法”的研究要突破聚焦在基于政治权威的立场和法的“地域性视角”而上升到全球层面[11]。全球法理论的出现应该是法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全球化使得法律突破了法律与国家两者传统的关系,而“全球法”突破了关于法与国家具有必然联系性的传统思维。从此,法作为“国家意志”、“国家权威”的传统认知被打破。“全球法”无需国家授权,也并不同于规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传统国际法,它不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依靠私人秩序 (Private Orders)本身(契约和协议)产生。“全球法”的效力存在于国家之外,同时,也存在于传统国家关系之外。这种新形态的法不依赖于国家权威,同样也不受国家的监督。也就是说,“全球法”与国家之间不存在必然连结,它是一种不依赖于国家的法律秩序。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法”突破了人们对法律二元论的看法,而有可能成为第三类法律秩序。
1.3 当前“全球法”的范例
对于“全球法”的研究,研究者一般都会以“Lex Mercatoria”(在研究全球法的学者著作中通常被译为“全球商人法”或“全球商事法”等)作为重要的例证。Mertens就认为,“Lex Mercatoria”作为经济贸易的是“无国家的“全球法”最为成功的例子[9]。而 Gunther Teubner认为,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全球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展自己领域的“全球法”[9]。Giddens也明确指出,这些全球化的领域是与国家、国际政治、国际公法相对隔绝的环境中进行的,“全球法”是全球化与“非官方法”的一种组合,全球化与非官方法律的一个类似的组合还可以从劳工法中得到体现。另外,关于人权的话语也已经全球化,它并不依赖于国家而以其自己的法律进行论述。Luhmann就曾强调,“如果在人权方面的法律被置于区域政治的随意性之中,那将是无法忍受的”[15]。在生态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生态全球法已经脱离与国家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正在形成中但不成熟的“全球法”的雏形已经开始出现。在全球体育领域,Ken Foster对“全球体育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针对“全球体育法”的研究多以“Lex Mercatoria”为范例进行比较或类推。“全球体育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形态、生成路径是什么?其合法性地位如何证立?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
2 全球体育法何以可能
关于“全球体育法”的研究已经有学者开始涉足,Ken Foster对“国际体育法”、“全球体育法”进行了区别,并以“Lex Mercatoria”为对象进行了比较。然而,体育与生俱来就具有其独特性,这些也是区别于其他领域的。当然全球体育实践也区别于全球商事实践。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根据“Lex Mercatoria”简单的就类推得出存在一个全球体育法体系的结论。我们必须根据体育领域本身的法律实践来探讨“全球体育法”的存在,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事先论证“全球体育法”是否可能?Wallerstein认为,全球化的发生不完全是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经济部门的逻辑,也通过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子系统的内在动力的逻辑。[19]全球性出现在多个社会领域,正如 Karl Mannheim所说的社会自治的部门不仅仅是经济,还有科学、文化、技术、健康体系、社会服务、军事、交通、媒介通信和旅游业都是今天自我复制的世界系统。所以 Wallerstein认为,相对于其他领域,“政治进程仅仅达到了一个原始的全球性”。除了政治,其他社会子系统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社会,或者更好的、多种多样的、片断化的全球社会。而体育全球社会正是这些多样化、片段化的全球社会中的标志性代表。体育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体育全球化自然就引出了全球体育治理的议题,那么,这一“全球体育法”体系(Global Sport Law)何以可能呢?
2.1 体育全球化是全球体育法出现的首要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体育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种国际性体育组织的出现、各类全球性体育赛事的开展以及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的参与,都是体育全球化的有力佐证。正如Olatawura所说,“体育是一种将职业化管理、身体竞技、商业和投资结合于一体的跨越了国界的全球现象”[16]。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认为:”人类有5种通用语言,金钱、战争、艺术、性和体育,而体育能把前四者融合在一起”[8]。时至今日,体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的重要文化现象。体育在国家间的壁垒被打破,而且,体育早就突破了地缘政治的局限。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国际性体育赛事之中,甚至超过了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这种以体育为纽带的跨国关系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国际关系①据统计,加入国际奥委会的国家已经达到205个,甚至已经超过了联合国192个成员国的数量。我们不得不叹服于体育的这种全球影响力。参见:IOC.Asof June 2009,there are 205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Olympic Movement[EB/OL].http://www.olympic.org/en/content/National-O-lympic-Committee/,2009-11-08.。在这种全球体育实践的有力推动下,一种新的适用于全球体育发展的治理秩序成为一种需求。所以,体育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引出了全球体育法律治理的问题。这样一来,“全球体育法”才能成为一种基本的实践需求而有了生成的可能。
2.2 法的多元创制途径使全球体育法成为可能
从传统的法律理论来看,法的制定与国家总是密不可分的。法是国家权威的体现。那么,脱离了国家的法是怎样创制出来的呢?“全球体育法”作为“全球法”之一,其主要特征,就是它不是一种由国家制定的法,而是一种“非国家法”。那么,“非国家法”在法的创制途径上是否有其正当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 Ehrilich的法社会学理论中找到答案。Ehrilich指出,“过去的大部分法律不是由国家创制的,即使在今天,大量的法律也来自于其他的源头”;“即使是国家万能的信奉者也不会认为国家可以制定调整人类所有行为的规则”[1]。所以,在法律发展史上,总是有一些力图使“非国家法”获得一个相应的地位的努力。这种努力一次出现在17、18世纪自然法学派的著作中,另外一次出现在历史法学派创立者萨维尼和普赫塔的著作中。这两个学派都不盲目地把国家宣称为法的东西接受为法,他们努力去探寻法的本质,并从国家之外去探寻法的起源。Ehrilich强调,法律并不是国家的专利,它还蕴含在社会团体和社会习俗中,因为,在社会团体的生活里,以及社会中人的行动里,存在着自然形成的、活生生的法律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举止,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活法”(Living Law)。由此可见,很多表面上是由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其实都可以在社群实际生活中找到它们的根源(活生生的法律,也就是社会团体的内在秩序)。他认为,社会团体中的风俗,就是广义的法律,而狭义的法律(国家法律)则需要以风俗为基础,也是风俗的一种。换句话说,国家法律只是社会生活中各种法律规范的一种而已。从这种法创制的多元途径看,“全球体育法”也是一种体育领域的内部社会秩序,“全球体育法”并不依赖于国家来创制,它的创制是在全球体育实践层面上进行的。所以从法的创制途径看,“全球体育法”具有出现的可能性。
2.3 全球性体育社会团体及其“内部秩序”的形成使全球体育法成为可能
法给我们的表面印象总是与国家分不开的。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国家制定的法更是具有重要地位。而在历史法学派那里,法则与民族这一概念联系得十分密切,他们认为法律是民族历史凝成的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Ehrilich则认为,以上两者对法的认识都忽视了法的社会本质。社会是彼此存在联系的人类团体的总体。这些构成社会的团体是多种多样的,国家、民族、国际法上的国家共同体、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文明民族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交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宗教组织、财团法人、阶级、阶层、社会帮派、宗派,这个由盘根错节的团体和相互交织的圈子组成的整个世界,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总归是可以感知的,而组成了社会[1]。Ehrilich主张,法形成的推动力来自于社会,法是社会团体的内部秩序。从这一点看,“全球体育法”的产生条件就是,先必须要有一个全球体育社会团体,这个团体的内部秩序则是“全球体育法”形成的最为重要的素材。那么,这个全球性的体育社会团体是否已经形成呢?其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电视媒体和其他广播媒介的发展,体育开始迅速传播,并开始了商业化的发展,体育的商业化发展使得体育从一种纯粹的休闲娱乐活动转变为一种职业化的活动,体育成为可以为人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一个独特领域。体育有着足够的魅力吸引着全球民众,体育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无法统计的参与者和观众数量。尽管存在地理上的距离和语言上的差异,然而,包括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在内的国际性体育赛事,都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因此,参与到体育中的一个阶层人数开始大量增加,这个阶层包括运动员(职业或业余)、裁判员、各种体育机构以及与体育发生各种社会关系的群体甚至包括国家。随着体育全球化这一社会推动力的促进,一个全球性的体育社会(团体)已经形成,而且,这一团体在当前全球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行动总是能吸引到全世界的目光。这个全球性的体育社会团体由国际性体育组织(如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联合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各国体育机构、运动员、裁判员、其他与体育相关的所有机构和个人组成。而国际体育组织在全球体育社会团体的管理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体育组织的管理规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这些规则得到国际体育参与者(包括国家)的普遍接受,它们已经成为对全球体育进行管理的普遍法则,成为了全球体育社会团体中的一种稳定而具有效率的“内部秩序”,这种秩序来自于全球体育社会实践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使得全球性的“内部秩序”逐渐演变,为“全球体育法”(Global Sport Law)成为可能。
2.4 具有全球体育事务管辖权的法律机构的建立
Foster提出,“全球体育法”的存在需要有一个全球争议处理机构。事实上,在全球体育领域这个机构已经存在,那就是国际体育仲裁院(the Court of A rbitration for Sport,以下简称CAS)。CAS在当代体育领域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其司法活动表现出其特有的特征。首先,CAS既是一个争议解决的仲裁机构,又是审查各体育组织裁决的“体育最高法院”。其次,CAS的司法活动展示了“超国家的”(Sup ranational)特征。CAS像其他许多管理体制中的法官、仲裁委员会或特别专门小组一样,对一般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CAS已经与各国,IOC、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反兴奋剂组织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一些分歧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CAS在全球体育范围内的管辖权和裁决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得到承认与执行,正如Nafziger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世界体育的最高法院’已经成长起来”。
CAS的成立和司法体制的形成对“全球体育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 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考察
当代法律社会理论将如何看待“全球体育法”和“无国家”的其他“全球法”形式呢?Hans-Joachim Mertens就指出,法律理论在其确定何者为法律和何者不为法律时,不应受到“Lex Mercatoria”实践的“拘束”[9]。也就是说,我们在确定“全球体育法”是否为法时,不一定要受制于“Lex Mercatoria”的实践,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排除“Lex Mercatoria”的实践来看“全球体育法”。或许从“Lex Mercatoria”中,我们能够发现能为我们所用的东西。下面将以“Lex Mercatoria”的方法来考察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
3.1 前提——全球体育实践中是否存在契约?
通常情况下,在考察“全球体育法”时,由于其与“Lex Mercatoria”的相似性,很自然的就使研究者联想到“Lex Mercatoria”。然而,“Lex Mercatoria”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如果要以“Lex Mercatoria”的方法去类推出“全球体育法”,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就是,全球体育实践中是否存在类似于“Lex Mercatoria”实践中那样的契约。Foster最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否定的回答。Foster对于用“Lex Mercatoria”来类推“全球体育法”的做法在IsThereaGlobalSports Law?一文中提出这是不合适的①Foster在这里将Lex Sportiva认为就是全球体育法.参见: Foster.Is There a Global Sports Law[J].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Law Journal,2003,2(1):1-18.。Foster在该文中提到,将全球体育法与“Lex Mercatoria”进行类比分析是错误的,作为民间自治的“全球法”,“Lex Mercatoria”最终能够被合理应用是基于契约,“Lex Mercatoria”作为私人全球自治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建立在契约上的,而“全球体育法”则依据的是虚构的契约[14]。Foster的依据是,虽然国际体育联合会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名义上被认为具有契约性质,但社会学的分析完全不同,对体育赛事行使垄断权的全球性体育组织与单个运动员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平衡的”。这类似于雇佣契约,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性的不平等和互惠的形式掩盖了不对称的关系[14]。所以,Foster认为这种法律形式不具有契约性质,以“Lex Mercatoria”进行类推“全球体育法”是一种误导。所以,我们要以“Lex Mercatoria”来类推“全球体育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论证“全球体育法”是否存在契约基础。全球体育领域契约是否存在成为我们以“Lex Mercatoria”方法论证“全球体育法”合法性的前提。
3.1.1 全球体育实践中的契约
从表面上看,Foster的观点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对全球体育实践中的契约关系进行仔细观察后发现,全球体育实践中的契约并不一定仅仅是 Foster所提到的运动员个体与体育组织之间的契约。除此以外,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也存在契约。Foster的观点可能完全忽视了国家、运动员、国际体育组织和“全球体育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体育法”虽然不受国家的监管,也不依赖国家来产生,但是,“全球体育法”却与国家发生着一定的特殊联系。
主要表现为:第一,当一个运动员参赛时如奥运会,大多数情况运动员是代表其国家参赛,那么,存在的契约就不完全是运动员个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契约,而是运动员代表所在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达成的契约。在这个契约关系中,运动员代表国家在参赛事项上有义务服从国际体育组织的管理,包括体育纠纷解决司法管辖权的问题,而获得的权力就是参与到全球体育竞争中去。所以,此时运动员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契约,其实是运动员所在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契约。第二,当一个国家要申办某个全球性体育赛事时,申办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就要形成一个契约,对于申办国家而言,契约中必然包含了它作为举办该赛事的东道主应该履行的义务,比如,场(馆)建设等赛事筹备的各方面,还包括涉及司法主权的相关事项,也即是赛事期间体育相关事项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如在奥运会期间,CAS临时仲裁对奥运会的所有纠纷有管辖权,因而,此时国家有义务将相关国家法进行暂时的悬置②这种在相关赛事期间国家法暂时悬置的状况类似于Agamben所描述的“例外状态”,所谓例外状态就是通过悬置法律(宪法),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措施进行治理的状态。这仿佛是一个无法的状态,生命被悬置、驱逐于法律之外,即成为赤裸的生命。。而在这项契约中,国家履行义务所得到的就是获得举办赛事的权力。
3.1.2 契约缔结主体之间是否平等
全球体育实践中契约包括了参赛者与国际体育组织、举办者与国际体育组织的两类契约关系,而两类契约都是以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为缔结契约的主体。那么,主体之间平等吗?首先,缔结契约的主体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国际体育组织是代表着一个行业的利益,国际体育组织行使管理的权力也是为了维护这一领域内的利益。国家作为参与者加入到体育竞争中来是为了获得利益的分享。一方面,是国家形象、国家实力、甚至是民主化进程的展示;另一方面,国家参与到全球体育竞争,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一些学者研究表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所以,目前世界各国都积极申办各类大型国际性体育赛事,也即是说,这种契约的达成总是出于国家的自愿,而国家的这种自愿可能主要来源于全球体育为国家各方面发展所带来的驱动力。从这一角度来看,缔结契约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不平等,两者达成的契约是互利性的,所以,这种契约并不是Foster所说的是一种虚构的契约。
3.1.3 全球体育法契约与“Lex Mercatoria”契约的差异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全球体育实践中存在着契约,只是这种契约与“Lex Mercatoria”实践中的契约存在不同。Gunther Teubner在论证“Lex Mercatoria”时认为,一旦商事契约主张具有跨国的效力,它们就切断了与国家的关联,而且,也切断了与任何法律秩序的关联[3]。而在全球体育实践领域,契约具有跨国效力后仍然会与国家产生诸多的联系。只是值得我们区分的是,这种联系不受国家的约束,而是国家在某种情况下会服从或者参与进这种契约。这种约束有时是来自于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契约,有些是来自于公法性质的国际条约(如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这种现象很难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国家通过与国际体育组织建立契约关系去取得参与全球体育竞争的机会,但是,国家必须依据契约服从于全球性体育事务的管理。所以,“全球体育法”与“Lex Mercatoria”有着很大的区别,并不像一些学者提到的两者之间完全相似。由于有了国家的参与,也正是有了国家的参与,才使得在这种特殊契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球体育法”表现出比“Lex Mercatoria”更具优势的特点。
3.2 “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论证
通过以上对全球体育实践中契约的论述,我们将可以采用 Gunther Teubner论证“Lex Mercatoria”的方法来论证“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
我们先假定“全球体育法”为一种“全球法”。此时“全球体育法”不属于国家法,也不属于国际法,由于不植根于国家的权威,也不依赖于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制裁支持,这种跨国家的新的法秩序似乎难以用现有的法律理论来进行分析。因为找不到全球基本规范(the global grundnorm)和全球承认规则(the global rule of recognition)。“全球体育法”仅仅基于一种契约,这种基于契约而在全球层面产生的法秩序,既欠缺国内法的依据,又不依赖于既有的法秩序。也就是说,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契约关系没有植根于某种特定的法律情境之中,这与“Lex Mercatoria”的契约一样,是一种所谓的“无法律的契约”。也就是一种自我生效契约。从传统的法律观点来看,所谓契约就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义务[5]。所以,任何契约都必须“根植”于既存的法律秩序。Gunther Teubner也提到,社会学家对于这种“无法律的契约”也持反对态度。自Durkheim后 ,社会学界对于自主契约论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社会学者们认为,契约的效力需要植根于广泛的社会情境。[3]基于这种“无法律的契约”的“全球体育法”要得到承认,就面临着与“Lex Mercatoria”同样的问题,此种基于全球规模的契约的非契约前提是什么?如果承认这种契约的效力,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效力自赋的契约,那么,就会立刻产生一个自我指涉的吊诡(Self Referential Paradox)或套套逻辑。在肯定意义上 (“我们同意我们的同意有效”),这是一种纯粹的同义反复(又译套套逻辑)(Tautology);在否定意义上 (“我们同意我们的同意无效”),这是典型的自我指涉的吊诡,其结果无法确定[3]。这种潜在的吊诡正是人们认为效力自赋的契约是不可想象的主要原因。从这点出发,”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地位成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一点和“Lex Mercatoria”面临的问题一样,只有当这种自我指涉的吊诡被解决时,体育事务方面的全球法律制度才能启动。然而 ,Gunther Teubner认为,理论的困境并不能否定事实的存在,社会实践比法律原理和社会理论更具创造性。从当前的现状看,全球体育实践本来就已经超越了当前理论的投射范围,“全球体育法”本身也是超出了现有法律理论和法律形态。事实上,全球体育事务的实践活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在解决效力自赋的吊诡。全球性的体育事务契约正在建立其自身的非契约基础。Gunther Teubner在论证“Lex Mercatoria”时提出了三种解除吊诡的方法,即层级化、时限、外部化[9]。所谓层级化就是契约内容同时包含当事双方将来行为的“首要规则”(Primary Rules),而且,包含了识别 、解释首要规则的“次要规则”[9]。Gunther Teubner认为,此时效力自赋的吊诡仍然存在,只是被隐蔽起来了。时限就是指契约延伸到过去和未来 ,它涉及对既存规则的标准化 ,涉及未来的冲突解决,并由此将契约转变成进行自我繁衍过程的状态[9];外部化,即是将契约生效的条件和未来冲突诉诸外部的“非契约”制度,这样就把效力自赋进行了外部转移[20]。这种外部制度是纯粹的契约内部的产物。这类自我创造的制度最突出的就是仲裁,仲裁必须评判契约的效力,尽管仲裁本身的效力正是基于契约。于是,契约效力自赋的恶性循环转化成两种法律实践的良性循环,即订立契约与仲裁。一种内部循环关系被转换成外部循环关系,正如斯坦因所言,在契约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循环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反身机制”(Reflexive Mechanism)。这种通过“反身机制”而促成的外部转移机制对于真正“全球法”的创建是非常重要的。于是通过层级化、时限、外部化这三者相互支持,形成了 Gunther Teubner所谓的“封闭循环仲裁”的契约。这是一种自我管理的契约,创建了一整套在全球有效的私域法律秩序 。除了实体规则 ,它还包含一些关于将冲突提交仲裁“法庭”的条款,这种仲裁“法庭”是一种私制度 ,而它对“立法”性的范式契约负责。这样一来,契约本身可以成为法源(比如国家要加入全球体育竞争,就必须要与国际体育组织达成某种契约,这些契约中必然就包含了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而首要的就是必须遵守国际体育组织的章程(如《奥林匹克宪章》),所以,这些章程作为全球体育管理的一些规则,自然就成为契约中的一部分,最终这些章程作为契约内容成为全球体育法的渊源,而且,还包含了自身的“承认规则”,处于自我正当化的情境中。
总的来说,“全球体育法”是一种“自我合法化”的法律,它的效力不是来自于国家,也不依赖于传统的法院,它是“自我繁衍”和“自我发展”的,应该与“Lex Mercatoria”一样被认为是“自创生”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全球体育法”的效力主要来自于全球体育实践中的各种契约,这些契约的效力并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契约本身,它通过一种被称作“外部化”的机制 ,创设了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机制。裁决的执行虽然有时诉诸国家的法院,这里主要指的是CAS所在的瑞士联邦法院,但法院已经趋向于关闭介入的大门,所以,裁决的执行是基于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契约或公约(如反兴奋剂公约)。全球体育法的效力及其纠纷解决机制均来自全球体育实践中的契约 ,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悖论式循环 ,即“全球体育法”的效力源于他们的契约 ,而该契约的效力又源于由契约创制的法律。
4 全球体育法的形态
全球管理体制和全球法庭的出现导致一系列自治规则、原则和程序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明显的现象。第一,这些体制模仿了国家机器,选择那些能够在其自身环境中运用的原则和机制。第二,他们试图去发展在他们领域内具有约束力的自己的法律原则。第二种就是试图建立一个自治和完全的法律秩序。然而,这种现象遇到了很多的障碍,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制度常常与国家相联系。全球体育法律管理体制选择的是第二种模式,它试图建立全球体育领域内具有约束力的自己的法律制度。虽然,这个法律制度的形成也与国家相联系,但是,其中产生的障碍正是基于体育的特殊性、国际体育组织与国家的契约和一些国际公约而得以很好的清除①CAS的裁决一般都可以得到各国很好的执行,这主要是基于1958年的《纽约公约》。如果要挑战CAS的裁决只能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上诉。。所以,全球体育法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
4.1 一种混合型的法律秩序
Lorenzo Casini认为,体育法不仅仅是国际性的,而且是非政府性的。它不同于所有其他形式的法律。体育规则本身就是一种天生的“全球法”,因为他们在整个全球范围内都是通用的,它们直接影响到每一位体育的参与者。比如,就国际体育组织的章程文本而言,《奥林匹克宪章》就是一个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的全球体育的“宪法性法案”[13],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全球范围内为各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家体育机构的反兴奋剂政策提供了一个一体化框架,这也是全球体育法的一个范例。因此,体育的全球性管理,包含了规则的产生和在国际、国内体育领域的贯彻的复杂性。这些规则不仅包括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制定的跨国的私人契约性的规范,而且,还包括公法-私法混合的规范(通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采用的反兴奋剂规则,组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私法制定规则,然而,这个私法体系又通过一些重要的公法要素,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和其他国际性文件、国家反兴奋剂立法和专业化的国家反兴奋剂机构而得以补充和充实。Lorenzo Casini认为,体育法呈现出多样性,它的全球性表现为,体育法的制定不依靠国家,而是全球性的体育组织,如国际奥委会、体育单项联合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此外,这些规则是直接适用于每一个运动员的。但是,全球体育法的来源仅仅是全球层面的机构,既包括国际性体育组织,又可能包括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公法性质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而国家只是这一法律体系的接受者。国家对这种法律体系的接受主要是基于上文中论述的某些契约。
4.2 全球体育法是一种“非国家法”
正如过去的年代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我们的时代也正在产生新的共同体、新的占有关系、新的契约,对于这些制定法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些新的关系不可能等到某个制定法上得到提及才能成为法律关系。所以,在全球体育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全球体育实践中的法律关系不会等到“全球体育法”全面形成才会出现。
在体育全球化时代,全球性体育组织成为体育法治的主宰者,民族国家沦为重要的配合者,它们分享着全球体育的治理权。Ken Foster认为,全球体育法是一个跨国家的自治法律秩序,它是由管理全球体育事务的民间性国际体育组织创造的。是一种契约性的秩序,其约束力来自于遵守国际体育组织的权威和服从其管辖权的协议。它不受国家法的监管。这就表明了Ken Foster也是将全球体育法界定为一种“没有国家的全球法”[14]。
4.3 全球体育法与国家、国家法的特殊关系
“全球体育法”虽然不受国家的监管,也不依赖国家来产生,但是,“全球体育法”却与国家发生着一定的特殊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法律现象。比如,当一个运动员参赛时(如奥运会),运动员代表其国家参赛,那么存在的契约就是某个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达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必然要与某国际性体育组织之间存在一个契约才能参与全球体育竞争,而契约中的某些内容必然将规定“全球体育法”对某些事项的管辖权。此时,国家作为一个参与者在赛事期间的体育事务管理需要服从“全球体育法”的调整。也就是说,国家不干预“全球体育法”,但是,它会参与到全球体育法律实践中来,甚至当国家法与“全球体育法”发生冲突时,基于国家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契约,国家法会作出妥协。因为只有国家依据契约履行其义务,才能参与到全球体育竞争中去。此时的国家法可能会出现类似于 Giorgio Agamben提出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国家法律暂时的悬置②都灵奥运会期间东道主意大利的反兴奋剂法律规定与国际奥委会的反兴奋剂规定相冲突。依照意大利法律规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将被视为刑事犯罪行为。而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选手使用兴奋剂仅仅面临取消成绩与禁赛的处罚,完全不受刑罚制裁。负责监督都灵冬奥会的意政府官员佩斯坎特表示尝试在都灵冬奥会期间使意大利反兴奋剂法规暂时失效,但该提议首先遭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强烈反对。然而经过最后的协商,意大利政府最终做出让步,决定在都灵冬奥会期间意大利的反兴奋剂政策暂停执行。。当然,这种悬置并不意味着废止。这样的例子可以从都灵冬奥会东道主意大利关于兴奋剂处罚规定的让步,以及CAS在奥运会期间体育纠纷管辖权的享有得到证实,国家法会在特定的时间让步于“全球体育法”。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因为国家法在特定状态下对非国家法妥协,这打破了传统法律理论的认知模式。从这一点看,“全球体育法”作为一种“全球法”相对于“Lex Mercatoria”而言表现出了更加有效的影响力。因为“Lex Mercatoria”并不能做到让国家法对其让步,而“全球体育法”已经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做到了。
事实上,在现实实践中,国家法或国家法院往往对全球体育事务中的组织和相关法律规定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如美国法院一般拒绝认为与美国奥运会举办城市有关的问题违反了联邦法律和州法律。这在Martin诉国际奥委会一案①Martin v.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740 F.d 670,673(9th Cir.1984).中和 Sagen诉 Vancouver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2010 Olympic&Paralympic Games一案得到了体现。还有西班牙Almería民事法院认为,国际自行车联盟(UCI)的“申报动向规则”没有违反西班牙宪法中关于保护个人隐私权利的规定。该法院认为,国际自行车联合会的“申报动向规则”是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建立的,参加自行车运动的运动员应该遵守[18]。以上案例的判决都表明国家法对全球体育实践中的法律规则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也许,我们似乎更适合将全球体育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视为一种互动关系。因为“全球体育法”并不是凭空出世,它的生成过程包含了部分国家法的全球化,同时“全球体育法”也会部分的国家化。这就是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法地方化和地方法全球化,即全球体育法与国家法的相互采纳和转化。总之,“全球体育法”与国家法是两个各自独立而又密切互动的法律体系。只是全球体育法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国家法的发展,毕竟体育的全球化需要各国适当调整其法律来适用全球体育管理实践。此外,“全球体育法”的出现,并不否定国家法的存在。“全球法”或者“全球体育法”只是法的存在形态之一。“全球体育法”和国家法只是在不同层面发挥各自的职能。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体育法治将出现法律多元的发展态势。
4.4 最小化政治干预的全球体育法
Gunther Teubner主张,虽然“全球法”与国际政治绝缘,但并不能防止“全球法”再政治化。“全球法”的政治化不是通过传统的政治制度,而是在各种不同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些进程中,法律与高度专业化的话语实现“结构耦合”。康德也对法的全球化提出了愿景,但是,康德设想的法的全球化是“公法的超越性公理”,是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是国际政治法律化的结果。就康德法的全球化的观点而言,只有当民族国家形成了政治联盟,在一个共同宪法下,法律的全球化才有可能。然而,当今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在民族国家政治领导下逐渐形成的世界社会,而是一个矛盾的、片断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已经不是主导的角色,地缘政治的冲突似乎在当前很难调和。正如Wallerstein的观点一样,“政治进程仅仅达到了一个原始的全球性”。尽管在民族国家中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与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政治和法的关系仍然是以民族国家的重心,然而,其他的社会部门已经在全球化道路上超过了政治和法律的固有关系,建立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全球村,而体育领域就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全球社会。这个全球社会和“全球体育法”的出现并不是依赖于政治而产生。当然,体育领域一直有着“去政治化”的理念,但从体育的历史发展脉络看,体育与政治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当代,随着体育对当今世界影响的加大,政治似乎很乐意将体育向自己拉近。诚然如此,在“全球体育法”的出现过程中,政治却不是主导性的角色。“全球体育法”在全球层面没有一个政治机构来支持,正如Luhmann所说,“法律与政治构成性结构耦合在世界社会层面已不复存在了”。同样,在全球体育领域,“全球体育法”与政治也没有出现结构性耦合。“全球体育法”是与全球化的体育社会、体育经济进程紧密耦合的,“全球体育法”是产生于一个法与体育高度专业化的和技术性属性的体育全球化过程发生结构性联系的自组织结构过程。全球体育领域的技术标准化和职业化的自我管理已经趋向于全球范围内的一致,这样,就有可能把国际政治对“全球体育法”的干预降到最小化。
5 结语
“全球法”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它不以传统国家法体系为检验标准。与国家法相比,它并不是结构上有瑕疵的不完整的法律,而是作为完全成熟的法律形式,其特有的特点区别于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法律。体育的全球化进程也正在孕育适合于全球体育法律治理的法律秩序——“全球体育法”。在“全球体育法”中,契约超越了国家的边界 ,并把仅仅属于国家的法律生产转变成全球的法律生产。“全球体育法”是一种“自我合法化”的法律,它的效力不是来自于国家,它与“Lex Mercatoria”一样被认为是“自创生”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全球体育法”作为“全球法”的一种典型类型为“全球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的例证。同时,“全球体育法”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非国家法”,但是,它却与国家发生着一定的特殊联系,正是基于这种联系使得国家法在特定状态下会对作为非国家法的“全球体育法”作出妥协,这是一种有趣的法律现象。“全球体育法”的这种独特性使得它作为一种“全球法”类型比“Lex Mercatoria”似乎更具有优势,这也为解决全球层面的其他事务(比如气候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总之,“全球法”的出现将为法律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而“全球体育法”的出现则将为“全球法”的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和动力。
6 展望
“全球体育法”还是一个新事物,即使是与它相似的“Lex Mercatoria”,虽然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历史,也还存在较多的争论,何况体育法学科的发展才刚起步。本文仅对“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及其形态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的论述,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如“全球体育法”的法律效力等等。
目前,体育法律治理还比较混乱,比如,针对职业体育的纠纷,提交至CAS裁决,如果纠纷双方所在国没有加入《纽约公约》或者和中国一样有商事保留的规定,纠纷双方所在国法院对CA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则变得未知。有时欧盟法院也会对其辖区内的体育事务作出干涉。再如,涉及到球场暴力、黑哨等非竞技性层面的问题,“全球体育法”将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纳入“全球体育法”的规制范围,还是由其他国际法或者国内法规制等,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全球体育法”甚至“全球法”的研究,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全球体育法”的研究将推动全球法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全球体育法”的研究中来,“全球体育法”的发展一定能为人类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1]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28-40.
[2]陈致中.国际法教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1.
[3]高鸿钧.清华法治论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41-279.
[4]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3.
[5]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5-6.
[6]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
[7]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4.
[8]朱赛佩.格罗索.罗马法史[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9]GUN THER TEUBNER.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M].Aldershot:Dartmouth Publishing,1997:3-43.
[10]HAROLD J·BERMAN.世界法[J].姜峰,张海燕译.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6,(1):1-5.
[11]INSTITU T FRANÇA IS DE RECHERCHEÀL’ÉTRANGER.Global law and global legal theory academic know ledge in question[EB/OL].http://www.msh-paris.fr/recherche/ aires-geographiques/monde/le-reseau-glsn/.2011-07-23.
[12]JEREM 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 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6.
[13]JEAN-LOUP CHAPPELET,BRENDA KÜBLERMABBOT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Olympic system:the governance of world sport[M].London:Taylor Francis Group,2008:106-120.
[14]KEN FOSTER.Is There a global spo rts law[J].Entertainment Spo rts Law J,2003,2(1):1-18.
[15]N IKLAS LUHMANN.Law as a social syste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464-471.
[16]OLA O.Olatawura.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international sport law[J].Int Sports Law J,2008,1:1-15.
[17]PH IL IPC.Jessup,transnational law[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106-107.
[18]UCI.The appeal by Carlos Roman Golbano is rejected[EB/ OL].http://www.uci.ch/Modules/ENew s/ENew sDetails. asp?source = SiteSearch&id = NjcxOA&Menu Id = M TI1ODA&CharValList=&CharTextList=&CharFrom List = &CharToList= & txt Site Search = Golbano + rejected&Lang Id=1.2011-07-04.
[19]WALLERSTEIN.World 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9:246.
A Study of Global Sport Law
TAN Xiao-yong,JIANG Xi
Traditional legal theory is mainly around the state law.Sovereign 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main target of legal research.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we will witnesse the advent of a new legal order-Global Law.This legal order breakthroughs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state and law in the traditional law theory.But it is difficult to this kind of new legal order in the absence of a new theory to exp lain it.For global law,“Lex Mercatoria”is an important example.When the sport globalization has been an objective fact,globalization is fostering a new type of global law-“Global Sports Law”.This paper,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comparative and logical analysis,discusses the advent of Global La,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law and investigates the legitimacy of“Global Sports Law”in method of Gunther Teubner,which is used to p rove the“Lex Mercatoria”,finally, discussed the form of the“global spo rts law”.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Global Sports Law to studies of Global Law,and open the gate of research of global sports law.
globalization;globallaw;sports;globalsportlaw
G80-05
A
1000-677X(2011)11-0077-08
2011-09-15;
2011-10-28
谭小勇(1964-),男,湖南慈利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法学,E-mail:txy641011@sina.com,Tel:(021) 39225210;姜熙(1982-),男,湖南益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法学与民族传统体育学,E-mail:xiaojiqingfeng@yahoo.com.cn。
上海政法学院体育法学研究中心,上海201701 1.Sports Law Center,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