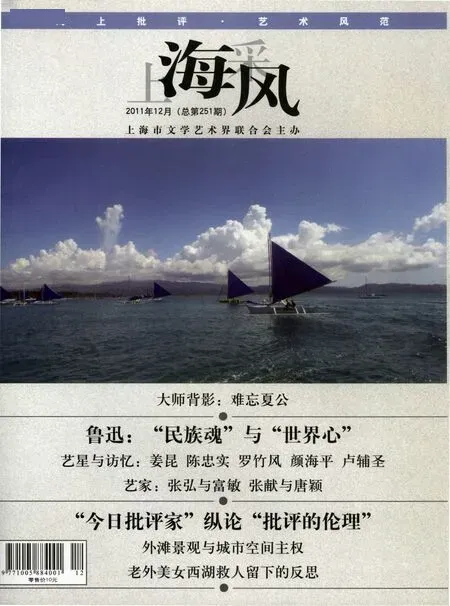“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双人舞
文/本刊记者 胡凌虹

张献和唐颖的家并不新,十几年前装修的,然而满溢出书架的各种书籍,精巧的配饰,像小舞台一样的榻榻米,使得他们的家别具一格。张献先接待了我们,他身着一件深绿色的悠闲外套,脸上挂着像窗外的秋日一样温和而随意的笑,很快,在里屋装扮片刻的唐颖一身靓丽地出来,玫红色碎花纹的衬衣映衬着灿若夏花的脸,她热情地招呼我们,泡咖啡、拿点心……张献和唐颖,前者是上海先锋戏剧的代表人物,后者是新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有着各自的成就,同时又是一对超级搭档。在最初跟他们的接触中,笔者不禁有些诧异,唐颖很OPEN,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而张献比较内敛,更专注于自己的小世界,他们是风格迥异的两人,可是他们的人生“双人舞”却跳得异常默契。随着深入的了解,笔者找到了答案,他们都是同样的淡泊名利,同样渴望自由地飞翔,他们有着同样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独舞
作为舞者,不是用自己的肢体给人提供视觉的愉悦,不是炫耀技能以提高自己供人消费的价值,而是通过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体,来书写和创造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既属于艺术,也属于生活。——张献
1986年盛夏,在郊区临时租房内,张献光着上身,用一个板条箱当桌,花了四天时间写出一个剧本《屋里的猫头鹰》。因为反感于舞台上剧目的因循守旧,张献是抱着不上演的死心写作这个剧本的。幸运的是,隔了两三年,此剧被搬上了舞台,轰动一时,张献也名噪上海,被称为先锋派剧作家。之后二十多年来张献一直在实验道路上探索,创作排演“抽屉剧目”、编导制作实验作品并巡演于世界各地,与朋友合建上海第一家民营剧场“真汉咖啡剧场”等等。
与此同时,他也创作了一些亲近大众的作品,这在一贯梦游于个人的戏剧世界、一向无视公共舞台的张献身上,无疑显得有些“另类”。对此,张献如此解释:“我搞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干预大众文化。我是用赤裸裸的东西、激烈的东西来蒸发娱乐,这对行业气氛是一种破坏,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投入戏剧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做这种戏剧。我认为那里的事情自会有人做。后来发现,有些事我不做,别人做不好。所以恢复上海的市民剧场,我贡献了我的剧目,我的目的是在市民戏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戏剧。”1993年张献策划并编写上海第一部民间投资制作的话剧《美国来的妻子》,倡导“市民戏剧”,获商业上的成功。1994年创作由影视明星出演的话剧《楼上的玛金》,推动了市民戏剧的商业化,再获成功。同时其任编剧的电影作品《留守女士》获第十六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茉莉花开》获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张献的才华得到了更大的肯定,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此地不宜久留。
2005年,张献认识了小柯、NUNU等民间舞者,他们反常规的舞蹈表现语汇,努力体现人性的舞姿深深吸引了张献。于是张献与他们组建了“组合嬲”舞团,创作演出以“肢体剧场”为主的表演艺术作品,上演于国内外各地,张献执导的舞蹈剧场作品《舌头对家园的记忆》还获2006苏黎世艺术节ZKB大奖。在舞蹈与戏剧的“越界”中,张献也找到了一种新的力量,“长期以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言论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如此。所以我们的解放必须从身体开始,其中,胡言乱语是必须的,不必要说出什么,而是要自己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当你有了自己的身体时,也就有了自己跟别人的身体关系,所谓你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对一的身体关系,你跟国家的关系也是一对一的身体关系,只有这样,你才能从内部获得做人的力量。”
可惜,肢体表演对国内来说还是全新的样式,在变动中,不得不转入更深的“地下”。然而探索不止的张献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剧场”,成为了“现实制造者”。“这两年,我和一些年轻人共同策划了一些新的活动,在城市的公共场合展开,可算是一种社会行为艺术。比如小珂多次在公共场合跳舞时,把摄像头绑在屁股上,很多来看她跳舞的人就会被拍下来,小柯把这做了一个实况录像,放在网站上传播,这种形式颠覆了一般意义上的观看者和舞蹈者的关系。”谈及最近的策划,张献神采飞扬,“我们也在做‘植物大战僵尸’系列, 植物是指有良心的生灵,而僵尸是指我们社会中一些缺少个性的、没有活力的、扮演他者的人,在现行价值观中,这些人往往被认为是成功者,但是在我们的词典中就是‘僵尸’。在这个系列中,我们经常去找活的制成品,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往往就是作品。”而这些在张献看来也属于戏剧范畴,是把艺术剧场扩大到社会剧场。其实“我是剧场”的概念早些年就存在于张献脑中,人到哪里剧场就到哪里的观念使得戏剧能够突破各种审查,并且能当场立即表达。事实上,张献一直在用自己的人生构造自己生命长度的“个人戏剧”。这也使得思想上羁傲不驯而生活上屡受挫折的他能一直隐忍、坚韧。

记者:1978年你考取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却在与外国留学生交往过程中被控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入狱,1980年出狱后遣返云南呆了六年。你有众多的“抽屉电影”、“抽屉戏剧”无法上演,各种实验作品经常遭遇封杀,纵有再多才华,却只能绽放于“地下”,可谓一路坎坷,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张献:良心是主要的问题,是身体性的问题,很难去排除它。对于我来说,没有过多考虑社会关系,只是考虑我自己要坚持做什么,愤怒悲哀都是基本情绪,可能都会影响你的坚持和态度的选择,但重要的是,如果认识到你所做的东西都是不可避免的,你就不会放弃了,就不会把挫折看得太严重。
记者:在戏剧探索中,你一路前行,一直处于潮流前沿,是怎样的力量使你能一直保持着先锋的状态?
张献:表面看起来我像在追求艺术的理想,戏剧的理想,其实我一直探究的是内心的秩序,内心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这是会不断变化的,我实际上不清楚这里面的内容,我选择了戏剧的方式,并且具体落实到作品,希望通过作品来照亮前面的路。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能清楚地讲出来,当然很好,但我一直没办法讲出来,如果我讲出来了一般是假的,多半是为了应付谈话的困境而找一些比较艺术的、冠冕堂皇的话。我也一直没有弄清楚我到底要什么,但人生命中的一种动力往往在不清楚的情况下推动着你,我乐于被这种力量推动着往前走,整个过程有一种激情,能感受到一种不断在实现的希望。
对于我,有“写作”的愿望比“写作”更有意味,生存意义因为它而有所提升……因之,写作生涯很像持续着的青春期,假如说反叛故土渴望异乡是青春期的特征,伴随着焦虑和不安宁的灵魂。——唐颖

唐颖是很上海的,有着上海女子特有的敏锐与精致,但是同时,她又是非上海的,有着超越于一般上海女子讲究实际、比较圆滑的单纯与执拗。
听说之前有媒体记者想采访唐颖,她先抛给人家一句:“你看过我的小说吗?”对方一愣,摇了摇头,唐颖立马拒绝接受采访,她的理由是:没做好功课怎么做得好采访。可以想象当时那位记者肯定是郁闷又不服的,在这个快餐化的娱乐时代中,在明星扎堆的媒体上,能给一个没啥绯闻、也没啥噱头的纯文学作家留个把版面,已经是“施恩”之举,唐颖却是那么“不识时务”。然而,唐颖就是这么自信又“任性”的。
1978年,唐颖入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然而这个当年很热门的专业,却是唐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医生,不是当作家。但当时阴错阳差进了中文系。”不过,对于文学唐颖也是喜欢的,“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晚上都会给我们念些简单的英语故事,比如《李尔王》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幼儿园到中学我都喜欢给同学讲故事。从小我也看了很多书,所以到了大学,老师开出的书单,我基本已经读过。后来又读了很多大量翻译进来的现代主义的作品,老师也认为我的小说写得不错,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期,作家是很出风头的,然而唐颖并没有当作家的想法,“当时我们中文系也是非常崇拜作家的,特别是一些老三届年纪比较大的,已经出版了一些作品,目标都很明确:要当作家。而我们年纪比较小,是迷惘的一代,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况且当时周围也有人觉得作家不好,包括我父亲不赞成我读中文系,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容易受到伤害,很危险。”1986年唐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之后又发表了《青春的梦魇》《那篇阳光还在》《海贝》等,不过回忆起这些,唐颖只是淡淡地说,“当时只是随便写写的”,继而她认真地说道:“我真的把写作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做是九十年代以后。1992年生了孩子,为了照顾小孩,我有了很多在家的时间,加上自身逐渐成熟,就开始静下心来专注于写小说,写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轻松与愉悦,最终我发现还是当作家比较适合自己。”
1993年,唐颖完成了长篇《美国来的妻子》,获全国城市报刊连载小说一等奖,之后又在《收获》《小说界》《上海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糜烂》《红颜》《丽人公寓》《随波逐流》《理性之年》《瞬间之旅》等等,获得诸多奖项,其中获“新市民小说奖”的《红颜》还被改编成电影《做头》,由关之琳主演。去年,唐颖又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另一座城》,最近,该小说更名为《如花美眷》发行了单行本。
多年来,尽管时有获奖,小说不断被转载、被选入各种选本,但唐颖的小说成就与她的名气并不匹配,在文学黄金期,淡薄名利、没有“野心”的她没有及时冒出来,而到了纯文学的沉寂期,即便新作不断,但特立独行、不屑炒作的她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她又是幸运的,正是这份“任性”的不随波逐流,形成了她自身创作的细水长流,使得她一直是充满生命力的“现在时作家”,而不是徒有虚名的“过去时作家”。
当然,同样的“任性”“自我”还体现在唐颖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读大学时,唐颖曾把习作寄给一些文学刊物,然而在红色年代过来的编辑看来,唐颖的作品太小众。“他们更喜欢宏大的角度,但是我不会写那类文章,反而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之类的我比较偏爱。”尽管小说时受争议,但是唐颖坚持关注个人命运的叙事角度,她的作品大多描写繁华都市中的人生故事,笔下的人大都为具有上海特色的小市民。余秋雨称:“写上海,要超过唐颖很难”。
记者:为何选择并坚持这个视角?
唐颖:这三十年城市变化很大,在非常剧烈的变化中,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着变化,有着挣扎,特别是女性,在专制社会中是非常受禁锢的,没有欲望,后来又转到了极端物质化的社会。我写了很多悲剧,很多女人从非常贫困的地方出来找外国人结婚,只是想找物质丰富的生活,婚姻是捷径,但是她们是否幸福呢?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下反思。与文学界大都关注整体的悲剧相比,我更在意个人的悲剧,我是想通过个人来反映这个社会,这也是文学界一直疏忽的。
记者:有人认为你一直集中于讲述上海女人,题材太窄了。
唐颖:题材窄不怕,就看你写得有没有深度,你写的东西越独特,就越有个性。我很怕给我一个“上海作家”的称号,我是中国作家,我反映的社会状态、心理变化不仅是上海的,也是世界的,之所以选择上海、上海女人,是因为写小说时作家要描述一个熟悉的场景,而我熟悉的就是上海。
双人舞
“如果我不是和张献结婚,1986年的戏被禁掉以后,我可能就和剧场告别了。”——唐颖
“唐颖生活在上海,她的小说,她的社会态度、文化态度都切切实实地让我和当下以及以往的上海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张献
唐颖的主业是作家,但同时她也一直跨界戏剧领域。1986年,唐颖写了一个剧本《20岁的夏天》,这出剧在长江剧场演了9场,1000人左右的场子场场爆满。可惜第一轮演完以后就被禁掉了,这让唐颖感到做戏剧的不轻松。“如果我不是和张献结婚,1986年的戏被禁掉以后,我可能也就和剧场告别了,但因为张献,我后来不时与剧场有着联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唐颖的小说《美国来的妻子》被张献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演出,唐颖在其中也参与了一部分工作。2004年初,张献根据唐颖的一部旧作《红颜》改编成小剧场话剧《做头》,成为上海剧坛的热点之一。2005年5月唐颖和张献应某公司董事长再三邀请,打理起了一家剧场。唐颖感叹:“这么多年来我目睹了张献整个艰辛的奋斗过程,刚开始我有点想帮帮他的意思。但真正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只是为张献做这件事情,而是为我自己的兴趣在做。”之后唐颖还做了“上海越界艺术节”的总策划,“‘越界’中都是些很当代的东西,而我的性格中有一些叛逆的因素正好在这里得到了满足。”更让唐颖欣喜的是,因为做先锋戏剧,他们经常出国巡演、交流,这也给予了唐颖特别的体验。
经常跨界先锋戏剧,其先锋性是否会对小说产生影响呢?唐颖肯定地点头道:“影响是相当大的,不过更多的是受意识方面的影响,并非在形式上非常古怪,我的小说还是比较写实的,因为我希望有自己的读者,尽量让他们理解,用他们能领会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我的小说中也有现代先锋意识,我写的人物还是很现代的,喜欢我小说的大都是年轻人,而且他们都觉得我是比较年轻的,这也算是一种成功吧,说明我的写作本身是引领潮流的。我的《红颜》是1994年写的,但是变成电影的时候是2005年,还没有过时。这也让我很欣慰,我的小说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如果说,张献的先锋戏剧探索让唐颖身上潜藏的叛逆的因子得以张扬,那么唐颖对于张献而言,可谓架起与上海这座城市,与日常生活联系的桥梁。因为唐颖,1986年,张献从云南回到了上海,阔别八年,从火车站出来,听到穿着睡衣的老妇用上海话谈家常,不禁让他流下眼泪。张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一直习惯于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而唐颖唤起了他的生活意识,与别人交流的真实。“她生活在上海,她的小说,她的社会态度、文化态度切切实实地让我和当下以及以往的上海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这个人有个问题,在生活上,我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其实我的朋友就是唐颖生活中的朋友,唐颖接触社会各种人,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张献坦诚地说道:“唐颖的性格比较开放,而我实际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会不断地封闭自己,我在电脑上写作是不需要和人交往的,其实当很多人都有手机时我还没手机呢。因为唐颖,这几年我社会活动也慢慢多了一点,也慢慢学会了和社会打交道。”在采访之后,张献通过Email发了二十多篇文章过来,都是他的戏剧思考、人生思考,他是渴望更多人能读懂他的。
事实上,按世俗的眼光,大部分人是无法读懂这对夫妻的,因为特立独行,他们即便再多的努力都是“无用”之举,无法让生活富足,也无法获得名利。然而试想,倘若越来越多的人看着他们的灵魂之舞能莞尔一笑,那么自由灵魂的群舞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