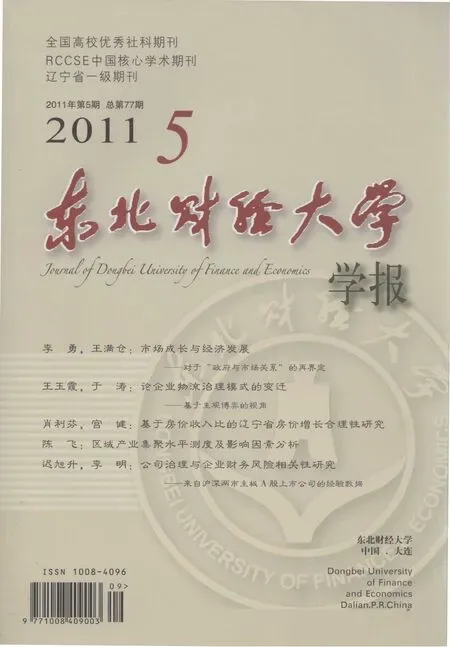市场成长与经济发展——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界定
李 勇,王满仓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一、引 言
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来说,改革开放过去的30年一定是一个奇迹。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在1978—2008年这30年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经济体制顺利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尽管在这3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了这样或那样的挑战,但中国社会在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在总体上保证了相对稳定,这种强调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模式最终被定义为“北京共识”。
然而,“北京共识”更像是经验的概括。其深刻的理论问题:应该如何通过主流的经济学框架理解中国这30年来的经济增长,如何理解中国在低水平的法制下能取得增长的原因[1],中国在金融压抑、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保护中能够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2],现有研究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其中,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却并不足以理解中国在这30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在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时,均是在制度既定、以完全竞争为主要假设来进行的。但中国在这改革开放30年间却经历着巨大的“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正在不断走向发展和成熟,这一系列的背景环境与主流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差异甚大。
既然标准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解释,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张五常和张曙光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由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轨[3-4]。但问题是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不仅仅只有中国,包括俄罗斯和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均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结果是这些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反而经济在短时期还经历了非常激烈的动荡,这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剧烈的反差。Qian和罗兰等则强调渐进式转轨的重要意义[5-8]。由于东欧国家所采取的“大爆炸”(私有化)转轨方式会造成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一旦来自于既得利益群体的损失超过了改革的收益时,转轨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变为负,而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转轨方式则是在承认既得利益前提下的边际改革,从而实现了经济绩效的巨大飞跃。
可以说,“渐进论”抓住了转轨过程中中国区别于东欧国家改革方式的差异性,但“转轨”论所隐含的假设前提却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是要优于计划经济的。从实践上来说,虽然二战后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表现要比市场经济国家差,但计划指令性经济在苏联建国后经济腾飞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成长和恢复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而二战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好转也得益于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引入,计划指令性经济并不一定总是抑制经济绩效的发挥。理论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越性早已被福利经济学定理所证实,但新近的理论却证明:在信息完全的情景下,组织中晋升激励机制的应用同样可导致帕累托最优产出[9-10]。这就是说,“转轨论”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假设前提是有待商榷的。由“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仅是单纯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带来经济绩效的改变这么简单,中间肯定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内生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我们重新回顾中国经济成长的脚印便会发现:指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总是政府,中国明显的是属于在政府指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改革,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11-12]。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性的力量在转轨过程中不断增强,虽然政府干预经济的领域减少,但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却不断增强,即计划指令模式与市场模式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增强。但不管是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提高政府效率的若干改革,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市场机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机制逐渐成熟,资源配置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代理成本不断缩小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3]①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归因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一书中,作者认为由于改革开放前所采取的“重工业化”化战略,一方面导致了巨大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市场以及分权机制的培养。而“比较优势”战略由于与世界市场相融合从而培养了中国的市场结构,而不再需要集中资金则使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代理成本逐渐减小,从而产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归结为一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正确地处理了政府 (指令性契约)与市场 (市场性契约)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短期静态关系,而更可能是一种长期动态相互影响的关系[14],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中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的节约,其核心是“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15]。
因此,本文以资源配置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的角度出发探讨政府 (计划指令性契约)与市场 (市场性契约)的关系[16-17]②Coase认为,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这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计划指令性模式,一种是以自由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市场性模式,两种模式都存在着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相等时则决定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企业的计划指令性模式与政府的计划指令性模式是相似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转轨经济的讨论统一到市场与政府关系框架中进行论述。,并进一步解释不同国家经济绩效差异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二、理论梳理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对其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1776年,斯密就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当了保证市场自由竞争的“守夜人”角色,在政策上“自由放任”,仅在治安、国防、教育、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发挥作用。而通过分工视角,作者还进一步论述了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应该随着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为长期动态相互影响的关系[18]。可以说,斯密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是我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石,斯密同时强调了市场和政府对于经济绩效的争相促进作用,而分工则是实现政府与市场动态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分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难以通过形式化的逻辑表现出来,马歇尔便抛弃了对于分工水平的探讨,而集中利用边际原理对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19]。后来,随着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的对于完全竞争市场导致帕累托最优这一命题的证明和萨伊定律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在抛弃了分工理论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也由长期动态相互影响的关系变成了静态相互独立的关系。
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在抛弃了分工传统后建立了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但福利经济学定理一定总是成立的吗?遗憾的是,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对福利经济学定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首先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过程所暴露的巨大缺陷 (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和“高频率性”、收入差距和垄断等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20]。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导致这类问题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唯有在生产关系领域 (公有制)的变革才有可能解决经济危机和收入差距方面的问题。随着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公有制便从理论转为了实践。公有制到底如何进行实践呢?列宁和斯大林等人提出了以国家为主体实行计划指令性经济的构想,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次,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同样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而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更是对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凯恩斯则一针见血的指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并不总是成立,社会往往面临的是“总需求不足”,于是为了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等方式干预经济,从而达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相一致的目的[21]。而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引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进入了将近2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其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缺陷的微观基础均未能给出明确的回答,于是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转入对于市场失灵的研究。可以说,市场失灵对于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缺陷的微观基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解决办法与马克思的做法相似,引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虽然“市场失灵”理论在这个阶段已经被一部分经济学家所认识,但从研究的深度及其解决办法上还有待深入 (尤其是未能解释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产品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①早期的“市场失灵”理论虽然指出了市场失灵对于经济绩效的负面影响,但其对于“市场失灵”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市场失灵”的微观机制和内生性原因是什么?早期的“市场失灵”理论均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但是,政府干预或者是计划指令性经济存在的范围是不是越大越好呢?新近的理论证明:在信息完全的情景下,组织中晋升激励机制的应用同样可导致帕累托最优产出[9-10]。然而,这也只是说明了计划指令性经济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其现实性仍旧值得怀疑,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场有关中央计划体制可行性的论战得到证明。在这场论战中,争论的一方坚持中央计划体制的有效性,而另一方则从实际操作性出发说明这种体制的不可行。市场论者对计划论者提出了最为根基性的问题:在一个个体知识极度分散的社会中,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这些分散信息以制订完善的计划,从而也不可能取得好的经济绩效[22-23]。而从现实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成就后大多经历了其后经济发展的停滞,这也是转轨经济学产生的现实基础。
那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多的可能是存在着最优边界的问题,不论是政府、计划指令性经济还是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存在着一定范围的。而且,政府干预经济与计划指令性经济到底有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科斯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中,计划指令也存在于现实经济的各个层面。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对于将供给直接简单的理解为生产函数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市场机制是最优的,那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于是,根据这个思路作者认为: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价格契约机制和以强制性特征的组织契约机制同时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而且市场机制和组织契约机制均存在着交易成本,当市场机制与组织契约机制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的最优边界也就决定了[16-17]。
可以说,科斯这两篇论文对于理解政府、计划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作者抛弃了以往将政府、计划指令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观点,作者认为组织契约机制与价格契约机制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并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同时,作者分析了企业不同于市场交易的本质性特征,从而使得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价格和市场机制,同时还对企业组织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政府结构特征提供了研究方向,从而回到了斯密传统。
尽管科斯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科斯只是指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性,但交易费用又是由于什么因素引起的呢?沿着这个思路,Alchian[24],Demsetz[25]和威廉姆森[26]等人分别从“资产专用性”、“队生产”以及“不完全合约”等角度阐述了交易费用的来源。同时,布坎南[27]等学者还将交易费用理论运用到了政府部分中探讨了政府失灵的状况。①新制度经济学是近30年来发展速度令人欢欣鼓舞的领域之一,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具体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每一领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弗鲁博顿和芮切特所著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交易费用引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不论是“资产专用性”、“队生产”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所造成的代理成本所致,这也构成了合约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正是由于代理成本才引起了交易费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对于组织契约机制的解读同时不仅为理解市场,还为理解企业、国家和政府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即使回到社会主义大论战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计划指令经济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代理成本高昂,这也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于是,通过代理成本视角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就可以将政府、计划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纳入到一个相同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三、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框架:代理成本的视角
依据上文所述,通过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的角度可以将政府、计划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纳入到一个相同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于是,我们进一步确立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框架。在进行分析前,我们需要明确信息不对称的两个类型:一类是机制性信息不对称。这类信息不对称是由于机制不完善(不满足制度设计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所造成的机会主义所引起;另一类是技术性信息不对称。这类信息不对称可以解释为:尽管机制设计是完善的,但由于时滞、市场失灵等原因的存在可能使参与者仍旧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两类信息不对称的区别在于:技术性信息不对称在短期内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演进以及竞争性行为的存在,技术性信息不对称终将消失。机制性信息不对称由于是制度本身的缺陷所导致,因此不管是在长期还是短期机制性信息不对称均存在。于是,在明确了上述概念后,实际的经济绩效便可以用下式表示:

式中,YR为实际的经济绩效,Y*为完美信息时的经济绩效,为信息不对称存在时其对于Y*的偏离,其由三部分组成:技术性信息不对称扰动项 ()、机制性信息不对称扰动项()和二者的交互作用 ()对于实际产出向下的偏离。另外,、和同时满足边际递增原则:。其主观的经济学意义为:机制 (技术)性信息不对称越大,那么人们的机会主义动机也就越强烈,从而导致、也就越大,实际经济绩效也就越差。二者的交互作用表现为:机制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使竞争性机制减弱,由于激励结构的改变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将减弱。
另外,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短期的经济绩效仍旧满足 (1)式。但从长期来说,由于竞争性行为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提高,导致技术性信息不对称扰动项和二者的交互作用逐渐减小,并在长期趋于0,即。于是,长期的经济绩效便遵循下式:

通过长期和短期的实际经济绩效决定式可以发现:在短期,技术性信息不对称和机制性信息不对称同时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发挥,但在长期,由于技术性信息不对称趋于0,实际的经济绩效便由所决定。在极端境况下,如果,那么实际的经济绩效便为负。
而政府与市场关系又应该如何确定呢?我们发现:不论是价格契约机制还是指令契约机制均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但由于自身禀赋的差异使得不同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存在着差异。于是,价格契约机制与指令契约机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可能存在着“比较优势”。如果指令性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扰动比较严重,价格契约机制便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优方式;相反,指令契约机制则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根据边际原则,当价格契约机制引起的成本与指令契约机制引起的成本相等时,政府与市场的最优边界也就确定。
四、对于若干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解释
通过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界定,我们证实了斯密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判断,并进一步将政府、计划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纳入到一个相同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于是,我们转入对若干国家不同的经济表现进行解释。但是,要将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行解释,首先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框架。李勇和王满仓等指出:不论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历的一个共同趋势是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市场成长,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同时也是分工水平的不断深化[28-30]。这样,基于市场成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行解释便成为我们的努力方向。
1.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
传统经济学更多地将发达国家的经济成功归因于市场的作用,是由于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才使得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看不见的手”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指令性契约同时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观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自资产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如今的市场成熟度是否比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成熟度更高呢?同时,政府干预水平在两时期又呈现怎样的变化特征呢?我们认为:就市场成熟度来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比古典市场经济成熟度更高,其重要表现形式便是经济波动的幅度也大幅减弱[28-30]。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成熟度还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从而导致技术信息不对称扰动项 ()减小,其原因可以主要归结为:(1)政府支出计划和日臻完善的宏观调控手段大幅降低了市场失灵问题。(2)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②小公司的“日益扁平化”趋势和大公司的经理人报酬计划无疑表明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日臻完善。也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大公司的代理成本问题;最终导致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和成熟。(3)科技革命和网络的普及和使用。另外,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水平是否比古典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水平高呢?答案同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按照斯密(1776)的观点,古典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只是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产生,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引入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大大提高,政府在充当“守夜人”角色、抑制垄断、收入分配以及弥补市场失灵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后来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有所下降,但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较,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还是大幅提高了,从而导致机制信息不对称扰动项 ()减小。这意味着:政府与市场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干预的减弱并不意味着市场力量的增强。机制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信息不对称的交互影响体现在技术进步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改善。
2.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
转型国家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后采取计划指令性经济,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停滞最终采取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转轨经济理论认为:计划指令经济由于不能处理极其高昂的代理成本,从而其经济表现是要劣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正如前文指出:转型国家计划指令经济在前苏联和中国等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不能被抹杀的,但后来为什么在长期的经济表现中又趋于停滞了呢?我们认为:在短期,由于理性人的前提假设,虽然在短期机制信息不对称扰动项是一个很小的值 (或者为0),从而实际的经济绩效为正,但长期由于机制不完善以及计划指令契约存在的范围过广,从而导致其代理成本将会越来越大,从而使得。从而实际的经济表现为负便不难理解了。而上述结论还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于计划指令经济完全摒弃了市场价格契约机制的作用,但而“市场竞争”有利于“风险最小化”和最大程度的解决“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市场契约本质的“分权结构”使得其在处理由于机制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扰动要优于计划指令契约[28-30],于是长期内“市场成长”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实施的经验来看,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更多的以解决信息问题的分权化改革为主要特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更多的是将计划指令不存在“比较优势”的领域转向“价格契约机制”。同时,就转轨的过程而言,为什么“大爆炸”产生了短期的经济震荡,而“渐进”的转轨方式又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呢?一方面,“大爆炸”的转轨方式使得本身存在的计划指令契约机制迅速的破坏,最终使得非常大;另一方面,“大爆炸”的转轨方式只是确立了“价格机制”,殊不知政府与市场的最优边界是由计划指令契约机制与价格契约机制的交易费用所决定,由于“大爆炸”只是确立了“价格机制”,其它的市场机制由于相配套的其它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从而导致非常大,于是我们发现更过的是由私人弥补政府留下的空缺——垄断 (寡头)。那么短期经济绩效表现较差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最终使得逐渐减小,而市场水平的逐渐提高又会促使政府调控水平的提高变小),并进一步使也逐渐减小,于是长期的经济绩效仍为正 (这需要保证政府与市场的良性反馈)。对于“渐进”的转轨方式来说,即使在早期,由于“边际改革”的特征使得旧有的计划指令契约机制并未太大的破坏 (没有退出本不该退出的领域—— “市场失灵”领域)(不大),而由于市场的确立使得市场所释放的能量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可能为正 (较小,Y*足够大)。于是,即使在短期,“渐进”的转轨方式可能在短期的经济表现也可能为正。另外,只要政府与市场产生良性的反馈,长期的经济表现与“大爆炸‘的方式相似,这进一步证明了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合理性。以中国为例,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意识到了计划指令性经济范围过大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于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代理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我们在农村、城市以及财税上分别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权让利”和“分权化改革”,这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使得计划指令性经济存在的范围大大缩小,大幅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机制性信息不对称扰动项()不断减小,但是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却并未退出,从而抑制了一部分技术信息不对称扰动项 ()的发挥。进一步,由于各项改革的进一步进行,又催生出对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需求,于是价格“双轨制”应运而生,“价格指令性”契约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领域的代理成本,政府的相应改革引起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从而使×MA进一步减小。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 (市场成长),出现了一系列技术进步 (电话、互联网等通讯设施范围的技术革命)以及产权领域的革命 (国有企业改革、对于私有经济的承认等方面),均使、和×MA逐步减小,并像完美信息下的最优产出水平Y*靠拢,这样便完成了对中国渐进式转轨成功原因的描述。按照我们的逻辑框架去理解“北京共识”,便意味着: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的干预市场,是否能够在长期能够起到培育市场的作用,而任何有碍市场作用发挥的政府干预是不可取的,①对于古典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经济绩效的局限性我们还可以从下述角度进行解释:由于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相信“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得价格契约机制超出了其最优边界,从而导致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存在范围太大,那么市场失灵领域的代理成本较高,从而机制性信息不对称扰动项也就越大;计划经济则与古典资本主义经济相反,计划经济是完全摒弃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完全相信政府的作用,认为价格契约机制总是失灵的,但公共选择学派却证实了政府失灵领域的存在,于是政府 (计划指令性契约)存在的范围又过于宽泛,从而导致政府失灵领域的代理成本过高,并进一步导致机制性信息不对称扰动项也就越大。但是不论是凯恩斯政府干预模式,还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其均承认了计划指令契约和价格契约在一定程度均是有效的,寻找政府与市场的最优边界也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这也是转轨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这与“华盛顿共识”的本质是一致的,苏联等东欧国家改革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并未理解“华盛顿共识”所致。
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本文认为不论是政府干预水平还是市场成熟度水平发展中国家均是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多的遵循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轨迹。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机制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信息不对称 ()扰动项要大于发达国家,从而导致其实际的经济表现要劣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
五、结 论
本文抓住中国转轨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特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在于正确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与以往研究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长期动态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认为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便不再合适了。经过对于前人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以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为研究前提区分了机制性信息不对称和技术性信息不对称两种类型,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的时序特征和截面特征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得出:(1)不论是市场成熟度还是政府干预水平,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均有大幅度的提高。(2)计划经济的经济表现要劣于市场经济的表现主要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指令契约机制存在的范围过大,从而使其代理成本巨大,因此其长期经济表现较差;“渐进”的转轨方式要优于“大爆炸”的转轨方式,主要是由于政府没有退出本不该退出的领域从而使得代理成本下降。(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则更多的表现为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轨迹。
我们的结论表明:如果以强制性视角来看待政府、企业以及计划指令经济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企业以及计划指令经济都是以计划指令契约管理经济。于是,本文认为:不论是价格契约机制还是指令契约机制均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但由于自身禀赋的差异使得不同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存在着差异。于是,价格契约机制与指令契约机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可能存在着“比较优势”。如果指令性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扰动比较严重,价格契约机制便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优方式;相反,指令契约机制则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根据边际原则,当价格契约机制引起的成本与指令契约机制引起的成本相等时,政府与市场的最优边界也就确定。
本文的结论证实:私有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并不能将私有经济占GDP的比重看做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同样,公有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所占比重也不能是判断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从而证实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目标均是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另外,不仅仅是市场机制,政府、计划指令经济在一定条件小均有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关键在于政府、计划指令经济是否能够缩小社会中的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水平。同时,我们的结论还有助于回答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要“政府”,“政府”与“市场”都要要,关键是要怎么样的政府与怎么样的市场②这一点,林毅夫的答案是选择符合本国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我们的结论与其具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同时还指出了比较优势长期动态的趋势—市场成长。),我们认为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禀赋优势和时间演进的轨迹选择政府与市场的最优边界,其检验标准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代理成本)实现最小,并在长期有利于市场成长。①因为价格契约的“分权”本质更容易满足契约实行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而计划指令契约的强制性特征(“集权”本质)与现代经济是不相容的。而与此相关的政策建议是应该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作为衡量市场成熟度的标准,政府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培育微观市场环境、提供宏观调控水平、保护产权等有助于培养市场成熟度的措施上来。
[1]卢峰,姚洋.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4,(5):42-55.
[2]王永钦,张晏,章元,等.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3-20.
[3]张五常.中国的前途[M].香港:香港信报出版社,1985.8-14.
[4]张曙光.从计划合约走向市场合约——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思考[J].管理世界,2005,(1):96-101.
[5]Qian,Y.Y.,Xu,C.G.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J].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3,(1):135-170.
[6]Qian,Y.Y.,Roland,G.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11):83-92.
[7]Qian,Y.Y.,Roland,G.,Xu,C.G.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4-6):1085-1094.
[8]热若尔·罗兰.转型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5-593.
[9]Fairburn,J.A.,Malcomson,J.M.Performance,Promotion,and the Peter Principle[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1,68(1):45-66.
[10]Gibbons,R.,Waldman,M.A Theory of Wage and Promotion Dynamics inside Firm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4):1321-1358.
[1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432-435.
[12]何晓星.再论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J].中国工业经济,2005,(1):31-38.
[1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83-100.
[14]冯涛,李湛.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演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2):94-100.
[15]刘瑞明,白永秀.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对于中国式改革的理解与反思[J].南方经济,2010,(12):59-70.
[16]Coase,R.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4(16):386-405.
[17]Wittman,D.A.,Coase,R.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M].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Selecteal Readings,1960.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玉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828-830.
[1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晏智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75-602.
[20]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2-1048.
[21]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82-785.
[22]Hayek,F.A.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M].London:Routledge,1935.1058-1075.
[23]Hayek,F.A.Socialist Calculation:The Competitive‘Solution’[J].Economica,1940,7(26):125-149.
[24]Alchian,A.A.,Demsetz.H.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niz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5):777-795.
[25]Demsetz,H.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57(2):777-801.
[26]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21-332.
[27]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M].吴良健,桑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01-212.
[28]李勇,王满仓.中国经济周期的实际轨迹:一个理论框架——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10,(3):91-104.
[29]李勇,王满仓.中西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评价与思考[J].西部论坛,2010,(5):87-93.
[30]王磊,李勇,王满仓.中国经济周期的双重性波动——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1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