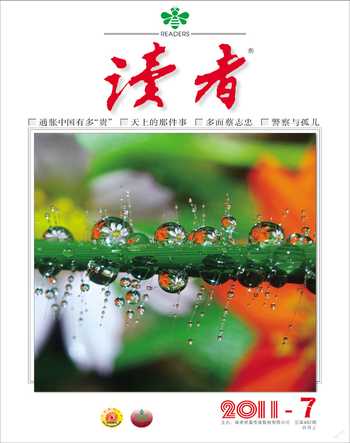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高中刚毕业,年龄和我相差5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要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携家带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拥出校门与不同的机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在那里可以抽烟,我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支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像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得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它还不走。它追着我,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10岁长到20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沙沙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5万字,150多场,粗算一下需要3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像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边眺望远处,远处北影的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时,我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着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些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科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到太原需14个小时,再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的墙上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欣。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我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想到这些我从小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消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使命。那一年,我27岁。
回到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画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我在长话室里打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我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500元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打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4月10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我永生难忘。4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得还算顺利,于是2000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的《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组委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3个导演,给钱让我们用DV拍30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见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却灰尘密布,人去楼空。在大同常见孤独的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近在咫尺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在回北京的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犯知道此去危险,想给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了少年心: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足于现实。
(何宇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贾樟柯故乡三部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