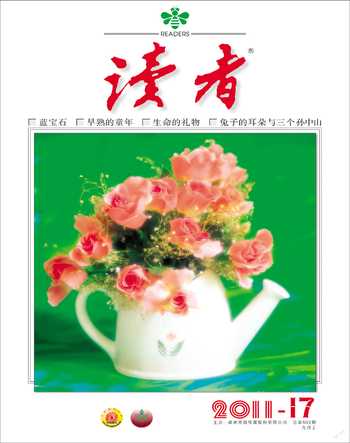夫妻
情人节那天,女儿告诉我一个笑话。说有一位先生,出门忘了带样东西,转头又回家去拿。走到家门口,他敲门,里头他的太太来应门,问道:
“谁?”
“我,你的先生。”
“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是我先生呢?”太太存心开个玩笑。
外头的人愣住了,只听他太太又问:
“这样好了,我问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让你进来。”
外头的人松了口气:“你问吧。”
太太说:“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外面那个人左思右想,竟然想不起来,急得结结巴巴地说道:“天啊,我不知道……”
太太说:“好了,进来吧。你的确是我先生。”
大女儿选在情人节那天告诉我这个故事,原因是小女儿放学回来时给我带回来一捧花。我很感动地说:“到底是女儿比丈夫好。”
大女儿赶忙说了这么一个笑话,弦外之音是:天下比爸爸不如的丈夫还很多呢。我因此过了一个愉快的情人节。
可惜,一年倒有364天是“非情人日”。我在这些非情人节的日子里,偶尔想起这个应当是笑话的故事,反而不以为是玩笑了。也许可以把它拿来当做《尺牍大全》之类的书本里的一则“范例”来看吧。
如果要编一本《夫妻大全》,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一定要编进去的——那个故事,我中学时读到,至今难忘,应当是一位法国小说家的杰作,恕我忘了原作者之名。还是说说那篇小说吧:
有个作家爱上了别的女人,很想跟太太分手,可难以启齿。后来想出一个主意,把他的外遇和希望写成一篇小说。他的文章,一向由太太誊写,所以他想太太读完那篇小说也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了,到那时他再来看太太的反应如何。
不料,太太抄完稿子,寄出去之后,完全不动声色。那位作家非常不安,他想,太太竟然完全只当做小说来看吗?我还得另外再想办法来表明心意!他整日惴惴不安。后来小说发表了。作家读着读着,心里大为感动,拿着帽子就出去了,他是跟那位“别的女人”告别去的。
原来他太太抄稿时,把故事的结尾全部改了。
这年头,谈“夫妻”似乎是很落伍的事。满街不都是些“快乐的单身女郎”吗?不久,“单身父母”(未婚的和离婚的)亦将流行起来。然而,青春短暂,难道现代人就不怕老吗?或者比较知道如何排遣老年时的孤单寂寞吗?
请别误会我有恢复旧传统的暗示,一点也没有。因为前面所说的两个故事,如果颠倒阴阳来看,依然是很可羡的夫妻。今天,聪明的男士应当知道他们往后的对策——趁早培养幽默感,才是上策。
夫妻之间的爱,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恩爱”这两个字。我有时候想,难道夫妻间也应当讲究恩遇与报答之情吗?说不定正因为我们已淡忘了这一点,夫妻情义在现世才逐渐淡漠了。
我们有时候希望对方像情人,可是情爱仿佛是纯精神上的爱,给得多取得少,而夫妻却要牵扯到肉身以及取予的平衡。我们有时候又希望对方像兄长(或母亲),可是亲情间得有次序和尊敬,夫妻却没有这样的距离。有时候我们又希望对方像朋友,可是友情与各自的私生活可以无涉,夫妻之间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太贪求的话,其实为夫的或者为妻的一方,能像情人、兄长或朋友其中之一就行了,不是吗?佛家说:恩爱狱——有恩有爱就失去自由。这个“狱”字用得真好。其实,人生不也就是一个大狱吗?而我们单挑“婚姻”制度来责难,或许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只是“借题发挥”而已吧。
前几天读《凌叔华小说集》,里头一篇《千代子》这样写道:
“支那女子很糊涂,男子叫缠足便缠足。女子缠了脚便不能自由行动,男人要怎样就得怎样了……我们日本女人可不会那么糊涂。”
这使我想起我一位在日本住过多年的朋友来。她告诉我:日本的老年人,男的比女的要慈祥多了,据说是男子年轻时没有受到性的压抑,到老时“归顺”他太太,自然心平气和。反倒是老太婆,一个个都像“慈禧太后”。
日本女人睁着眼装糊涂,中国女人闭着眼装糊涂。现在的女人不糊涂了,可是清早六点起床时,孩子吐了还发高烧,九点却有重要的会议要出席,那滋味也不好受。聪明,是自设的陷阱?
最近美国又流行起老式的婚礼来了:白纱礼服,大捧大捧的鲜花,祝福与眼泪等等。不过,听说保险公司也正计划推出一项新尝试——离婚保险,为的是防止因离婚而破产,或因拿不到赡养费而受穷困之苦。
中国女子用缠足来缠住男子的心,日本女子用等待来等待男子的心,美国女子明白心是会变的东西,世上还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可以追求。
怎么样可以不必自苦又能获得对方的心呢?我想,这就是现代夫妻的理想主义吧!
以前读过一首旧诗,意译如下:
我遇到一位先知,
手中拿着智慧之书。
我请他让我一读,
他说我还年幼无知。
我说我已读过千百本书,
相信他手中的书亦难我不倒。
先知于是递给我,
智慧之书。
啊,多么奇怪,
我一打开那书,
竟如同瞎子一般。
写到这里,想起《夫妻》这本大书,我心上也忽然“混沌”起来。
(余仁杰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喻丽清散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