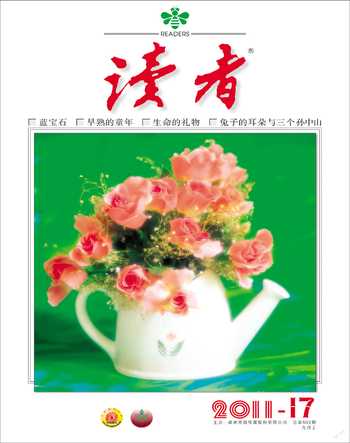兔子的耳朵与三个孙中山
邵毅平
先说一篇日本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叫“兔子的耳朵”: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我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
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呦!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小作者时年七岁,叫悦子。她阿姨叫雪子。晚上悦子睡觉以后,雪子看了这篇作文,觉得“用脚”的举动不雅,连忙把它涂掉,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雪子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的。但悦子仍难以理解阿姨的改动。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子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是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的举动很粗野。”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这篇作文,以及围绕这篇作文所发生的故事,都被写在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里了。
这篇作文有我们所谓的“思想性”吗?没有。有我们所谓的“意义”吗?没有。但是,“悦子的作文被教师评为优等,这篇作文写得很出色,雪子借助字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可见日本学校的作文评价标准与我们的很不一样。雪子的改动还算有限度,只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假话,但悦子的疑惑表明,即使这样的改动,也有违她所受的教育。这就说明,在日本对作文的要求中,如实地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义”,则显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国,老师大概会要求最后加上几句“点睛”“升华”之语,诸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做个科学家,这样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了”之类。
这篇作文是直接来自孩子,还是小说家捉刀代笔的呢?读者自然会发生这样的疑问。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作文在日本能够得优等!我们关心的是,大作家显然欣赏这样的小作文!
我曾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让日本的大学生写作文。读他们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悦子的作文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没有空话套话,不会硬塞入我们所谓的“思想性”,不会硬赋予我们所谓的“意义”。也有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日本“小海龟”,文风明显华而不实:“啊,老师(或母亲、父亲),你是我生命里的红烛,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却燃烧了你自己……”
我读日本文学作品,也有同样的感受。用我一个学生评论小泉八云《怪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中国式的伦理纲常,想淫就淫,想要钱就直接去做”(别误会,说的是文学里,不是生活里)。也正因为这样,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润一郎有《细雪》,也有《疯癫老人日记》。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为全无顾忌或禁忌。我们缺少这一类作品。
再说一篇中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不详,姑且叫它“三个孙中山”吧,转引自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人”是怎么不见的》: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黄老师的点评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我想,被掐断了的,不仅是孩子的灵气,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中国小学生的灵气不比日本的差,但我们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们;中国作家的天赋也不比日本的差,但从小受的作文教育会拖累他们一生。
想起在“新鉴真号”轮船上听到的广播:“……美丽的濑户内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很文学也很中国,撰稿者当年的作文成绩一定不赖。但看看舷窗外面,风景确实美丽,帆却一片也无——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就是我们作文教育的成果。这样的作文、文章比比皆是。
当然,这种所谓“思想性”“意义”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心雕龙》就主张,诗要“持人性情”,鲁迅讥之为“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又说,“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读汉赋,最怕曲终奏雅;读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载道;看今日的小品,最怕音乐起,说教来;看报刊上的“优秀”作文选,最怕“大文化”排比铺陈,“假大空”议论抒情,“格式化”起承转合……
二十多年前,有人曾问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异同”,章先生回答“只有一条”:“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得到过有影响的国外文学奖,这是同;中国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学奖,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异。”
我们的文学离世界水平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据我对当代中日文学作品的有限阅读,我知道我们离日本文学还有点距离。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的感觉和看法,原是不作数的,大家可以无视。
但如果真有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应该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中国文学,至少现在的文学,与日本文学相比,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
要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首先需改革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题,少规定写法,少要求所谓的“意义”和“思想性”,多让学生“我手写我口”,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三个孙中山”受肯定了,中国文学才有希望。
(李苏杰摘自《文汇报》2011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