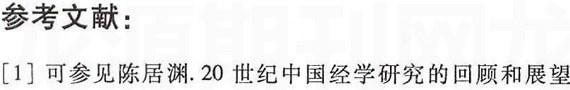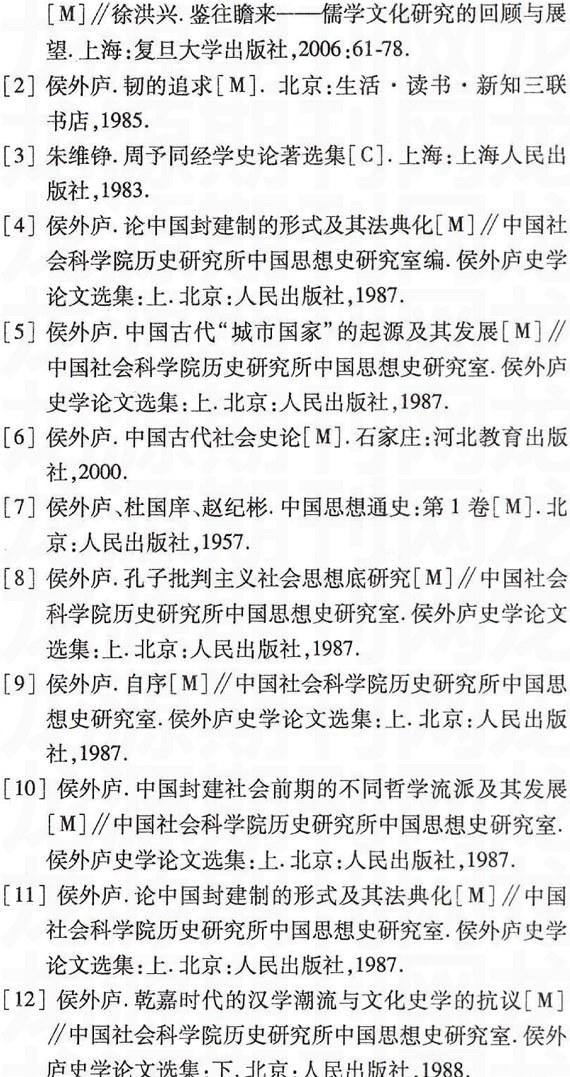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的特色及意义
陈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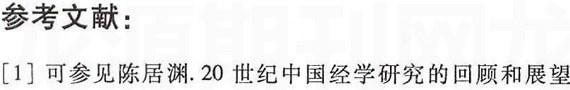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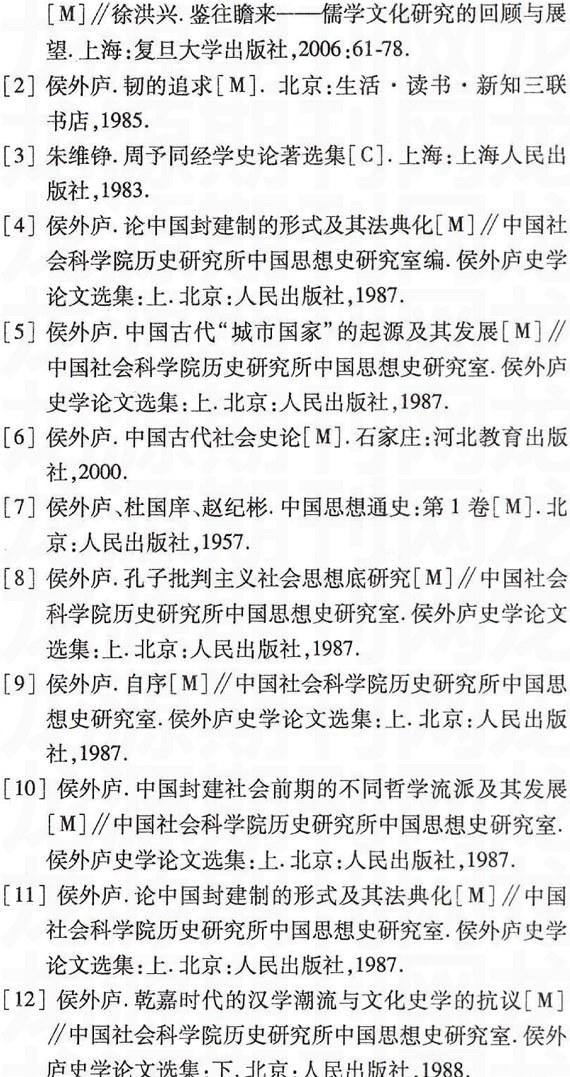
摘要:通过对侯外庐先生经学文献研究资料的实事求是分析,揭示侯外庐先生将经学文献(包括经学元典和经学研究作品)作为考察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的主要依据,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路,特别是利用《诗》《书》等,结合出土金文和流传的历史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概括和论述先秦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演进,独获良多,特色鲜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蕴含着不少对开拓和深化经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关键词:侯外庐;经学研究;特色;意义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065-06
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1903-1987)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卓著贡献,涉及方面很多,其中也包括经学研究。侯外庐先生的经学研究与特色,目前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笔者不揣浅陋,略论一二,以求教于方家。
一、在经学研究上注重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
侯外庐先生对经、子素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自己晚年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坦言:“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样,早年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中,经、子、史、集构成为主要内容。其中,我的兴趣所在,偏于经、子两类,对诸子百家学说素有兴趣。”侯外庐先生的经学研究与其一贯的学术思想史研究相统一,注重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融会和沟通。按照《韧的追求》记载,侯先生在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准备马上着手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定下的计划是:尽先努力完成秦汉社会的研究,而后搞秦汉思想;先着手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构成,而后研究中古玄学史;先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而后再探讨宋明理学思想”,后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改为先着手研究近代历史与近代思想,形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对《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侯外庐先生有很自信的评价,认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清理古代重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思想发展的路径,那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则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草创研究另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明清之际思想发展途径的一种研究方式。在40年代初,我这种研究思想史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决定这两部书是拓荒性质的作品。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变革时期思想发展路径的清理和力图有所发现,通过对一系列疑难问题的涉足和作出自己的回答,我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基业终于得以奠定。
侯外庐先生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探讨学术史变迁(包括经学问题)方面也同样体现了这个特征。这种研究路径在经学研究中也有一定新意。例如,《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董仲舒”部分,虽然初稿基本出自赵纪彬先生,但在动笔之前,赵先生与侯先生作过深入的讨论和沟通,所以能够反映侯外庐先生关于董仲舒的学术评价。《韧的追求》谈到《中国思想通史》对董仲舒的评价“极严厉”,与受到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章氏称董仲舒为“神人大巫”)不无关系。侯外庐先生认为:“董仲舒思想反映了大一统的需要,但它是一种神学思想,它既经出现之后,又被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奉为原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把儒家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加以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行说加以唯理化,把秦汉王朝更替归结为奉天承运的天道之必然,把专制制度神化为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法则。董仲舒思想,就是如此一整套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需要而创立的颇具中世纪神学色彩的儒学”,“董仲舒神学一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钦定,进而又被确立‘为群儒首,‘为儒者宗,也就是说,被钦定为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封建正宗思想。董仲舒神学对两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危害,远不是他形式上师承的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本身所能比拟的”。侯外庐先生甚至由对董仲舒《春秋繁露》“繁露”一词的语义考察,折射出董仲舒《公羊春秋》学与统治者意志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如果仅从《公羊春秋》学的经学研究考察,侯先生的分析和研究存在未惬人意的地方,但是如果从思想史或哲学史角度分析,他对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学术本质的揭示却是独到和深刻的。这种经学研究与思想(哲学)研究各有优长、瑕瑜互见的情形,在经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前辈学人多有精彩的论述,如周予同先生在分析朱熹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时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在研究经学人物和作品时,不将人物和时代割裂开来,不对作品进行孤立的抽象的分析,这是侯外庐先生历史学研究方法和特点在经学研究具体实践中的体现。如关于《白虎通义》的法典化性质的揭示,“不论封禅之于皇帝,自己神定所有权,或者封建之于列侯,赐赏臣下占有权,都是国有土地的形式,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编制的一个特征。《白虎通义》以神权的固定形式,把这种原则用经义来法律化起来,代表了一部汉代的最高法典”,这已成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观点。
侯外庐先生对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要领有自觉的意识,与一般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有根本的区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种结论,既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泛泛言之的浮词剩语,而是科学的坚实的结论。对思想史的要求,则在乎对于前人的思想学说,区别精华与糟粕,按其实际作出历史的评价。研究历史,贵在能解决疑难,抉露本质,这不同于摄影师的照相术,摄影唯肖是求,研究历史则要求透过现象,找寻本质,淘汰杂伪,探得骊珠,使历史真实呈露出来,使历史规律性跃然在眼。这与调和汗漫的研究态度相反,既不能依违于彼此之间,亦不能局促于一曲之内。”
正因为如此,侯外庐先生的经学研究视野很开阔,他主张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抓住思想学说的本质,努力呈现历史的真实。简要概括就是“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
二、运用《诗》《书》资料创造性地研究和发掘了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典型特征
侯外庐先生运用《诗》《书》资料创造性研究和发掘了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典型特征,收获丰富,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结合甲骨、金文材料的基础上,这些《诗》《书》史料被侯外庐先生辩证而谨慎地使用,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勾勒西周到春秋时期社会及思想观念的变动状况,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体现、城市的发展、国民的存在、公子与富子(大
夫)地位的变迁、天命观念的递革等问题。
侯外庐先生根据《诗经》《尚书》记载考察周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他说:“把《诗经·周颂》和大、小雅相比,《周颂》的创作最可能是生昭、穆两王的时代,大小雅各篇却是在不同年代创作的。《周颂》近古,除了追思后稷远祖而外,各篇所说的都是文、武立基,成、康光大,传说很少。《周书》也只尊崇文、武,如说‘丕显文、武。西周金文都祖文、武,例子很多。”他根据《诗经·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诗经·大雅,皇矣》“万邦之方”、《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武王成[城]之”等审视了周世代作邑建国的承继关系;根据《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维丰之垣”等,论定文王封树国家,即氏族贵族统治的城市,“国便是城市”,认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初期的筑城是封树,后期是土墉,一开始并没有‘筑和‘城、‘邑和‘都的严格分别”,这些论断无疑是有新意的,而且整体上具有系统性,对于文字的考辨也都有字源学的佐证,将《诗经》的史料性充分彰显出来,并触及到人们不甚关注的领域。
他在《诗经》中的《我将》《赉》《桓》等篇中发掘出了文王、武王受民受土的历史事实,揭示了其中隐藏的争取劳动力、占有土地的历史秘密。在国野讨论基础上,侯外庐先生探讨了西周时期土地制度的问题,他根据《诗经》中的《齐风·甫田》《魏风·十亩之间》《小雅·甫田》等论证了“甫田”与“南亩”的区别与联系,其中的联系恰恰显示了“亚细亚的特殊之点”,主张“甫(大)田、大田是鄙野之公田(氏族专有之田),而南亩、十亩,则为小生产市民的小私有田(疑即使有所谓授田之制,亦限于这里国中),后者当然是土地制度的从属意义,支配者还是前者”。在此基础上,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情形作出推论,认为:“‘耦国或城市国家的多元发展,固然为‘富子与‘宗子之‘国与‘家相争,但大夫‘有国的现象只是氏族制的分化,而不是氏族制的结果。我以为‘陪臣执国命颇有古典显族的意义,但并不典型,而且到显族‘有国的时候,古典社会的周制便将结束了。”
“国人”的社会地位也是侯先生格外注意的,他依据《诗经》《曹风·鸤鸠》“淑人君子,正是国人”,《陈风·墓门》“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等加以论述,主张:“没有自由民,不会产生希腊的悲剧艺术,同样地,没有国人,也不会产生中国的古代悲剧诗歌(《诗经》)。其原因,在于相对的民主。”这给我们把握《诗经》诗歌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侯外庐先生根据“变风变雅”揭示周代思想的变化。他对《大雅》中的《板》《抑》《瞻印》《召曼》《云汉》《小雅》中的《小宛》《周颂》中的《维天之命》《武》等作了比较细腻的勘查,揭示了人们对上帝天命观念的转变。变风变雅充斥着对上帝天命信念的动摇,对先公先王的不信任。因此,侯外庐先生扼要地指出:“在这种悲剧的历史中,道德观念渐渐发生了变化。周初的德字和哲字,都限于先王配天的专称。宣王中兴前后,道德观念渐渐向下面转移。这种转变是指示氏族组织的破坏反映在人类观念形态上。”
从思想史角度揭示“变风变雅”在思想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意义,即作为诸子思想的先驱,无疑是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的一大亮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花朵,以诸子百家为代表。但它的先驱,不能说不是变风、变雅的诗篇。”侯外庐先生正是抓住“厉王失国”与“宣王‘中兴”社会变革中的矛盾运动以及思想的悲剧性特征,即“一方面对于旧制度采取一定的保守态度,另一方面又对于民众的力量具有着一定的同情心”,“从这意义讲来,变风、变雅无疑是先驱的悲剧诗歌”,在思想内涵上,这些诗歌暴露了周初“王道”思想的矛盾,特别是其中的天人矛盾,奠定了“东迁前后开放出思想之花”的基础,这样,侯外庐先生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春秋时代既有搢绅先生所传授的六艺思想,又有暴露阶级矛盾的悲剧思想”,揭示了社会变动时期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和具体特征。因此,侯外庐先生认为,“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应该是说‘《诗》亡然后诸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侧重经典形式的角度,即由重视讽诵的《诗》到寓以褒贬笔法的《春秋》,显示了礼乐文明的松弛;“《诗》亡然后诸子出”却是侧重思想意识的继承角度,突出了“变风变雅”对诸子思想的先导价值,自然更为深刻有力。
另外,他将《诗经》部分诗歌所体现的这种悲剧思想,最终仍然归结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矛盾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基本治学理念。即使今天,关于前诸子时代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依然是经学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需要不断加强的环节,侯外庐先生对“变风变雅”与诸子思想内在联系的揭示有助于启发更多的后来者,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如果联系侯外庐先生对孔子等思想的分析,就更容易明白这种悲剧性的传承和学术意义,它使思想学术的内在逻辑链环更加完整,使思想观念的变革脉络更加清晰,并且时刻根植于社会变动的土壤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面貌和传统是与“变风变雅”相呼应的。
三、探讨《六经》形成中的“具文化”和“道德化”的问题
在具体分析社会变动及学术思潮的基础上,侯外庐先生对某些经学现象和问题有深刻的洞察,比如关于后来所谓的《六经》的形成中的“具文化”和“道德化”的问题,这应该是《六经》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经学研究和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侯外庐先生认为:“西周的文物典章,在春秋的反动内战(族战)与外战(氏战)之下,已经不是有血有肉的思想文物,而仅仅作为形式的具文,背诵教条罢了。”实际上,这是“礼坏乐崩”的典型写照,《六经》的形成和阐释不得不与这个阶段联系起来,才能寻觅出经典意义生发的转折点。
侯外庐先生认为:“诗、书、礼、乐已经成为邹鲁搢绅先生的专门职业,这虽保存了西周文明,但却成了好像礼拜的仪式。例如‘礼在西周为‘‘惇宗将礼的维新制度,氏族君子所赖以治‘国的优先权。《诗》在西周为社会思想的血脉;然而到了春秋,公子与‘富子(大夫)争夺,富子大夫取得政权,礼固失其基础,《诗》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变风、变雅)。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诗》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贵族交际场合的门面词令,朝宾的乐章唱和,使于外国的教条酬酢(赋诗,即背诵一首《雅》《颂》)等等。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变成了死规矩”。侯外庐先生以“诗”“礼”为例揭示了春秋时期西周文明的貌存实亡,西周文化的具文化和形式化是这种发展趋向的典型表现,“赋诗断章”也是这个运动的重要内容。
但是侯外庐先生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种具文化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搢绅先生一方面因了社会的黑暗,把西周的思想作为‘儒术
而职业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传统上则相对地保持着文化遗产,这亦只有邹鲁这样周公遗教可能存在的国度里,才没有将历史传统的文化斩绝。”
侯外庐先生抓住春秋学术思潮变动的枢纽,将“学术下私人”在文化承革中的意义简明地勾勒了出来。“儒者将西周思想文化形式化,正是春秋制度将西周‘王道形式化的照映。同样地,诸侯而大夫的过渡阶段成为战国不完全典型的‘显族时代之桥梁,因而,春秋的搢绅儒术亦成为战国显学之过渡桥梁。学术下私人的运动,乃适应于经济相对的国民化(显族路线),所以,由儒者蜕变而出的显学,一方面是对于春秋文化具文的批判,他方面又是开启‘子学发展的源流。这一中国古代思想的流变,极关重要。前人很少注意。”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侯外庐先生指出孔子与搢绅先生的不同,并肯定了孔子在儒学形成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贡献,经典阐释的道德化源于孔子,这也是经学研究的关键之一。他认为“孔子确是由儒术建设了‘儒学的第一人,批判的活动有程度地复活了学术的新内容……他自认为儒者的正统,和他对于西周制度的正义心是相一致,同时他又批判儒者,亦和他把诗、书、礼、乐道德化(系统学说)而否定形式具文相一致”,孔子的“诗书礼乐之说(书乐合于诗礼),不同于搢绅先生的牧师说教。‘立于礼是他的思想中心,但他附加了道德情操,而不是具文了”。侯外庐先生认为:“‘立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在孔子的时代,具体而言是指西周遗制,即一种过时了的氏族宗法和古旧的宗教仪式。孔子断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的‘礼将西周遗制纳入其中,是一个观念化的范畴,用来作为社会极则的。”“孔子的‘礼‘仁观,都交织着主观上对旧制度的相对‘正义感和客观上对新陈代谢的悲剧感的矛盾,交织着主观历史理想和客观历史动向认识的矛盾。从作为我国古代学术开山祖孔子的矛盾意识,一直到战国末年的诸子论争,逻辑地,雄辩地反映了先秦显族社会的难产过程。”尽管孔墨在关于文化内容和形式先后、高下方面侧重不同,但他们都受到诗书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都努力复活和发展西周文化,所以侯外庐先生认为“孔墨在春秋末与战国初,是批判了春秋传统而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化”,这是考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流变的关键,也是研究子学源流的基础,对于经学研究而言,把握《六经》的形成过程和研究的道德化倾向,也需要在这个整体的学术思潮变动中加以审视。
四、反思“经学笺注”传统及经学研究方法
整体上,侯外庐先生的经学研究与其思想史研究是相互统一的,但是他对经学研究的独特性及传统经学研究的方法与成果也很重视。
侯外庐先生对思想史研究的复杂性有明确而自觉的认识,他认为:“一般说来,思想史(包括哲学史)上的范畴、概念之新旧交替,反映了人类思想本身变革的过程,亦即反映了人类认识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正像历史向前发展中总会出现曲折反复一样,人类认识的长河也不会是直线前进的。因此,在思想史上并非所有新的范畴、概念都是趋近客观真理的思想变革,有的甚至还可能是它的反面……考察人类新旧范畴更替与思想具体变革的结合,关键在于依据不同历史条件,具体分析各种范畴在不同思想家的头脑中所反映的实际内容。”人类文明史上的这种普遍状况,或许给学术研究与创新创造了契机和条件,“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至于对前人思想遗产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则是由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条件、阶级地位及其思想性格、学术渊源等诸种因素决定的。当然,继承并不意味着对前人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甚至是不同性质的改造。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取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思想的继承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儒家的经学所以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和它通过笺注形式的继承关系而不断扩大其自身的积累是分不开的”。经学的笺注传统,正是儒家思想不断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形式和途径。
侯外庐先生特别关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经学笺注”传统及其意义,他认为:“有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作为凭借,中国中世纪的不同哲学流派,都通过古代学术的丰富传统,对各自所选择的古代思想材料来继承和改造。在儒学居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哲学家的著作大多采取了笺注或论释经籍的形式,而在经学外衣下面的实质则贯穿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神学、统治阶级正宗思想与富有人民性的异端思想之间的党派斗争。”“‘经学的传统,在经师世代相承的系统上,虽然表现出中世纪拘于传统习惯势力的狭隘性;但在古代文化的保持上,又起着强固的传授或维系作用。这样层累地积蓄起来的文化,对于中国中世纪的思想史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这种经学笺注形式后来也应用到道家经典或佛教内典。”
但是,关注经学笺注并不能抹煞经学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特征。这就涉及经学的形式及本质问题,侯外庐先生有独到的体会,他将经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术形态来对待,谶纬、玄学、理学等都是这种经学的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经学本身所包含的思想学术也具有复杂性,排除对经学观照的简单化倾向。侯外庐先生曾具体论证过这一问题,“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它本身都是借助于传统的思想材料,改变其形式,进而增补其内容。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可能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中国中世纪历史上的经学笺注主义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不论秦汉人的经学的谶纬化,魏晋人的经学的玄学化,唐宋以来的经学的科举以至八股化和道学化,都应该从这里去了解。”
如:“清初学者开风气者,气理、文辞、学问并没有分家,即以博雅者顾亭林而言,亦以考证为手段,经世致用为目的。亭林所谓‘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并提,而且是以后者为内容,和乾嘉学者的经学实在是两种东西,不容混同。因为以经学挽救理学的空谈是一回事,而以经学只限于训诂名物(甚至东原的由词通道)又是一回事。”“专门汉学,自康熙以至乾嘉二朝,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学术,其间指导的主流,是企图腰斩清初活文化的人民性与社会性,在古典的经籍中使之失去个性的发展,从文化上‘开明的烙印冲淡那异族统治的仇恨;然而这亦可能产生了副作用,即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以及由经学的整理而扩充到一般文献(尤其子学,如与章实斋同时的汪中即招来墨者的头衔)之探寻。”他对经学研究和影响的复杂性有充分的关注。
从方法论角度,侯外庐先生对经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无论研究社会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论断,均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实可靠的史料。考据学本身算不上历史科学,但它却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专门学问。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训诂、史料考证辨伪方面下一番工夫。要遵守前人的严谨的方法,不可随意采择史料。例如,如果拿《周礼》来论证周初的制度,如果拿《管子》来论述管仲思想,就会犯错误……历史科学要求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流入夸诞和虚构。”侯外庐先生在学术研究中,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主张“考据学是一门专门学问,我从来反对虚无主义地对待考据学”,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色。
侯外庐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很重视“阐微决疑”,“阐微”指“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从古文献中发掘历史的隱秘”;“决疑”指“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阐微决疑”“学贵自得”的精神目的在于不断创新。前文所涉侯外庐先生对《诗》《书》的研究,即是这种“阐微决疑”的鲜活例证。
总之,侯外庐先生通过对经学文献资料实事求是的钻研,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路,与传统的章句训诂、义理阐发、考据学研究不同,另辟新途,别树一帜,特别是利用《诗》《书》等,结合出土金文和流传的历史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概括和揭示先秦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演进,独获良多,特色鲜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蕴含着不少对开拓和深化经学研究的宝贵启示。侯外庐先生的经学研究是对唐代王通、宋代吕祖谦、清代章学诚等主张的“六经皆史”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他将经学文献(包括经学元典和经学研究作品)作为考察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的主要依据,在全面搜集、分辨勘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不拘一曲,互证抉微,在经学研究视野和深度上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