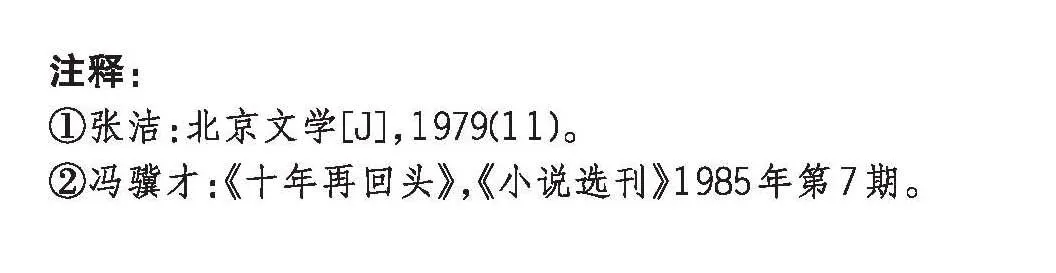论上世纪80年代启蒙话语模式下的欲望叙事
邱玥
20世纪80年代的欲望话语叙述源于叙述主体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发现和肯定,经历了张贤亮试探性地、策略地对“食”、“性”等基本生存欲望的细致描摹与书写,经过对市井生活的叙述和对市井人物的刻画,至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新写实作家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客观化书写。
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人都被叙述为具有历史深度和现实广度的强有力的理性化的欲望主体。欲望不是文学叙事的核心,叙事的核心是人的精神成长、人的生命价值以及人对终极价值追求等。卢新华的《伤痕》以“文革”后一个女儿的忏悔为主线,表现“文革”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1980年代初期,张辛欣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清晨,三十分钟》《疯狂的君子兰》等率先发现了人的“动物性”或“生命属性”,触动了人内心中隐秘的部分。随后出现了一大批以大自然为叙述客体、以江河湖海、崇山峻岭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如邓刚的《迷人的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孔捷生的《大林莽》、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洪峰的《脖尔支金荒原》等。这些小说描写大自然的宏伟壮丽,表现人对大自然的亲近和热爱,对大自然原始生命力的热切渴望,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体现出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的意味,这种精神意味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启蒙精神的土壤和情感气候,来自于古老的中华民族欲重振雄风的时代背景,表达了民族的青春活力和人们对原始生命力的渴望。人被叙述为自然之子,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发现自然,并重新发现自己。邓刚的《迷人的海》写出了大海的神秘莫测、变幻无穷、凶猛狂暴和自由不羁,作为海之子的大小海碰子的身上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险、勇于征服的意志、精神和力量,大小海碰子们腾波踏浪,从强有力的大海里汲取了无穷的力量,燃烧起征服大海的强烈欲望,即使刚摆脱惊涛恶浪的撕扯,又遭到鲨鱼的袭击,也浇不灭、吞不掉他们寻找神物的信心和意志,小说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智力和顽强的意志力。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则把人带入北方大地喧嚣轰鸣、纵横蜿蜒的河流之中,主人公“黄河之子”勇于面对、勇于承担、勇于探索,横渡黄河是他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奔腾怒吼的黄河成为他精神上的父亲,北方的河激发起他征服自然、挑战自身生命极限的强烈欲望。这是那个时代对原始生命力的独特歌咏,振奋了民族精神。
1979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倾心相恋,一生接触过的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拉过,但爱是不能忘记的,钟雨守着这份凄凉而悲惨的爱,孤独忧郁直到枯萎,她说自己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是一个爱情彻底战胜性欲的经典,爱到深处无形无色,这种无言的默契是对人的本能性欲的彻底否定,是爱的升华或最高境界。而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女儿却说:“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别管它多么美,多么动人,我可不愿意重复它!”①母女两代对爱情与性的理解已发生明显的分歧,女儿这代人不仅要爱情,还渴望婚姻的实质和形式,这是五四新文学妇女解放与启蒙话题的延续和发展。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是一个典型的欲望故事,小说以象征人的物欲和爱欲的“葵绿色的毛线衣”为中心意象,叙述了母女两代人的三个“爱情”故事,控诉了那个特定时代对人的原始本能的压抑。故事中欲望的实现方式是“压抑——满足——毁灭——更强烈的压抑(隐喻着更强烈的反抗)”,爱欲在母女两代三个故事的叙述中完成了一个循环,至荒妹又回到了原点。揭示了文化启蒙在中国农村任重而道远,作者还来不及讨论爱欲与肉欲的区别,二者只有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在作者看来,党的富民政策使农村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根本保障,于是,欲望叙事被成功地转换为对国家现行政策合法性的阐释和确证上。小说的深层结构模式——欲望叙事被政治主题所遮蔽,爱情的角落被“政治”发现,小说厚重的历史感和宿命感被政治话语悄然解构,爱情的角落或买卖婚姻的恶习并没有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而消失或改变,小说深厚的文化意蕴被淡化了。采用同样叙事策略的小说还有高晓声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何士光的《乡场上》等,只不过“爱情”被尊严、人性、人权等主题词所置换,温饱问题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金钥匙。可见,这些作品还没有摆脱文化启蒙的基本模式。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沿用了这种叙事策略,将欲望叙事隐藏在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表层结构之下,“食”、“性”这两种自然本能成为主体精神成长必须经历和跨越的因素。小说通过章永璘对食和性的深切体验和超越肯定了人的自然本能,证明人不仅是精神的存在,而且是生命的存在、物质的存在。叙述主体将他者对主体的本能欲望的压抑作为对主体的考验与磨砺,作为主体道德完善的必经之路,这是中国古代主体人格成长的传统模式,主人公对食物深入骨髓的痛彻渴求及其对异性的神秘向往与知识分子主体诞生及成长的人文化神话叙事具有了同一性,从而淡化了欲望叙事的主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性饥渴、性幻想、性吸引、性诱惑、性压抑、性无能等人类性行为的模式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刻画与描述,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不同情境下,人对性欲和爱情的不同态度和表达方式,涉及到文化在性行为中对人的压抑和制约,男女在性爱观念及行为上的个体差异,等等,从生理、心理、文化、审美等角度对性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探索,文本几乎成为性爱的百科全书,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虽有争议,但对小说中的欲望叙事,评论界和读者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作者采用了五四以来启蒙话语模式,将欲望叙事隐藏于政治叙事和成长主题之下;其二,审美化的欲望表现形式,如“性描写”唯美节制,致使接受主体在阅读体验中不自觉地接受了叙述主体的引导将欲望看作人性表达和主体精神成长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从而彰显了欲望的形而上意义、社会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人们对政治的狂热和干预现实的热情逐渐被世俗生活的情趣所取代。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等作家对乡土的诗意叙述和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等作家的市井通俗小说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情怀。市井通俗小说以生存于市井闾巷中的普通市民为对象,致力于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文化传承,通过对庸常、琐细的日常生活的叙述揭示他们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对万花筒般的市井胡同进行了独特的审美观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在文学中承认了世俗社会和认识人生的社会文化价值。邓友梅的“民俗小说”(如《烟壶》)对老北京晚清遗民人生世相的再现,刘心武的“四合院家族小说”(如《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等)展现了当代北京普通市民的生存现状和社会转型期人们复杂的心理流变;冯骥才的“津味儿”市井传奇(如《神鞭》《三寸金莲》等)用现代精神观照与反思天津卫底层的奇人异事,对传统文化中愚昧、迂腐、落后的一面进行了善意的嘲讽与批判,作家“想用小说寻找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元气、民族情感以及我们民族对待困难和战胜困难的独特方式”②;陆文夫的“小巷系列”(《小巷深处》《小贩世家》《美食家》《井》等)沿着苏州的古朴小巷,踏着石板铺就的街面,执著地探寻着人生的真谛,挖掘凡人小事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意义,揭露了左倾路线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危害,以及因袭守旧对现实人生和人物生存方式、思维模式的负面影响。
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等作家的市井通俗小说对市井人物的叙述和刻画是对主流文学中缺情少欲、只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所谓英雄人物的一种有意的疏离与反拨,旨在对断裂、缺失了的世俗生活和人间情怀的呼唤、肯定和超越,其创作动机是寻找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表达了作家对民间世俗伦理和生存方式的强烈的认同,在叙事风格上仍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文学精神依然是启蒙主义的。但市井社会更多地保留着民间社会古老纯朴的善与美和重信守义、重义轻利、处世中庸、随遇而安等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市井社会是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心理和民风民俗积淀最深厚的区域,凝聚着本地区、本民族特有的精神与性格,然而,市井社会并不能代表城市文明,更不能代表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未来,市井文化中落后、守旧、愚昧、琐屑等因素难以跟上现代化城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逐渐被现代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所淘汰。竞争意识和商品法则不仅冲击着传统的乡村文明和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对市井社会构成了新的、严峻的挑战。
于是,随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将文化启蒙的意义模式彻底放逐,消解了宏大叙事强加在主体身上的先验的理念原则和价值观念,他们关注普通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和需求,原生态地展现小人物琐碎、艰难、窘迫的生存挣扎和生命体验,客观真实地诉说着粗糙乏味、循环往复的世俗生活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所造成的磨损与伤害,还原了底层人生存的原始风貌,满足了作家们强烈的自我表现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