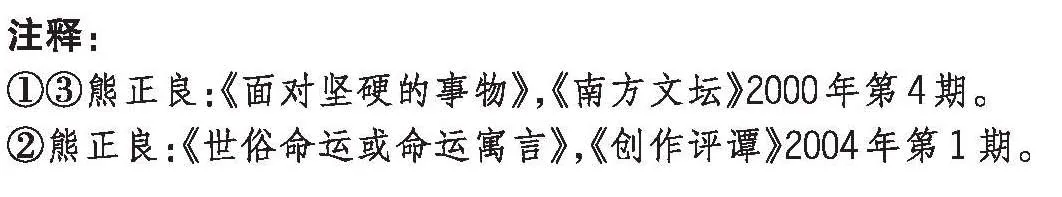熊正良的焦虑写作
江腊生
熊正良的创作来自于红土地。从“红色系列”中营造神秘而厚重的红色的梦,到执着地为“卑微的灵魂”寻找最简单的“祝福”,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诉说“别看我的脸”,到坚定地刺入人性的“残”,熊正良似乎总是充满焦虑地寻找着“红土地”般的坚硬与厚重。他没有倾诉历史的欲望,也没有代言底层的奢求,他的文本总是在一般人认为应该热的时候显得相当的冷,应该温软的地方,却令人触摸到一些生活的坚硬。或许这正是红土地上走出的汉子带出来的红土味儿。当我们感慨,红土地上的封闭与落后时,却无法回避他“红色系列”中的先锋气息与似乎来自天外的“匪风”;当我们慨叹文学失去了骨力的时候,却无法忽视他穿透生活硬度的执着与良知。或许作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考虑,他只是凭着红土地给他的神秘召唤,默默地逡巡于这块土地。
一、红土地上的宿命之梦
熊正良的“红色系列”包括中篇《无边红地》、《红河》、《乐声》、《红薯地》、《飘香松林》、《红蜘蛛》及长篇《闰年》等。他凭着对红土地的熟谙,以通灵之情构建了一个浑厚的带有红色野性的生存之梦。他侧重的不是地方风情与民俗的炫耀,而是通过逼真的写意与梦幻的灵动,构建了一个无极状态的生存之梦,书写了红土地上几千年来生命的延续、挣扎与困惑。梦总是一种现实与历史、自然与人性的胶着状态的体现。如果有人想从梦中导出现实的理性,那是一种枉然,同样,有人想从熊正良的“红色系列”中归纳出一些理念的东西,似乎也总会辞不达意。这些小说在自然与人性、男人与女人、暴力与爱情之间徘徊驻足,几者相互交融,呈现的是似梦非梦的混沌状态。他无意传达一种或诸种理念,也无意褒贬其中的一维,却在浓浓的神秘之色中表现淡淡的宿命之痕。
在熊正良的小说文本中,暴力/爱情这一对立模式似乎在刺探人性,又似乎在触摸历史,更好像在无意中淡然地倾诉他的宿命之梦。《红河》中,野狸子一方面是一个深受了旧文化规范浸染的女人,旧文化的心理沉积使她性格具有慑服于生活的种种重负,另一方面她充盈的性爱需求与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使她的性格又具有冲决文化束缚的心理走向。原始生命力的勃发,或者解构男权社会的女性主义等,这些来自异域的理论都无法真正贴近红土地,贴近红土地的生命。
野狸子作为一个充满热情与活力的青年女子,她有追求纯真爱情与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在男人的眼里她只是一个满足男人性欲望的生育机器。当她不幸生下“葡萄胎”之后,在男性社会的视界里就成了不吉利的祸害而被遗弃,她只能与丧失了性功能的莽长结合。面对如此厚重巨大的男权压力,野狸子的反抗只能是被动的,并且她的反抗最终也只能重新依附于男人而结束。当莽长再次想用刀自残时,野狸子抱着莽长,发誓不再去会油倌,但又痛不欲生的发出悲怆的呼叫:“就这么熬着活呀,莽长你也苦哇!”这里,我们无法单方面解读出原始生命力所具有的野性,它根本不具备横扫一切的冲决能力,仅仅是人生长河中生命之光的激变出来的闪亮瞬间,相比《红高粱》更具红土地上的厚重感。
自然界的生生死死在熊正良的笔下显得残酷、神秘而富有诗意,成为他构建红土地的宿命之梦的一个重要组成。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一些句子:“这两个小坟包像一对刚刚发育的鲜红玉润的乳房”(《红薯地》),“她的肚子在枯树一样的哭声中隆得像一座小山。这时候我便想起我娘的坟,我娘的坟也像一座小山”(《红河》)。坟包是死亡的象征,而乳房与怀孕的肚子则都意味着新生的鲜活有力的生命。二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叙述者的想象中却把二者并列组合在一起,直逼存在的本义,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人类存在的真谛。文远与文香的爱情被世俗偏见所扼杀,割破喉管而走向死亡之路时,毅然痛苦地解开牯牛鼻头那根滑腻腻的牛绳,让生命和魂灵都被牛绳羁绊住的牯牛获得自由。文香因为出身不好,被几个女子和一个男人以令人震惊的野蛮方式逼疯后,在她迷乱的精神世界里仍有充满自由精神的小鸟。她愤怒地扑向罩住鸟们的大筐篮,仍赤脚追着雪雾到处寻找被自己弄伤的鸟儿。她奔走的身影,是对古老落后的文化氛围的抗议,也是对文明生活的呼唤与向往。
在这红色如血的土地上,卑微的存在与生命的偏执并立,原始的欲望与神秘的意念共生,精神的麻木与生命本能的冲突同存,生命力的渲泄与生命本身的卑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透过这些宿命之梦,你能了解他们的生存与时间、死亡与命运的关系。熊正良将属于生命的整体性、丰富复杂性和神秘混沌性,融入无限地循环着、轮回着、重复着的红土地上的一切,力图书写出这片红土地的精髓与神韵。
二、梦里梦外的执着
对于熊正良来说,红土地上的宿命之梦,注定了要回到现实的坚硬基座上来。如果说,红土地上的宿命之梦,能够安置一个个卑微的个体,只是限于他们生命的存在,而他们渴望挣脱这一命运之网的精神一维却是毫不安分的执着追求,甚至达到一种偏执状态。野狸子与油倌的结合,是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召唤与执着,荞麦花与五义叔的相遇,同样是对两情相悦的执着,这些梦里的执着开始展露了作家的创作个性。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像脚下的红土地一样,显得坚硬而执着。同时,从熊正良的红土地之梦的营造中,已经按耐不住显现出他日后回到残酷、坚硬的社会现实中来的迹象。正如作家自己坦陈,“我曾经想把红土地上的故事当做一个梦来做。1986年春天登上鄱阳湖南岸,站在满目褐红的丘陵上,确实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受,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在这儿住过,一切似曾相识,于是就有了那么些缓慢的、梦幻般的故事。但这个梦没有做完,我发现我无法做下去了,现实离我太近,我无法混淆它们”。①熊正良无法逃离红土地上的宿命之网,他的一系列作品回到现实的大地之上,书写他们卑微的灵魂。这些卑微的人物、卑微的灵魂、卑琐的境地,已经不再有早年的原始野性的勃发,也没有红土地上的神秘之气,而是踏踏实实行走在坚硬的红土地上,执着地信守他们卑微的灵魂,甚至不无偏执地信守他们近乎本能的生存理念。
马福是一个卑微而又善良,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在生存的底线不断遭到侵犯后,他开始变得出乎意料的坚强。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他潜藏在心里的正义感终于像火山一样喷涌出来。当他得知因为儿媳遭老扁强奸,儿子才万不得已与老扁格斗后,他原谅了他的儿子。他也原谅了跟他儿子同居的按摩小姐李美芳,认她为自己的媳妇,而且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儿媳不再被侵犯。年迈的马福不顾一切跟年轻的老扁格斗,最终靠自扎一刀这种庄严的力量吓倒了嚣张的老扁,马福的行为让我们重新看到小人物身上所跃动着的人性的光辉。
如果说,马福的执着为的是捍卫做人的尊严,那么在《谁在为我们祝福》的徐梅等人则是为了做人的信念而生。生活的无奈,让徐梅一直生活在历史的因袭和现实的错位相互编织的网结中。为了达到返城目的而与刘义结婚,在与刘义闹离婚后却又被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儿女们碎断心肠。她是一个跋涉岁月的负重者、内伤外伤老伤新伤皆有的伤痛者、无助的挣扎者、绝望的反抗者。当得知女儿做了鸡之后,徐梅拖着受伤的身体,到处刷寻人启事,甚至不顾一切铤而走险,拿刀刺杀拉皮条的李红卫,为的是寻回自己的女儿。“寻女”这一事件,书写了一个妇人的强韧与自身的可笑并立、艰辛的挣扎与无谓的偏执共生、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与生命本身的卑微融为一体的形象。在“笑贫不笑娼”的今天,徐梅这样的人本能地恪守一点为人的根本,正是作家努力在世俗的生存图景中寻找一个栖居人性的人生之梦。
写作到了这里,作家似乎更多地逼视生存的残酷、无奈,以及其中依然固守的一份执着。“我骨子里还是对个体的生命感受、对我们眼下的生活或我们在生活中的种种际遇感兴趣,一些在世俗庸常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一些突如其来的、我们无法预料无从把握的东西,还有欲望,性格,包括某一时的情绪之类的因素,外部的或内部的因素,等等,怎样勾结编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人的所谓命运,在一条被这样构成的命运轨迹里,生命或生活会呈现一种什么状态,是不是更易于接近它的本质,是否具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义。”②
三、现实之硬与叙述之冷
关于“底层生活”的叙事一直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重要的一脉。在传统左翼文学的视野中,“底层”被赋予了“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性内涵。因此,在任何时代,无论是被允许还是被禁止,“底层叙事”总是首先在“道德”上占据话语高地。近年来,“底层叙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具有“思想时尚”意味的热门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生活”的讲述往往借助于浓厚的情绪化书写来表达作家的叙事态度、道德立场等,却无法真正探入命运深处,触摸到一些坚硬的地方。
在熊正良看来,梦是柔软的,现实是坚硬的,甚至是尖锐的。“一些充满个人审美趣味的意象和一种越来越坚硬的事物常常呈现出分离状态,而且一不留神便相互背离”。③因此,他无意制造或追随思想的时尚,却注重将探头伸入生活的内在,触摸到生活中一处处坚硬的内核。《我们卑微的灵魂》中的马福、刘成等一干老年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敢于对抗来自社会一般人无可奈何的流氓老扁,用自己的身体、鲜血来保护自己的儿子、儿媳,护犊情深只是其一,重要的是捍卫最底层民众的尊严。他们的执着,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自救行动,直接面对的是现实中最为坚硬的一面。其中的慷慨、坚定将他们的卑微牵引至一个社会弥足珍贵的品质。各种苦难与沉重,甚至有些愚昧,激发的是他们心中原始的生命跃动。熊正良努力要做到的正是揭开这些文化与现实的冲突,将其中的坚硬之核抖落出来。
从叙述上看,纵观熊正良的小说创作,毫无疑问表现出一种趋势:从红土地上构建一种神秘而不无幻彩的宿命之梦,到直逼生活的坚硬内核的艰难挺进。作家的写作越是努力抵达生存的坚硬之处,小说文本越是表现出一种“冷”。这种冷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来自后现代式的冷漠叙述,也并非是外表上作出来的一种“酷”,而是弥漫在文本中,甚至成为小说的叙述主人公。
随后,熊正良的文本叙述逐渐皈依于一种叙事的平淡,一切都不动声色,让小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叙事的技巧让位于事情的真实展示。《我们卑微的灵魂》中,作家只是冷冷地站在一边,看着马福等一帮人,拿着自己的身体、性命来捍卫卑微的灵魂。他们捍卫的是作为一个最为底层人物的存在,他们面对来自社会的强势力量,开展了自救,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的呐喊式的情感流露,只是诉说着他们无言的抗争。
《残》选取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后艰难返城的特定历史时段,却没有像当年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般血泪历程的哭诉和历史进程的反思,而是通过李玖妍的短暂的生命图景,折射出生活的一些坚硬之处。透过残障的李文兵叙述视角,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态的、扭曲的生活形态。它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的底色和氛围更多一些灰暗和阴冷,现实显得更为严酷坚硬,扭曲了的现实关系使得人的生活变形,情感变形,人际关系变形,乃至使整个时代的人性变得残疾。小说以李文兵的残疾开始,又以李文兵的希望结束。用他举重若轻的视角,书写了李玖妍的一生,牵引出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一个残疾的群体精神景观,更潜藏了一个人生去残的希望。众人以李玖妍的处女膜为谈资,将其身体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不断加以践踏,并在践踏中得到无尽的快感。李玖妍不断写大字报来为自己申诉,然众人仅仅将其视为生活的笑料,视为心理和精神的残疾。她被暴尸野外而无人收尸,自己的父母和姐妹却避之不及。作者意在通过一个残疾人的叙述视角,深刻地指出:比肢体的残疾可怕的是心灵上的残疾,比心灵的残疾更可怕的,则是那个年代群体性的精神残疾。透过这种群体的精神残疾,李玖妍作为一个异类,却赢得了憾人心魄的生命力量。
就像从冰窟里拿出的寒冰一样,极冷总是会不断冒出蒸腾之气,这是极冷之后蕴藏的极热的一种体现。叙述的冷,并非意味着熊正良的小说失去了内中的能力,而是能力以另外一种冷的方式释放出来。当我们阅读《我们卑微的灵魂》,感受作家冷冷地叙述马福等一干人捍卫他们的存在,捍卫他们的灵魂,却无法不被其叙述之冷下面的人性关怀所惊叹。当我们感受作家以近乎嘲讽的方式书写徐梅寻女的故事,小说最后BP机上出现的“我为你祝福”呈现的是一种冰窖之下的热流,作家还是无法按耐住他极力铺陈的冷,转而借一个女孩的口吻传达出对徐梅对所有人的温热的祝福。小说《残》中,苗幸福是一个残疾,却奏出人性世界的最强音。他从乡村最根本的伦理意识出发,用自己的爱唤醒了李玖妍的精神,并在残酷恐怖的环境下,为暴尸野外的李玖妍收尸。他的对李玖妍的关爱,正是一个来自乡村话语的弱者对弱者的关爱,这是乡村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也是人性中温暖而又坚定的一面。
作家往往通过一些残疾人、未成年人的视角叙写生活的坚硬形态,意义不在于写出这种底层生活的贫穷苦难,写出所谓“弱势群体”的艰难挣扎,以唤起人们的同情怜悯。我们透过作品中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作家对这种生活形态冷静的、甚至是冷峻的审视与描绘。他让我们看到,那种艰难沉重、无奈而又无助的生存现实,是如何使人陷入冷漠麻木;那种缺少阳光的生活形态及其扭曲了的现实关系,是如何吞噬良知使人性异化,使人的心灵情感滋生怨恨仇视的毒菌,以至我们在读到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描写时,会禁不住心生恐惧与冷颤。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近年越来越着眼于现实生存的逼真叙述,却忽略早年小说中那种如史如梦的诗意飞升,让人感受力量有余却诗意不足。小说逐渐滑行在一个个流行事件或新闻报道上,虽然经过作家有意的叙述加工,但仍感觉太着眼于现实的坚硬与残酷,难免带上一种难以自耐的焦虑情绪,弥散在文本当中,文本的叙述节奏显得过于峻急,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想象的空间。如果作家能够将早年的梦境般诗意的营造与近年现实生存的近距离观照融合起来,让诗意的宿命之梦穿透现实生存的坚硬,那正是我们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