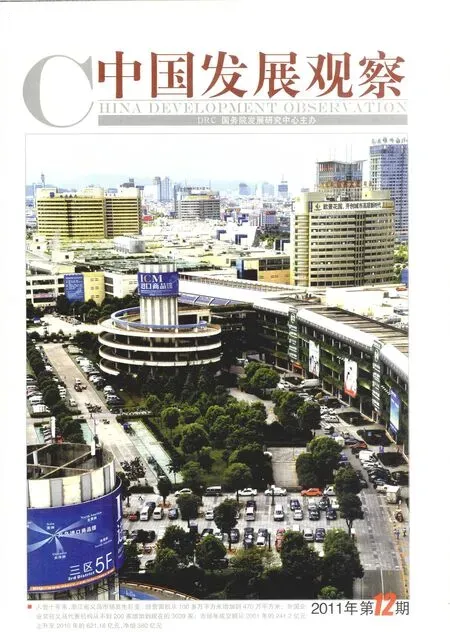在复杂的环境中决策——读《抉择时刻》
◎ 丁元竹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真正的决策共同体一定是一个密切合作的群体
在这里我没有使用“智库”这个概念,因为“智库”只是决策共同体的一部分,从布什的叙述中,我看到决策的制定需要由多方面组成的决策共同体。
近年来,热衷预测中国未来的人越来越多。其实,20世纪末这种预测也不少。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使得中国处在一个新的位置之上。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其在国际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对中国刮目相看,大唱赞歌;另一方面,中国环境资源人口的巨大压力、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性、地区城乡和群体之间的巨大社会差距,以及社会矛盾和问题凸现,使得一些人唱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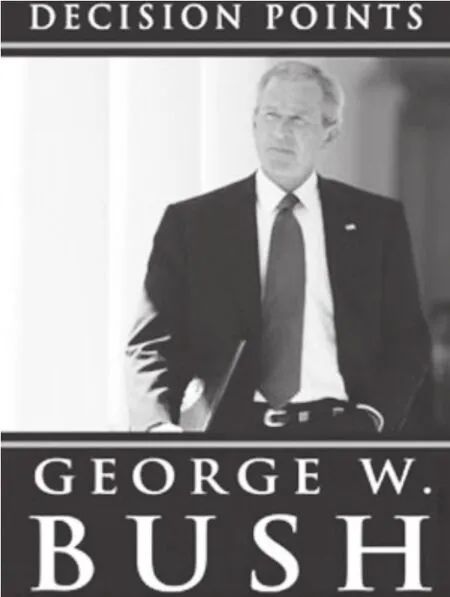
这些都不会影响中国正在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在走向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上逐步知道了“中国的特色”,这个特色形成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政治、时代等特征,从而也就知道了“是什么”和“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尽管如此,中国依然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要总结自己发展的经验,还要不断创新。中国地区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鉴。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探索永无止境,创新也永无止境。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创新已经摆在了中国决策共同体面前。
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决策共同体不仅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历史视野。1929年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在经过短暂恢复之后,不到一年又陷入了低潮,反反复复。2009年底和2010年初,有人预料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复苏就在眼前。2011年以来,随着美国国债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全球经济又进入变动不定之中。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政策不能没有历史感。决策只有建立在历史基础上,才会厚重。通过有全局性的历史视野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根据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性特征来制定政策,这一点在当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重要。中国决不能因为自己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而固步自封,中国的创新必须借鉴各国的经验与教训,必须吸收各国专家参与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去。更大包容性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选择。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对于在一些地区是问题的问题,在另外一些地区可能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有现成的答案。寻找解决问题的方略是复杂和艰难的。“描绘天堂比指明通往天堂的路容易得多,只描绘了天堂而没有考虑指明道路的人其实没有做出任何有益的事情”。((美)彼特·伯恩斯坦:《繁荣的代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学术研究之要义,“怎么办”是智库研究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二者分野于此。不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很难提出解决问题之道的,但知道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也未必能够道出“怎么办”。“怎么办”涉及对政策的把握和理解,还需要对现代政策机制熟悉。智库可以自己去探索“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可以通过学者们的学术研究直接获得答案。现代社会中,最好的方式是合作。真正的智库一定是一个密切合作的群体。
中国宏观决策的困难来自其地域的辽阔、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发展的不平衡。在谈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决策时,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入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第8页)他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说这番话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治理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体制,而这种中央集权体制由于不能对基层实行精细化的管治,在基层就衍生出了伦理制度,也就是高层的完善集权体制和基层完善的伦理规范,也就造成了历史学家吴晗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谓的以“皇权与绅权”为主线的社会治理结构。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也在不断完善,从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绝对比例,到目前的非公经济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和就业人数达到75%,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数万家社会组织,到目前拥有数百万家社会组织,表明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都是决策必须考虑的因素。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中国太大,发展极其不平衡,在一些地方是问题的问题,在另外一些地方却不是问题,或者说已经解决了,也有经验。别的地区可以借鉴,学者可以总结,提炼出理论和政策,供别的地区学习和参考,也可以提升为新的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国际经验的启迪意义。针对中国面临的问题,看看国际上主要国家在这方面如何做的是会有启发的。国际经验可以提供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思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对它们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对我国现阶段的一些问题的思路也就比较开阔了。当然,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一定不要离开被研究国家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便是考虑了历史发展阶段,也还要考虑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和政策。很多研究离开了历史的阶段性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会混淆视听。另外,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研究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都是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也有不成功的范例。要摆脱那种“凡是外国的都是先进或好的”理念。同样,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全盘否定国际经验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创新的任务已经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这是一项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一些全局性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是自身发展绕不过去的,也是国际发展中需要解决的,诸如金融体制、税收结构、收入分配,等等。中国一旦走在世界前列,领跑世界,就必须提高对失败的容忍度,在这点上,需要解放思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就是要从传统的简单模仿思维路径中走出来,去学习驾驭新形势。
发展是沿着多个路径进行的,有的是在理论创新基础上,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取得突破。有的是通过实践实现自身的创新。中国当前这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许多是前沿性的,没有理论和经验可循,实务者自己在摸索,研究者要跟进,否则就会落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各地实践基础上逐步成熟的。眼下各地正在进行的社会性试验,诸如社区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会有一个巨大的突破,就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样。
最后还是想说说智库问题。尽管人们对于智库的作用还心存疑虑,中国还是需要发展自己的决策咨询机构——智库。在国际上,智库(think tank)又叫做政策研究机构,它主持、倡导一些领域的研究,包括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经济、科学或技术问题,产业和商业政策,或军事咨询。在加拿大和美国,许多智库属于非营利组织,有免税地位。也有一些智库由政府、组织或企业资助,它们从咨询或项目研究中获得收入。不同的社会中,智库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截止到2009年,世界上有5465家智库,其中1777家在美国,355家在华盛顿。全球化导致智库跨越国界,在世界各地布点并开展研究。当前也许中国比任何时候需要更多的智库参与决策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