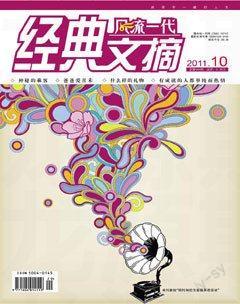因为白骆驼知道
刘继荣
我到鸣沙山时,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游人渐散,阳光渐淡,只余静默的山与山的影子。
牵骆驼的是个清瘦的男孩:月白衬衫,脸黝黑,眼神羞涩,正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像一株青叶青穗的高粱。
看看我的票,他眼睛里笑意一闪,指给我看那匹伏着的白骆驼。第一眼,我便爱上了这秀气的小家伙。长长的睫毛,双眼皮,大眼睛,如贪玩的小仙子,目光里有隐隐的淘气。
一时间,我竟不舍得骑到它背上。忽然,后面的小女孩扑过来,欢天喜地地抱住了白骆驼的脖子,再也不肯松手。女孩的妈妈,牵骆驼的男孩,都笑了。我也笑,谁忍心同玲兰这样皎洁的孩子争呢?
于是,我换乘了女孩的黄骆驼。它高大健壮,温驯安静,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我几乎不用握鞍上的扶手。坐在它背上,听着清脆的驼铃,心如静沙般稳妥。难怪男孩会让它做领队呢。
而那个小白骆驼,驮着神气的玲兰公主,紧紧贴在我身后。它果然活泼,一会儿也不肯安分下来。再加上小姑娘手舞足蹈地喊着“驾!驾!”,它越发心急,动不动就想越过我去。
好几次,它将嘴伸到了我的脚边,好奇地嗅啊嗅的。我的登山鞋套是绿色的,莫非小家伙饿了,错认为那是一蓬可口的嫩草吗?
玲兰公主心花怒放,笑得前仰后合。她脆生生叫道:骆驼哥哥,为什么不让小白当排头呢?男孩脸红了,紧张地嘱咐她坐好。他认真地解释道:小白第一天上路,路不熟,又淘气……玲兰公主抗议了,说小白最聪明,可以当排头,你看,你再说它就要生气了!
适逢一段下坡路,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大漠的落日下,那吹箫的人是谁……立刻有人接上来:荒凉的古堡中,谁在反弹着琵琶……顿时,驼队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将一首本是荒凉婉转的歌,吼得欢天喜地。后面鼻息咻咻的小白更加兴奋起来。
前方有人大叫:嘿嘿,看过来了,看过来了!摆个最酷的姿势,照相啦!
我笑了,冲着拿相机的人扭头、扮鬼脸、两臂作飞天状。牵骆驼的男孩急了,高声叫大家不要把两只手都松开。
忽然,骆驼的身子猛地倾斜了一下。我赶紧抓牢扶手,却听得后面传来惊叫。一回头,玲兰公主连人带骆驼都摔倒在沙梁上。男孩立即冲上去,扶起小女孩和骆驼。
女孩妈妈挥舞着手臂尖声叫着,男孩抱着哭泣的小玲兰,惊惶得不知所措。忽然,那个照相的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你家小姑娘又摇又晃,把骆驼弄倒了!”妈妈疑惑地看着女儿,小女孩满脸的泪,抽噎着点头。
那照相的越发理直气壮。看看!你姑娘自己都承认了,不能赖骆驼!女孩的妈妈忙着给老公打电话,男孩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抱过去,让她们母女合乘一匹。小白骆驼不再撒欢,低着头,一步一步,怯生生地跟在最后边。
驼队刚到月牙泉,一个面色铁青的中年男人冲过来,对男孩叫道:我女儿究竟是怎么摔倒的?那照相的赶紧跑过来,比划着解说事情的原委,小女孩也承认是自己的错。父亲见女儿无碍,脸色慢慢好转。
那清瘦男孩静默半晌,突然开口:是小白调皮,不好好走,陷到旁边的沙窝里了。父亲的脸倏地一变,逼视着那个照相的。
照相的怒道:你走在前面,难道脚后跟长了眼?男孩争辩道:我刚好回头,我一直担心小白会出事。
照相的忽然发怒,操起沙窝里的一根棍子,疯了似的去打白骆驼。白骆驼静静地垂着头,一动不动,仿佛也知道自己犯了错。小女孩惊叫,男孩扑过来,挡在骆驼前面,硬生生地挨了一棍。
这时,景点负责人也来了,要大家一起去办公室商谈。我站在山顶,俯视着清澈的月牙泉,心里却一直牵挂着那男孩,还有那匹惹人怜爱的小白骆驼。
下山时已是黄昏,凉风拂面,炊烟袅袅。我忽然看见男孩牵着小白,走在空旷的沙滩上。我问他事情是怎么处理的,他说陪小女孩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受伤,他们一家回宾馆了。
只是,他以后不能来这里牵骆驼了;还有,小白也不能来了。
我又问,那个照相的怎么那么凶?他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那是我哥,他一直在替我攒学费,最怕我和小白被景点辞掉。本想等小白长大一些再带它来的,可哥心急,说我明年就要上大学了,等钱用。
他爱怜地抚摸着白骆驼,像抚摸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小白细长的腿,轻轻战栗着,长长的睫毛垂下来,眼睛如清澈的月牙泉。
我忍不住问:既然那女孩都认了,你为什么还一定要说是小白的错?
风愈发的凉,沙粒私语。男孩忽然改用本地方言,轻声说:小白从出生起就跟着我,它虽不会说话,可心里什么都清楚。如果我说谎,它会难过的。
城市的霓虹灯已开始闪烁,那一人一驼,拖着长长的影子,踏着沙,慢慢向炊烟升起的月牙村走。
我相信,那匹白骆驼一定听懂了男孩的话。
(倪志君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心灵的质地》)
——沙窝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