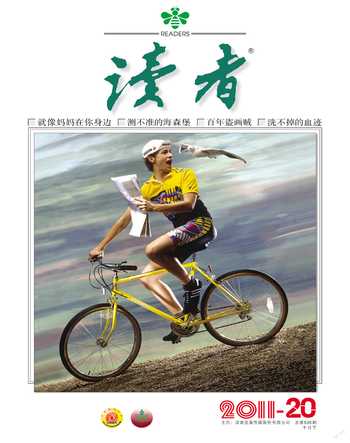父与子
李御
2007年6月7日,是儿子参加高考的第一天,早晨8点前,我按照事前约定,送儿子去考场。以前类似比较重要的考试与活动,都是他妈妈送他,但面对人生第一次大考,他妈妈似乎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
当我与儿子到达考场时,大门前已是黑压压一片。儿子似乎还是一如既往的轻松,我不敢多说什么,只是说:“儿子,好样的!爸爸相信你。”儿子回答我的还是他常说的那句话:“不就是一次考试嘛!”我轻信了儿子的那份轻松。
事后我才知道,儿子临近高考的轻松是快要绷断了的弦所奏出的无奈乐章。他平静地对我说:“爸爸,你上班去吧。”我过分相信了自己的感觉,说了声“小伙子,加油”就离开了考场。
我从未企望儿子成龙成凤,儿子多年来的考试成绩还是让我放心的。在此之前,市、区、学校进行了多次模拟考试,他每次的成绩都达到了一本线。
儿子进了高考考场,我也回到了办公室。刚刚坐定,我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至今也说不清。莫名的恐慌、担忧毫无来由地向我袭来。这是否就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我快步下楼,走到一楼大厅,面向东西南北祈求保佑。这在我的一生当中是不曾有过的事情,但我的直觉引导我去做这样的祈求。
我正准备离开大厅上楼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我预感到了什么。手机里传来儿子班主任刘老师焦急的声音,他告诉我,儿子身体非常不舒服。他接到了考场老师的电话,要家长火速赶到考场。
在考场的红线外,我见到了坐出租车火速赶来已是满头大汗的刘老师。他是从另一个考场赶来的。他同我说了几句话,就往里冲。我哀求道:“刘老师,请你给我儿子捎句话,要他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坚持。”
难挨的一个小时。当我打通刘老师手机时,他正在休息室陪着儿子。事后我才知道,儿子当时汗如雨下,身体严重不适。监考老师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但无济于事。他需要休息,因武汉太热,连日吹空调让他感冒了,但他一直硬撑着。当他来到休息室之后,已经失去了再回考场的资格,这就是中国的高考。
刘老师陪他熬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两个多小时。当考场大门洞开,儿子满脸疲惫满脸泪水扑向我时,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爸爸,我12年的心血白费了!”然后放声大哭。
这句话犹如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直至今日,也无法拔除。
也就是在那一刻,做父亲的惶惑与无助,让我刻骨铭心。
做了20多年的记者,经历过难以历数的人和事,但这样超乎意料的事降临的时候,我确实难以自持。第一科的考试,儿子在考场只待了不到20分钟,即使后面所有科目的考试都能如愿,又能怎样?我不敢往下想。
儿子是小男人,我毕竟是大男人。我紧紧抱住儿子,一刻钟后,我说:“儿子,如果是个男子汉,你中午还要好好吃饭,把剩下的科目考好。即使无用,你也对得起你自己。”
儿子最终还是听了我的话。吃了饭,服了感冒药之后,他参加了后几科的考试。每一科都考得比较出色,但他笑不出来,毕竟第一科的考试几乎等于零,最终成绩单上,语文仅得了不到20分,而这一科是他的强项。
2007年6月7日,儿子参加高考的第一天,也是我生命中最难支撑的一天。
买补品,上培训班,找心理医生,给予一些其他的特殊服务,这些比较普遍的为高考生所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不存在。我始终相信儿子所说的那句话:“不就是一次考试嘛。”
事后反省,我对孩子的了解还是太少,他的轻松是为了宽慰父母。而他的内心,承受了他自身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直到6月6日晚上,我才有了些微的觉察。儿子临近午夜12点还不能入睡。我很着急,我知道,没有充足的睡眠,第二天人的脑力是很难适应高强度的智力考试的。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父亲,我犯下了一生中难以饶恕的罪过,我将我常服的安眠药悄悄地放了一片在儿子的水杯中。安眠药溶解后,儿子喝过,安静地睡了。如果我将儿子没有喝完的杯中水倒掉,也许我不会负疚一生,可恨的是,我自己也睡过去了。等到早晨醒来,儿子已经在小桌前做最后的温习,杯中的水也已喝光。到了考场,需要神经高度兴奋,而安眠药的作用,感冒的作用,内心巨大压力的作用,足以击倒任何一个坚强的身躯。他大汗淋漓,所以只能离开考场。这是做父亲的心中永远的痛。
直到今天,儿子对此事尚不知晓。我太轻率,我太不顾孩子的承受能力。很多好朋友听我诉说后,都骂我、埋怨我。但儿子至今不知,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冯遥摘自《散文》2011年第8期)
——您的下一个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