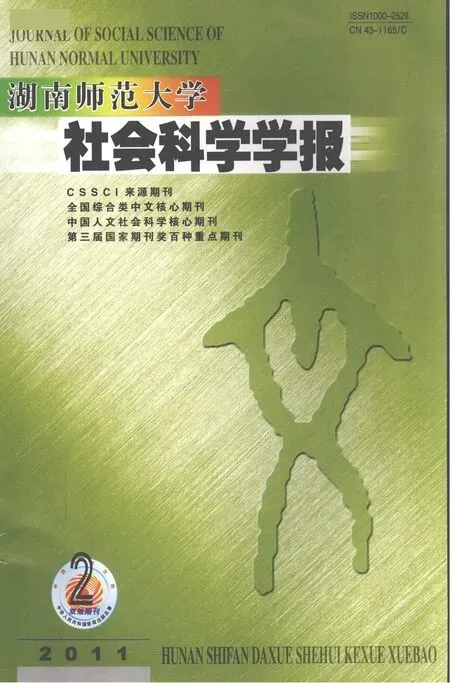《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的“人格面具”主题探析
陈 盛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的“人格面具”主题探析
陈 盛1,2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罗在自传体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细诉了她艰难的青少年成长历程。借用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人格面具”和“自性化”概念,并结合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霍尼、马斯洛等的相关理论,对该作品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玛雅的成长历程是一个逐步摘下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转而寻求能适应社会生存、保持自尊与个性、实现自我理想的有效“人格面具”,并达成个体“自性化”的过程。该书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人格面具;自性化;归属感;认同感
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1928-)①是美国当代极富盛名的黑人女诗人、人权活动家、畅销书作家,也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之一。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1969) 是玛雅·安吉罗撰写的6部自传体小说中的第1部,是流传最广、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作品。1994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被美国青少年图书服务协会(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列入100部最佳青少年图书;1995年,被美国图书协会下属机构——知识自由办公室(Offic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评为美国最具挑战性的作品;1997年,连续 153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P30)。(Introduction xi)这部作品记述了玛雅幼年、童年、青少年时期(1931-1947)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段经历对其日后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主要采用瑞士分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人格面具”和“自性化”概念,同时运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卡伦·霍尼(Karen Horney)、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Maslow)等的人格心理学相关理论,对该书展开分析,认为玛雅的成长经历是逐步认识伪装性“人格面具”的消极性,并最终摒弃它,进而寻求适应社会生存、保持自我尊严、实现自我理想的有效“人格面具”,完成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整合,达成“自性化”的过程。
荣格认为,“人格面具”指一个人按他人期待的方式行事,即角色扮演,是我们的社会角色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人一味屈从于社会性角色的要求,那么,自我就会被“人格面具”主宰,与真实的自我相异化,终将导致心理冲突、人际关系紧张等后果。反之,如果能协调好“人格面具”和个体其他方面以及社会环境的关系,个人就能与社会和谐相处,还能保持发展个性特征,并实现自我。[2](P163-168)荣格这一理论在玛雅3岁到16岁的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荣格的“自性化”概念是指人格的进化和整合过程,“自性化”进程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独立、整合和实现自我的个体。荣格认为:“自性化的目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个体剥去人格面具的虚伪外部;另一方面,消除原始意象的暗示性影响。”[3](P432)显然,“自性化”的进程,首先是对“人格面具”的扬弃,目的在于使个体适应环境,其次,是发展个人的内部独特性格,使人格健全发展。玛雅青少年时期人格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迷惘、困惑、自我意识的唤醒、自我肯定等阶段契合了这一“自性化”过程。
一、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的形成与更替
玛雅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的形成阶段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美国黑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虽然1865年的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可是种族歧视并未随着奴隶制的废除一并消失,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同一城市里,黑人、白人要分居在不同的区域,学校、教堂、餐饮等公共场所和设施也必须分开使用。种族迫害、种族冲突的情况仍旧严峻②。在玛雅童年的居住地——南部小镇斯丹普,种族隔离现象尤为严重,就像“一道光影打在黑人社区与白色世界之间”[4](P48),以至“大多数黑人孩子根本不知道白人长得什么样”[4](P24)。在种族歧视大环境压迫下,大多数黑人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压抑感和自卑感,这使他们有意无意地戴上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以被动的方式求得生存。同样,为了掩盖自卑等消极情感,玛雅在幼年和少年时期也戴上了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幼年的她常常以幻想型伪装性“人格面具”示人,少年时期的她则习惯以疏离型伪装性“人格面具”示人,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冲突,对社会产生了无所适从之感。
长辈(如父母)未实现愿望的心理延续,是幼年玛雅戴上幻想型伪装性“人格面具”的原因之一。幼年的玛雅拥有一个重复而单一的“白人梦”,就是要“像一个可爱的白种小姑娘一样”[4](P2)。幻想,又称“白日梦”,弗洛伊德认为,“白日梦”的梦境,是一种通过幻觉来弥补现实生活中不足的一种表现,幻想者能在梦境中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5](P41)。身为美国非洲裔黑人的小玛雅,一出世就感觉到她属于一个低于白人的社会阶层。荣格指出,幼童,“他们还没有独立的个性,这时候子女的精神完全反映着父母的精神。因此,父母的精神失调,也必然要反映到子女的心理中来”[6](P53)。“儿童的梦与其说是反映儿童自己的心理,不如说是反映了他们父母的心理。”[6](P53)玛雅的长辈们,有的模仿白人的行为举止,希望通过与白人相似的外在表现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则将自己的黑人身份和白人划分得清清楚楚,只谋求在黑人的特定领域中获得生存,他们要么憎恨与生俱来的黑人身份,要么无奈地接受它。黑人身份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玛雅那充满自卑感的“白人梦”的确是父母乃至祖辈心理的一种反映。幼小的玛雅无意识地躲在一张幻想型伪装性“人格面具”后面,试图在幻想中改变黑人身份,以赢得尊重与自我心理满足。
玛雅幻想型伪装性“人格面具”形成的另一原因来自她对自我身份、自我归属的极度困惑。童年的玛雅不断在“白人梦”中获得满足与自尊,但这梦中高贵的“白人小姑娘”,却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我:“一个体型奇大的黑女孩,黑头发毛烘烘的,脚板又宽,牙齿的空洞都能塞得下一枝二号铅笔。”[4](P2)另一方面,离异的父母将3岁的玛雅送到斯丹普奶奶家寄养。玛雅失去父母的庇护,对陌生环境倍感恐惧,她本能地将奶奶称作“大妈”,表现出她对失去父母、家庭的恐慌和对自我归属的困惑。身份的不确定、自我归属的缺失,使幼小的她集幻想、健忘、羞怯和屈辱于一身,因总是在教堂里背不出简单的颂歌词而成为众人的笑柄。内心冲突甚至导致了生理失控——便溺,这种失控使无法宣泄的心理冲突转化为生理排泄,暂时释放了心中淤积的苦楚[4](P3)。
接下来的一起让她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创伤的突发事件,则影响了玛雅的整个少年时代,她不得不躲在一张疏离型伪装性“人格面具”的后面,用沉默来对抗几乎将她毁灭的世界。
玛雅8岁时,遭其母亲的男朋友弗里曼强奸,出庭作证无果,舅舅们打死了强奸犯。一连串恶性事件,使玛雅几近崩溃。不堪重负的她沉默了,开始疏离外部世界,外在的感观世界,被她无意识地拒绝,也令她感到困惑和焦虑:“声音传到我这里就沉闷乏味了……颜色也不再逼真……我记不住人的名字,于是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精神健全”[4](P95)。出于本能,玛雅小心地包裹着这揪心的记忆,生怕一朝梦醒,周遭已满是流言蜚语。这种心理折磨日益严重,迫使她离开了事发地,返回斯丹普(奶奶家),斯丹普就像一枚能为玛雅提供保护的蚕茧,于是“朝着这个蚕茧,我爬了进去”[4](P92)。
霍尼将这种疏离社会、离群索居、回避他人的需求,归于心理的基本冲突。她认为,这一类人在内心有一种与他人保持感情距离的需要,要保守个人的隐私,任何对他个人生活的提问,都令他十分不安,他总是想把自己包藏起来[7](P44)。
对人群与环境的疏离,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扼杀灵性,导致绝望,另一种则是唤起自我意识,玛雅的情况正是属于后者。霍尼指出:“在一个充满虚伪、狡诈、妒忌、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弱者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诚实而遭殃,与他人保持距离则有益于维护自己的品质。”“自我孤立,倒可以通向内心的安宁和沉静”,“假如患者在他所划定的‘魔圈’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窒息掉自己的感情生活,那么,他的自我孤立,还会使他产生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感情。”[7](P54)马斯洛也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需要离群独处,才得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对象上,同时也能沉思[8](P188)。值得庆幸的是,玛雅的离群索居、自我封闭,并未遏制她的精神世界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在内外因合力推动下,她的自我意识反而萌发了。
在孤独、困惑中挣扎的玛雅自我意识的激活与唤醒,离不开弗莱沃夫人的指导。及时出现的弗莱沃夫人,充当了玛雅的人生指导教师。这位令白人也刮目相看的黑人女性“给我抛来了第一条救生索”[4](P96),上了“人生第一课”[4](P102)。凭借睿智的方法,弗莱沃夫人不漏痕迹地调整了玛雅某些不和谐心理因素,让玛雅第一次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个体感到骄傲。在她的引导下,玛雅自我意识萌生,开始关注自我,并有了完善自我的愿望。
二、摒弃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达成个体“自性化”
马斯洛强调,一个能自我实现的人,首先必须是有归属感的人。他认为,人类的归属感是一种社会感情,觉得自己“属于某个集体,感到自己与集体的目标和胜利联系在一起,感到被人承认,有了一个位置。”[8](P84)玛雅的成长过程也恰恰是一个寻找归属感的过程。
玛雅两段亲身经历直接导致了其归属感的产生:第一段经历是废旧车场的生活。玛雅从父亲处出走,与一群流浪儿在废旧车场生活了一个月,这群孩子肤色不同,人种不同,包括黑人、白人和墨西哥人。玛雅第一次融入一个多种族的环境,体验到了四海一家的人类亲情,萌生了人类是一个整体、并无种族之分的观念。流浪儿之间平等的人际交往方式彻底改变了玛雅的思维,她的自我感觉空前美好,连“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了”[4](P265)。第二段经历是在旧金山“哈莱姆”区(黑人居住区)的生活。二战期间,日本人在美国遭到驱逐,旧金山的日本人居住地很快入住了大量的黑人居民,成了“哈莱姆”区。“集体迁移的气氛,战时生活的变动不居,新来者的笨拙拘谨,所有这些,消除了我自己那种没有归属的感觉。”[4](P221)玛雅已不再将自己狭隘地划分在黑人群体中,而是将自己归置于旧金山人、美国人、全人类。
玛雅在获得归属感的同时,也获取了社会认同感。弗罗伊德把“认同”看作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9](P12)玛雅来到旧金山后,很快就“认同了那个时代和城市本身”[4](P221)。玛雅的自我期待与社会期待开始趋于一致,她开始设计未来的自我形象,这个形象不再是幼年“白人梦”的延续,而是对自我气质、特征的一种定位,跨越了肤色的障碍:“这个城市成了我理想中的成年人形象:友善而不过度热情,冷静而不淡漠和疏远,高贵而不僵硬可厌。”[4](P221)
在自我意识产生和拥有归属感、社会认同感之后,玛雅开始为取得人格尊严而努力。通过长时间观察、比较、鉴别,玛雅发现自己的亲人都戴着被动、消极、委曲求全的伪装性“人格面具”。如父亲大贝利的高档丝织衣服、一尘不染的“德索托”汽车、纯正的英语、“哦儿”的口头禅、“装模作样”的举止,都是他虚荣型伪装性“人格面具”的具体表现,而这一切不过是掩饰自卑的种种小伎俩。威利叔叔,瘸腿、脸部不对称、口吃,工作和生活范围仅限于大妈的小店。可是,在光顾小店的白人夫妇面前,威利藏起拐杖,站直身体,尽力用流利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为了照顾母亲、侄女和侄儿,他至今没有成家,他刻意塑造出健康、有责任感的自我形象,让他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可是,玛雅深刻地认识到,大贝利和威利不但失去了自我,而且并未获得真正的人格尊严,仅仅是用虚荣掩饰了自卑,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徒劳无益的行为。如果说虚荣型伪装性“人格面具”不能带来人格尊严,那么究竟怎样的面具能帮助她获取人格尊严呢?玛雅把目光投向了两位面戴现实主义型伪装性“人格面具”的女性,奶奶(即书中的大妈)和母亲薇薇安。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奶奶,具有忍耐、顺从的性格。当一群白人女孩来到她的小店,大呼小叫,学奶奶噘嘴的模样,一名女孩甚至在她面前故意露出阴部,侮辱她,而她仍在轻轻地哼唱。不过,玛雅却发现此刻奶奶的“漆盖却像是锁住了一般,似乎再也无法弯曲。”[4](P30)用表面的轻松来掩饰内心的屈辱,这就是奶奶在种族歧视的大环境下采取的现实主义生活法则。而母亲薇薇安,无视道德,成日周旋于复杂的男女关系中,徘徊在乌烟瘴气的酒吧、大麻铺里。可是,玛雅从“薇薇安枪击他人事件”中看到了玩世不恭的母亲原来对“婊子”的称谓有着如此强烈的反感。放荡的背后,母亲仍然渴望得到尊重。
玛雅顿悟了,一个失去自我的人,无论多么努力维持表面风光,其内心将永无宁日。人格尊严的缺失,让亲人们远离了真正的幸福。亲人们的实例告诉玛雅:无论处于怎样的生存环境,她必须要保持自我个性与尊严,否则,她的命运势必成为某位亲人的翻版。这时的玛雅完成了她青少年个体“自性化”的第一步,决定摒弃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紧接着,她开始主动寻求能协调人格发展与社会环境的有效“人格面具”,并努力完成其个体“自性化”的整合过程。
玛雅决定以积极的态度,直面人生,用实际行动争取自我的人格尊严。
捍卫名字、保卫自尊是玛雅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人类学家班顿(Michael Banton)认为,“(对于非洲人来说)宣布一个新名字,表示对过去身份的贬低、拒绝,一个设想的新身份的诞生。”[10](P85)对黑人而言,名字等同于身份。在以白人为主导的社会中,黑人对自己名字的叫法尤为敏感,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被叫做黑鬼、脏鬼、乌鸦、擦鞋的、鬼怪等。玛雅“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对‘不以本名相称’的做法怀有极端的恐惧。对黑人想叫什么就叫什么,这种做法很危险,会被简单地理解为侮辱……”[4](P112)玛雅 10 岁时,在白人库里南夫人厨房帮工,夫人无意记住一个黑人女孩的名字,执意称玛雅为“玛丽”,玛雅故意砸坏库里南夫人两件珍贵餐具,结束了这尴尬境地,赢得了获取尊严的第一场战争[4](P113)。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玛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这时期的玛雅仍爱做“白日梦”,但梦已不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体现出对自我的关怀,“我把自己想象成被囚禁在一束阳光里的一粒尘埃,空气最微弱的颤动也会把我推来搡去,但永远不会自由自在地落入诱人的黑暗里”[4](P115)。玛雅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将会是一条荆棘路,但是,她也肯定自己将选择积极的生活方式,不会沉沦。
接着,通过初次驾车的经历,玛雅感受到了驾驭自我和主宰命运的快乐。在父亲醉酒的情况下,玛雅生平第一次握住了方向盘,居然很快就能驾驶自如,她发现了自我的力量:“是我,玛格丽特,正独自对抗自然的伟力……我主宰着墨西哥,主宰着权威、孤独、涉世未深的青春岁月,还有贝利·约翰逊(父亲),我主宰着死亡、危险、甚至地心引力”[4](P249)。书中一连串的“主宰”,表现出一种自我肯定和主宰命运的强烈愿望。玛雅渴望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对变化的渴求已在我心中生了根”[4](P276),她要证实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再者,玛雅通过极端的方法,证明了自己的女性身份。虽然玛雅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却没有巩固,内心还缠绕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对肢体的自我毫无信心,怀疑自己“可能是名女同性恋者”[4](P293)。为了证实自己是百分百的女性,她主动“诱惑”了一名男生,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成了一名16岁的单身母亲。正如玛雅所言“成长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毫无痛苦的过程”[4](P267)。为了证实、认同自我,玛雅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我们在扼腕慨叹的同时,也被她的巨大勇气所震撼。
最后,玛雅通过找工作一事,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是玛雅“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重要进程。玛雅积极主动地确定了工作目标,当一名电车工作员,这是一份当地黑人没有涉足过的工作。母亲的怀疑、招聘人员的冷淡以及与各个部门发生的冲突,都没能打消玛雅志在必得的信念,终于“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我成了旧金山电车上第一个受雇的黑人”[4](P282)。玛雅跨入了美国大社会,挣脱了黑人生活圈的限制,“不再那么需要黑人贫民窟这块挡箭牌的保护了”[4](P282)。
三、结束语
玛雅的成长经历体现了一个“人格面具”更替和个体“自性化”过程。从幼年佩戴幻想型伪装性“人格面具”,到少年佩戴疏离型伪装性“人格面具”,再到自我意识的唤醒,玛雅最终摒弃了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在经历了归属感、社会认同感、自我意识的产生与巩固等几个阶段后,玛雅终于找到了积极、有效的“人格面具”,让她能从容面对社会生存,保持自我特性与尊严,实现自我理想。玛雅冲破了白人为黑人划定的狭小生存空间,完成了青少年时期的人格整合,主动融入大社会,迈向了自我实现的漫漫长路。《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玛雅·安吉罗为弱势群体撰写的一部启示录,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注 释:
① 玛雅·安吉罗至今仍活跃在诗歌、教育、历史、电视电影等文化领域。她曾协助马丁·路德·金工作。1993年,她应邀在克林顿总统的就职仪式上朗诵个人诗作《早晨的脉搏》(On the Pulse of Morning),充分展示了其个人魅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② 美国官方人口统计局相关资料表明在1882到1935年之间,有超过3000名的黑人遭受私刑。在1865到1940年间,有超过500名的黑人在种族冲突和屠杀中丧生。
[1]Wallace,Joanne Megna.Understanding 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A Student Casebook To Issues,Sources,and Historical Documents[M].London:Greenwood Press,1998.
[2]Jung,Carl Gustav.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ume 7)[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3]Jung,Carl Gustav.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ume 9)[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4][美]玛雅·安吉罗.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杨玉功,陈延军译)[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5][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6]Jung,Carl Gustav.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ume 17)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7][美]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王作红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8][美]A.H.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Banton,Michael.Racial Consciousness[M].London:Longman,1988.
(责任编校:文 一)
Replacement of Maya’s Persona and Process of Growing-up
CHEN She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In“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Maya Angelou reconstructs some hard growing-up experiences in her childhood and early youth.In order to analyze her growing-up process,this paper employs Carl Jung’s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of“persona”and“individualization”,in addition,it also refers to some theories of Freud,Horney and Maslow.It concludes that Maya’s growing-up is a process of obtaining a much more effective“persona”in place of her disguisable ones and it is also a process of“individualization”.The book offers vulnerable groups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persona;individualization;sense of belonging;social identity
Z042
A
1000-2529(2011)02-0113-04
2010-11-20
陈 盛(196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从体、相、用出发
—— 玛雅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