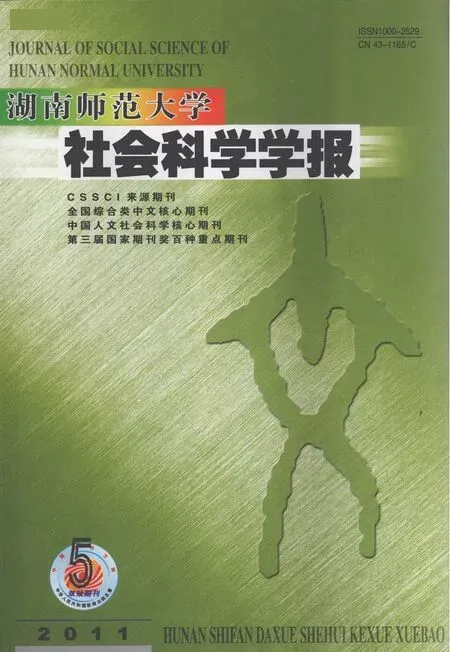寻找公共行政的价值
杨冬艳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寻找公共行政的价值
杨冬艳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公共行政价值研究既是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基于以下两个前提: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消解;实践背景——对官僚制工具理性的超越,而运用伦理学方法构建以公共行政正义为核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是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不容忽视的路径与方法。
公共行政;价值;二分法;官僚制
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效率是其最基本的“善”。“行政科学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人力和材料消耗来完成手头的工作,因此,效率是行政管理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学的大厦得以建立起来的价值基石。”[1](P123)然而,这种效率至上的官僚制行政模式摒除管理中的人性化倾向,实行对行政人员的非人格化管理,对道德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忽视或摒弃平等、公平、民主等价值,体现为对公共行政“工具性价值”的极端追求,而对公共行政“目的性价值”的极端轻视的行政模式,在实践中导致了种种弊端,如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出现的人格冲突,行政机构内部官僚主义之风盛行,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威信受到质疑等。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也使得这种效率至上的公共行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不少学者试图采用一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以克服传统公共行政的弊端,如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断尝试着行政范式的变革。我国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对于行政价值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的模式。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官僚制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就,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西方的行政官僚制,为政府公共行政注入伦理价值,实现公共行政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而明确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前提,研究公共行政价值体系构建的路径与方法则是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关键。
一、寻求公共行政价值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消解
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形成于20世纪初西方理论界的形式主义思潮,直接受到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文得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影响。然而其基本的思想和方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休谟看来,价值判断完全在理性的领域之外,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事实陈述”是能够“客观为真的”,而且同样能够被“客观地保证”,相反,价值判断不可能成为客观真理和得到客观保证。因此,当一个“是”判断描述一个“事实内容”时,那就无法从中导出“应当”判断。休谟的这种“事实内容”的形而上学构成了从“诸是”(ises)到“诸应当”(oughts)的所宣称的不可推导性的全部根据[2](P16),从而也蕴涵了事实与价值分属于两个相互分别的领域。但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言:“说到底,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并不是一种区分,而是一个论题(thesis),即‘伦理学’与‘事实内容’无关的论题。”[2](P21)以后这一理论经过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秉承,并进一步地使世界相信“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如何地有效和不可或缺,从而认为传统规范伦理学不是理性讨论的主体,尽管他们所秉承的思想家休谟本就是一位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伦理学家。按照希拉里·普特南缜密和细致的思考和研究,无论是在休谟还是卡尔纳普那里其理论构建的基础——关于“事实”的界定都是不能成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是根据对于什么是“事实”的狭隘的科学想象得到辩护的,正如休谟式原型是根据关于“观念”和“印象”的狭隘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得到辩护的。休谟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背后的“事实”概念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事实就是与感觉—印象相符合的某种东西。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不是奠基于对价值或评价的本性的任何严肃的考察,他们所考察的“事实”的本性是根据狭隘的经验主义进行的。用普特南的话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概念上看,那些论证起源于一种贫困的经验主义(后来是同样贫困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希拉里·普特南不仅从抽象的层面论证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何以是拙劣的,作者还从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事实与价值的缠结的重要现象来否定那种二分法。并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多年以来一直在倡导和捍卫的一种强有力的论证——关于福利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的理性论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颠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充分的论据,表明评价与事实的“确定”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活动。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正如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论文集》中所指出的,经济学的贫困化是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曾一再强调,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地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3](P89)。
对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产生与颠覆的回顾,是因为“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世正是基于“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分离,当然还有公共行政体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着的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这一直接根源。但公共行政与政治的分离在思想根源上直接受到20世纪初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不仅伦理学、政治学内部出现了“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格局,而且将公共行政学从蕴涵价值目标的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也得益于这种思潮影响下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至少从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世和研究来说,这种分离是有着其积极性的一面的)。近代以来,政府从混为一体的国家机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相对独立的国家意志的执行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行政管理与传统的统治管理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统治性和政治性特征。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工业化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原有的行政管理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了适应政府行政从消极走向积极的转变,以缓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门科学理论来指导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以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主张,将公共行政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其《行政学研究》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威尔逊的行政理论的直接的思想渊源来自当时德国集权政府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基础上的行政管理理论,因此威尔逊认为公共行政是“一门外来的科学”。之后,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古德诺(Frank J.Goodnow)为了更进一步阐述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在他1900年发表的《政治与行政》中明确指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4],从而使威尔逊开创的公共行政学更加明确地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以及20世纪初泰罗对科学管理原理和方法的创设,为威尔逊实现对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管理提供了具体的组织安排和管理模式,标志着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在行政学家们看来,政治所体现的是国家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价值判断与价值取舍的过程,离不开政治价值和道德目标的指导”[5](P11),而政府行政不是对政治价值和道德目标的追随,仅仅是执行已经制定好了的政策,是一个纯粹“形式化”、“技术性”的“事实”过程,用威尔逊的话来说,行政管理是一个“实用性的细节”、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6]。因此,“行政中立”成为政府行政的基本原则,公共行政只是执行决策的一个“事实领域”,与政治学、伦理学等“价值领域”无关,公共行政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履行行政职能。
但是,不管学者们的意愿如何,也不管实践者是否承认价值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事实上,公共行政自产生以来,其理论与范式越来越突显其价值诉求。公共行政作为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无论是哪种理论指导下的行政范式都离不开社会伦理精神的导引,都是一定时代伦理精神的体现。行政与伦理、事实与价值,一直是彼此伴生和互动的两个方面。由传统公共行政的以工具性的效率作为核心价值,到新公共行政对公平、民主等人文价值的追求,再到新公共服务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公共行政越来越蕴涵着对伦理精神的诉求,也越来越倾向于用伦理的视角去审视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伦理精神也越来越成为政府行政乃至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灵魂。诚如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戴维·K.哈特所说:“公共行政并非一项专业技能,而是一种社会实践道德的形式。”[7]正如阿马蒂亚·森论证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不可分离一样,公共行政是不能与价值无涉的,20世纪70年代公共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产生,正是这两个领域沟通与融合的结果。公共行政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对公共行政产生之思想基础——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的消解,在其思想渊源上更是对于事实与价值二分这一思想方法的消解,也为我们从伦理的角度审视公共行政、研究公共行政价值开辟了道路。
二、寻求公共行政价值的实践背景:对官僚制工具理性的超越
“官僚制”,亦称科层制。“官僚制”的英文为bureaucracy,由法语bureau和希腊语cratos复合而成。bureau的原意是指写字台,后引申为官员办公的地方。后缀cratos的意思是管理、治理、统治。bureaucratie在18世纪已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政治学词汇,并具体指称实施管理的政府行政机构。官僚制作为一个国家对社会实行统治和管理的组织和行为体系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无论是在东方或是西方,作为组织形式的官僚制在古代中国、埃及和晚期罗马帝国就已经存在。中国古籍中最早出现“官僚”一词的典籍是《国语·鲁语(下)》,文中有“今吾子之教官僚”之说。中国古代的“官僚”与古埃及、罗马官僚的产生一样,源自于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根据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于中国官僚制的研究,“家产官僚制最初起源于对初潮(vorflut)的治理与运河的开凿,也就是说起源于建筑工程”[8](P64)。韦伯将官僚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但中国的官员资格的获取却不是由技术或财富决定的,而是以人文素养作为评价标准。“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和德国的情形。”[8](P127)中国古代的官僚由于缺乏抽象的、成文的规范为基础的法理程序,行政实施是以理想上的公道观念为基础的,所以,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机构,用韦伯的话来讲,是前官僚制的[9](P128)。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难以发展出现代官僚制的原因。在现代汉语中,“官僚制”一词往往带有贬义,与行政的“低效率”同义,强调该制度下产生的烦琐公事程序、拖拉工作作风以及泛滥成灾的各种公文和会议记录等状况[10](P52)。这与马克斯·韦伯所研究的现代“官僚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制只能产生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只有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才拥有既具合理性又具合法性官僚制的“土壤”——法理型统治的理性国家,中国古代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合理化”的因素,而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世俗主义精神,这样体制下的官僚制只具有合法性而缺乏合理性。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古代中国和欧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他对于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作一种“合理性”的论证。
韦伯对官僚制的分析视角主要是考察官僚制的结构和作用,从分析社会组织结构入手,指出任何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的,并提出历史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前两种类型的权威以及依据这两种权威而作出的支配行为和建立在其权威基础上的组织都属于非理性范畴,不宜作为现代官僚组织及其行为的基础。只有法理型组织才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特征。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最有效率、“最纯粹类型”的组织形式,其特征表现为:(1)固定的、正式的权限范围,这一范围一般由法来加以规定;(2)权威由组织的层级结构和各种等级授予,有一种固定而有秩序的上下等级制;(3)管理有章可循;(4)管理人员专业化;(5)官员有较强的工作能力;(6)公务的管理遵循一般的规律[11](P65)。由上可知,韦伯设计的官僚制是一种理性化、技术化和非人格化的组织体制,为了避免权力滥用,抛弃了人治因素,体现了科学精神与法制精神,在功能与效率上远远优于非理性的行政行为。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建基于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上的行政组织和管理理论,从它诞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行政实践过程中都遭致诸多的诟病,甚至这个理想化的行政模式还被指责为是现代政府失灵的根源。面对公共行政实践中的诸如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益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对韦伯官僚制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根据韦伯官僚制原则而不断修缮、建构起来的官僚体制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另一方面,也说明韦伯官僚制理论本身存在着逻辑断裂带”[12](P60-61)。对于官僚制在实际运行中和官僚制本身存在的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客观地分析。韦伯是在历史的叙述中建立其“理性官僚制”的理想类型的,这种理想类型秉承了法理型权威的“理性”要素(形式理性),并将历史和现实中的具体的个别的官僚制的某些主要特征抽取出来综合而成,是对现实官僚制的一种抽象与综合,是思维构造的一种完美理想境界。韦伯在建构官僚制的理想模型时就知道这种模型与现实的差异性,而且在他建构官僚制的理想模型的时期,官僚制也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并遭遇到结构性危机,因而对于韦伯官僚制的反思,不能仅从经验事实入手,以经验观察的结果来指责概念建构对经验世界的偏离,这种指责恰恰是对韦伯“理想类型”方法论的偏离。因此,值得反思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对现代官僚制得以建立的合理性概念的反思。
韦伯从实证主义出发,把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其中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或称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在韦伯看来,实质合理性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是一种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强调行动的社会道德评价,忽视行动的效率,是一种主观性的合理性,是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形式合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是消解了价值判断、祛除巫魔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以计算为手段并尽可能对于行动本身以及行动所能达到的预期目的进行计算,是一种科学高效、纯粹客观的合理性,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合理性。韦伯对于合理性的论说是为建构其现代官僚制服务的,韦伯割裂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将其官僚制理论建立在“纯粹客观的”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中又进一步表现为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冲突。韦伯所建构的官僚制在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原则下,片面追求行政责任的制度化设计,官僚制的科层体系仅仅表现为行政官员按章程办事、受规则约束的运作体系,它遵循的是“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它“不因人而异”[13](P243,251)。以这样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合理性是一种“形式合理性”,而不具有“实质合理性”,行政过程是不包含价值、信念的纯粹的技术过程,行政官员在这个体制和过程中只是一个工具,只对其所承担的岗位负责。然而事实上,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建立在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统一之上的,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形式的公共行政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其产生和运作必定包含着一定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精神,存在着伦理评价和价值判断,政府行政官僚体系应该是一定社会政治、伦理精神的有效载体。另外,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个人也不应该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尤其是拥有公共权力的行政官员,在行政事务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复杂化,行政管理的专业性、技术性不断增强,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加大的现代社会,其行政过程中“有许多事情非法律所能规定,这些事情必须交由握有执行权的人自由裁量,由他根据公众福利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14](P99)。能否及时、公正、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就在于行政主体是否坚持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而且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不仅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以及公众对于行政主体角色的理性设计和合理期待,而且还源于行政主体出于信念、良知而对于自己角色责任的主观认同,是一种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统一。因此,将公共行政科层体系中的行政主体当作一个没有良知、没有价值判断的“工作机器”显然是有失“合理性”的,必然会在实践中遭致种种诟病。
在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的政府改革和诸多“摒弃官僚制”理念的浪潮中,人们已开始注意到官僚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中立性带来的问题,开始了超越官僚制工具理性的思考,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与范式的不断发展与变迁,以及行政伦理学的产生都昭示着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断为公共行政组织注入价值理性。
三、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方法和路径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伴随着新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公共行政学界越来越重视对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公共行政伦理学的应运而生就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忽视价值研究的回应。然而,总体上来看,公共行政伦理学研究较为关注对行政实践问题的伦理探讨,缺乏对行政伦理基础理论形而上的思考,对于行政价值的研究也往往是基于学者各自不同的学术立场,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行政价值体系。笔者认为,研究方法是存在于理论体系之中的,一方面理论体系通过方法来表达,另一方面,方法本身也是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伦理学研究上的不足,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上的滞后与不完备。即使是公共行政伦理学,虽然关注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但价值只是作为其研究内容被考量,缺乏用伦理学的方法去探究和建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的尝试。因此,无论是公共行政学对于价值研究的关注,还是公共行政伦理学基础价值体系的构建都不能忽略伦理学方法。只有充分利用人类历史上丰厚的伦理学资源,不仅要在公共行政研究中贯穿伦理精神,更应该将伦理学方法应用于现实的公共行政研究来表达公共行政本身的伦理特征,伦理学方法和路径选择是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
博登海默在他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的前言中说道,“对一般法律理论的实质性问题所作的论述,乃是以某些蕴含在我研究法理学问题的进路中的哲学假设和方法论假设为基础的”[15](P11)。同样,对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也应该将伦理学方法作为表达公共行政价值的实质性内容的基本立场、维度和视野。不仅如此,对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必然与人类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诉求——正义相联系,正如博登海默紧接所指出的,“这些假设中最基本的一点也许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法理学专业论著都不应当回避或忽视那些与在人际关系中实现正义有关的重要问题,尽管任何企图用客观的标准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都会遇到困难。我们认为,法律的功能乃在于促进这些人类价值的实现,因此,如果法律理论和法律哲学忽视这些人类价值,那么它们肯定是贫乏的、枯燥无味的。”[15](P11-12)公共行政作为一个“与在人际关系中实现正义有关的重要问题”,公共行政价值研究必然是与正义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虽然形成客观的标准解决处理公共行政价值问题是有困难的,但伦理学方法必然成为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且公共行政价值研究必须体现正义的主题。也就是说,对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应该将“正义”作为其核心而展开,公共行政正义是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价值。
伦理学是一门哲学理论科学,“伦理学研究社会道德现象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道德事实的记录和单纯的描述上,而是要深入到道德现象内部去揭示其本质和发展规律”[16](P9)。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中伦理学方法的运用必须紧紧围绕公共行政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公共行政权力而展开,通过揭示公共行政权力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矛盾,抽象出“公共行政正义”的一般概念。在此基础上运用伦理分析的工具进一步阐发“公共行政正义”的多元伦理维度。因为公共行政正义具有综合的品质,能够具体表达其他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如效率、平等和公共利益等价值。公共行政正义作为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价值,它的功能是帮助官僚制通过普遍接受的和为统治政体价值所认可的合法的实践服务于社会正义的目的。也就是说,当官僚机构以追求正义的目标行动时,正义要求他们为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有分歧的伦理和价值提供一种统一的分析视角,并在最终的价值追求上达成一致。公共行政正义不仅表征了行政本身的价值诉求,也体现了对行政主体的伦理要求,既体现了公共行政的工具性价值也是其目的性价值的体现,是公共行政正义的义务论、目的论和德性论三重伦理维度的有机统一[17]。不仅如此,“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16](P12),对公共行政的伦理学阐释不能脱离开公共行政的实践本身,现实中公共行政正义的客观存在本身就是多重维度的,只有采用不同的伦理视角去关照才能够客观地反映其实际存在,才能避免研究方法上的偏执并保持理论构建的完备性。公共行政正义作为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的核心价值要求,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8]。因此,对于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路径选择除了伦理学分析方法外,还必须克服西方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立场、各自为政的现象,必须对公共行政自身价值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并整合公共行政正义不同维度的指向,形成以公共行政正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研究路向。
[1]Robert A.Dahl.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ree Problems[A].Jay M.Shafritz and Albert C.Hyde (eds).ClassicsofPublic Administration[C].MoorePublishingCompany,inc.OakPark:Illinois,1978.
[2][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M].东方出版社,2006.
[3]Amartya Sen.On Ethics and Economics.Oxford:Blackwell,1987.
[4]Frank J.Goodnow,Politicsand Administration:A Study in Government.New York:Russell&Russell,1900.
[5]郭夏娟.公共行政伦理学[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6][美]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J].国外政治,1987,(6):32-37.
[7][美]戴维K.哈特.善良的公民,光荣的官僚与“公共的”行政[J].公共行政评论,1984,(44 卷):116.
[8][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9][英]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阎步克译)[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10]丁 煌.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H.Gerth and C.Wright Mills.Essays in Sociology.Oxfoed :Oxfoed University Press,Inc.1946.
[1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1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6]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7]杨冬艳.西方公共行政及其正义价值[J].伦理学研究,2007,(2):102-106.
[18]郭渐强,刘 薇.实现政府公共性的伦理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2):37-40.
In Search of the Valu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G Dong-yan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China)
The valu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but als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lue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premises: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dissolution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fact and value;the practice context——surpassing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bureaucratic system.The application of ethics for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s value system which takes justice as the core,is the route to research the valu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at can’t be ignored.
public administration;value;dichotomy;bureaucratic
B82-051
A
1000-2529(2011)05-0039-05
2011-04-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行政核心价值研究”(09BZZ02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优化研究”(2010-JD-008)
杨冬艳(1964-),女,湖北云梦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