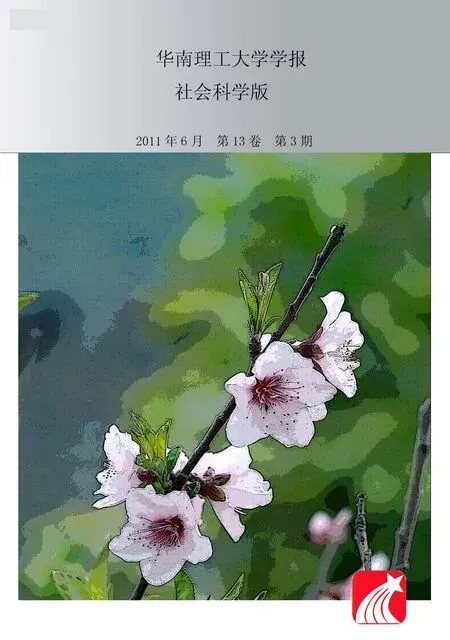政治多元化与美国政治极化: 迈向关系网络的理路
李钧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学系, 美国 纽约)
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西方民主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术语, 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其含义而言, 政治极化往往指涉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民意和公众态度的分歧甚至极端化过程, 或曰大众极化(mass polarization或popular polarization); 另一方面, 在两党制或多党制政体中, 处于竞争态势的两党或多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滑向两个极端的过程, 或者, 某种极端的意识形态、 派系或精英在某个党派地位显著上升, 甚至占据主流地位的过程, 意即精英极化(elite polarization)。
上述两个方面显然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 政治精英的极化无疑有扩散至公共态度的可能; 而公共态度的分歧也可能是政治精英意识转化的结构性诱因。问题在于, 我们在谈论美国的政治极化时, 常常对这两个维度缺乏应有的辨析, 从而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 张业亮的《“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2008)当属中文学术界对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最为深入、 全面的研究, 但全文讨论的实际上只是精英政治极化, 而对大众政治极化几乎无从涉及。。
基于对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梳理, 本文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精英与大众维度进行了考察。基本结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的政治精英出现了极化态势, 但大众政治极化的趋势并不明显。本文试图传递的另一个信息是:政治极化最大的威胁在于它所引致的政治结盟对政治多元化的破坏。作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文引入关系网络概念, 指出这一视角能够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新的洞见。
一、 美国的精英极化
在美国, 政治精英和政党活动家的意识与行动的极化并非新生事物。其建国初期, 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已经就政体, 尤其是联邦宪法的性质和联邦制的实施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争论。尽管当时全国性政党体系尚未成型, 这仍可被视为美国政治精英极化的雏形[1]8。在联邦党解体后, 从1916年到1824年, 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在多数政治议题上达成了妥协, 激烈斗争暂时平息, 在重大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这一时期的主题是合作与共识, 被称为美国政党史上的“和睦期”(Era of Good Feelings)。然而, 这一蜜月期相对短暂, 从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美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三段重大的政治精英极化时期[1]8-10。
二次大战后, 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核心价值上达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 其最为关键的表现就是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福利国家的综合。抛开各自的成见, 两党一起将罗斯福的“新政”核心理念在经济领域延续, 而在政治领域, 力图在全球输出政治自由主义, 倡导民主政治。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甚至认为, 20世纪50年代标志着政治思想的穷尽, 将这一时期描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2]。
情况在随后的十年发生了变化。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 民主党的纲领日益向左翼转移。而以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为标志, 右翼偏保守人士开始执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1973年, 在著名的罗诉韦德(Roe v. Wade)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得克萨斯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作出了违反宪法的判定, 将妇女的堕胎权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从而引发了影响至今的生命权运动(pro-life movement, 又称反堕胎权运动)。在政党政治上, 这一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以福音派(evangelist)为代表的宗教保守人士公开介入政治生活, 试图以控制共和党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上台标志着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内部的主流化, 乃至在美国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作为里根政权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后果, 政党精英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结盟[3]。尤其在共和党党内,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宗教保守主义的结盟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为了对抗共和党, 民主党在经济、 社会与政治层面分别就税收、 堕胎权、 外交及国防战略方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 这又直接加剧了民主党的左倾化。
到了1990年代, 精英政治极化趋势开始加速。一群年轻的、 来自美国南方的、 持强烈保守立场的政治精英置换了共和党内的温和分子[4]。与此同时, 克林顿政权在同性恋权益、 堕胎权、 税收与公共医疗保障等议题上的左倾自由主义政策激怒了国会山上的政治家们[5], 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开始呈现出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分歧, 而两党之间的合作也相应减少[6][7][8]。1994年, 民主党在40年间首次同时丢失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 而这一结果一般被归咎为在经济上存在不安全感的“怒气冲冲的白人男性”, 这些人对堕胎权、 积极平权(affirmative action, 或称种族优惠)措施、 同性恋权益、 枪支管制、 移民政策甚至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表现得怒火中烧。尽管克林顿政权随后采取的“第三条道路”以及成功连任似乎缓解了精英政治极化的趋势, 1998年的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丑闻将美国政治精英们的共识分裂展现得一览无余。[9]564
随后的几次总统大选中, 这种极化态势仍然成为政治观察家们议论的焦点。在2000年的大选中, 政治观察家开始用红蓝地图来描述竞选态势。红色代表持保守宗教立场的, 支持布什的南部和中部诸州, 蓝色则表征持左倾自由主义立场的, 支持戈尔的东西海岸各州及五大湖地区。在2004年的大选中, 受伊拉克战争拖累的布什正是收到了宗教保守界人士的“价值选票”(value vote)的鼎力支持才得以连任成功。在2008年的大选中, 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赢得了许多“泛红”州的支持, 似乎又为两党共识制造了契机。然而, 随后国会山上民主党对全民医保的强力推行、 “茶党”(Tea Party)运动的兴起以及2010年共和党重夺众议院掌控权, 都表明这只不过是政治极化过程中的短暂插曲。
简单说来, 民主党的左倾自由主义色彩越来越浓, 共和党则日益向右翼保守主义靠拢[3][10]。大部分政治学家认为, 美国的政治精英与政党活动家的立场已经变得更为极端。换言之, 美国政治生活自1960年代延续至今的一个主题是政治上的精英极化。
政治精英的极化具有一种骨牌效应, 通过两种机制导致了政党活动家的极化: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劝说与表率作用, 以及前者对后者的选择性招募和淘汰[11][12]。在1996年的美国大选中, 党派忠诚感对投票行为的影响达到了近五十年的最高峰[13][14]。美国政治的现状似乎表明, 政治精英越强调意识形态维度, 其政党越有可能吸引为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活动家。而反过来, 这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政党活动家的加入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极端化。
二、 美国的大众极化
对大众极化的担忧由来已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社群生活的贫瘠以及随之产生的公民孤独感进行了研究。这些学者往往得出对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稳定与政治极化后果的偏向悲观的结论[15][16]。
半个世纪之后, 社会科学家对政治极化的讨论仍旧集中在类似的议题上[17][18]: 对政治的公众参与的缺乏与不连贯性[19][20]以及社群活动参与的衰落[21][22]。通过将新近的研究与半个世纪以前的文献相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 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始终担忧一个问题: 社会凝聚力的缺乏有可能导致不良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现有研究对美国的精英政治极化达成了基本一致, 对另一个问题却存在较大的分歧: 意识形态极化在多大程度上扩散到了美国公众的身上?对大众极化最著名的担忧来自美国右翼政治家, 1992年总统候选人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在1992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宣告了争夺美国灵魂的“文化战”(culture war)的到来。然而, 实证研究对极化加剧这一假设同时提供了正面与负面的证据[23][24]。下文将对这些证据进行重点考察, 这里要先指出, 对于互相冲突甚至矛盾的实证研究,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民意(public opinion)极化在具体实证研究中往往有不同的概念化理路和操作手段。具体而言, 研究者必须在两个方面予以明确和取舍: 第一, 极化的社会边界是什么?换言之, 何种社会类别或群体与社会分化甚至极化有关?是阶级, 抑或族群, 还是性别, 甚至宗教?第二, 民意围绕什么方面分化?换言之, 是单一议题, 多重议题, 还是左倾自由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的总体性分界?
关于第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对美国公民态度的分布进行一番简单的考察。如果存在极化, 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民意分布形态的变化, 或具体说, 从正态分布向平坦分布或双峰分布的变动。我们还可以追踪群体内部的变动, 按照社会人口特征来加以区分, 例如年龄、 性别、 教育、 宗教、 社会阶层或地理位置。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测量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意识形态距离的变动, 或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意识形态距离的变动, 以此来估测党派忠诚感的影响。
而在第二个方面, 极化与民众对特定议题的看法有关。具体的测度可以采用一套意识形态的综合指标, 或采用民众在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维度上自我界定。而正是在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时, 实证研究得出了存有矛盾的结论。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同他的学生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和贝瑟尼·布赖森(Bethany Bryson)(1996)首次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实证研究。他们先对整个受访者样本的极化假设进行了检验, 然后考察不同群体内部的极化, 最后研究了群体之间的极化。关于总人群的极化程度, 他们发现, 极化增强的假设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具体而言, 他们发现, 就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角色、 对种族融合的接受以及对犯罪与正义等方面的看法而言, 美国民众的思想趋于一致。或者说,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向自由主义倾斜, 支持种族融合, 性别平等以及严厉打击犯罪。但在另一方面, 就缓解贫困的政策, 尤其是堕胎权而言, 美国人的看法呈现出更深的分化[17]。埃文斯(2003)进行了后续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 并发现了有关性倾向的观点极化的新证据[25]。
为了考察能否在群体内部观察到极化趋向, 上述研究者对投票者内部的不同群体进行了研究。考察的群体包括政治活跃分子、 大学毕业生以及年轻人群。只有政治活跃分子呈现出极化特征, 而年龄与教育水平并不成为极化的坐标[25]。
最后, 研究者对不同类型的受访者进行了比较, 发现群体之间极化的证据极为稀少。在考察了年龄、 性别、 教育、 宗教等范畴之后, 研究者观察到了群体之间差异的稳定趋向, 甚至发现了去极化(depolarization)的例子。只在自我认同的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 以及党派身份之间, 研究者发现了极化现象[17][25]。
莫里斯·菲奥利纳(Morris Fiorina)等人同样对“极化美国”(polarized America)这一命题加以驳斥, 认为所谓的“文化战”只不过是政客与媒体处于政治目的的建构产物。在菲奥利纳等人看来, 美国并不存在大众极化, 而只有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换句话说, 与早先相比, 有党派归属的美国人现在更有可能附属于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政党。真正极化或表面上极化了的是政治精英与少数政党活动者。这项研究还指出, 美国民众的心态普遍具有不确定性和两难性, 因此不太可能采取极端的立场, 而往往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采取折中态度, 对不同的议题抱有不同的立场。然而, 在另一方面, 菲奥利纳等人也认识到, 与过去相比, 大众对堕胎和同性恋权益等道德议题的看法确有向两极延伸的趋势[26]。
上述观点遭到了其他一些学者的抨击, 后者认为保守倾向与自由倾向的州之间、 信教者与非信教者之间、 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的极化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少数政治精英与政治活动家身上。这些学者认为, 极化现象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美国的公共领域, 并在将来有可能进一步激化, 成为影响美国社会, 影响美国政局的一股长期力量[27][28]。
抛开种种具有误导性的称谓和标题, 如果对现有研究进行一番深入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 社会科学家至少在下列三个方面达成了事实上的一致:
第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美国公众在堕胎议题上的分裂开始显现, 而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 对于同性恋和伊拉克战争问题的分裂开始显化。在大部分其他议题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稳定的趋势, 甚至发现去极化的例子。
第二, 党派极化呈增长趋势。积极参与政治、 党派认同感强烈以及自我认同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美国民众往往比其他人呈现出更为极端的观点。
第三, 美国民众并没有以性别、 年龄、 教育、 种族、 宗教等范畴为基础而分为两极。在这些范畴中, 美国民众的观点仍然呈现折中态势。然而, 以宗教信仰和行为作为划分标准, 美国民众呈现出极化趋势。例如, 每个星期固定去教会做礼拜的美国民众与不去或较少去教会的民众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尽管上述结论基本不存在争议, 对于它们是否支持意识形态极化假设, 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一些研究者看来, 意识形态极化指的是民意在一系列广泛的议题上的分歧与分化[17], 或反映一系列连贯的不同信念[26]。从而, 他们得出民意没有极化的结论——美国民众态度的极化只表现在少数几个议题上, 并且民众的观点并不明晰, 甚至往往难以连贯。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 只要围绕某些议题的分化存在, 例如基于宗教信仰或党派归属, 即使只是少数几个议题, 就应当承认意识形态发生了极化[27][29][30]。
三、 政治极化对政治多元论的挑战
笔者认为, 现有研究忽略了政治极化的真正影响力。思想意识的极端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心理和社会过程, 涉及到许多内在的机制[31]。对于政治研究来说, 政治极化的真正挑战是它对多元政治的潜在破坏力。
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是西方民主政体的核心理念之一。它首先是对多元化的肯定。在政治层面上, 多元论认为, 尽管政治活动与决策制定主要存在于政府这一框架中, 许多非政府群体可以通过它们所掌握的资源来施加影响。由于不同的
“叠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本年一月十三日惠函,备承关爱,不胜感谢……先生及夫人因南京气候不适,拟于四月间或五月初提前回归国,我虽觉得非常可惜,然为先生及夫人之健康起见,我又不敢挽留。我想这一次请先生到中国来,累先生及夫人冒这种危险,已经不安之至,岂敢再有久留的要求……我已告知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为先生及夫人预备川资,何时需用,候示即送。先生的月俸,当送至四月为止;虽我与其他同事的月俸,因本院经费困难,不能不欠发一部分;然而先生处必按月全送,去年十二月份欠发之一半,已嘱会计处补送矣。”[11]5
群体都在试图最大化它们的利益, 政治生活可以被视为竞争性群体间的持续讨价还价和竞逐的动态过程, 从而, 冲突无处不在, 并处于时刻变换的状态中。权力当然不是绝对平等的, 但由于多元群体的存在和资源的多样化, 权力最终在由个人组成的不同群体间得到平均分布, 达成均衡状态。在民主政体中, 政治多元化的最大好处是政治的稳定, 因为任何变化只能是渐进的、 增量的[32]158-184。
政治多元论的另一个推论是: 对治理的大众直接参与不再成为必要。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指出, 由于“政治是喧嚣生活中的一项附带活动”, 而群众有比参与政治更宝贵的时间与资源, 低度的政治参与具有其合理性[33]305。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则指出, 大众参与并不是一种美德, 因为大多数公民缺乏作出合理决策的经验与技能, 从而, 人民大众必须由“一个超越了狭隘利益的特殊阶级”来治理[34]195。这两种多元主义观点都认为, 大众在政治过程中的有选择性的、 有限的参与有其合理性, 不应被视为一个问题。从而, 为了维持政治的稳定性, 公共政策应由一个政治阶层来制定, 因为领袖们比普通公民更有可能对“游戏规则”达成一致, 从而更有可能就政治分歧达成和解。
在社会层面, 多元化仍然利大于弊。“社会”(society)常常被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概念。例如, 我们常常谈论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异。 在社会科学中,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也被绝大多数研究者作为单数形式使用。而德国古典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对持反对意见*John Levi Martin对此作出了现代表述。参见Social Structur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按照齐美尔的理解, 现代性(modernity)不能简单理解为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社群(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对立或者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与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式的二律背反, 也不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与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主张的线性历史发展趋势。相反, 他为当代社会中的个人体验提供了一幅裂变性紧张关系的生动图像。
对于齐美尔来说, 社会是由一系列的社会交往(sociation)类型的集合体*齐美尔([1908]1950: 9)认为, 社会交往是明确化了的社会互动形式, 例如家庭、 协会、 教会、 社会阶级与组织, 以及其他不甚明显、 较不稳定的关系形式。。 在社会中, 不同甚至对立的趋势结合在一起, 达到无法解决的、 不稳定的局面。社会化了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双重关系——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 又与之存在对立关系;个人作用于社会, 同时有具有自决性。不仅如此, 社会交往表现为一种两难局面:冲突与一致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构成力, 它们都维系了社会关系。正如齐美尔所说:“为了获取其固定形式, 社会需要在和谐与不和谐、 合作与竞争、 有益趋势与不良趋势之间达成某种比例。”[35]15
从而, 个人可以被看成是处于相互交汇的不同社会圈的交汇点, 而这种交叉关系对个人具有广泛的影响, 并产生常常是相互抵触的压力, 它既允许个人的自我实现, 又限制了其他可能的实现。一个人所处的交汇点越多, 意味着团体对其的控制力越弱, 他所面临的选择自由度就越大。
更具结构主义取向的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Blau)将齐美尔的交叉社会圈的概念加以系统化阐述,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现代社会中诸多群体的宏观社会融合依赖于其源自诸多交叉参数的多重形式的异质性[36]。布劳并没有将社会融合基于共享的文化或价值来界定, 而是依据基于个人交往的群体间关系。如果异质性促进群体间关系, 而不平等增强了基于等级化身份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37], 那么, 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结论随之产生:差异化或多元化有利于社会融合。
那么, 政治极化和政治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如前所述,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广泛的利益群体具有通往权力的渠道。换言之, 权力的持有者呈现多元化态势。群体之间的竞争防止了单一行动者对权力的垄断, 保障了自由民主政体的开放性。同时, 互有交集的利益防止了身份认同的无限膨胀, 从而减低了公开冲突的可能[24]409。作为一种社会建构, 激化的身份认同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38]。单一的、 统领一切的身份认同的弱化往往能防止社会冲突的产生或升级。
政治极化的威胁在于, 它诱致了潜在社会群体的联盟, 将原本松散的多元群体转变为少数具有内部同质性的板块。相应地, 个人或群体的排他性认同容易形成, 少数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得以固化。不妨设想一下,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如果不同群体的意识形态依照少数几个议题而结盟或固化, 即使这些观点本身并不极端化, 这种结盟的本身也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的极化[24]409。
四、 从关系网络的视角研究政治极化
就社会范畴来说, 尽管它们具有分析上的便利性, 并在某些场合可以较好地衡量社会团体, 例如阶级或族群, 真正生成并增强人的政治态度与认同的是可见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相应地, 在解释人的态度及其持续性和变动时, 我们应当考虑人所嵌入的关系性网络与社会群体, 以及他人的政治观点与自我的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39][40][41]。
笔者认为, 如果我们吸取前述齐美尔和布劳的创见, 将个人看作是处于不同关系网络的交叉点上, 政治极化现象就可以从关系网络这一新的视角来探讨。这一视角不但能解释对美国意识形态极化命题的看似冲突的观点, 而且能分析政治极化对政治多元化的潜在破坏。这种视角要求我们从社会背景来研究个人, 将对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视为动态的集合, 并解释行动者如何处理其政治观点中的不一致之处。
尽管已经有了少数开创性的研究[23][24][40], 通过关系型网络来研究政治极化仍属于前沿课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阐述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在笔者看来, 具体说来, 后续研究必须面对下列问题:
第一, 美国政治极化的思想与结构前提是什么?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民意的变动?社会关系的类型如何受民意变动的影响?政治极化一般是围绕单一议题还是多重议题发生?
第二, 党派极化对个人政治意识的影响是什么?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与选举投票行为之间越来越密切的正向关系仅仅是政党(以及候选人)的再结盟, 还是民众政治态度变得更为连贯的结果?存不存在议题的联盟?政治分歧与议题具有重合性还是交叉性?
第三, 人们对其周围人群政治信念的了解有多深?人们的社交圈是处于均分状态, 还是极化状态?社交圈的异质性与个人的政治忠诚度与极端化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四, 如果政党活动家的极端化暗示了社团生活其他方面的选择、 接纳与排除的类似动态的可能性, 那么, 公民社会群体成员有没有呈现极化趋势?政党政治有没有传播到公众生活中?
参考文献:
[1] 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J].美国研究, 2008, 22(3):7-31.
[2] Bell, Daniel. [1960] 2000.TheEndofIdeology:OntheExhaustionofPoliticalIdeasintheFiftie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Abramowitz, Alan I., and Kyle L. Saunders. 1998.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 Electorate”[J]. Journal of Politics 60 (3):634-652.
[4] Wilcox, Clyde. 1995. The Latest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1994 Elec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5] Quirk, Paul J. and Joseph Hinchliffe 1996. “Domestic Policy: The Trials of a Centrist Democrat”[A]. Pp. 262-289 in The Clinton Presidency: First Appraisals[C], edited by Colin Campbell and Bert A. Rockman.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6] Jacobson, Gary C. 2005. “Polarized Politics and the 2004 Congressional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J].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20 (2): 199-218.
[7] Poole, Keith T., and Howard Rosenthal. 1997.Congress:APolitical-EconomicHistoryofRollCallVotin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Trubowitz, Peter, and Nicole Mellow 2005. “’Going Bipartisan’: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J].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20 (3): 433-453.
[9] Fiorina, Morris P., and Samuel J. Abrams. 2008.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J].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11: 563-588.
[10] Rohde, David W. 1991.PartiesandLeadersinthePostreformHouse[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Saunders, Kyle L., and Alan I. Abramowitz. 2004.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san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J].AmericanPoliticsResearch32 (3): 285-309.
[12] Grynaviski, Jeffrey D., and Shang Ha 2004. “Party Activists and the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arties”[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13] Bafumi, Joseph. 2004. “The Stubborn American Voter”[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4] Bartels, Larry M. 2000. “Partisanship and Voting Behavior, 1952-1996”[J].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44 (1): 35-50.
[15] Converse, Phili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A]. Pp. 206-261 inIdeologyandDiscontent[C], edited by David E. Adler. New York: Free Press.
[16] Mann, Michael. 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35 (3): 423-439.
[17] DiMaggio, Paul, Paul Evans, and Bethany Bryson. 1996. “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2 (3): 690-755.
[18] McCarty, Nolan,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2006.PolarizedAmerica:TheDanceofIdeologyandUnequalRich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 Eliasoph, Nina. 1998.AvoidingPolitics:HowAmericansProduceApathyinEverydayLif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 Patterson, Thomas E. 2002.TheVanishingVoter:PublicInvolvementinanAgeofUncertainty[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1]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JournalofDemocracy6 (1): 65-78.
[22] Skocpol, Theda. 2003.DiminishedDemocracy:FromMembershiptoManagementinAmericanCivicLife[M].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3] Baldassarri, Delia, and Peter Bearman. 2007. “Dynamic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72 (5): 784-811.
[24] Baldassarri, Delia, and Andrew Gelman. 2008. “Partisans without Constrain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rends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14 (2): 408-446.
[25] Evans, John. “Have Americans’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An Update”[J].SocialScienceQuarterly84 (1): 71-90.
[26] Fiorina, Morris, P., with Samuel J. Abrams, and Jeremy C. Pope. [2004] 2010.CultureWar?TheMythofaPolarizedAmerica(Third Edition)[M].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7] Abramowitz, Alan I., and Kyle L. Saunders. 2005. “Why Can’t We All Just Get Alone? The Reality of a Polarized America”[J/OL].TheForum3 (2), Article 1[2011-01-11]. http://www.bepress.com/forum/vol3/iss2/art1.
[28] Hunter, James Davison. 1991.CultureWars:TheStruggletoDefineAmerica[M]. New York: Basic Books.
[29] Greenberg, Stanley B. 2004.TheTwoAmericas:OurCurrentPoliticalDeadlockandHowtoBreakIt[M]. New York: St. Martins.
[30] Mayer, Jeremy D. 2004.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 and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Middle East: Israel’s New Best Friends?” [J].SocialScienceQuarterly85 (3): 695-712.
[31] Sunstein, Cass R. 2009.GoingtoExtremes:HowLikeMindsUniteandDivid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 Held, David. [1987] 2006.ModelsofDemocracy(Third Edition)[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3] Dahl, Robert A. [1961] 2005.WhoGoverns?DemocracyandPowerinanAmericanCity(Second Edition)[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34] Lippmann, Walter. 1922.PublicOpinion[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35] Simmel, Georg. [1908] 1950.TheSociologyofGeorgSimmel[M]. New York: Free Press.
[36] Blau, Peter M. 1974. “Presidential Address: Parameters of Social Structure”[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39 (5): 615-635.
[37] Blau, Peter M., and Joseph E. Schwartz. [1984] 1997.CrosscuttingSocialCircles:TestingaMacrostructuralTheoryofIntergroupRelation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38] Sen, Amartya. 2006.IdentityandViolence:TheIllusionofDestiny[M]. New York: W. W. Norton.
[39] Kim, Hyojoung, and Peter S. Bearman. 1997.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ovement Participation”[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62 (1): 70-93.
[40] Knoke, David. 1990.PoliticalNetworks:TheStructuralPerspectiv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 Watts, Duncan J., and Peter Sheridan Dodds. 2007. “Influentials, Networks, and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34 (4): 441-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