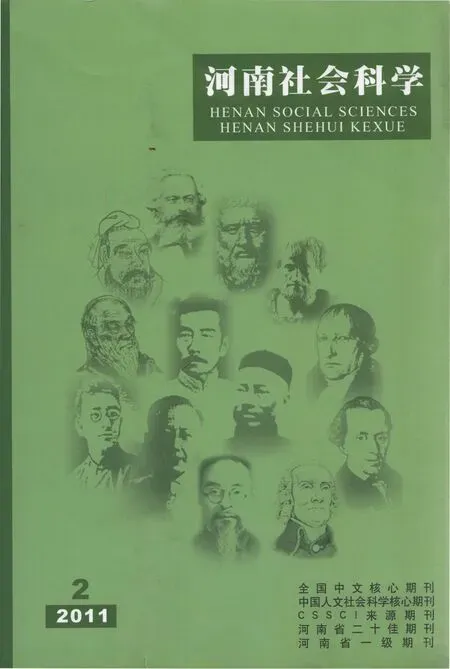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保护的经验
——以融水苗族坡会群为例
徐赣丽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保护的经验
——以融水苗族坡会群为例
徐赣丽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当前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大多关注单项知识或技艺层面的生存状态、社会意义、传承价值和保护方略,不大重视社区整体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及文化对社区民众的意义。人们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略时,强调加强政府的资助力度;在实践中,保护任务又交给了政府部门的文化工作者。因此,许多民俗成为“官俗”,失去了对社区民众的意义。民众不参与,文化遗产就有可能空壳化,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么成为暂时性的工作,要么已经变味。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初期,周星曾提出把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的意见[1],但未引起大家足够重视,在此有重申的必要。
社区保护之说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文化空间内当地民众创造的及文化与人相互依赖的道理,从特定区域的整体空间出发,借助文化主体的积极性和社区力量把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较为可行的。另一方面,特定社区或文化空间本身具有文化遗产的属性,同时又是众多单项文化遗产的有机共生区域,这就决定了特定社区的遗产财富远胜于单体文物或遗址,包括单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存在于特定社区空间内的单项文化知识,更要把文化视为一个完整、功能齐全的自足系统,从空间整体和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网络中探究文化保持的方略,不仅要注重单项重要的文化遗产,而且要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有计划地进行整体性动态保护。本文拟从具体案例说明社区保护的意义,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是更为有效、实用和可行的。
一、融水苗族坡会概况
融水县是广西境内唯一的苗族自治县,位于桂西北山区,与贵州从江县相邻。境内居住的苗、汉、壮、侗等民族,呈大分散小聚居状态。苗族大都居住在县境中部、东部和北部边远山区,主要分布在14个乡镇。坡会是融水境内以苗族为主的民间传统节日,是一个在村外田边、山坡或河滩举行的交际和娱乐性节日。坡会期间,各村苗族小伙子们扛着芦笙,姑娘们身着盛装,男女老少皆喜气洋洋一起赶坡。当地的坡会习俗由来已久,如良双乡“整依直”坡会,据历史文献记载在1687年就有了,至今有300多年历史,其他坡会也大多有上百年历史。坡会承载的苗族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是苗族文化遗产的综合体现,包括芦笙文化、苗族音乐舞蹈、服饰文化、祭祀仪式以及打老同和芦笙会等社会组织习俗、婚恋习俗等。融水境内十多个村寨存在时间呈连续性的系列坡会活动,从正月初三至十七日这段时间内,各地的坡会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文化空间,并因其具有“序列的连续性、仪式的完整性、群众的自发性、内涵的丰富性、文化生态空间的原生性、坡会的群体性和教育功能、多民族团结融合性的显现”等显著特征[2],于2006年以“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之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之所以会有系列坡会活动传统,是因为当地苗族共有一些文化传统。坡会是整个苗族地区的文化象征和文化认同标志。各个村寨的芦笙队在邀请和被邀请之间相互走动,使得附近相邻苗寨村社的坡会在时间上被接续起来。目前,融水系列坡会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文化的保护与延续的经验具有可借鉴性。
融水苗族坡会活动丰富多彩,既有传统祭祀仪式,又有多种竞技活动,其中以吹芦笙踩堂为主,同时还有斗马、赛马、跳芒蒿舞等。以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香粉古龙坡会为例,“这天,方圆数十里的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在坡上赛芦笙,跳芦笙舞,赛马、斗马、斗鸟,对歌,舞狮和鸟枪射击比赛,尽兴娱乐。古龙坡会地处苗区前沿,商品经济较其他地方发达,坡会同时又是物资交流会,各种土特产品和民族时兴商品较多,给坡会增添了节日气氛”[3]。坡会活动的过程、内容在保持传统的节目不缺失、传统程序不变更的基础上,适当结合当代生活,故有了一些新项目。总之,吹芦笙和跳踩堂舞是坡会的主体活动,同时兼有文艺和体育竞技娱乐,还有打同年等社交活动。此外,坡会也是物资交流的场所。
二、坡会的价值与功能
融水苗族坡会年年举行,民众为何能保持高涨的情绪?有苗族学者说:“苗族芦笙是欢乐、喜庆和丰收的象征。苗族吹芦笙,除了娱乐、友谊、交流和婚姻等目的外,还在于祈祷保佑,获得风调雨顺、田园丰收。因此,没有芦笙,不赶坡是一种不吉利,人心难得统一,生产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只有痛痛快快地娱乐,尽情地吹芦笙,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参加,增加节日的热烈气氛,使神灵满意,民众欢喜,来年生产才有精神上的保障。所以,苗族群众心目中,芦笙坡会规模越大越好。”[4]由此可知坡会的多种功能和坡会对于当地民众的意义。融水坡会像许多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一样,拥有多种功能[5],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男女择偶和村寨联谊
苗族坡会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但大多数坡会跟婚姻习俗有关。苗族传说讲到,苗族曾实行远距离的外婚制,造成很多不便,许多年轻人因此不能成婚,于是人们就举行芦笙坡会号召年轻男女相聚,给他们提供一个在野外自由交往的机会[6]。赶坡范围的逐渐扩大,也使得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面得到扩展。相当多的人的初恋都是由坡会开始,后来才走向婚姻的。
坡会上,小伙子围绕芦笙柱吹起芦笙,姑娘们在外围跳起踩堂舞,互相交流。吹芦笙的小伙子,有的在芦笙上插羽毛,随着吹奏乐曲身体左右摇摆,羽毛被挥舞起来,有时会甩到姑娘脸上,吸引其注意。姑娘们都盛装出行,展示美貌以吸引未婚男子的目光。在盛大、热闹的坡会上,姑娘和小伙近距离接触,互相认识,留下美好记忆。通过年复一年的坡会,一聚再聚,年轻人就这样结成良缘佳侣。坡会具有的这一功能使得年轻人对坡会抱有向往和期待。
打同年一般是指村与村之间整体的交流,是以村为单位的联谊活动。邀同年要先经全村人同意。如果邀请某村打同年,就在坡会上吹起芦笙邀请曲,围住对方的芦笙堂转三圈,然后在对方的大芦笙上贴邀请书。受邀方同意后,可在坡会散后跟着邀请方回去打同年,也有的会选择其他合适时间受邀。打同年由村里年长的男性带领全村小伙和姑娘前往,是为了让两个村的年轻人互相认识,寻找恋爱结婚的对象。打同年除了在芦笙坪上进行芦笙踩堂外,还有同年仪式。同年仪式在芦笙坪上进行,主人要宰杀牛、猪等牲口款待客人。同年仪式就是把这些牲口拿到芦笙坪上展示,主要程式是牵着还未宰杀的牛或猪,给牲口戴上大红花、插上芭芒草,绕芦笙坪转三圈;同时展示的还有款待客人的米酒、糯米饭等。展示完后,经过三轮芦笙踩堂,同年仪式就结束了。晚上,在芦笙坪上进行同年宴会,之后,青年男女便可相邀回家或到村外对唱情歌。一般打同年进行三天,三天过后,客寨返程时,主寨要送给他们肉、糯米饭、米酒等食物,让他们带回给那些没有来打同年的村民们一起吃。当客寨回到自己村子,便在本村芦笙坪上,由全寨人集中享用带回来的食物,会餐期间还会进行芦笙踩堂活动。第二年,原来的主寨要到客寨打同年,客寨按照同样的接待规格回敬。打同年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两个村寨之间的感情、消除矛盾。同时,也是为了给未婚男女提供相互认识的机会,以解决其婚姻问题。至今打同年仍是当地男女青年进行婚恋的主要方式。
(二)娱神娱人
虽然现在我们了解的坡会功能主要是为了社交或娱乐,但当地各类坡会活动的第一项都是祭祀。仪式通常是绕芦笙柱三周,吹三曲,主事者面向东方蹲下,口念祭词。祭祀的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芦笙踩堂是苗族民众娱乐活动中最具普遍性的。民国《融县志》载:“正月,侗苗则皆以男女集会,以芦笙跳舞相赛……(芦笙之会)盖为男女间最大最爱之公共娱乐;集会则因人数而见笙之多少。女子衣华服,亦集为一班。每至一村,宾主各奏笙,互答三次而后作友谊之比赛,于是笙歌跳舞,声韵抑扬。”[6]值得一提的是坡会的吹芦笙活动中会有一位吹芒筒的人,他常扮演喜剧演员,以滑稽的动作令观众捧腹大笑,增加欢乐气氛。
坡会上的娱乐还有斗马、斗鸟、耍狮、舞龙灯等,其中以斗马为多。斗马的刺激、惊险会吸引许多民众到场,其中以男性居多,围观人群中常传出欢笑声。这项竞技活动深得当地人喜爱,也非常吸引外地游客或摄影爱好者。斗马比赛的马是专门喂养的,从不用于运输;临近比赛,主人要拌以黄豆粉、碎米、甜酒等喂食,使马变得膘肥体壮,生性冲动。但斗马本身并不能给主人带来经济收益,斗马比赛的奖励一般有村民自发捐献和政府的资助,奖金数额不多,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当地人说:斗马有点奖励,但不大,这里的人就是喜欢。民众的精神需求与自我满足使这项活动一直传承下来。
(三)贸易交换
坡会也有物资交流的作用。坡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上万人,甚至数万人,小的一两千人。每年的坡会都同时形成人数多、流动量大的集市。苗族居住的村寨多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平时贸易往来少,节日期间人们把山里、地里的产出作物带到集市出售,商人小贩也趁机运送物品来坡会进行交易,这满足了供需两方的需要。在商品短缺时期,坡会成为展示商品和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求的重要场所。
(四)传承文化和强化族群认同
坡会伴随历史发展一直在传承和传播着苗族的文化传统。芦笙是一种多功能的文化复合体,坡会则是苗族芦笙文化传承者的聚集点,分散在较大地理范围的苗族人民相聚一起,有助于这些传承者互相学习借鉴。在无文字的苗族社会生活中,有约定俗成的规约:到12岁的男孩必须习吹芦笙。因为在祭祀、娱乐、求偶、婚嫁、节庆等场合都要使用芦笙,他们主要是通过学芦笙——念唱芦笙歌、背记芦笙词,获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每首芦笙词都有明确、稳定的歌调,其内容广泛,包括历史传说、生产知识、爱情婚姻、社会公德、乡规民俗等方面[7]。现在,学校教育几乎替代了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孩子们只有在坡会期间才可比较自如地学习吹芦笙和踩堂。尽管当地中学现已开始教授吹芦笙,但在乡村现实生活中,坡会期间一系列活动仍是孩子们非常珍惜的学习民族文化的机会。在芦笙踩堂活动中,常可看到孩子们举着芦笙跟大人学习吹奏的场景。坡会上男孩学习吹芦笙,女孩则在母亲细心装扮下加入芦笙踩堂队伍。孩子们从小在这种氛围里生活,习得民族传统文化,并保存共同的记忆,有利于把文化传承下去。
坡会不仅是一个教育子孙后代学习本民族文化的场域,同时也可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坡会作为融水苗族人民全民参与的活动,每年重复其仪式和活动内容可起到强化认同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行为,节日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娱乐或审美,而是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是为了通过集体的庆祝活动和人人参与,来建立一套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8]当地政府在“申遗”材料中对坡会作为苗族文化遗产的价值是这样归纳的:“融水坡会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坡会链,正是这样一个链条,可以显示出当地苗族地区传统的厚重、民风的淳朴,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比较团结一致,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坡会是民族文化集中展现的时空。每逢坡会,当地苗族与各民族男女老少举家举寨前往赶坡;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觉得在城市失落或缺损了民族自尊心,也会利用春节假期积极参与。苗族同胞共同参与民族文化活动,进行村寨、群体乃至个体之间的交流,并以村寨、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开展各项比赛,以争赢夺冠为快。共同的记忆、利益和文化特征使人们聚在一起,采取一致行动,坡会在无形中形成一种认同。总体来说,在当代,坡会的娱乐功能和寻求民族自信心、认同感的功能增强了,而其婚恋功能和信仰功能却有所减弱。
三、坡会传统延续至今的原因
前已述及,融水苗族坡会的文化内涵丰富,功能多样,不同年龄、性别和有不同需求的人参与坡会都能从中获得满足,这就为其传承和兴旺形成了必要的条件。此外,坡会的组织者、参与者等因素也是不断推动坡会年年相续、代代相承的重要原因。
坡会的组织者是坡会持续办下去的主要力量。融水坡会是民间传统的组织形式,苗族坡会的建立与废弃都由埋岩决定。埋岩是苗族议定和执行习惯法的社会组织,遇有大事各村寨老或各村代表以至全体人民,会聚一起商讨、决定处理办法。当场要立一块石头让其大半截露出地面以示决定,日后大家共同遵守。至今,融水苗族的民间组织仍发挥很大作用①。坡会的规模大小、举办目的、日期和场所以及坡会之间的关系、坡会的管理者等,都需要众人商议来决定。为保证其法律效力,使大家共同遵循,要举行埋岩仪式。一些大的坡会多经埋岩建立,未经埋岩的坡会也要经过当地父老商议,并征得村寨群众同意才能建立。因此,坡会一旦建立便长期保留,不得更换,除非坡会建立后,年年遭灾,人民生活困苦,或坡会给民众造成过重负担,或坡会期间伤风败俗之事剧增,群众忧心忡忡等。
坡会的确立有专门的民间组织负责,而坡会上吹奏芦笙也是有组织的。坡会均为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出面组织。通常每个苗寨都制作有一堂三十至五十大中小三种型号的芦笙,每堂芦笙都有一两个举足轻重的“芦笙头”,芦笙头有一定威望和社会活动能力。他们一般多为中年男子,既是芦笙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苗寨的活跃分子;多数会唱古歌、说理歌、酒歌、情歌,能熟练吹奏引调、走寨、送亲、踩堂、杂调、合调、留客、打同年等各类芦笙曲,懂得各种礼仪和规则。如正月十六的古龙坡会远近闻名,承办该坡会的“古龙坡筹委会”是成立有一百多年的民间组织,有自己的办公地址,有固定的人员进行组织策划。红水良双坡会主要由良双村洞寨杨氏家族主持,至今已传十几代人,最年轻的第13代传人才40多岁。
既然组织者基本上是地方民众或地方精英,那么,融水县政府是否就仅是旁观客呢?其实作为苗族自治县,县政府领导多是苗族出身,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深厚感情,也曾亲自参与坡会建设。安太十三坡就是由政府出面整合周围的小坡会重新建立的。1985年的正月十一至十八日,全国苗族学术讨论会在融水县城召开,为重振芦笙雄风,恢复芦笙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时任自治区民委副主任梁彬及县里四大班子的建议和支持下,在安太乡建立了县境内规模最大的芦笙坡会,把安太一带过去分散、时间不统一的芦笙坡会统一起来[9]。随后,县直机关的干部们于1986年成立了县芦笙协会,每年组织芦笙队下乡,参加不同地方的坡会活动。现在县级文教机关等多个单位都有芦笙队。县里成立芦笙协会,带动了芦笙文化的传承,消除了民众顾虑。坡会组织除了民间的,有时基层政府也会出面。近年,良双村村委渐渐介入坡会的组织,负责筹集捐款用作芦笙比赛的奖励和赞助每个村的踩堂队伍。随着村寨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以前芦笙自我管理的传统改变为芦笙由村委干部负责收藏、作为公共财产管理。
但同时,政府并没有对坡会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政府办节或保护文化遗产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灌输意识形态,使民间活动被政府征用,或成为宣传政策的途径,这样往往会使当地民众视之为政府工作或任务,从而失去参加活动的兴趣和热情。目前,融水坡会尚未出现因旅游开发带来的民族文化资源商品化问题,旅游公司尚未接洽前来赶坡的游客,县政府也没有着手干涉坡会的策划与安排,只是派出交警管制交通,以及有一些单位在坡会上摆摊宣传政策而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常涉及的问题之一是经费。许多有关呼吁都提到要加大政府的资助力度,但政府财政经费有限,诸多文化遗产都需政府扶持,政府恐怕顾不过来。融水苗族坡会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坡会作为地方传统,活动经费一向是当地苗族民众捐助。苗族民众人人热心公益,都把做公益看做是尽义务。苗族民众里修路、搭桥、建亭,都是群众自愿完成的。遇到大型公共活动,人们踊跃捐款捐物,这是传统的美德。坡会要用到谁家水田或旱地,主家会提前整好场地,为节日到来做准备而不要任何报酬。坡会中打同年、赛芦笙等所有开支,都由村人共同负担。当地苗族人民认为,年节中多一份喜庆、多一份欢乐,来年田园里将多一成丰收。在这样的乡俗民风里,大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积极性。
许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讨论都谈到“传承”、“传承人”是关键。目前,政府对传承人的补贴确实是一项支持,但在政府作出补贴前,当地的传承谱系也没有中断过。这主要是出于民族情结和文化自觉意识以及民族文化生存的危机意识。融水县是广西唯一的苗族自治县,苗族本是一个不断迁徙、历经艰辛的民族,融水苗族主要从贵州迁来,为了不忘祖先、不忘民族文化,故特别注重以自己本民族文化来强化认同和凝聚民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只是由几个民间艺人来传承的,而是整个生活在这一文化空间的所有人共同继承的财富,如果只注意保护几个传承者而不关心当地广大民众,不关心他们的文化难以传承下来的原因,那我们想保护的就真的会成为即将过去的“遗产”,而不能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要求的“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的生命环链”,对遗产的保护还“包括它由生成、传承到创新的全部过程”[10]。
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保护文化主体,参与者应该是社区居民,甚至是全民参与。融水坡会“申遗”时没有使用“融水苗族坡会”的宽泛统称,而是明确地以“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为名,同时列出15个坡会,这就使各地坡会都纳入保护的范畴,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各地坡会是组成系列坡会文化链上的一环,尽管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但谁也不想从这根链条中脱离出来。韩国东国大学历史系教授任敦基指出,各种遗产不应厚此薄彼,各种遗产项目有各自不同的形式,且每一个表演者都在传播自己的版本。如果遗产中不同版本之一被列为国家的文化遗产,那就有可能在被列为遗产的版本得到传播的同时,其他地方和艺术家的其他变种版本被排除在外。如果试图在民间艺术的保护上具有更广泛的多样性,就应该考虑一种方法,使其能够超越被列为遗产和没有被列为遗产的民间艺术之间的关系,并能够长久地保持民间艺术的多样性[11]。这番话很有道理,我们应该重视。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保护之理由
古人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12]地方土壤的特殊性培育出特别的物种,当地生态环境构成相生相克的生物平衡系统,很多物种只能生存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同理,文化也有自己的生态环境。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在其本土社区而不应悬置在社区之上或移植到与文化生态不相适应的异地。文化遗产被从原有社区抽离出,离开其生长土壤,得不到营养,迟早都会枯竭。在文化遗产产生的特定社区保存着跟遗产相关的文化记忆和情感依托,如果抽离了其原生土壤,就会导致文化脉络的断裂,使遗产成为历史的碎片和化石,难以在当下民众生活中获得发展、产生意义。有学者指出,如果以政府政绩工程的形式对待遗产保护,取代遗产传承的主人,不但会影响到传承人传承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也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从而使民俗变成“官俗”[13]。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有如下理由。
(一)社区保护可以保证社区民众的幸福和利益,促进社区进步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社区的意义,是其保护的动力。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条件之一,是要求这一文化须扎根于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历史中,能够作为一种手段来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对社会团体起到促进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地方民众是有价值的,前述坡会的功能就是当地民众一直坚持的动力。当地大量青年外出打工,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在外地人生地不熟,也会遇到婚姻问题,这时他们仍需要回到家乡来解决,因此,坡会的传统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存续。日本民俗学者菅丰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在能给当地人带来幸福。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获得的利益,理所当然地应当还原给保持这种文化的普通人为主的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其本身有价值,而是在传承这种文化的人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之中其价值才得以生成[14]。
(二)社区保护可以依靠地方民众的力量,以民俗的方式进行
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其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是要延续或更新其功能,包括娱乐、祭祀、认同和凝聚等。既然是文化遗产,则其对当地人就有切身的意义,它曾经满足过人们的需求,是大家的情感寄托。社区保护可以发挥文化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只要社区成员认识到遗产的内涵和价值,就会激发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激发他们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研究者在对彝族“火把节”的研究中提出:“未来火把节在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上应首先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包括情感需要、文化认同需要和心理归属需要。”[15]社区保护便于动员地方文化精英参与,不仅能促使人们更好地保护,也可适当增加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使社区民众受益,或给他们带来娱乐和各种机会。有人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原因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最主要的原因是公众保护意识不强。我国有一些传统文化传承至今,并没有消亡,反而兴旺起来,原因是这类文化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人们会主动保护并延续。现在有一些被列为文化遗产的对象不能跟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关系,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或让其感兴趣,他们觉得与己无关,这就导致了文化遗产的无意识流失。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强调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需要激活其功能、转化其价值、使民众喜好,尤其是为社区民众所应用。
社区保护的好处很多,例如,可依靠基层自己的基金或乐捐的方式以及民间原有组织力量来落实保护,不需依赖国家,降低运作成本。依靠基层社区民众的力量具有可行性,具体说来,不妨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推行民间社会的教育,不只依赖学校教育。二是发挥文化精英的作用。许多地方文化精英都有为家乡的文化保护和建设出力的愿望,希望借助文化的力量增加家乡的社会资本,寻求发展机会,而他们往往在地方社会也有较大的影响力。三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年轻人外出打工,许多地方的老人协会主管着社区的传统文化活动,老人们有时间并且保存了关于遗产的记忆,愿意为恢复和传承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出力。四是发挥宗教向心力和号召力的作用。民间信仰一直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力量,利用民间信仰的相关活动,也能带动文化遗产活动的复兴和保存。五是可由单个社区逐渐扩展到周边社区。那些有保护民俗的民风和优良的公益生活传统的社区,常常能自觉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16]。如果先从这些社区着手,再形成保护区,可以带动和促进相邻社区的文化传统的恢复。
(三)社区保护更有可能保证遗产的本真性
社区保护方式可以使文化遗产的内涵得到正确阐释,因为社区民众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遗产中最真实、有价值的部分。方李莉曾针对文化主权问题提出“谁拥有解释文化的权利”这一问题②。瓦努阿图国家文化委员会和瓦努阿图文化中心主任拉尔夫·雷根瓦努认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特征是它的动态存在,即是不断地由承载这一文化的人重复创造,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文化当中什么是最值得保护的,并且积极参与保护措施的决策以及这些措施的实施[1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人们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本真性”,即要保护具有本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本真性的追求,源于许多申遗项目其实是为了争夺文化资源提出的。地方文化精英或政府官员的一些全新诠释,往往缺失现实中的根基。因此,尽管有些文化项目已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却不被地方民众所认可和接受。融水坡会的申报书尽管也有整理和美化痕迹,但基本符合现实。无论用多美的辞藻形容此类活动,都是为了给外人看,但对当地民众来说,坡会有着悠久的传统,有着多种文化内涵,苗族民众从小就沐浴其中,谁都懂得它的内涵和意义。
(四)社区保护可以使文化遗产在原生地继续生长
坡会的影响不仅在于增强民族认同与集体意识,它还促使后辈们在坡会氛围中明确了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坡会是集体性的,集体的共同参与强化了后代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塑造了后代将文化继承下去的责任感。这正契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要旨:“要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申报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坡会年复一年的举行,使参与其中的广大苗胞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有学者提出:“节日最大的特点是周期性复现,传统节日在年度时间中循环,人们可以不断地脱离日常世俗时空,回到神圣的历史时空中,直接面对自己的祖先,反复重温传统、体味传统,从中汲取新的文化力量。”[17]周星曾指出,社区保护的好处之一在于“由于社区文化生态和社区人文背景的支撑,不仅有可能使‘遗产’持久地‘活’在民众的生活之中,而且在新的条件下,它还可能获得‘再生产’的机会,亦即成为社区文化创造力的源泉”[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要保护其形态,更要延续和传承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活的内容,是发展着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具有流动性。社区保护不仅能使遗产得到保护、传承,还能使之发展,容纳民众的创造,并能保持其核心的价值。这才是许多学者所强调的整体保护、活态保护。
(五)社区保护可以唤醒和复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其他文化元素
社区保护能保护好遗产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其他相关的文化元素和社区及周边居民的生活需要相关联,使内部需求循环起来。这有利于增加社区和谐与稳定,唤醒居民的爱乡情结,提高文化自信。坡会综合了各种苗族文化元素,它包含的各文化成分之间有较强的内在逻辑性和关联性。节日中吹芦笙踩堂、穿民族服饰、斗牛、斗鸟等都与社区苗族人民的生活紧密相关。芦笙世代传承,苗族制作、吹奏芦笙和听芦笙,已形成了生产、销售和享用的路径和规则;苗族服饰在这一特定场合也成为自我认同和强化认同的符号。由坡会带动,社区保护可以连带保存苗族的芦笙文化、音乐、舞蹈、服饰、宗教仪式、社会组织习俗、婚恋习俗等。
总之,社区保护既必要,也可行。社区保护的关键是恢复和转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区中的功能,依靠地方民众的自主性,并借助政府相关政策。社区保护并不排斥国家保护,当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尚处初始阶段,政府的引导、指导、监督、宣传及财政支持都是必要的。当某些遗产项目已经失去功能和市场时,社区保护需要依靠国家给养,同时依靠遗产本身的价值,使之继续得到延续。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涉及的领域众多、内容复杂、覆盖面广、任务艰巨,包括人员编制、经费投入等都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支撑,而政府的力量也有限度。因此,最终仍要落实到社区才能进行持续、有效的保护。
(注:本文的部分资料来源于广西师范大学2007级民俗学专业研究生郭悦、韦婷婷的实地调查,在此致谢。)
注释:
①直至今日,当地的许多村民对国家法知之甚少,而熟悉本村的村规民约。绝大多数村民都认为习惯法才是管得到的“法”,只要按老传统办事就不会违法。
②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36567792_0_4.html。
[1]周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基层社区[J].民族艺术,2004,(2):18—24.
[2]柳州市文化局,融水苗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申报材料汇编[C].柳州:柳州市文化局,2005.
[3]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志编撰委员会.融水县志[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8.
[4]吴承德,贾晔.苗族芦笙[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5]罗安鹄.鼓楼文化、坡会文化与现代化[J].广西社会科学,1998,(5):108—112.
[6]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7]余佳.苗族芦笙文化的现状及思考[J].艺术教育,2009,(9):100—103.
[8]王霄冰.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A].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3—15.
[9]戴民强.融水苗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
[10]方李莉.请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J].艺术评论,2006,(6):22—28.
[11]震刚.各国学者共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EB/OL].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5-01/28/content_5771618.htm.
[12]卢守助.晏子春秋·杂下之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3]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2):1—8.
[14]菅丰.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J].文化遗产,2009,(2):106—110.
[15]李玉臻.从边缘到中心:旅游背景下民族传统节日转型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J].学术论坛,2009,(2):90—93.
[16]董晓萍.论民俗保护区的方案及其构成[J].河南社会科学,2007,(2):18—21.
[17]萧放,廖明君.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学术访谈,2009,(2):21—27.
2010-12-08
徐赣丽(1967— ),女,江西宜丰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民俗旅游等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