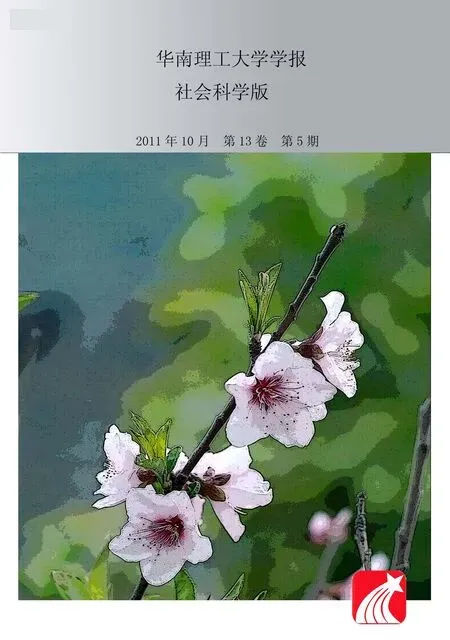再论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理论
——与王富、欧宗启商榷
罗世平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笔者于2006年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理论》(以下简称《后殖民》)一文,简要地阐述了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思想。近期,王富、欧宗启两位学者在《社科纵横》(2009年11期)上发文《论权力与后殖民语言现象—兼与罗世平先生商榷》(以下简称《论权力》),对《后殖民》的基本观点提出异议。本人对两位学者积极参与探讨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问题表示真诚欢迎,同时希望更多学者关注后殖民语言势差现象。在此,本人愿与王、欧两位学者就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理论问题交流思想,提高认识,崇实求是。为此,笔者再论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理论,就《论权力》提出的异议做出阐释。
在论述之前,我必须对本文中反复使用的两个重要概念“东方”和“西方”做出明确的界定。《后殖民》中“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根据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关系,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加以观察界定的,“西方”指自十五世纪欧洲列强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以来,向海外殖民扩张并在世界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东方”则指同期被“西方”国家或民族殖民的国家和民族。根据这一定义,“西方”主要指欧洲殖民主义列强,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德国、俄国等,以及美洲的美国。虽然美国人在“独立宣言”之前是英属殖民地,但真正称得上“被殖民者”的人并非是早期从欧洲移民到美洲十三个州的外来者,而是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应是西方殖民者,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才是真正的东方被殖民者。《后殖民》中“东方”主要指非洲、美洲、大洋州、亚洲、加勒比海等被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如非洲的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毛里求斯、加纳、津巴布韦等,美洲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多巴哥等,大洋州的新西兰、格林纳达等,以及亚洲的印度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不在此定义的东方被殖民地国家或民族之列。尽人皆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完全不同于上列东方被殖民地国家或民族。虽然中国曾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如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俄国、荷兰、美国、日本等)侵占,但从来没有任何外国势力能够完全征服中国、侵占中国的全部领土、夺取中国国家主权、统治中国人民、控制中国经济。
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哲学、文艺等方面是一个强国,欧洲列国也多是强国。西方列国的强大使中国难以避免遭受侵略,但中国的强大又使西方列强都不能完全征服中国。结果,自1840至1949的百余年间,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既不像印度那样被完全殖民,也不像日本那样从未被殖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如此,中国从未失去其主权。①香港、澳门、台湾岛除外。另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日本建立的满州国独立于中华国民政府的统辖,但除日本及很少几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外,它没有得到其它国家的承认,而且很快随日本投降而夭折。所以,满州国并未对中国主权形成威胁。故此,本文中的“东方被殖民地”不包括中国。
现针对《论权力》提出的异议展开论述。《后殖民》的基本观点是:语言势位不等于权力势位,而等于文明势位;语言势差结构的根本是“文明势差”;“语言势差”是“文明势差”在语言体系中的移植,由人类进化的不平衡造成,不受权力支配和控制。[1]61-65对此,《论权力》提出异议并阐述了不同的观点:权力是语言势差和文明势差起作用的先决条件,没有权力的帮助,语言势差和文明势差的作用都是潜在的因素而已。后殖民语言现象……是由权力因素来决定。权力因素才是后殖民语言现象得以产生和持存的重要因素。[2](82-84)为阐释这一不同观点,王、欧两位学者引用《后殖民》中“西方殖民者通过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而将西方的高势语言带到了东方殖民地,与当地的低势语言发生了近距离或零距离的接触或冲突,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作用于东方低势语言,从而实现了对东方国家的语言殖民”[1]64[2]82(引文与原文有出入)这句话,并且认为此言本身“就逻辑地包含了承认权力在殖民语言认同中的作用。”[2]82随后两学者又言:“这不是很明确地说东西方语言之所以能够接触或冲突,是因为有殖民者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作为前提吗?”[2]82此言实乃王、欧两学者对《后殖民》的误解。为更好地说明问题,让我们回到《后殖民》原文考察上述引文的意义。在《后殖民》的第二部分“文明势位与语言势位”中,作者强调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西方语言的势差结构早在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军事入侵、政治控制、经济垄断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在前殖民时期,西方强势语言与东方弱势语言没有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两者间的势差结构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殖民时期的军事入侵和政治统治以及在后殖民时期的军事撤出和权力丧失都不能改变此前固有的、由文明势差决定的语言势差结构。[1]63
另在第三部分“语言势差、语言势能、语言势流”中,作者再次强调:
同语言势差一样,语言势能早在西方对东方进行军事入侵、殖民统治之前就已存在,只因西方强势语言与东方弱势语言相距甚远而没有释放出来罢了。殖民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入侵和政治统治把西方高势语言带入东方殖民地,与当地的低势语言发生近距离或零距离的接触或冲突,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作用于东方低势语言,实现对东方国家的语言殖民。[1]64
以上两段原文反复强调并明确指出,语言势差和语言势能早在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军事入侵、政治控制、经济垄断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论权力》对此只字不提,且倒果为因、弃本逐末,错误地认为军事入侵和政治统治是语言势差的“前提”。此外,上列第二段原文中“殖民时期”四个关键字被《论权力》的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掐掉了。显而易见,此处的“殖民时期”从时间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表明前句描述的事实发生于后句描述的事实之前;也就是说,前句中的事实是后句中的事实的前提条件,即语言势差(文明势差在语言体系中的移植和表现形式)或语言势能的存在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军事入侵和政治统治东方殖民地民族等的前提条件。同理,先有语言势能的存在,后有语言势能的释放;如果根本不存在语言势能,又何以谈语言势能的释放及其对东方低势语言的作用?
毋庸置疑,殖民时期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是东西方语言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的重要前提之一,但绝非语言势差或语言势能生成的前提条件或决定因素,因为不同语言的近或零距离“接触”或“冲突”不是语言生成本身,也不是语言势差和语言势能本身。再者,上述《后殖民》原文清楚地表明,“作用于东方低势语言,实现对东方国家的语言殖民”的力量是西方高势语言在近或零距离接触东方低势语言时释放出来的强大能量,而不是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本身。所以,《论权力》所说的“权力在殖民语言认同中”的“作用”在此仅限于缩短西方语言与东方语言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使两者能够彼此接触。
显然,王、欧两学者将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视为权力(硬权力)运作形式,并认为这种权力是西方语言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作用于东方语言,实现对东方的语言殖民的先决条件或前提条件,甚至是语言势差和文明势差起作用的先决条件。这一看法显然颠倒了语言势差或文明势差与权力(硬权力)之间的本来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真像王、欧所认为的那样是实现西方语言对东方语言殖民的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那么一旦这一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消失,西方对东方的语言殖民或语言势差也必然随之消失。换言之,西方语言在东方殖民地的强势地位一旦失去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这样的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就不复存在。但事实证明,在后殖民时期,大多数东方殖民地国家摆脱了西方帝国的殖民统治而纷纷获得独立,西方殖民者被迫从东方殖民地国家撤回西方军队,并丧失了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统治权,但西方帝国的殖民语言却没有随其主子返回西方本土,而是依然保留其强势语言地位,继续在殖民地国家独占鳌头,以强势语言自居,凌驾于众土著语言之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王、欧两学者承认的事实:“20世纪中叶,许多东方殖民地国家在经过长期艰苦的反殖民统治斗争之后,纷纷获得了独立。按理获得独立后的它们本该消解殖民统治期间使用的西方殖民语言,取而代之以本民族的语言,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独立后的东方国家仍然使用西方殖民语言,继续保留它们的强势地位。”[2]82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西方后殖民语言完全能够脱离西方帝国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权力(硬权力)而发挥语言殖民作用;由此可见,后殖民语言不受权力支配和控制。
王、欧两学者又强调说:
殖民统治结束之后,西方殖民语言在后殖民国家中的地位曾经一度发生过动摇。一些后殖民国家,如肯尼亚,提出了在学校里禁用英语,要求本土作家完全用本土语言进行写作,有的国家甚至把那些坚持用西方中心语言写作的作家视为民族叛徒,一些后殖民国家的本土作家,也公开反对用英语写作。但是风雨过后一切还是归于原样,英语、法语等西方殖民语言仍然是后殖民地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像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官方语言或是通用语就都是西方殖民语言,多数非洲作家仍然坚持使用英语进行写作。[2]83
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王、欧两学者所言的这段话本身就充分而有力地证明了东方殖民地国家软权力(肯尼亚学校禁用英语等)不能够决定或改变东方殖民地民族语言与西方殖民语言之间的势差(风雨过后一切还是归于原样,英语、法语等西方殖民语言仍然是后殖民地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王、欧两学者的这段阐述否定了他们自己在《论权力》中试图阐述的“后殖民语言现象……是由权力因素来决定”的基本观点。
即便在殖民时期,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也不是西方实现对东方语言殖民的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笔者在此要问,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硬权力)的前提条件和先决条件又是什么?为什么只见西方对东方殖民地国家实施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而不见东方国家(如非洲、加勒比等地区的国家)对西方实施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究竟是什么使西方人能够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东方他者?又是什么使东方国家不能够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西方?显然,是文明势能(文明程度)使然,是文明势差使然。如果说,是权力使西方人能够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硬权力)东方他者,那就等于说权力的使然是权力,这种重复同义词的说辞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对同一片海洋,双方享有同等的航海机会和航海权力,但为什么西方民族能够远渡重洋,到达海洋彼岸军事入侵东方本土民族而东方民族不能够远渡重洋军事入侵西方国家(如欧洲国家)?是什么使西方民族能够远渡重洋去征服东方民族?又是什么使东方民族不能够远渡重洋去征服西方民族?人类史上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新大陆”的发现、环球航行等重大历史事件大都由西方(而非东方)发起。我们必须追问人类历史发展为什么大角度地向西方倾斜?尼采在其《道德谱系学》一书中说,“数千年来,在这个世界上,好与坏、善与恶两个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激烈斗争不断发生。”[3]尼采这里所说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是指西方贵族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东方黑奴的道德价值体系。由此可见,东方民族一直坚持与西方民族进行斗争,试图夺取权力。也就是说,东方民族同样有强烈的权力欲望,但他们却难以战胜西方民族而赢得权力。当早期的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面对同一片海洋、享有同等航海权力和机会的时候,权力的作用为零,所以权力不可能是西方远渡重洋军事入侵东方的前提条件或决定因素。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西方民族能够远渡重洋到达遥远的异国他乡,而东方民族则只能望洋兴叹,不能够越洋航行到欧洲大陆。在十五世纪早期,葡萄牙人航海到达非洲西海岸,占据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Madeira)和亚速尔群岛(Azores);1487年,巴塞罗米欧·戴斯(Bartholomeo Dias)航行绕过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大陆;1498年瓦斯科·达·伽玛(Vasco da Gama)抵达印度。不久,西班牙探险者抵达美洲,建立了西班牙政权,统治巴拿马、古巴岛、以及墨西哥。而东方民族则没有航海涉足遥远异邦(如欧洲国家)。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海上强国都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非洲西海岸许多沿海国家为什么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加勒比海地区有那么多的岛国却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印度有相当长的海岸线但也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上列问题的答案是:西方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其较高的文明进化程度(文明势位)使然,东方弱小的海上力量是其较低的文明进化程度使然,因为海上力量的强弱是由文明进化程度的高低决定的,即文明势位的高低决定权力的强弱。这就是说,一个民族海上力量的强弱从一个方面显示出这个民族文明进化程度的高低,一个民族的航海能力、科学知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思想意识等是这个民族文明势位和文明势能的标志和表现形式。只有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达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时,这个民族才能够拥有足够的航海能力、科学知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思想意识等去对别的民族实施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所以,文明势能和势位是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的决定因素和先决条件,而不是相反。
西方文明进化程度较高,东方文明进化程度较低,人类文明进化出现失衡,形成文明势差。这种进化失衡现象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和星期五身上得到真切的体现。文明进化程度高的鲁滨孙使他能够使用先进武器猎枪征服使用原始武器木刀的土著人,使被征服的星期五俯首称臣,沦为鲁滨孙的奴隶。相对“木刀”而言,“猎枪”是一个较高文明进化阶段的产物和标志;相对“猎枪”而言,“木刀”则是一个较低文明进化阶段的产物和标志。正是“猎枪”与“木刀”之间的文明势差(落差)决定鲁滨孙能够征服、控制、支配星期五,同时决定星期五不能够征服、控制、支配鲁滨孙。所以,文明势差决定权力关系,而非相反。
再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达尔文作为一位博物学家受邀随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贝格尔号”(Beagle)航海到南美洲东西海岸、太平洋诸岛屿、澳大利亚等地作环球勘探旅行。当“贝格尔号”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时,当地的土著人使达尔文大吃一惊。如保罗·斯特拉瑟恩(Paul Strathern)所述:
达尔文见到第一批巴塔哥尼亚人时确实深感震惊。在类似于英格兰冬天的阴冷天气里,大船派出小艇在离合恩角不到100海里的火地岛南端某处登陆。在海滩上,他们受到尖声叫喊、挥舞着手臂并做出“丑恶鬼脸”的裸体野人的迎接。一些巴塔哥尼亚人甚至连枪都不怕——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枪为何物。枪声与水手中的棒状物没有联系。被子弹击中的伤口被看作是某种神秘的自然发生的疾患。达尔文尽管思想开明,但也感到自己怀疑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同类动物”。他反而将巴塔哥尼亚人比做“另一个世界的苦恼的幽灵”。[4]
这个描述反映出欧洲人与巴塔哥尼亚人之间文明进化程度的落差之大,以至于一向思想开明的达尔文都怀疑巴塔哥尼亚人是另类动物或“另一个世界的苦恼的幽灵”。正是鲁滨孙与星期五、英国人与巴塔哥尼亚人之间文明进化程度的落差使得英国人能够远涉重洋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东方殖民地上像星期五、巴塔哥尼亚人这样的土著人。同理,两者间的这种文明落差使得星期五和巴塔哥尼亚人不能够远涉重洋到欧洲对欧洲人实施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所以,文明势差决定权力关系;权力仅是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标志和表现形式,而不是文明的决定因素或前提条件。例如,欧洲人的坚船利炮是文明进化较高程度的产物和标志,殖民地土著人的长矛弓箭是文明进化较低程度的产物和标志。如果欧洲民族当初的文明进化程度没有到达一个足以使其能够制造远洋舰船、掌握航海技术的高度,欧洲人对美洲、非洲、亚洲、加勒比等地区的军事侵略(硬权力)是不可能的,政治统治更是空想而已。
另外,西方高势语言与东方低势语言之间近距离或零距离的“接触”不能产生语言势差或语言势能,也不是语言势差或语言势能本身,而只能体现或呈现语言势差。此处所说的西方高势语言与东方低势语言之间的近或零“距离”与“语言势差”中的“势差”(也可称“位差”或“落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前者指不同语言之间的地理空间和相互接触的紧密度,后者在《后殖民》中是用来说明后殖民语言现象、表示不同文明进化程度之间落差的特定概念。“势差”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我们知道,自然界中河流的水位有高低之分,高水位与低水位之间的位差称为水的落差或势差;河水由高水位向低水位顺势流动,而不能由低水位向高水位逆势流动;河水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的过程中释放出一定的能量而做功(如水电站发电);水流做功的能力称为势能,推动河水由高到低流动的动力是自然力量,即地球引力。《后殖民》将“势差”概念引入后殖民语言现象研究,提出“语言势差”概念。人类不同语言(如英语与几内亚语)之间也有高低之分,有的语言(如英语)占据较高的语言势位,有的语言(如印地语、毛利语、几内亚语、班图语、美洲印第安语等)则占据较低的语言势位,高势语言与低势语言之间的位差构成“语言势差”。“语言势差”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进化水平之间落差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形式。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改变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但没有明显地改变语言势差,因为没有明显地改变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势差。
在此顺便说明一下,本人在《后殖民》一文中根本没有使用“与权力无关”这样极端的言辞。《后殖民》中的原话是:“语言势位不等于权力势位”,“‘语言势差’是‘文明势差’在语言体系中的移植……不受权力支配和控制”,“语言势位不是由权力的高低决定的,而是由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的。”但王、欧在《论权力》中“内容摘要”里说道,“罗世平认为主要是语言势差和文明势差在起着作用,而与权力无关。”在同文同页,两人又重复说道,“罗先生进而认为,西方语言支配东方语言与权力无关”。[2]82其中的“与权力无关”并非本人所言。
接下来,王、欧两人又言:“罗先生还认为殖民地人民认同西方语言,完全是语言势能在起作用,是来自语言自身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一说法也很令人生疑。教授琼·艾奇逊就指出过,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大的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就与英、美国两国的力量有关。”[2]82两人的生疑完全是多余的。《后殖民》通篇都在阐明这样一个观点:语言势差(包括语言势能)与使用语言的民族的文明程度或文明力量密切相关,受文明力量的影响和支配,由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而不受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这个观点与琼·艾奇逊的观点并无二致。王、欧两学者为何对此生疑,反倒令笔者费解。本人在《后殖民》中专门提到,“语言势能不是权力,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产生于语言内部结构,来自于民众社会,是人类文明的长期积淀和文明力量的语言积蓄;它不需要外部强制力量而自发地作用于他者、并得到他者自愿或自觉的‘认同’”。[1]64在此,“语言内部结构”指“语言势差结构”,而“语言势差结构”,包括“语言势能”主要“来自于民众社会,是人类文明的长期积淀和文明力量的语言积蓄(即使用语言的人的文明程度)。”当然,与某种语言紧密关联的“力量”是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明力量,而非权力(即本人所言的“不需要外部强制力量”)。目前英语之所以占据世界语言霸主的地位,主要是由于英、美两国民族的文明程度已经到达足以使其所用的语言成为国际超级语言的高度。所以,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与英、美国两国的文明力量相关。另需说明的是,“完全是语言势能在起作用,是来自语言自身力量作用的结果”根本不是《后殖民》中的原话,非笔者所言。
王、欧甚至说道:“罗先生的权力观念还停留在传统权力观的水平上。”这个说法纯属不实之辞。本人在《后殖民》中第62和63两页不仅阐释了“统治”硬权力,而且用了近半个页面的篇幅专门论述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并对《后殖民》中的权力概念做出界定。而且,本人还在其它多篇文章中论述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福柯的“话语”、尼克鲁马哈(Kwame Nkrumah)和杰克·沃迪斯(Jack Woddis)的新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权力观念。不知何故,王、欧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却又信口妄言“……还停留在……水平上。”此言不实不逊、无状无征,非但不能说明言者“水平”高人一筹,反而证明其本人的权力观念之褊狭和偏失(只见西方权力不见东方权力)。
在《论权力》的第二部分,王、欧集中论述权力对后殖民语言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的转变,认为“在殖民统治时期,权力以传统的‘统治权’的形式在发挥作用”,[2]83在后殖民时期,权力又以“认同”、“规训”等不同形式发挥作用,“硬权力”转换为“软权力”继续作用于后殖民语言。在此,笔者提醒读者注意,权力(包括硬权力和软权力)不是西方殖民者独有的,东方被殖民地国家或民族也拥有权力(也包括硬权力和软权力),特别是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后殖民地国家更是如此;换言之,既有姓“西”的权力,又有姓“东”的权力。如果像王、欧所说的那样,权力决定语言势位,那么西方殖民者拥有的权力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权力都同样是语言势差的决定因素;如果西方殖民者的硬权力能对语言产生作用,那么东方殖民地民族的硬权力也应对语言产生作用。但事实证明,后者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能够削弱西方殖民语言(如英语)的强势地位,更不能逆向使东方殖民地语言在欧洲国家占据强势地位。如果说,在后殖民时期,丧失了硬权力的西方殖民者改用比较隐蔽的软权力继续对后殖民语言产生作用,那么,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软权力也同样应该对后殖民语言产生作用,东方殖民地民族也有自己的经济模式、文化传统、道德标准、科技文教卫生机构,也力图以“规训”方式行使权力,争取本土语言的支配地位。有非洲作家就公开宣称要用本土语言进行写作,以维护本土语言的尊严。如著名肯尼亚作家古吉·瓦·匈沃(Ngugi wa Thiong’o)就强烈反对非洲作家使用英语创作。1986年他专门写出《精神非殖民化:非洲文学语言的政治》(Decoloniz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一书向世人宣告:他永远告别英语。[5]又如,1968年9月20日,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英语系的代理主任向人文学院院委会第42次会议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废除英语系,新建一个非洲语言文学系取而代之。对此,古吉·瓦·匈沃发表了两条意见:“第一,废除英语系;第二,建立一个非洲语言文学系代替之。”[6]439究其原因,古吉·瓦·匈沃解释说,“这不仅仅是个名称的更换,我们要在这个系建立一个非洲中心。我已经说过,无论从哪方面方面讲,它都是无可非议的。最重要的是,教育是传播关于我们自己知识的手段。”[6]441这个例子至少说明两个事实:其一,肯尼亚掌握权力,控制着阿尔都塞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或葛兰西所说的“民众社会组织”之一“学校”,她有权废除英语系而建立非洲语言文学系代替之;其二,肯尼亚想要通过非洲语言文学系向非洲本土人灌输非洲道德价值和文化思想,力图使非洲本土人能够自觉接受或本能认同非洲道德价值和思想意识。但实际结果表明,匈沃能够运用权力废除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英语系、新建非洲语言文学系,但却不能动摇英语在肯尼亚的强势地位。英语在肯尼亚仍是广泛通用的语言,许多肯尼亚作家,如沃特·拉迪尼、艾弥卡·凯布拉尔等,仍然用英语写作。此例说明,非洲殖民地国家权力(包括软权力)不能够动摇西方殖民语言(如英语)在非洲殖民地国家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说,权力不能决定语言势差或语言势位。
同是权力,为什么东方殖民地民族拥有的软权力不能削弱西方殖民语言的强势地位,不能使东方殖民地本族语占据支配地位?读罢《论权力》第二部分,笔者还要问:西方殖民者为什么能够发展深加工型经济而东方殖民地国家为什么只能发展原料型经济?究竟什么因素真正决定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现象?是什么因素决定东方殖民国家在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包括科技、文教、卫生等关系)方面依赖于西方殖民国家?为什么总是东方殖民地国家依赖于西方殖民国家而不是相反?为什么众多的东方殖民地本土人向往西方殖民国家留学,甚至想尽办法移民西方国家?为什么少有西方人逆向留学或移民于东方殖民地国家?王、欧两学者要论证权力是后殖民语言现象的决定性因素,就不能回避上述问题。但两人在《论权力》中回避了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避开东方殖民地国家“软权力”,只谈论西方殖民者“软权力”的作用。再说,如果王、欧两人将经济模式、文化关系、科技力量等看作“软权力”,就不能够用“权力”解释“权力”,不能说权力决定权力,不能够说西方的经济实力、国际威望、文化水平、留学政策、移民制度等决定上述的经济失衡、文化依赖、留学西方、移民西方等现象。这要求我们必须在权力之外而非权力内部探究决定权力的因素。
如果我们同时考虑西方殖民者的权力和东方殖民地国家或民族的权力,我们不难发现权力是有强弱之分的,而且权力的强弱是由权力拥有者的文明势差或文明势位的高低决定的。王、欧两学者说道,“西方宗主国还可以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威望以及在相关的国际组织中占据的领导权,施加自己的无形影响力。”[2]84须知,西方宗主国的国际威望、国际组织中的领导权和无形影响力均来自高度的西方文明;只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和国家才能享有高度的国际威望、拥有国际组织领导权、对其他民族产生无形影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原始、野蛮、落后的民族或国家能够享有高度的国际威望、拥有国际组织领导权、对他民族实施影响。所以,文明决定权力,而不是相反。西方殖民者和东方殖民地民族都拥有“软权力”,但高度的西方文明决定西方殖民者的软权力较强,而东方殖民地国家相对较低的文明程度决定东方殖民地民族或国家的软权力相对较弱,这种软权力的强弱程度是文明程度高低的表现。由西方和东方不同文明程度决定的西方殖民者与东方被殖民者“权力”(如软权力)之间的强弱之差,又决定弱者在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科技交流等方面依赖于强者。影响后殖民语言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王、欧两人所说的经济、文化、科技、文教、留学政策、移民制度等软权力,而是文明程度或文明势差。
《后殖民》中的“文明”指人类演变进化的程度或阶段,其理论基础是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其事实依据是人类演变进化的不平衡,即人类有的民族演变进化程度较高,处于较高的进化阶段;有的民族演变进化程度较低,处于较低的进化阶段,高进化程度或阶段与低进化程度或阶段之间的落差可称为文明势差;文明势差反映在语言层面上就表现为语言势差。一般地讲,高文明民族的本族语占据高语言势位,低文明民族的本族语处于低语言势位,两者间的落差形成语言势差。所以,语言势差是人类文明势差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形式。
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最先提出生物进化论。米勒和隆恩在谈到拉马克学说时说道,“拉马克对传统的大生物链学说深信不疑。他认为自然界是由分等级但有序列的物种组成的:从最简单、最微小到最大、最高级。他的学说与传统大生物链学说的区别在于:他把这种生物链看作一架自动扶梯而不是一段楼梯……拉马克指出,有两种自然力量推动了生物的不断向前、向上发展。”[7]据拉马克,大生物链中的物种像自动扶梯一样按最简单、最微小到最大、最高的等级顺序排列起来,其中每一物种为了自身的生存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力图向前、向上发展,升向更高或最高的等级。这种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过程就是物种的演化和变异过程,即生物进化过程。达尔文的“逐步上升的进化阶梯”(the ascending scale)[8]概念非常贴切地表示了“势差结构”的含义;达氏“进化阶梯”就是“势差结构”中“势位”的定义;而不同“进化阶梯”之间的落差正是“势差结构”中“势差”的含义。所有的族类像自动扶梯一样不停地向前、向上发展,向更高等级演变进化。但这种演变进化是不平衡的,有的族类已经登上较高的阶梯,而有的族类仅仅踏上较低的阶梯。所以,不同的族类处在不同的进化阶梯上,不同进化阶梯之间的落差构成不同族类之间的文明势差。进化阶梯的高低决定权力的强弱,同时决定语言势位的高低,所以,文明决定权力,文明势差决定语言势差。这是后殖民语言现象的根本原因。东方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独立仅仅改变了西方殖民者与东方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没有改变两者间的文明势差,后者的文明进化程度仍然低于前者的文明进化程度,两者间的文明势差决定了独立后的东方殖民地国家不能削弱西方殖民语言(如英语)的强势地位,也不能有效而明显地提升本土语言的势位。
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其他某些因素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后殖民语言现象也不例外,它与东西方文明程度等因素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如因果关系等)。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后殖民语言现象时,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使然。所以,我们不可割裂后殖民语言与文明势差等因素的关系来孤立地考察西方殖民者的权力对后殖民语言的作用。然而,《论权力》抛开文明势差,忽视东方殖民地权力(如软权力)的存在,割裂语言势差与文明势差、文明势差与权力、西方殖民者权力与东方殖民地民族的权力之间的联系,孤立地阐述西方殖民者权力对后殖民语言的作用。这种见木不见林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错误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
问题已经很清楚:文明势差是语言势差的决定因素,文明势差决定权力关系,语言势差是文明势差在语言体系中的移植和表现,由人类文明进化程度的不平衡造成,不受权力支配和控制;王、欧所持的“权力是语言势差和文明势差起作用的先决条件……后殖民语言现象……是由权力因素来决定”的观点倒果为因、本末倒置,颠倒了文明与权力的本来关系,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