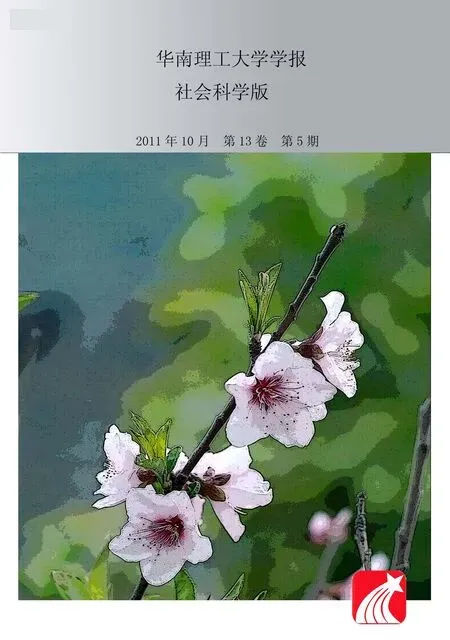碳减排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卞家涛,余珊萍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一、引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碳减排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其中,全球碳减排方案(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由于关系到各国的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2排放大国,今后的长期排放数量及排放路径被全球广泛关注,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日俱增,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因此,对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文献梳理,以厘清研究脉络和进展、明确未来研究方向,对于公平的确立“后京都时代”的全球碳减排格局,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高效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二、全球碳减排方案述评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危害,减少碳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由于涉及经济代价、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一个覆盖世界各国的碳减排方案始终没有达成,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界定或分配各国的碳排放权”,对此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一)主要国际组织、国外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曾静静、曲建升和张志强(2009)通过研究主要国际组织、国家、研究机构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情景方案后,得出:温度升高的控制目标总体以2℃为主,即到21世纪末,将大气温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前2℃的范围内;一般都倾向于在2050年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10-6~550×10-6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内,但各个方案中有关具体的减排责任分配、减排措施和减排量分歧仍然较大。[1]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提出《公约》中的40个附件Ⅰ国家,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40%,到2050年则要减排80%-95%;对非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拉美、中东、东亚以及“亚洲中央计划国家”,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减排(可理解为大幅度放慢CO2排放的增长速率,但排放总量还可增加),到2050年所有非附件Ⅰ国家都要在BAU水平上大幅减排。[2]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提出全球CO2排放在2020年达到峰值,205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发达国家应在2012—2015年达到峰值,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到2050年则减排80%;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达到峰值,到2050年则要比1990年减排20%。[3]
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08)提出以2000年为基准年,2030年全球应减排3%,其中OECD国家减排18%,金砖四国排放可增加13%,其他国家增长7%;到2050年全球减排41%,其中OECD国家减排55%,金砖四国减排34%,其他国家减排25%。[4]
GCI(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2004)提出了“紧缩趋同”方案,设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逐步向人均排放目标趋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上升,到目标年都趋同于统一的目标值,实现全球人均排放量相等。[5]
Stern(2008)提出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应该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0%,即2050年排放量应该减少为每年不到20 Gt CO2e,以后进一步降到每年不到10 GtCO2e。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应该控制在2tCO2e左右,发达国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到2050年至少减排80%;多数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应该承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6]
Sørensen(2008)提出在2100年比2000年升温1.5℃目标下,对2000-2100年期间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空间直接作了分配,同时为各国匹配了明确的年人均排放额度。根据“人均未来趋同”(即当前排放高者逐渐减排,低者可逐渐增高)的分配原则,到2100年左右时,达到不同国家人均排放相同。[7]
Browne和Butler(2007)提出创建一个国际碳基金组织(ICF)来解决减排问题。ICF的首要任务是设定减排量,将碳浓度保持在参与国一致同意的上限水平之下,然后通过政治磋商来分配减排目标比例,以反映目前人均收入和排放水平的变化。[8]
(二)国内学者关于上述方案的评价
丁仲礼、段晓男、葛全胜等(2009)认为IPCC、UNDP和OECD等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以上的人均未来排放权,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并指出IPCC等方案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没有资格作为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参考。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从确定全球及各国减排比例出发,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的做法,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并最终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认为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从分配排放权出发,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最符合公平正义原则。[9]
潘家华、陈迎(2009)认为GCI提出的“紧缩趋同”方案,从公平角度看,默认了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趋同过程中的不公平,对仍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构成严重制约。[10]
吴静、王铮(2009)采用MICES系统对Stern方案进行模拟,得出Stern方案虽然能明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但不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均排放的角度来看,均牺牲了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世界上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认为Sørensen方案的设置较为激进,在实施上存在技术困难。[11]
黄卫平、宋晓恒(2010)对Browne&Butler提出创建ICF的提议给予了肯定,但认为ICF必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实行一国一票制(基金以消费基数形成认缴义务),并主张ICF初始资金的认缴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不能根据各国的经济规模来确定,即初始资金发达国家承担50%,剩下的50%再由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消费基数认缴。[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发现:在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方面,有些缺乏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有些则充满实用主义和主观价值判断。这些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13]
(三)中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陈文颖、吴宗鑫和何建坤(2005)提出了“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法:一个趋同是2100年各国的人均排放趋同(或不高于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另一个趋同是1990年到趋同年(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趋同。趋同的1990-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以及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将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不同的水平这一目标来确定。并认为:在这种分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发展空间,其人均排放在某一时期将超过发达国家从而将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14]
丁仲礼、段晓男、葛全胜等(2009b)根据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通过计算各国的排放配额和剩余的排放空间,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国家。[15]
樊刚、苏铭和曹静(2010)基于长期的、动态的视角,提出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并根据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关系,通过计算两个情景下1950-2005年世界各国累积消费排放量,发现中国约有14%-33%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别国消费所致,建议以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16]
潘家华、陈迎(2009)设计了一个同时考虑了公平和可持续性的碳预算方案,即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设为刚性约束,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满足基本需求,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碳预算方案涉及初始分配、调整、转移支付、市场、资金机制,以及报告、核查和遵约机制等,建立了一个满足全球长期目标、公平体现各国差异的人均累积排放权标准。[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假定T0代表工业革命时期,T1代表当前,T2代表未来某一时点(如2050年)。首先,根据目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总的累计留存量以及人均相等的原则,界定T0—T1期间各国的排放权。各国排放权与实际排放之差,即为其排放账户余额,从而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并将超排国家模糊不清的“历史责任”明确转化为其国家排放账户的赤字,欠排国家的排放账户余额则表现为排放盈余。其次,科学设定T1—T2期间未来全球排放总额度,并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分配各国排放权。每个国家在T1—T2期间新分配的排放额度,加上T0—T1期间的排放账户余额,即为该国到T2时点时的总排放额度。方案既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的优点,又克服了其覆盖范围小、发展中国家缺乏激励,以及减排效果差等缺点。是一个具有理论依据且能很好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后京都时代”公平减排方案。[13]
通过对碳减排方案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的分配原则。在此原则上形成的方案,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减排方案相比,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具有公平性、正义性、合理性。
在今后的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中,我们可以将我国学者提出的方案作为谈判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同时,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使国外相关主体能够逐步了解、认同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以便在“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分配中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三、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作为CO2排放大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深入剖析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积极寻找减排途径与对策,既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又是高效实施节能减排、加速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与碳减排对策
王锋、吴丽华和杨超(2010)研究发现:1995-2007年间,中国CO2排放量年均增长12.4%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GDP、交通工具数量、人口总量、经济结构、家庭平均年收入,其平均贡献分别为15.82%、4.93%、1.28%、1.14%和1.11%,负向驱动因素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交通工具平均运输线路长度、居民生活能源强度,其平均贡献分别为-8.12%、-3.29%和-1.42%,提出通过降低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来实现碳减排。[17]
王群伟、周鹏和周德群(2010)对我国28个省区市1996-2007年CO2的排放情况、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CO2排放绩效主要因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平均改善率为3.25%,累计改善为40.86%;在区域层面,CO2排放绩效有所差异,东部最高,东北和中部稍低,西部较为落后,但差异性有下降趋势,CO2排放绩效存在收敛性;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能源强度和所有制结构则抑制了CO2排放绩效的进一步提高。作者建议:既要注重科技创新,又要大力加强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提高人员素质,以更有效地控制CO2排放;针对区域CO2排放绩效的差异性,可加强节能减排技术、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交流和扩散;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降低能耗结合起来,并考虑所有制的变动,以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作为改善CO2排放绩效的重要举措。[18]
陈劭锋、刘扬、邹秀萍等(2010)通过IPAT方程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在技术进步驱动下,CO2排放随着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依据该规律将碳排放演化过程划分为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等四个阶段,发现在不同演化阶段下,碳排放的主导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依次为:碳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驱动、碳减排技术进步驱动、碳减排技术进步将占绝对主导。并指出:碳排放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不能脱离基本发展阶段,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起点和基础不同,发达国家应以人均和总量减排指标为重点,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减排行动则应以提高碳生产率或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导向。提出中国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强国际合作,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来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19]
除了上述文献在研究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之后,提出的针对性碳减排对策,学者们又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一些碳减排的途径。
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2002)研究发现: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CO2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20]高鹏飞、陈文颖(2002)研究也得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1]不过,王金南、严刚、姜克隽等(2009)认为征收碳税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但对减缓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22]
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系统应始终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工作,要从强化金融机构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有效的信息机制、对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能力配置给予市场和政策方面的支持、理顺价格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等角度入手,运用金融市场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3]梁猛(2009)提出通过转变资金的使用方式,将直接投资于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转变为项目的坏账准备;完善配套的运行机制、建立二级市场;发挥保理工具在节能减排融资方面的独特作用等途径来加强金融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24]彭江波、郭琪(2010)认为金融具有的资金、市场、信用等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造金融工具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创造流转交易市场、改变微观主体资信等级等途径支持节能减排市场化工具的创新与应用,从而助推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25]
潘家华、郑艳(2008)认为减排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利用;充分利用各种市场机制:进一步拓展CDM的范围和规模,发挥其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设立一种作为个人消费性排放标准的碳预算,对于超过标准的碳排放征收累进的碳税,对于低于碳预算的消费者进行适当补贴,从而约束奢侈浪费性碳排放;在积极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成本较低、更具适用性的一些成熟技术推动减排。[26]
陈晓进(2006)提出:在近期,通过节能降耗,尤其是大幅降低建筑能耗和提高工业用能的效率,能有效地减少CO2排放;在中期,发展和利用CO2捕集和封存技术,是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最佳途径之一;在远期,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燃料或者无碳能源替代煤炭,是减少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途经。[27]
(二)碳减排与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工业增长
林伯强、蒋竺均(2009)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得出,中国CO2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即2020年。但实证预测表明,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后发现,除了人均收入外,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都对CO2排放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工业能源强度。提出降低中国CO2排放增长的关键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强度,建立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能源的合理消费和提高效率。[28]
林伯强、姚昕和刘希颖(2010)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满足能源需求的角度,将CO2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通过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并通过CGE模型对能源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以及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决定了中国目前重工化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所以,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应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径来节能减排。[29]
张友国(2010)研究得出:1987年至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的GDP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6.02%。指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等政策措施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并降低碳排放强度。建议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整个生产部门的能源利用技术。[30]
张雷、黄园淅、李艳梅等(2010)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始终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中部地区碳排放在全国的比重表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西部地区比重虽较小,但基本保持着上升趋势。通过分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发现: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基本空间格局,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成熟,其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速越减缓;缓慢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导致难以降低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原因。提出:积极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演进速率;推行现代能源矿种的资源国际化进程,最大限度地改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次能源供应结构;加大对非常规一次能源开发利用的研发力度。[31]
陈诗一(2009)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作为与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列的投入要素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生产率,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研究发现,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甚至为负。指出为了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完全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32]
陈诗一(2010)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从2009-2049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了模拟,认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通过均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在2039年达到最高峰,其后继续均匀减排至2049年的-1%的减排率”是通向中国未来双赢发展的最优节能减排路径。在此路径下,节能减排尽管在初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实现提高环境质量的既定目标,而且能够同时提高产出和生产率,最终实现中国工业未来40年的双赢发展。[33]
通过对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启示我们:在制定我国碳减排目标时,需要综合考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地区发展等具体因素,从战略高度系统性地实施碳减排行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实现保护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四、展望与结语
综上所述,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碳减排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1)加强定量估算以增强全球碳减排方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的研究;(2)以人民币为碳交易结算货币,争取碳定价权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的研究;(3)碳减排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4)碳减排与碳政治的关系研究。
何建坤、陈文颖、滕飞等(2009)为我国当前碳减排行动指明了方向,即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对外要努力争取合理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统一认识,提前部署。推进技术创新,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消费方式,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是我国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的根本途径。[34]
————不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