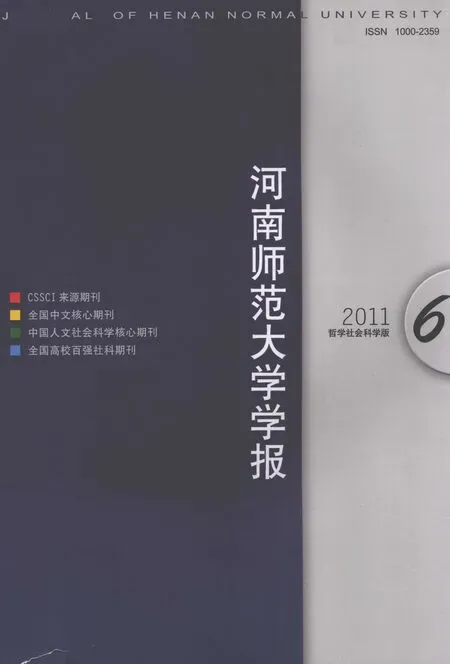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本土化表现及主要动因探析
陈 康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 焦作454000)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呈现出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制度有着显著差异的“西学”特质,对此,已有专家学者撰有论著进行过探讨。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问题的另一侧面,即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本土化表现及其主要动因。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本土化的表现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本土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大学相应的“中国化”的内部调整。教会大学初期照搬欧美模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独立系统。进入民国时期,1922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化的社会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大学据此相应提出了“中国化”的调整方针。从1926年开始,多数教会大学向民国政府注册立案,聘请中国人担任教会大学的校长,有些教会大学则弱化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按照北洋政府的教育训令设置了中国化的课程,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其办学模式、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也都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较大调整。特别是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少教会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所)或国学系,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比重,在当时教会大学数量占据中国大学半数左右的情况下客观上起到了大学本土化的一定成效。
第二,各大学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了研究和讲授国学的热潮。北洋政府时期,自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院之后,清华、燕京大学等校相继成立、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中国、齐鲁等大专院校成立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1932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省教育厅等又提出了《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要求切实加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其目的是解决“改变我国大学西学成分过浓而自己成分较少的问题”[1]。此后,各大学讲授与研究传统传统文化更起高潮。
第三,部聘教授的主观努力对于本土化功不可没。1940年5月,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学术审议委员会”,在其推动下实施了部聘教授制[2]。其目的是“本着提高战时人文科学教员之待遇,保证优良传统文化不致流失”[3]。经过一年多的评选,在战时经过迁徙已经初步稳定于西南、西北诸省的中国各大学先后产生了两批部聘教授[4]。在部聘教授人数与学科设置上,设计者有意识地对旨在提高中国传统学术科目水平、推介中国本土文化知识的学科和备选人员进行了精心考量,人选均为抗战时期人文学科的高水平专业人才。而部聘教授们也确实不负众望,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国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深慨培养学生民族自尊心的重要性,因此借助部聘教授这一有力地位,蓄志阐述中国文化政教的源流,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抉择中国文化的精华因素[5]。例如柳治徴以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为主干,归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本土化的史学功能观[6]。汤用彤以“鉴往知今”的历史文化意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念,坚定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即使在遭受外来文化激烈冲击的时候,也不会丢失其固有的民族精神,反而会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而创造出新的文化[7]。部聘教授尤其注意宏观性的方法论研究与讲授,更注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文学科理论体系的框架建设,并将其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直接面对大学生讲授的内容,以科研促进了教学内容的本土化。
第四,本土化也体现在大学教科书编写和讲授方式的中国化上。民国初年,国内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呈现外文教材当家、中文教材点缀的局面。这些外文教材所载内容存在着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问题。有感于此,蔡元培1931年在大东书局作了《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认为国人动手编著适合国情的大学教科书乃高等教育同仁的当务之急,并联系大学各专业著名教授,努力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教材。大夏大学教授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国人教材出版资助宣告书》中,阐明了自编教科书的重要性:“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的目标终不能达到也。”[8]商务印书馆1935年编辑出版的一套“大学丛书”,涵盖了不同学科的内容,该套丛书出版后,国内各大学均乐于采用(彼时大学教材的选用各校师生均有自主选择权),从而初步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自编中国化大学教材与参考书的基础。以历史学为例,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乃民国时期史学界第一部系统的白话本的通史教材,并成为高校流行的标准教材[9]。教授们还在大学讲坛上为教学方式的本土化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是改变西籍教员授课不注重体系与框架的总览而只求快速进入自己感兴趣的细节问题的模式,注重从总体到细节的有序渐进、逐步深入的教学方法,比较符合国内大学生平素养成的“先鸟瞰全局再扩大细节”的思维方式,同时鼓励大学生适当选修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而各大学的学术讲座则体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成为始终不弃的主题[10]。教授们在开讲文化史讲座时,体现出博大精深的学问及深厚扎实的教学功底,其人格和修养本身就具有一种现代大学文化与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之魅力[11]。熊十力在讲座中认为,对西方的学习不能盲目跟从,应当具有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意愿和一种敢于正视人类存在本质意义的深层次的勇气。据此而开设的各类中国传统文化讲座,体现出有思维深度的大学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革故鼎新,适应时代潮流,完成现代转型的深思熟虑,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态度深得学生的赞同。
第五,一些教授对于讲授内容本身具有西方文化内涵的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尝试。例如,柳无忌在主持南开大学英文系期间,对于英文系这样西化色彩很重的专业系科,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改造[12]。该系的一个措施是建立了中国古代书院式的教师与学生关系,教师经常邀请学生到家里来“坐拥书城”,热心地把家里珍藏的中国文化典籍让学生阅读,此种家庭读书模式对学生开眼界和拥有风雅阅读的生活非常有帮助,成为当时民国时期大学的一种特有情况。在艰苦的流亡办学岁月里,师生们仍然利用本校一些硕学鸿儒的家庭藏书室的读书活动进行着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这些师生以坐拥书城、拥书而读而感到一种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巨大乐趣,在民国动荡不安的时局背景下,师生努力追求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明窗净几、竹榻茶垆、棋局诗酒的读书风雅生活。在书院式的互动中,教师忠厚平和、宽以待人的长者风度,扎实、严谨的治学风格,无疑对于学生有着醍醐灌顶的人格魅力。
第六,本土化还体现在“传统士人文化”的续存方面,体现在彼时被指称为具有“公共智识分子”特质的传统士人特立独行、狷介狂放,内心忧国忧民的精神风骨在大学校园中的得以续存方面。在民国时期大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一批具有传统士大夫特立独行性格的教授学者的主观努力与奔走呼号不可忽视。陈寅恪一生专心求学、教书、著述,崇尚气节,不媚俗,不曲学阿世,奉行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道德行为高山仰止[13]。这样的群体,因其秉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传统文化续命而被人带有褒义地称为“公共智识分子”。他们被时人称为“独行学人,真情君子”。我们看到古代某些士人的特质——感情丰富细腻而容易冲动,与人为善而又性情偏执,在狂傲不羁外表下面实际上掩映着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真知灼见[14]。诚如其门下学生的评价:先生们是外表幼稚单纯而性情纯真、思想深刻的儒者兼时政评论家[15]。
正是在这些具有古代士人风骨亦旧亦新特质的民国大学学人的热心推动下,高等教育逐渐形成了本土化特征[16]。其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不放任的率真性情,教育独立的天真理想,则无疑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以霖雨苍生、泽被天下为抱负的优秀传统,以及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治学授课毕生追求的群体的普遍心态与人格感染力。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关于原因,学界一般多以国人近代以来对待外来文化的“西学中用”的总体观念加以笼统的大而化之的解释。笔者在此谈些自己的不同看法。
首先,高等教育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过程中必然要求具体当事人处理好历史发展的“悖论问题”。毋庸置疑,中国清末洋务运动时期萌发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处于此种悖论困境之中而努力前行。西方的大学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本来就有着巨大差别。西方大学以工具理性主义为核心,而萌芽于洋务运动的中国大学则具有很强烈的应急性质。有学者将此种做法归结为官方“西学中用”思想使然,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问题是,作为清末大学延续者的民国时期大学的本土化的动因是否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判定为是这些中西文化因子的简单叠加或何者多何者少的比例问题,这样的分析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值得商榷的。应当认识到,在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相碰撞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理念的政府层面的倡导者与一所大学内部具体制度的设计者、管理者和当时讲求“教授治校”背景下掌握大学事务的教授群体也必然会呈现出方法论上的相悖。对于这种政府官员与大学学人之间的思想冲突(按照西方模式还是采用中国本土模式来举办大学的冲突),尽管目前因为材料的局限还无法进行十分清晰的针对民国官方人员的陈述和分析,但是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依然隐约可以体察到各所大学内部的具体细节情况。在民国高等教育历史过程中所见的本土化情状,究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处在中国当时具体环境之中,由于“历史惰性”而造成的大学具体的创办者所具有的“传统士人风骨”与西方大学教育机制所要求的现代理性主义之间有意或无意的冲突与相悖以及相应的心态、处理措施、处理技巧造成的。应当承认,在民国时期得以主导中国各所大学发展的具体人士(主要是各所大学的具体创立者、管理者和教授群体),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通晓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与机制的教育家,而是一批具有传统士人风骨的、具有忧患意识的“公共智识分子”。在蔡元培等人身上,与其说是体现出近代西方性质高等教育创办者的因素,不如说更多是体现着身兼传统士人、时代弄潮儿、力挽狂澜者、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数重历史使命为己任的“公共智识分子”因素。他们不是中国的杜威,也不是中国的岩仓具视,他们开创的清末民初乃至经历了八年抗战离乱岁月的民国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必然打上了深深的传统中国士人风骨的烙印。前文提到的所谓“教育独立”思潮之勃兴、大学教育中增加人文通识教育以及彼时大学教师中一部分人士的特立独行、行为乖张(被人欣赏为“有个性”、有“学术自由”),笔者认为,都可以从这种中国传统士人风骨中的唯天下为己任、将高等教育与现实政治需求紧密挂钩、将大学作为实现人生政治抱负的养成或曰宣泄窗口的核心因素中找到“本土化”最初的内心动因。实际上,这种“士人风骨”是与西方大学的学术独立、崇尚自由、超越现实的现代理性主义是相悖的。但是,高等教育是由人来创办的,具体由哪些人来主导高等教育,决定了这一历史阶段高等教育建设过程中会真正体现出何种文化特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本土化似应更多地从民国时期大学内部教授群体具有的传统士人风骨、“公共智识分子”的特质上去加以考量其动因。在某种程度上,此种士人风骨中的忧国忧民意识在民国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国家长期面临抗击外敌入侵、恢复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的重大历史任务)下,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就会外化体现为大学的“本土化”措施。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如何处理好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高等教育因素与以激情、浪漫、关注现实为特质,以传统士人风骨为引领的“本土化”高等教育因素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关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都曾遇到的一个历史悖论问题。民国时期的各大学创办者们已经将此关系客观上处理得较为妥善,这个群体在进行设计和操作时,他们的措施一方面维护了西方意义上的大学具有独立地位与学术尊严、力图使大学一定程度上超脱于现实政治之外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当时民国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包括长期抗击外敌斗争)背景下,延续了中国自东汉太学以来的士人关心现实、关心时政、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即体现出主要为民国时期政治现实服务的“本土化”。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人士为此确实做了十分艰辛的探索,而且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而是付诸实践,这是值得景仰的。这些人士往往被后人冠以“学贯中西”的赞美词,其实我们更多观察到的是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命脉的紧密连接,甚至可以说是终其一生。民国时期大学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征,另一个原因也与中国古代传统书院具有的独立办学、追求性情陶冶因子在民国时期的惯性存在是分不开的,更与当时那批深得儒家传统文化真谛的大学创办者的内心追求分不开。梅贻琦认为,明清的书院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应防止这种传统在欧风美雨侵蚀下日渐式微,应防止工具理性主义的日渐扩张,大学应当如同古代书院那样注重民族气节的教育。
其次,民国时期的民族觉醒、奋起抗敌的政治氛围也促使了大学本土化。基于中国的知识阶层,特别是部分接受全盘西化观念的青年士子中,其欧化倾向随着大学内部接受西式教育(包括自然科学、“泰西之学”)日益增加而呈泛滥之势,这大大激发了刚由中古传统士人转型而来的大学学人维护与弘扬本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意识[18]。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国学学术研究”外表之下闪动着大学学人的拳拳爱国情怀,当然,与前清旧式训诂学者的纯粹复古倾向不同,民国时期大学校园内的国学倡导者大都因职业之原因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手段进行文化传播教授,其研究对象也明显发生下移,由专注于所谓上层精英而转向民间地方社会。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本土化的动因。
最后,在民国大学本土化过程中,有远见卓识的大学学人也借助这一过程逐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人文学科门类体系。讨论大学本土化得以推进的原因,也应当注意当时学者们的这一基于学术追求的内心动因。陈垣就公开主张传统的国学应按照现代学科去进行重新归类分解。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本土化,虽然已含着本文前面叙述过的在大学校园内弘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内容,但却必须清楚这并非主张一味的复古守旧,也并非完全为当时的时局现实服务。我们这里讲的“本土化”实际上有另外一层更加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国民时期的大学学人力图通过本土化过程,按照近代西学分类建立起比较科学的“中式内容,西式方法”的人文学科体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经学已被基本化解,整个学科按照现代西学规范被大师们重新分类,现代意义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考古学、博物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等一整套体系借助于本土化过程而逐渐形成[19]。
[1]齐思南.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热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638.
[2]张瑾.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J].近代史研究,1998(2).
[3]教育部三十年度工作成绩考察报告[R].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纪录,1942年11月,河南省档案局民国档案,卷宗号189,案卷号8:6.
[4]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R].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教育部档案,1942年12月,卷宗号5,案卷号2491:26.
[5]柳治徵.中国文化史[M].台北:有正书局,2009:688.
[6]任士英.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34.
[7]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222.
[8]王余光.教科书与近代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1990(3).
[9]张培富,易安.留学生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6).
[10]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
[11]余振基.蒿庐向学记:吕思勉生与学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08.
[12]任士英.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322,329
[13]毛彦文.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事[N].民国日报,1940-12-28.
[14]李继凯,刘瑞先.追忆吴宓[M].北京:社会科学文出版社,2001:36.
[1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68.
[16]柳光辽.柳无忌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07.
[17]陈寅恪.陈寅恪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188.
[18]发刊词[J].国学季刊,1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