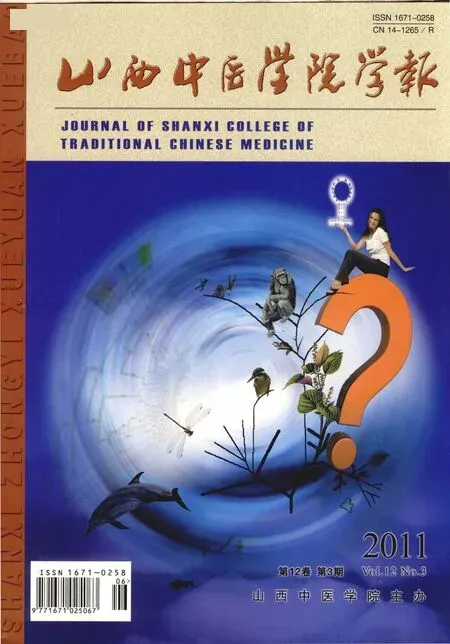“治神”——针刺素养之本
郭冠华,王 平,张维骏
(山西中医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针刺“治神”的理论,始见于《黄帝内经》,提出了“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以及“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的论述。此处“治神”、“本于神”是针灸医者在行医过程中必备的基本要求,也是施针疗效好坏与否的前提之一。其积极的意义被历代至今的诸多针灸名家所印证、发扬。
1 “治神”——针刺素养之本
关于“神”,《素问·八正神明论》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帝曰:何谓神?岐伯日: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1]所谓神,古人有“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解释。对于事物规律的认识,只有大智大慧的人才能“慧然独悟”、“昭然独明”,这种感悟“若风吹云”,突然而来,顿然领会。它并不完全依靠逻辑思维而是用整个心灵去体验和领悟。但直觉领悟并不等于随心所欲,胡思乱想。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萌生的,它的产生既需具备非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技巧,更需要具备广博深厚的知识,并立足事实,对有关问题锲而不舍地追究深思。《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黔首共余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治”字,《说文》释为“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本义是山东的一条河流名称;《荀子·解蔽》中:“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此处“治”当“修养”讲。《周礼·大宗伯》“治其大理”,注解是“治,犹简习也”。是说道家的修炼方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血脉治也,而何怪”,此“治”应当“正常”讲。故纵观《内经》的成书年代,其“治”应是长期的修炼、调节,以趋正常之义,而决非临时之举。《内经》中“治神”不仅仅是对医者医疗技能的要求,尤为重要的是指精神状态而言,包括医者和患者两个方面。《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明确道出针灸医者在针刺施术之前,要全面诊察患者的精神状态,而在诊察之前,必先调整自身的精神状态,同时在针刺过程中,时时刻刻以调整患者的精神状态为要,由此可知早在《内经》时代的医疗服务就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
所谓素养,也是素质,是指一个人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内在特质,广义是包括技能和知识。素养是一个人能做什么(技能、知识),想做什么(角色定位、自我认知)和会怎么做(价值观、品质、动机)的内在特质的组合。一个人的素养就好比一座冰山,技能和知识只是露在水面上冰山的一角,他的自我认知、动机、个人品质以及价值观这些东西,都潜藏在水面以下。如《汉书·李寻传》就说:“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
现在,笔者把“治神”和“素养”放在一起,不仅仅想说的是“治神者”的心神状态以及针刺操作技能水平的高超,更想说的是“治神之素质”是反映中国古代一种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反映一种以人为主,以人为本的医患关系,也是中国传统医学之一大特色。作为一名医者,我们基本职业素养不仅仅是治疗患者的伤痛,至为重要的是建立患者治疗疾病的信心,使之精神状态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保持最佳状态,处处体现“以人为本,治神为要”的宗旨。
2 “治神”素养之内涵
《内经》成书于秦汉之际,但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主要是以医疗实践为基础,加之时代背景下蕴育产生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了具有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人文关怀的辩证论治的中国传统特色医学。“治神”做为在一定时代的人文背景下的专业素养便产生了。
“神”在中国古代是近乎哲学的概念,其基本意思是精神,常与形体相对。中医学认为心主神明,所以形与神的关系,也就是物与心的关系。《大学》中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正是物与心关系最好的说明。回溯源头,据古文献记载“治神者”首先要塞聪弊明,“涤除玄览”(《老子·第十章》)清除杂念,察看内心,使心空彻明净,保持虚静的状态。庄子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通》)。人在虚静恬淡的状态下,能够回归本真,能够回复到“万物之本”——气的状态,人的身心能够与气所构成的世界融为一体,正所谓“堕肢体,黔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有人引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素朴”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现象,“当感官追逐外部事物的认识途径被阻断,人也就将心灵完全敞开。这时候的心与物就组建成为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抱朴子》谓“守一存真,乃能通神”也是这个意思。
“治神”思想贯穿于医者诊治疾病的整个过程,此理论的提出反映了古代医者在诊治疾病过程的对自己、对患者所提出的基本要求,“虚静恬淡”、“守一存真”的治神内涵应为我们每一位医者所尊崇。
3 “治神”素养之体会
“积神于心、以知往今”(《灵枢·五色》)。针灸医家把“治神——感应——致知”这一过程作为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手段,先反求诸已,再推已及人。“常以不病调病人”(《素问·平人气象论》)作为诊断方面衡变的依据,当然这远远不是“治神者”应有期许。
“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李时珍《奇经八脉考》)。在心与物化的境界中,许多生理现象可以通过直觉映现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针灸医家特别重视心所发挥的作用。“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素问·六脏象论》),心主之神不仅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而且还应该包括对事物的感知认识能力。这种天人相应、心物一元的认识论,一直被后世针灸医家作为不传的秘术继承下来,被视为针刺臻于极至,入于化境的理想境界。明代针灸家杨继洲在《针灸大成·头不可多炙策》中说:“然则善灸者奈何?静养以虚其心,观变以运此心,旁求博采以旷此心,使吾心与造化相通,而于病之隐显,昭然气候之疾徐,由是而明呼吸补泻之宜,由是而达迎随出入之机,由是而酌从卫取气,从荣置气之要,不将从手应心,得鱼兔而忘筌蹄也哉!此又歧黄之秘术,所谓百尺竿头进一步者。”[2]这是对“治神”最具代表性的阐述,也道出了“治神”的真谛。
汤液、醴酪、毒药、针石、艾灸等只是医疗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是否产生治疗作用,关键是患病机体神的作用状态,即“神机”,与邪气相对时称“正气”。《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灵枢·小针解》云:“神者,正气也。”这是无数医家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灵枢·本神》强调:“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并阐明其道理谓:“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伤,针不可以治之也。”张介宾说得好:“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经气不应,此神气已去,而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而已,是即所谓不使也。”
关于“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的理解,指病人的精神与志意为正气。滑寿《读素问钞》云:“药非正气,不能运行,针非正气,不能驱使,故曰针石之道,精神进,志意治则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虽用针石,病亦不愈。”提示临床治病当时时关注患者之神机盛衰。
总之,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蕴育产生的哲医——中医学、特别是针灸学,在其产生之初,便将人文和科技融为一体,突显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色彩,体现出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亲近、沟通、交流、启发、融合,是生命对生命的靠近、尊重和超越。这种内在的精神气韵,而决非形式造就了一位位历代针灸名家。
这种针灸医家的“治神”所修炼而成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心怀善、以人度已,以已怀人,抱楚而治,是大善也”,“常怀悲悯之心”,“至虚极,守静笃”是根本、是道、是人文;“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灵枢·终始》)是技术,是器也,故“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甚至不遇之以心而遇之以气(《庄子·人间世》)才是“道也,进乎技矣”的道化圆通,与道合一的“治神”之高境界,也是我们所追崇的职业素养之高标准。
[1]山东中医学院,河北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364.
[2]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针灸大成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36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