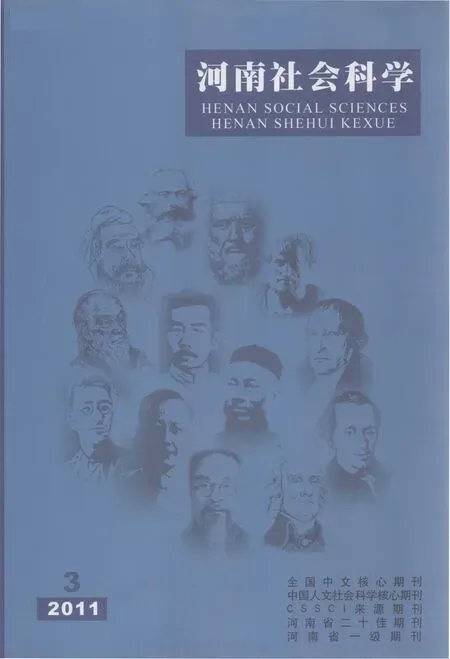中原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义”
胡爱玲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原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义”
胡爱玲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原传统文化围绕着财富利益的分配、友善适当的行为、正直公正的良知,特别是对个人自由追求应得正当利益的维护、对他人正当利益的尊重,彰显了一种既维护自身自由又不去干涉、妨碍、损害他人,追求总体和谐的公平正义思想。这种价值理念规范了我们的行为,塑造了我们的民风民俗。今天,我们需要从中汲取合理思想,为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支撑。
中原传统文化;公平;正义
中原文化生生不息,无不得益于中原圣贤对义利正确关系的倡导、坚守和践行。中原圣贤在对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追求及利益的分配、管理上给我们指出了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正是在他们的智慧引导下,我们围绕公利和私利的辩证关系,探求社会的公平、公正。他们的义利观规范了我们的行为,塑造了民风民俗,培养了我们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疏通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围绕时代问题,回顾和发掘中原传统文化中对利益、欲望与道义关系的精辟见解,当能引导我们自觉处理好利益分配中差别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关系,建构和谐的公平、正义社会。
一、正视和维护合法正当利益
中原传统文化的创始人及其追随者认识到,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是公平、利益共享的社会。个体无论身处何种地位,都应该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管理制度下实现自身应当得到的利益保障。恪守道义、合理追求利益满足的社会才具有活力,民众才会幸福、有尊严地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应谨防私欲无限膨胀,以道、义为行为准则,不能沉溺于物质利益追求中无法自拔。精神上的富有和充实对人的发展同样不可或缺。人活着意义的丧失,和精神上的虚无有很大的关系。
儒家对正当、合理的利益追求予以充分的肯定。孟子讲:“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1]追求利和义本身无可厚非,但追求的方式及实现利和义的方式必须得到规范,不能违反人的内在属性,特别是在对待民众“利”的问题上,要坚守“有恒产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1]。如果“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1],就此,孟子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1],做到“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鳏、寡、孤、独都能得到妥善安置[1]。儒家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2]同时又强调:“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2]墨子的义利观同样能给纠结在“义利”问题上的人们提供合理性指导。诸如“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3],“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3]。上述真知灼见把义利统一起来,认为义即利,利即义。认为人与人交往要做到互惠互利,和谐共赢。墨家正确的义利观念,为秦国一步一步走向强盛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程颐、程颢(二程)也曾针对义利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指出追求欲望的实现,要遵天理,反对私欲横流。主张协调义利的关系,追求私利,不忘公利,以“义”导“利”,倡导合理的功利主义,即对于正常合理的需求和利益要给予满足。在他们看来,“口目鼻四支(肢)之欲,性也”,“利者,众之所同欲也”,“以富为贤者不欲,却反人情”,“圣人所欲,不逾矩”,“不与民同欲,故民疾上之为,诗人言为君与民同欲也。能同袍,则虽寒不怨矣。若推同袍之恩,则民亦同上之欲”[4]。追求利是人的共性,如片面地、不当地宣传和要求圣贤无私欲,是极为虚妄的道德说教。不管是圣贤还是平常之人,他们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都是要得到尊重和满足的,否则将违背人的本性。在充分肯定人的合理需要满足的同时,他们还探讨要采取正当的方式来谋取利益。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的诠释,对“以义取利”、“放于利而行,多怨”[5]的强调,有力说明不择手段的牟利方式是他们所不齿的,应超越对私利的片面追求,要“见利思义”[5]。他们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5]。如此看来,正当的利益追求与合理的获利方式是中原传统文化中“正义”的内涵之一。
二、道义主导下的利益共享
维护社会秩序,要培育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分配不公,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政府就无法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弱势群体就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社会就有可能陷于无序动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集中民智投入改造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了。
中原圣贤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促使他们积极说服统治者要关注民生,施政时着眼于使民众富足,通过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诸如“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来使他们懂得“恭、宽、信、敏、惠”[5]。适时引导普通民众处理好追求个人合法利益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个体基于合理需要积极追求利益实现,同时不忘“义”字当头,普通民众在享受富裕殷实的生活时,不忘关注和帮助那些陷于困顿中的民众。对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先义而后利”,“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2]。统治者遵循上述原则,才能赢得民众的自愿认同。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此进行过论证:要做到正义,领导者要节制自身的欲望,扶持弱者,积极维护和尊重民众的正当利益追求。只有满足民众的生活所需,民众才能顺从领导者的领导;如果领导者一味地放纵追逐自身的利益和欲望满足而不顾民众的合理需求,那么他们难以保持自身的领导地位。遵道守德的执政者应该把国家的财富返还给民众。老子反对损不足以补有余,认为这种做法违背自然规律,不能保证统治长久,所以,要保护社会个体不受外来强力干涉的基本自由。“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6]在处理个人的利益追求和需要欲望满足方面,老子倡导知足寡欲。这一思想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显得特别珍贵,特别是当我们深感消费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生态上的脆弱感及内心难以适应的困惑时,重温老子思想的意义更为非同寻常。老子指出:“罪莫大于可(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6]又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定矣。”[6]
论及财富分配,二程也明确指出:不管是管理者、被管理者,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在追求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上都是应该平等对待的。作为领导者尤其要重视“与民同欲”,力求把个人利益与群体、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另外,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诱惑,要保持清醒,充分认识到欲望无限膨胀的危害性。“利者,众人所同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故夫子曰‘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餍,圣贤之深戒也。”[7]“好胜者灭理,肆欲乱常。”[8]这表明,不合理引导欲望,将会损害天理。而“存天理、灭人欲”并不像以往片面理解的那样,它指涉的内容非常明确和具体:“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同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力争,故若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辞也。苟不偏己,合于公道,人亦益之,何为击之乎?既求益于人,至于甚极,则人皆恶而欲攻之,故击之者自外来也。人善,则千里之外应之。”[7]“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椅子,人坐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利之弊也。”[8]如此看来,二程语境中的利与义、人欲和天理是辩证统一的,“存天理”要求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保障个体利益的实现,维护最广大的公利。它在价值上体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渴望人人都为共同利益的实现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灭人欲”灭的是那些不仅不能带来公共善,反而致使个人或社会处于纷争不断甚至自相残害的可悲境地中的利。鉴于此,他们呼吁满足合理利益追求,捍卫天理公利,反对私欲无限制的膨胀。
中原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义”,首先,不管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追求基本需要满足方面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重视。秉承正义的基本理念,就要尊重个人通过正当劳动取得的利益所得,正确处理、平衡义务和权利的关系,构建能保障个人人身权利和思想权利的制度。就像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所讲:每个人都基于正义而拥有一种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在于个体的合理利益和权利不被牺牲、不受挫折和不被剥夺[9]。其次,要在正视社会上存在的差别特别是贫富差距的基础上,不能使差距拉得过大,更不能损害弱者为强者谋取不当利益。鼓励利益既得者,重视对普通弱势群体的照顾、教育和提升。中原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就提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0]。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是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主题。中原真正崛起需要集中精力促进经济增长,更需要结合实际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帮助他们走出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
实现中原崛起的目标,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既要维护个体的正当所得,又要兼顾社会弱势群体,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追求效率和功利时,不忘价值理性,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引导民众在性格或品质上独立自主,主动担负起责任,树立起奉公的精神,热忱追求理想,守望正义,信仰科学、民主和法治。不迷信权威,追求创新,拥有自由的行动意愿和能力,唯有这样才能为公平正义社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才能真正消除特权。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关注金钱以外的精神价值,追求心灵的快乐和富有,爱憎分明,关注公众的利益与安全。高度尊重、主动认同与自觉遵守经得起合法性质疑的规则和制度。为富者要仁,富有的人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了,自身才是安全的。通过给予那些弱势群体以帮助,而不是施舍,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公平、正义社会需要促进民意的崛起及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良性互动。就像罗尔斯所强调的那样:个人在政治思想、信念等方面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以任何名目牺牲的,但在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时,却可以坚持一种最大限度地改善处境最差者地位的原则,真正做到利益共享,充分关爱普通民众,保护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使他们远离不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不仅是先人憧憬的理想目标,更是我们实现中原崛起的内在必然要求。
三、汲取中原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构建公平、正义社会
当下,处于转型期的民众,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特权意识和个人私欲膨胀、社会显失公平和正义的现象,幸福感和安全感都深受影响,难免会出现精神荒芜。这种状况如得不到及时改善,将制约着中原实现崛起。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诸多原则极易使生活商品化、市场化,人被物化,滋生极端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集体主义观念不同程度地遭到贬损,民众对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的信仰,被置换为对眼前利益包括金钱和物质的极端追求。虽然,市场经济自身最终能淘汰这种极为恶劣的敛财方式,但它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损失确是无可挽回的,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给人的挫伤,日益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安全。实现中原崛起,规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深入领会中原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梳理出合理的成分,为我们正确地从事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中原传统文化中有关义利的思想,有助于深化理解和贯彻胡锦涛同志阐述的正义思想。目前,深入解读中原传统文化,引导民众坚定信念,相信通过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当能建成一个公平和正义得到彰显的和谐美好的社会。结合时代出现的新课题,追求正义的实现,正如博登海默所讲的那样:“满足个人合理的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继续文明社会所必需的——正义的目标。”[11]
实现中原崛起的目标,要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同时,力避富者愈富、贫者愈穷、赢者通吃的现象出现,把维护最广大民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评判工作的价值尺度。引导民众在追求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关注和发现更多的共同利益。推进中原传统文化的顺利转型,完善制度设计,围绕民众的利益诉求,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保证公民义务和权利的统一,保证各项政策顺利贯彻执行。
具体而言,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在追求平等的同时,客观理解差别原则,照顾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复兴传统文化中那种“义利双行”的先进功利主义理念,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富足视为我们追求公共利益实现、维护个体尊严和自由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明确利益原则,实现义与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道德提升与经济利益追求的内在统一,以给人们积极健康的价值指引。在追求利益满足的同时,一定要秉承先人遗训,不能见利忘义,应正确理解规划自己的需求,合理地引导自身对财富和地位的欲望,积极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明确公利和私利、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决不能因私损公,更不能借助公权力侵害个体正当利益,以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兼顾全体公民的利益,防止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以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保证社会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保障每个个体都得到自由和恰如其分的尊严。
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破除“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切记“义利双行”,反对空谈义理。坚持义利统一的观点,鼓励人们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正当途径和合法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以调动民众创新的积极性,使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统一起来。一方面要满足老百姓的自然生命的基本需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6];另一方面,要时刻关注随着社会发展民众渴望的精神需求,包括被尊重的需求、发展和完善自身的需求。增加公共服务机构、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福利体系,发展经济以保证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完善民众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中去,创造一个既能保持充分竞争,又能保持身份认同、社会凝聚、人性关怀、相互信赖的社会,以保持社会凝聚力。这是弘扬中原传统文化的主旨。
[1]孟子[C].
[2]荀子[C].
[3]墨子[C].
[4]河南程氏粹言(卷一)[M].
[5]论语[C].
[6]道德经[M].
[7]周易程氏传[M].
[8]河南程氏遗书[M].
[9]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礼记[M].
[1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G12
A
1007-905X(2011)03-0179-03
2011-02-01
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0513033200)
胡爱玲(1979— ),女,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