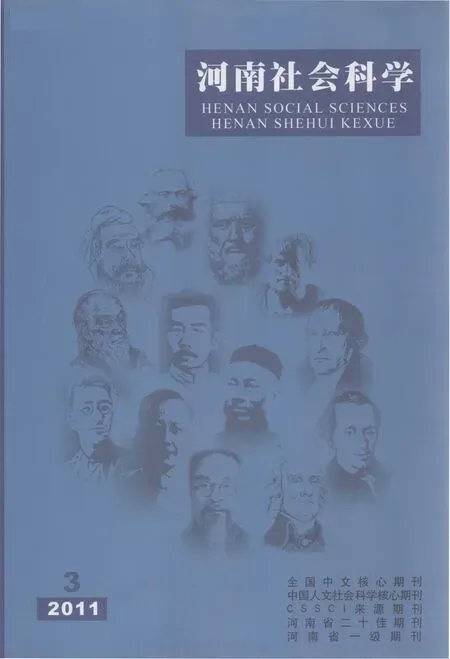和谐的审美之维
——中国古代文艺学范畴的现代转换
寸 悟
(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陕西 宝鸡 721013)
和谐的审美之维
——中国古代文艺学范畴的现代转换
寸 悟
(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陕西 宝鸡 721013)
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专题研究
编者按: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在当前如何更好地提升、转化,以适应当前的现实需要,怎样在当前语境下更好地把握古代文论的精髓,是进一步研究古代文论、反思古代文论阐释的重点。本专题从“和谐”的现代转换、“以意逆志”的再阐释以及对20世纪陆机文学思想阐释的反思三个方面选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更好地把握古代文论的精华,发挥古代文论在当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一方面表现出古代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以特有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和把握中国文艺的特点和本质,以促进文艺实践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更高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中华民族的人的生存意义的审视、建构,以促成更加丰满的人性、更加伟岸的人格、更加健全的社会,这也是一切艺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和谐,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本原性范畴。其与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观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认识和把握这一重要的范畴,分析其内涵及发展、流变与转换,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强烈的实践指向。
一、和谐的文化学审视
和谐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丰沃的厚土中生长出的一株思想奇葩。其与中国哲学和艺术理论中的“道”、“气”、“象”等基元范畴等共同催生了中国文艺林苑里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
“和”字出现很早,甲骨文、金文中已有。修海林先生指出:“‘’之初义,犹如一首形象化的田园诗,其中洋溢着一种生活的谐和感。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谐和,人与社会之间的谐和,其中浸染着一种篱墙之内的安居足食,内心陶然的谐和体验。”[1](P172)杨树达先生说:“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说文》:‘和,调也。’‘盉,调味也。’乐调谓之和,味调谓之盉,事之调适者谓之和,其意一也。”[2](P28)和字从西周开始,在文化典籍中频频出现,《周易》、《尚书》以及儒学、道家无不论及,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观念。这不仅成就了周代的礼仪制度、诗教传统、人格范型,而且对模塑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母题,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当然对这个问题的阐发和辨析绝不是一篇文章可以承担的,本人只想在此概略地阐明和谐这一范畴的丰富复杂的艺术文化学和诗学价值。
《尚书·尧典》有这样的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神人以和”)的观念、和谐的思想已经产生了,也表明了天人合一与和谐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西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喷发期、奠基期。这一时期各种典籍中涉及和谐的话语不胜枚举,此处不再赘述。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中国文化在其形成期,和谐、天人合一这种观念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观念、始元范畴,决定了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古希腊)文化的不同走向,根源何在?
如果说古希腊的奴隶时代是从原始时代的母体诞生的,它一出生就割断了与母体的脐带,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发展历程,以地缘政治代替了血缘关系,人的自我独立的个体意识也形成了,那么,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却深深打上母体的胎记,是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前行的。其一,原始时代以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也成为新的社会组成形式,新的社会依然重视家族群体、社会群体意识,且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法制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形式,家国一体,重视道德伦理,谦谦君子成为人格范型,人们独立的个体意识未真正形成。其二,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大陆内陆性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农耕方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生存方式。由人与自然(天)之间的依赖性、亲和性所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和谐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由是,中国文化艺术对自然的崇敬和赞颂就成为一个重大的主题。带上原始时代泛神论的色彩,这一点在许多现在的民俗文化中都可以反映出来。特别是“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对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阶级的精神情操影响至深,寄情山水、吟风诵月是他们思想情趣的寄托。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关系对中国艺术的题材主题、表现方式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在天人合一、和谐这样的基本范畴中得到了集中反映。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智慧在允执厥中,保全大和,故能尽生灵之本,合内外之圣道,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充分完成道德自我的最高境界!……总括此中的根本精神,千言万语一句话,便是‘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光照之下,普遍流行于其他文化的邪恶力量最终将被完全克服。”[3](P370)中国文化重视人的道德理性的培养,重视人的社会群体性的养成,由此来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思维方式上重视物我同一的主客体关系,保持了对世界的直观、感悟式的生命体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是最清楚的表述。所以中国文化被称为“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就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总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4](P19)这也似乎就是意大利人类学家维柯所提出的“诗性思维”方式,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指称的“诗意的栖居”之意,这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的魅力所在吧!
二、和谐:中国文艺理论的价值取向
和谐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不过不及的中庸的思想方法,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君子人格。和谐也是以理节情、乐而不淫的诗教传统,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中国古代的艺术观念、艺术理想、艺术批评及接受的各个环节,都受到和谐思想观念的制约和导向,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所有范畴,如形/体、文/质、虚/实、情/理、物/我等都体现出与和谐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艺术与艺术观念作为中国文化构成因素之一,受到天人合一、和谐哲学观念的制约与影响,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和谐是中国先哲一个深刻而丰富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形成的周代就有许多思想家论及: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惟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左传·昭公二十年》
桓公为司徒……(问于史伯)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去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会敬同爱矣。
《乐记·乐论篇》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和谐绝不是简单的同类相聚、毫无差别。古人已经明确地表现出对世界现实事物的一些根本性的认识。因为任何范畴,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理解。事物之间互相差异又互相依存,相因相成又互相转化,这是最朴素又最深刻的一种辩证思维。“和”与“同”的区别,表现出先哲以非常睿智、精深的感悟力,把握了事物内部包含着的差异性、矛盾性。正是这些差异和对立,才导致事物产生变化,不断发展,和而不流,化而不滞,充满了生命的创造力量,无论是对自然、社会,还是对艺术而言,都是一种真理性揭橥。
和谐就是美,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协调和合,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表述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真善美的统一。中国先哲所谓的天,绝不等同于西方人所讲的与人对立的客观的形而上的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儒家的天理是追源天命、流衍无穷、体仁继善、人物均润。道家的天道是涵养生命、大方无隅,大公无私、自由平等。所以这里所谓和谐、天人合一就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就是美的最高境界。中国哲学、美学讲的真,是合目的性的真,而不是西方的天人对立、真善分隔,体现出对人的欲望和需要的规范和提升,对扭曲人性的权利和金钱的拒斥。提倡以天合人,以人合天,天人和合,这是社会的至境,是人性的至境,也是艺术的至境。
儒家、道家虽然对艺术本性的理解有差异,但对艺术的本性就是和谐这一点是共同的。儒家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的情与理的适度原则。儒家的经典《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乐礼》也有这样的意思:“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都强调和须中节、和而有序的“中和”思想。在艺术观念上,要求坚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以礼节情、情理相宜的表现原则。道家的和谐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通向生命体悟的协调原则。道家推崇自然,其中包含着对儒家道德理性的批判,主张道法自然、物我一体,涤除玄鉴,澄怀观道,追求一种更深刻更自由的精神和谐,即“天和”。天和就是至美至乐的人生体验。庄子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谓之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也,谓之人乐;与天和者也,谓之天乐。”[5](P458)庄子的哲学可以说就是审美哲学,他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天和达到天乐、人乐,这就是无待无我的“游”的精神,就是超越一切名缰利锁而实现的人的精神的真正自由,也是审美和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可以看出,无论儒家、道家(后来还有佛教的禅宗)提倡的和谐观念一直是中国古代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国艺术史的许多卓然大家,莫不是追求这种艺术观念,才创造出流芳百世的作品的。所以,和谐的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观念和艺术创作所发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造就了中国艺术、艺术理论在世界艺术格局中独具一格的品性。
三、和谐艺术观念的转换与延异
从20世纪开始,中国思想文化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使中国文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断裂。西方以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全新的思想观念为这个古老民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域。中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民主、科学成为最响亮的口号。中国人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这里所说的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思想观念,自由平等的社会意识、自由独立的公民意识、客观无私的理性思维是其根本精神。
在中国古代和谐、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中,天作为自然理性、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彻底对象化、客体化,未真正形成西方那种形而上的本体论思想。如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思考世界的本体,是火、是数、是理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哲学流派。而中国的哲人从人的需要的角度,从生存的目的来感受对象,“道”与“德”是一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中国人在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价值观念,是一种伦理哲学。仁义道德是自然之性,也是人的本然之性,人和自然是浑然一体的。相应地,人也未像西方人一样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主义观念。《礼记·中庸》指出:“人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老子认为,“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对主体要“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人自身并未获得独立的价值,不重视个人情感欲望的表现,不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古代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出严重的保守僵化的历史惰性,对人的创造性的压抑,对人的自由张扬的个性的阉割,这些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对传统文化毫不留情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必修课。今天,在国学热潮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冷静的态度,看看我们电影电视中那些古装、历史题材的作品,表现出的那种正统思想、极权主义思想难道不应该叫人警觉吗?
德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曾独创了一个词——“延异”(也有译成“异延”、“分延”的),其想法主要是把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不确定性推到极致,其意思是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的时间或文化背景下,其内涵是发展变化的。德里达曾指出,意义只有在如下情况才能产生:存在一个在场感,并且和曾经过去的、即将来到的几乎无限的可能性相互联系。我感到这种阐释思想对于我们把握和理解和谐并转换这一范畴具有启示意义。和谐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文化语境已经“退场”甚至“缺席”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也已解体了。100多年以来西风渐进,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观念已经是主观/客观、本质/现象、物质/精神这样的二元对立、天人分裂。当代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但是现在也显露出其局限和盲点,如工具主义、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导致的异化、陌生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导致的生态失衡、能源危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天人分裂的倾向已经很明显,天的形而上的性质被突出了,成为自然理性、历史理性,再不具有人性的关怀,真与善分裂了,成为一种玄远而冰冷的规律和制度。天的另一含义——人的天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孟子·尽心上》),则失去了真(历史理性、社会理性)的规范和制约,变得猥琐卑下、自私贪婪、急功近利。善与真分裂了。这种分裂,可能就是中国人性道德的一种现状,可能就是失去原来传统的“和谐”之后走向新的“和谐”之际的阵痛。现在,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古代的和谐观念当做旗帜来挥舞,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其所包含的精神畸形。因为国人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应不断提升,自由民主的观念应不断加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国人的对象性意识要不断提高,树立理性思维、科学精神,不断发展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是在更高层次上超越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也超越西方天人对立的观念,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状态的天人合一——和谐。
对于中国古代“和谐”的文艺观念也作如是理解。今天,我们的艺术观念、艺术理论、研究方法莫不受到全球化的冲击。我们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所运用的基本是西方的观念、范畴,所以20世纪90年代才有一些学人惊呼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失语症”。的确西方文化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一方面,西方的文艺理论以其概念明确、逻辑严密、体系完备见长,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难以匹敌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显现出的西方文艺理论难以达到的深刻、贴切的感性优势,恰恰极深刻地体现出人类的艺术活动不是一种简单的理性思维活动。对这种感受性、体验性极强的精神活动用抽象的概念、严密的推理并不能曲尽其妙,语言符号、结构形式只能摹其形貌,不能窥其堂奥。宋代严羽就明确指出,艺术作品的意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是“非关书”、“非关理”的。中国艺术理论概念的模糊表达有时恰是最精深的表达。所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仍以其独到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见长。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来提升和转换、来完善和发展我们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话语和体系,这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开掘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美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来丰富和完善人类艺术理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是一切艺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之,对于“和谐”,作为一种文艺思想、艺术观念,我们必须重新来检讨其内涵,促成其转换,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思想观念、人生价值的一种表现,与今天的社会生活,与当代人的精神追求、人生理想相去甚远。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生活、艺术发展的需要,填充其内涵,使其以更具生命力的思想观念来表现我们今天的人生愿望和艺术追求。实际上,不少学人在这方面已作了很多努力。如“意境”这一中国美学、艺术理论的范畴,已经被国内一些美学、艺术理论教材列专章来探讨、研究。对于“和谐”这一更基本的重要范畴,我们虽然常会论及,但对其内涵的分析与检讨、提升与转换,还未曾真正展开,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本文只是从宏观上对和谐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梳理、思考,疏而不密,思而不精,具以求教于方家,以促成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1]修海林.古乐的沉浮[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
[2]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方东美.方东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5]郭庆藩.庄子集释(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4.
I206.2
A
1007-905X(2011)03-0139-12
2011-02-10
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科研项目(ZK082)
寸悟(1949— ),男,陕西凤翔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