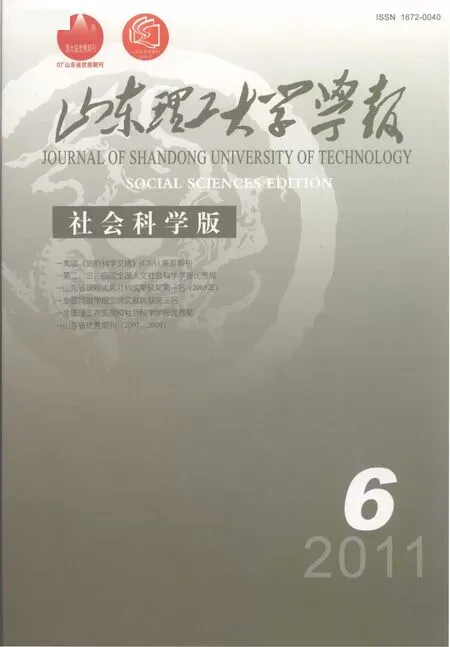从边缘到中心:第六代导演的皈依之路
贾梦,张玉霞
(1.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北京100024;2.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从边缘到中心:第六代导演的皈依之路
贾梦1,张玉霞2
(1.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北京100024;2.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第六代导演刚登上中国电影舞台时,在体制内很难获得拍摄影片的机会,为了进行拍片实践,他们不得不走过一段长时间的“地下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他们的影片大都具有一种边缘化的色彩。待经历了一段“地下时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声誉后,他们又思考如何获得体制的认可,研究观众的接受心理,拍摄观众乐于接受的影片,让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认可他们的电影。由此,从边缘到中心,第六代导演走了一条艰难的皈依之路。
第六代导演;边缘;中心;电影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影坛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批风格独特的年轻导演绕开中国电影的既定规则,另辟蹊径,自成佳境。学术界给予了不少关注,对这一电影现象,目前学术界大体有两种意见,黄式宪、郑洞天、戴锦华、林少雄等人称其为“第六代”导演,倪震、尹鸿、贾磊磊等人称其为“新生代”导演。笔者在这里也采用“第六代导演”这个称谓。一般认为,第六代导演是以北京电影学院85、87届学生为主体,包括中央戏剧学院部分毕业生在内的电影导演群体,有人认为也应该把一些拍摄纪录片的创作者归入第六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包含的范围也在逐渐增大,如北京电影学院93级的贾樟柯也被划入这个群体。
张元的《妈妈》拉开了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序幕,自此出现了大量的“第六代”影片,如张元的《北京杂种》,胡雪杨的《留守女士》,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娄烨的《苏州河》、《西施眼》,管虎的《头发乱了》,路学长的《长大成人》、《非常夏日》,张扬的《过年回家》、《洗澡》,贾樟柯的《小武》、《任逍遥》、《站台》、《世界》、《三峡好人》,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扁担·姑娘》、《极度寒冷》、《十七岁的单车》,金琛的《网络时代的爱情》,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王全安的《月蚀》、《图雅的婚事》,等等。
一、边缘化书写
第六代导演显然没有第五代导演那样幸运。他们登上电影创作舞台时大部分人都没有享受到体制的便利,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没有获得进入电影厂的机会,有的即使是进入电影制片厂,由于第五代导演创作的繁盛,他们也很难获得独立拍片的机会;加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政治、社会领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国家对于电影事业的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又分流了大批的电影观众。第六代导演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拍摄影片的问题。因为没有名气和经验的他们获得电影制片厂投资拍片的机会很小,国家也不可能拿出钱资助。最终,他们只能采取一种别样的方式:独立制片或者称为地下制片。“地下制片”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早期,第六代导演拍摄的大部分影片都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种“地下活动”,第六代导演得以进行拍片实践,并且通过国际影展,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如张元的《妈妈》获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这次获奖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对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类似于第五代导演早期的境遇,他们也开始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创作之旅,同时他们由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感也在发生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不仅认同西方国家的文化,而且对于西方人所认同的东方文化也持赞同态度)。中国的电影观众也逐渐开始关注第六代导演。
二、边缘的表现
(一)边缘人物书写边缘镜像
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具有一种“边缘化”倾向,这种边缘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影片内容上。他们的电影一般是以城镇为背景的,但在影片中出现的又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高楼大厦、便利的交通、繁华的商场、舒适的住所,而是人们很少注意的杂乱的建筑工地、拆迁中的楼房、肮脏的旅馆等。影片中的人物角色,也选择了小偷、妓女、摇滚歌手、智障儿童等,多为以前电影中所不常见的生存于城市边缘的人物形象。这些镜像的出现与第六代导演的特殊身份有着密切关系。第六代导演登上中国电影舞台之初,是地地道道的“边缘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国家电影体制,即使是少数进入体制之内的导演,也很难获得独立拍片的机会,就更不用说获得国家的资金了。作为导演群体中的边缘角色,第六代导演一旦获得拍片的机会,就必然会在影片中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情感与见解,用一种边缘的视角来表现边缘人物、边缘场景及特殊情感。影片中这些边缘人物正是第六代导演用以表达自我的一些特殊符号,“第六代中很大一部分人自己处在社会的边缘,在他们的作品中透射了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1]张元《妈妈》中的智障儿童,《小武》中的妓女、小偷,《北京杂种》中的地下摇滚乐手,这些人物都处在社会的边缘,很少有人来关注他们。第六代导演却将这些人物角色作为影片叙事的中心,并且在表现这些人物时,大都展现了他们生存中不幸的一面,这也正是第六代导演边缘生存状态的再现。
(二)边缘冲击中心的张力
第六代导演也把表现边缘人物和边缘场景的创作方法作为突破第五代导演的一种方式。第六代导演曾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电影需要一批新的电影制作者”,[2]26这批新的电影制作者当然指的就是他们自己。作为享受着“特殊权力”的人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占有着常人难以获得的资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这个中国唯一的电影专业院校。他们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期待:将来成为中国新一代的电影导演。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又不是边缘角色,而是地道的中心人物,至少可以说是中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作为中心的边缘部分,第六代导演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个团体中很少有发言权,很难获得拍电影的机会,只能采取独立制片的形式来进行影片拍摄。张元筹集到了资金,拍摄完成了《妈妈》,贾樟柯、王小帅等人同样也是用这种方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妈妈》表现的是被人遗弃的妇女和她的智障儿子的故事;《小武》描写的是关于小偷小武的爱情、亲情和友情的故事;《北京杂种》讲述的是地下摇滚歌手的生活状态。第六代导演抛弃宏大的历史结构,将关注点转向日常人物,是对第五代导演宏大叙事的一种反叛。第六代导演采取这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创作风格,来突破第五代导演架设在他们面前的障碍。作为对中心的冲击,第六代导演早期的创作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国际上频繁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不幸的是,早期很多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在国内无法获得公映的机会。可以说第六代早期的电影是以牺牲体制认可的代价来换取生存的空间。
三、关于边缘的解读
(一)纪实的边缘,而非真实的边缘
很多学者称第六代导演的拍摄手法为纪实主义手法。这与第六代导演经常运用的长镜头的处理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长镜头的纪实性造就了一种真实的感觉,但笔者在这里却要强调另一点:纪实不等于真实。王海鸰在《大校的女儿》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把一个人七年的错误、毛病一一挑出来做一种片断组合,这人当然是一坏人;但要是做一种相反方向的组合呢?结论就会截然不同。传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人一辈子没有谁能做到只做好事或只做坏事。片断组合法高明就高明在,既可达到目的,又能保证句句属实。”第六代导演也是在运用这种特殊的组合方法,他们将某些边缘人物不幸的一面集中起来做片断组合,这种片段组合表现出了边缘人的某些生活侧面,但却蒙蔽了其他的侧面。如果一部影片只表现出其中的一个方面,那这部影片可能是纪实的,但却很难是真实的。这其实包含着导演的一种倾向性,“在我看来,影像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你的世界观,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不管你跟世界抱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所作的实验,冷漠的或是热情的,僵化的还是生动的,都会泄漏作者的动机”。[3]238第六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中,大多都表现了边缘人的不幸或无奈。《北京杂种》中的地下摇滚歌手不停地居无定所,《小武》中小偷爱情、亲情、友情的丧失,《安阳婴儿》中下岗工人的落魄、黑社会老大的身患绝症,等等,都是在表现边缘人物的不幸或者无奈。将边缘人不幸的片断组合起来就表现出了边缘人的不幸,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是第六代导演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的感悟,表现了他们的边缘化视角。当然,通过这种视角反映出来的影像不等同于真实的世界,边缘人物也并不是真实的边缘人物。
(二)对于“东方主义”视野的迎合
关于第六代导演关注的大都是边缘人这一问题,有学者曾指出第六代导演也如第五代导演那样是在迎合西方的期待。戴锦华认为:“一如张艺谋和张艺谋式的电影提供并丰富了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镜像;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再次作为‘他者’,被用以补足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先在的、对90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4]407在西方有一种“东方主义”的理论,所谓“东方主义”并不是东方实实在在的景象,而是西方人对于东方的一种独特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很多时候是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他们眼中,东方还是落后的、不发达的、不民主的。第六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中大量出现了破败的场面和摇滚乐手、小偷、妓女等边缘人物形象,这些镜头的出现正迎合了“东方主义”者的期待。另一方面,西方人对于地理名称的命名也是有意味的,“后殖民理论家发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语言,发现了‘远东’、‘近东’、‘中东’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5]近东、中东、远东的划分是西方根据距离的远近而划分的,而处在远东地区的中国当然是边缘的。在边缘的世界里西方人所乐于看到的当然就是边缘的景象。第六代电影中大量出现的边缘人物:小偷、妓女、民工、地下摇滚歌手、街头流氓等等正是边缘景象的理想阐释。当西方人看到的景象与预想的景象一致时,就觉得这些影片是好的,应该来看一看,甚至是投它一票让它获奖。这种评奖策略的实施,一方面是对影片水平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于中国电影导演做大电影产业的一种麻痹。这种麻痹导致的结果就是,“当时的态势正是几乎所有的外国电影和大公司正竭力进占充满潜力的中国电影市场,而一些‘第六代’却与此走出了相反的路线”。[6]186
四、艰难的皈依之路:向中心靠拢
第六代导演通过自己特殊的地下时期,一方面已经在国际上大有收获,在国内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当时几乎所有的外国电影和大公司正竭力进入并占领中国电影市场,这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于是,如何获得国内观众的广泛认可并占领中国本土市场,就是摆着第六代导演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毕竟我们的电影是为中国观众拍的,为的是给国内观众看”。[2]26
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反叛或出走只是他们获得生存的一个权宜之计。他们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在第五代导演垄断中国电影市场的情况下获得一线生存的机会,他们选择的也正如第五代导演早期曾做过的那样,由国外向国内渗透。第五代导演采取那种策略正当其时。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民族的自卑情绪,认为西方的东西就是好的。第五代导演也正是抓住了观众的这一心理,拍摄了一些能够迎合西方期待的影片,结果在西方大受欢迎并能够频频获奖,其中张艺谋是获奖大户,陈凯歌在西方也多次获得大奖。第六代导演初登中国电影舞台,自然受到了前辈们的影响。通过由国外向国内渗透的方式,第六代导演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效果已经很难与第五代导演比肩了。因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人们的心理也由80年代末的自卑逐渐转向自尊。另外,“墙内开花墙外香”、由外而内的策略是第五代导演炒过的冷饭,再来拿它做文章,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国内,从本土做起,抓住中国的观众。而要抓住中国的观众,首先必须能够获得公映的机会,“没有一个导演希望自己的电影仅以纸质媒介来传递,不能在影院上映自己的影片的确是一个折磨人的事”,[3]272这就必然要与国家的有关的电影管理部门发生联系。而这些部门又是第六代导演在早期所“得罪过”的部门,但当时“得罪”这些部门主要是程序上的问题,影片的内容基本上不是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比较优秀的所谓中国地下电影,很多都具有一种探索现在的人们存在价值的精神,构不成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6]129因此,当第六代电影在程序上渐渐向电影体制靠拢时,相关部门也表达出了一定的宽容和理解。
对于国家电影体制来说,不仅不会拒绝第六代导演的皈依,而且还欢迎第六代导演的皈依。因为,体制外操作对体制的尊严来说是一种威胁,而且体制外制作的电影在内容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对于体制不利的或不良的内容,所以,中国电影从体制上也实施了一些促成第六代导演皈依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演进和电影管理部门的主动努力,多数第六代导演与体制的关系已不再是剑拔弩张,张元、贾樟柯、王小帅分别在1999年和2004年被电影局恢复了导演资格。其间被解禁的还包括因《苏州河》获禁的娄烨”。[7]得到体制的认同,第六代导演的回归总算完成了一个阶段。但在第六代导演面前有个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吸引中国广大的观众来观看他们拍摄的影片,这才是回归过程中他们所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皈依后,王小帅拍摄了《十七岁的单车》,“只是遗憾的是,回归后的这次创作,还没有产生影响。这使一些‘第六代’的个人创作道路,再次增加了某些不确定性”。[6]194
如何获得观众,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导演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使是大师也需要赢得观众的认同,否则就会影响自己的创作。摆在第六代导演面前的同样也是这个重要的命题。同时,电影的制作往往需要大量的投资,资本的属性决定了电影投资者必定会注重电影的利润。利润的获得和观众的数量一般来说是成正比的,因此如何获得最大数量的观众就是电影的投资人最为关注的。这对于习惯于拍摄个人化电影的第六代导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他们的影片在很多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但“由于影展的评委只有十几或几十人,而且教育程度较高,满足他们的口味主要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以及艺术水准两方面”。[8]244然而当要面对广大普通观众时,就必须要考察好观众的审美欲求,生产适合观众审美口味的电影。在当前环境下,能反映观众的生活,能使他们在观看时获得解脱、净化、放松、娱乐的电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毕竟“电影已经沦落为‘风尘’,成为‘堕落天使’。观众买票进入电影院,首要需求是消遣、娱乐、寻找梦幻”。[9]83而第六代导演执导的大部分影片都不能提供这种体验。第六代电影中的很多场面不够壮观、好看,也没有大牌明星的加盟,故事也多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虽然说思想上有一定的深度,对生活也给予了深刻的反思,但主题的沉重性、形式上的粗糙往往使观众望而却步。因此观众也就不太愿意买票进电影院观看第六代导演拍摄的电影。这对于作为产业来说的电影就是不利的,毕竟电影不单单是一门艺术,它还是一种产业。第六代导演中的一些人还沉浸在艺术电影或个人电影的创作道路中,很难走出来。但我们也看到了第六代导演群也在分化,一些导演开始尝试拍摄商业电影,路学长拍摄了电影《卡拉是条狗》,获得了近千万的票房收入。路学长聘请了葛优、夏雨等明星,是影片的一大看点。影片将视角对准了北京的一个普通人老二,影片中既有世俗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充满了爱心和人情味。影片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烦恼,又表现了他简单的快乐和幸福。观众在电影中多少找到了类似于自己生活的痕迹,因此这部影片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卡拉是条狗》的这些做法是值得其他第六代导演借鉴的。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要去适应观众的口味,才能真正占领中国电影市场。
[1] 吕晓明.90年代中国电影景观之一——“第六代”及其质疑[J].电影艺术,1999,(3).
[2] 陈犀禾,石川.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3] 程青松.看得见的影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4] 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张建军.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6] 吴小丽,徐甡民.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7] 侯庚洋.流变中的第六代[J].艺术评论,2006,(12).
[8] 周黎明.好莱坞启示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9] 陈晓云.中国当代电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J90
A
1672-0040(2011)06-0075-04
2011-09-07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金项目“影视艺术与文学比较研究”(06BWZ004)的相关研究成果。
贾梦(1987—),女,山东淄博人,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艺术研究。
(责任编辑 杨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