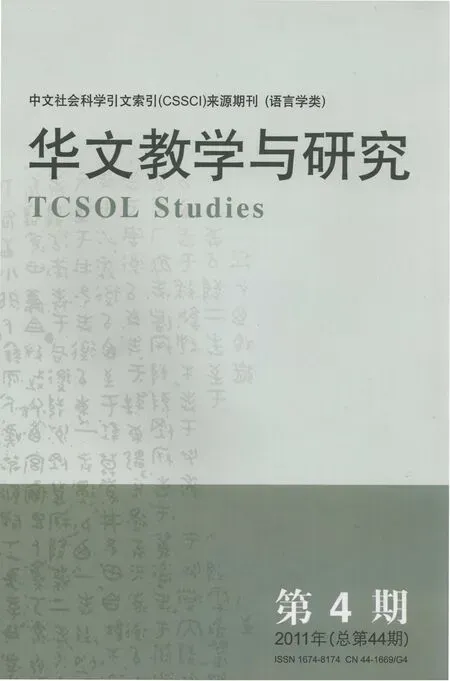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刍论①②
刘 慧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10)
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刍论①②
刘 慧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10)
现代汉语;评价系统;评价项;层次性
以往关于汉语评价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微观,在全局观和系统性方面存在不足。本文运用语言学相关理论,在界定“评价”概念、概括“评价”特征的基础上,初步勾勒出现代汉语评价系统的面貌。该系统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系统,主要由词汇层、话语标记层、句子层和语篇层评价项构成。
1.引言
从广义视角来看,评价是人类对自身及外界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具有多大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评定的活动。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1987)曾经说过,“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这里的“赋予事物以价值”正是人类对事物作出评价,探索意义的过程。
语言是评价表达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Hunston等学者 (1999)曾指出,评价语言在反映说话人的看法,表达说话人及所在团体的价值观、建立和维持说写者和听读者间的关系、组织语篇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外语言学界,加拿大语言学家Martin J.R.和澳大利亚语言学家White P.R.R.(2005)从语篇语义学的视角研究了英语的评价系统,俄国语言学家在语义、语用等领域考察了俄语的评价系统。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蕴含着一个复杂的评价系统。汉语语言学界的前辈时贤对现代汉语中的评价表达进行过专题研究,如赵元任 (1968)将副词分成九类,其中一类就是“表评价的副词 (adverbs of evaluation)”。朱德熙 (1981)指出“值得,配”都有“表示估价”的作用。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对象和成果大多较为零散,缺乏全局观和系统性。本文将对汉语语言学领域的“评价”概念进行界定,分析归纳“评价”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零散而丰富的评价性语言资源进行整合,初步勾勒出现代汉语评价系统的整体面貌。
2.“评价”的界定及其特征
哲学领域的“评价”是“人把握客体对人的意义、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冯平,1995),参考哲学中“评价”的定义,刘慧 (2011)将“评价”界定为作为评价主体的说写者对评价客体的主观价值判断,及评价主体所体现出的情感和态度③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情感”是指人脑对客观现实与个人需要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是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而产生的主观体验和评价,“态度”是对外界刺激形成总体评价与稳定的反应倾向 (周家骥等,2002)。可见评价主体的主观情感和态度也属于评价的组成部分。。其中“主观价值判断”体现为下文所述评价的价值负载性,而“评价客体”包括人、客观事物、命题、主张、想法等具体和抽象的对象。
刘慧 (2011)对语言学领域的“评价”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评价”最显著的特征是“主观性”,因为评价的实施与评价主体的主观把握和判断密切相关。“主观性”之下又可细分为五小类:表述性、价值负载性、比较性、相对性、层级性,这五方面共同构成了“评价”的特征。
根据评价客体的差异,评价“表述性”的体现方式主要有两种。当评价客体为某种事物,“表述性”表现为对此事物属性的主观概括和表达,如“老张家的姑娘不但长得漂亮,还勤劳能干”一句中,说话人针对评价客体“老张家的姑娘”的外貌特点和内在品质,分别用“漂亮”及“勤劳能干”进行主观概括和表达;当评价客体为某种主张、想法或命题,“表述性”表现为对其的主观看法和情态,如“他确实是个好人”一句中,说话人用副词“确实”对命题“他是个好人”进行确认性评价,同时表达了说话人的态度和立场。
评价的“价值负载性”指的是评价结果体现了评价主体在“好-坏”、“真-假”、“善-恶”等方面所做出的价值判断。Hunston等 (1999)将“价值负载性”概括为四类: “好-坏” (goodbad)、确定性 (certainty)、期待性 (expectedness)、重要性 (importance),统称为“评价参数”(parameters of evaluation)。
评价的“比较性”指评价的实施须依赖评价标准。评价标准既可以是具体的评价参照体,也可以是抽象的评价指标。美国社会语言学家William Labov(1972a)曾指出,比较性是评价的重要特征,评价结果是评价主体将评价标准与评价客体相比较而得出的。
评价的“相对性”指的是,应用不同评价标准对同一评价客体做出评价,或是不同评价主体基于不同视角对同一评价客体做出评价,所得出的评价结果是不尽相同的。因而评价行为的实施和评价结果的表达是相对的。
评价的“层级性”指评价结果一方面包含着评价主体对客体属性的主观判断,同时也包含着对属性程度量的主观表达。如William Labov(1972b)所提及的英语副词和形容词的比较级及最高级。评价“层级性”的另一佐证是,汉语中“他难过”、“这件衣服贵”等主语加上光杆形容词的句子在句法上不成立,使其合法的途径之一就是在形容词前加上表程度量的副词如“比较、很、非常、特别”等,使其成为具有层级性的评价句。
国外语言学界在评价系统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对我们描绘和勾勒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在英语评价系统的研究方面,Martin和White(2005)首先将其分为“介入”、“态度”、“级差”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下又划分为若干小类。此项成果填补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人际意义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空白,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词汇层面;对子系统的划分缺乏理论依据,子系统一些成员存在交叉;“介入”子系统分类过繁,界限也不够清晰 (刘世铸,2010)。
从整体来看,现代汉语评价系统体现出层次性的特征。索绪尔 (1980)强调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些符号不是散乱地堆积在一起,同层的语言符号单位在形成线性组合关系的同时,还共同参与构成更高一级的单位,体现出较强的层次性。现代汉语评价系统是由各级语言单位有序组合而成,成员包括词汇、话语标记、句子、语篇,我们将其称之为“评价项”,其所包含的评价意义为“评价义”,各层“评价项”及“评价义”共同参与构成了一个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现代汉语评价系统。
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另一重要特征体现在其内部成员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在划分典型性与否的标准上,我们以能否明晰表达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情态为标准,如果某一层级的评价项能明确表达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或主观情态,就是典型评价项,否则就是非典型评价项。之所以设立这样的判断标准,是考虑到一个完整的评价结构通常包括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标准、评价结果四部分,其中评价结果是评价主体依照评价标准对评价客体所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包含着评价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主观情态。评价结果集中体现了“评价”五方面的特征,是评价结构中最为重要、最受关注的要素。其他评价要素如评价主客体和评价标准,虽然也是评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但主要是为得出评价结果服务的。
3.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各层评价项特点分析
按照语言单位的层级排列,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可依次分为词汇层、句子层、话语标记层、语篇层评价项。各层评价项的构成及特点如下所示:
3.1 词汇层评价项的构成及特点
3.1.1 典型评价性词汇
依照能否明晰表达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情态,我们对词汇层评价项进行了划分,其中的典型评价项包括评价性形容词、评价性副词、评价性动词、叹词。
1)评价性形容词
形容词概括表达的是人及事物的性质和状态。我们在依照前文所提到的标准的同时,还利用“VA了”作为验证框架,根据马真、陆俭明 (1997a,1997b)的研究,“VA了”述补结构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4种:①预期结果的实现;②非理想结果的出现;③自然结果的出现;④预期结果的偏离。其中的“A”即形容词的评价性对该结构的语法意义有明显的影响。如果“A”是积极性评价形容词,它只能表示语法意义①和③,不能表示语法意义②和④。如“做对了”表示的是①义,“变聪明了”表示的是③义。如果“A”是消极性评价形容词,它只能表示语法意义②和③,不能表示①和④。如“弄乱了”表示的是②义,“发臭了”表示的是③义。如果“A”是非评价形容词,它可以表示除②之外的其它三种语法意义,如 “(那堵墙)砌高了”可以兼表①义和④义,“(他)长高了”表示的是③义。我们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根据形容词进入“VA了”结构之后表示的不同语法意义,可以鉴别形容词是否具有评价性、具有何种评价性。
验证结果显示,一些表达颜色、空间、度量等客观属性的单音节形容词如“高、矮、细、粗、空、满”等可归入非评价形容词。除此之外,大多数形容词都具有评价义,能够直接、明晰地表达评价结果。其中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如“好、坏、美、丑”等,双音节形容词如“聪明、愚蠢、庸俗、高雅”等。一些评价性形容词词义可以分析成“程度量+性质义”,如积极性的“英勇”和消极性的“愚蠢”所包含的程度量比“勇敢”、“笨”所表示的标准属性值更高。还有部分成员如“壮丽、富强”等,词形上是两个单音节形容词性语素的组合,但它不仅仅是两种属性的叠加,还产生了两种属性在程度量上的增值。当评价性形容词位于非谓位置,如主语之前的定语位置时,其评价辖域限于主语部分,无法使整句具有评价功能,如“愚蠢的敌人被我们包围了”。当评价性形容词位于谓语位置时,其评价辖域可以延伸至整个句子,这类句子多为评价句,如“那些敌人非常愚蠢。”
2)评价性副词
能够明确体现说话人主观情态及价值判断的副词都可以归入“评价性副词”。按照评价辖域的大小和词义的虚实,可以分为“实义评价副词”和“虚义评价副词”,前者比后者的词义实在,评价辖域比后者小。“实义评价副词”如:
(1)(联信公司)自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业务一直稳步增长。
(2)考官没买他的账,还是秉公办事,让陆游中了第一名。
上述两例中的“稳步”和“秉公”在句中作状语,对评价客体“联信公司”和“考官”的动作行为做出了积极性评价,这类副词还有“蓄意、擅自”等,它们的词义较为实在,常位于形容词或动词之前,评价辖域是其后的谓语部分,不能位于句首。
“虚义评价副词”的句法位置较为灵活,既可以位于句首也可以位于句中,表达评价主体的主观情态,或是对句中的评价客体进行价值判断。这类词构成了“评价性副词”的主体,赵元任(1968)所指出的“表示评价的副词 (adverbs of evaluation)”指的就是这一类副词。如下所示:
(3)他心中马上想明白:怪不得人们往城里逃,四处还都在打仗啊!
(4)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他才变好,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他都弄糟。
(5)幸亏我是个达观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
上述三例中加点的副词“怪不得”和“幸亏”,既可以位于句首也可以位于句中,“怪不得”所针对的评价对象是小句“人们往城里跑”,表达了说话人一种恍悟的主观情态。例 (4)和例 (5)中的副词“幸亏”既对其后子句所包含的条件“有了他”或命题“我是个达观的人”进行积极性评价,也表达了评价主体一种庆幸的主观情态。
3)评价性动词
评价性动词按照评价特点可以分为三小类,其中第一小类明确表达了评价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动作性也较强。该小类动词中所包含的动作发出者多在句中,而评价主体即说写者多在句外。从语义的角度来看,消极性动作类动词可以分为很多种。如:①说写者认为动作施事的行为超过了合理的度。如“滥用、贪图、纵容、苛求”等;②说写者认为动作施事过于抬高自己。如“逞能、摆阔、吹嘘、夸耀”等;③说写者认为动作施事用言行取悦对方。如“谄媚、巴结、吹捧”等。积极类动词也可以分为若干小类。如:①“对动作行为特点的评价结果+行为”类的“完胜、彻悟、奇袭、妙用”等;②“对施事情态的评价结果+行为”类的“畅谈、欢唱、善待”等。
第二小类评价性动词是能愿动词,也称为“助动词”,如“能、会、要、应该”等,集中体现了评价主体的主观情态。齐沪扬 (2002)指出助动词常被看作意志语气类别中的形式标志,并将“意志语气”界定为一种按照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态度和情感所划分出的语气类别,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彭利贞 (2007)依照能愿动词后搭配对象的不同,将情态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类,前者在句中表现为能愿动词与动态动词的搭配,常用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和立场;后者表现为能愿动词与静态动词的搭配,常用来表达确认性评价。
第三小类评价性动词是心理动词,也就是吕叔湘 (1942)所指的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如“爱、怨、恨、悔、害怕、感激”等,较为明确地表达了评价主体的主观情感。与能愿动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动词的语法化程度低于能愿动词,其评价主体多为句中主语,而能愿动词的评价主体多为说话人。
4)叹词
叹词多用于口语,集中体现出说话人较为强烈的主观情态,音高变化非常灵活。如叹词“嗬”可表惊讶、“唉”可表感伤或惋惜、“哎呀”可表埋怨或不耐烦等情态。杨树森 (2006)指出叹词常独用,很少入句,可作为独词类感叹句表达惊讶、赞叹等主观情态。
3.1.2 非典型评价性词汇
词汇层的非典型评价项虽然也包含着一些评价要素,但是其无法独立而明晰地表达出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或主观情态,需要和其他词语一起才能完成表达。这类成员主要包括:带评价义的名词、认证义动词、程度副词、带评价义的量词、语气词。
带评价义的名词指的是词语中包含评价客体、评价结果等评价要素的名词,尽管这些评价活动要素无法改变名词表指称的基本功能,但它们的存在使得名词词义中包含了评价义的成分。与完全不带评价义的名词如“地板、大树、灯光、茶叶”等相比,带评价义名词在内部结构、句法及语用特点方面具有一些不同之处。
从评价要素的视角来看,带评价义名词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若干小类。其中数量较多的如:①“评价结果+评价客体”类,消极性的如“泼妇、酷吏、暴政、丑行”等,积极性的如“淑女、精兵、胜地、妙计”等;②“评价结果”类,消极性的如“恶棍、坏蛋”;积极性的如“佳丽、瑰宝、英豪”等;此外,还有一类比喻义具有评价性的名词,消极性的如“铁公鸡、老油条、朽木、破鞋”等,积极性的如“活地图、老黄牛、泰斗、栋梁”等,这些词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文化色彩。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典型评价性动词以外,还有一类“认证义动词” (方梅,2005),如“想、看、觉得/觉着”等,作为标志性动词引导评价句的出现,但其本身不能表达主观价值判断或评价主体的情态,所以我们将其归入非典型评价词语。方文指出,这类动词语义已经高度虚化,成为表示评价的语用标记。这类动词的动作性很弱,且必须与包含评价客体和评价结果的小句相伴出现。如“他很帅,我觉得”和“我看这件事错不在他”两个例句中,认证义动词“觉得”和“看”与评价客体“他、这件事”及评价结果“很帅、错不在他”同现,否则句义表达不完整。此外,判断动词“是”也是常规评价句的标志词,有学者称之为评价句中的“铰链词 (hinge)”(Hunston等,1999)。
程度副词常与形容词搭配,共同表达评价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大部分程度副词既可以修饰积极性评价词语,如“花岗岩的颜色非常美丽”;也可以修饰消极性评价词语,如“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也有部分程度副词如“极、透、死、坏”常修饰消极性评价词。以往观点认为“绝顶”、“透顶”常分别与褒义词及贬义词语搭配,张谊生 (2008)考察后指出,近年来“透顶”也逐渐和褒义词语搭配,表达积极性评价。
量词的基本功能是计称数量,但有少数成员由于高频搭配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的词语,产生了“褒化”或“贬化”现象,可以和句中其他词语搭配,共同表达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故称之为“带评价义的量词”。如名量词“员、位”修饰表人名词时带有表尊敬的积极评价色彩,“撮”放在表人名词前具有消极评价色彩,如“一小撮敌人”;动量词“顿、通、气”修饰动作行为时常带有消极评价色彩,如“一顿毒打、一通乱骂、瞎说一气”等。
语气词无法独立而明确地表达评价主体的主观情态,但是语气词可参与构成带有主观情态的固定格式,齐沪扬 (2002)指出,“X就X吧”可以表示说话人不介意或者不满意的态度、“V啊V啊”可以表示对动作程度量的高量评价。齐文还指出,一些非典型语气词如“也好、着呢”可用来表达评价主体容忍、夸张等主观情态。
3.2 话语标记层评价项的构成及特点
话语标记指序列上划分言语单位的依附成分,具有主观性和程序性等特点 (董秀芳,2007)。话语标记通常不具备词汇及语法意义,但其能明确反映出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在表达说话人交际意图、影响听话人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纳入现代汉语评价系统的典型成员。
汉语中有很多颇具特色的评价性话语标记。许多学者对这些评价性话语标记做了个案研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表赞同态度的话语标记“这不、可不”;表出乎说话人意料及提醒听话人注意的情态性话语标记“谁知道、别说”;表委婉指责的话语标记“不是我说 (你)”;表指责或抱怨的话语标记“你看你、你瞧你、都是你、真是的、别提 (了)”;表负面评价的话语标记“问题是”;表疑惑情态的话语标记“天知道”;表达反对及不耐烦情态的话语标记“好不好”等等。
话语标记在会话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使用模式及功能,交际策略、语体动因、主观化等因素在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对我们了解汉语评价系统形成的动因、机制等具有较大的启示和帮助。
3.3 句子层评价项的构成及特点
句子层评价项可简称为“评价句”。依据陆俭明 (2004)所归纳的句子意义及影响其产生的要素,我们将评价句分为三类:基于句式义的评价句、基于具体词汇意和抽象关系义的评价句、基于语气义的评价句。
基于句式义评价句也可称为“构式评价句”,其评价义主要来源于句子构式,是汉语中很有特点的一类评价句。表消极评价的句式如“NP一副X的样子”、“(X)整个一 (个)Y”、“NP为X而X”、“NP动不动 (就)VP”、“哪 (里/儿)是A,简直是B”、“都是+NP”等;既可以表积极评价也可以表消极评价的句式如“他这样做是X的”。表说话人主观情态的句式如“V也得V,不V也得V”、“NP爱V不V”、“A也不是,B也不是”等。
有学者指出汉语中表积极评价的句子远多于表消极评价的句子 (邹韶华,2001),可见消极评价句属于有标记格式。消极评价句为了遵循一些语用原则 (如礼貌原则)、突出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在格式、语序等方面与常规句式存在不同之处,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基于具体词汇意的评价句可分为“量性评价句”和“量质结合的评价句”两类。“量性评价句”是对事物量的大小进行主观评价的句子,句中表达主观量主要手段有句重音、副词如“就、才、都”等、语气助词如“而已、罢了”等 (陈小荷,1994)。“量质结合的评价句”是对事物的性质及性质所包含的程度量进行主观评价的句子。可归入量质结合的评价句的句子如:谓语部分分别包含述补结构如“穿大了、炒咸了”、“动词/形容词+程度补语”结构如“聪明得很、倒霉透顶”、“程度状语+动词/形容词”结构如“有点小、超帅、相当漂亮”的句子。
基于抽象关系义评价句的成员有比较句。“比较性”是评价的特征之一,而比较句是其在句子层面的重要体现。从语义角度来看,比较句的组成成分主要有比较主体、参照对象、比较结果三个部分,分别相当于评价结构中的评价客体、评价标准和评价结果。其中“比较结果”无论是由程度副词搭配形容词性词语充当,还是由心理动词或带有“数量变化”义的动词充当,都必须具有[+程度]的语义特征 (邵敬敏等,2002)。这些特点也与评价的“比较性”、“层级性”、“相对性”等特征相符,能明晰表达价值判断,属于典型评价句。
基于语气义的评价句主要包括感叹句和反问句。感叹句的主要作用是表达说写者的主观情态。与其他句类相比,感叹句表达情感的程度更强、方式更直接,是一种典型的评价句。相对比较句而言,感叹句的评价标准更主观,而比较句的评价标准更为固定、客观 (李成军,2005)。反问句在表否定的同时也带有说话人明显的情感态度 (张志公,1962;邵敬敏,1996),且否定与消极性评价之间具有无标记匹配性,因而也可归入基于语气义的评价句。
4.结语
本文在界定“评价”概念、概括“评价”特征的基础上,初步勾勒出了一个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具有层次性的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并重点对该系统的词汇层、句子层和话语标记层评价项进行了分类描写。本文的研究尚未涉及语篇,但语篇层评价项是现代汉语评价系统中最复杂也最能完整体现评价意义和功能的成员。语体动因对语篇评价意义和功能有着何种影响,典型和非典型的评价性语篇在结构和评价性词汇、句式分布等方面存在哪些异同,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此外,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进一步考察现代汉语评价系统中各级评价项之间的互动情况,如评价系统中词和句关系、句子和语篇的关系等,将个案研究和宏观思考相结合,力求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现代汉语语言形式与评价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
陈小荷 1994《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就”、“才”、“都”》,《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董秀芳 2007《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方 梅 2005《认证义谓宾动词的虚化——从谓宾动词到语用标记》,《中国语文》第6期。
冯 平 1995《评价论》,东方出版社。
李成军 2005《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刘 慧 2011《现代汉语评价系统研究述略》,《汉语学习》第4期。
刘世铸 2010《评价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外语与外语教学》第5期。
陆俭明 2004《“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中国语文》第5期。
吕叔湘 1942/1990《吕叔湘文集 (第1卷),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马 真 陆俭明 1997a《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汉语学习》第1期。
—— 1997b《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二),《汉语学习》第4期。
彭利贞 2007《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齐沪扬 2002《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安徽教育出版社。
邵敬敏 1996《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邵敬敏 刘 焱 2002《“比”字句强制性语义要求的句法表现》,《汉语学习》第5期。
索绪尔 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维特根斯坦 1987《文化与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
杨树森 2006《论象声词与叹词的差异性》,《中国语文》第3期。
张谊生 2008《“透顶”与“绝顶”的句法功能和搭配选择》,《语文研究》第4期。
张志公 1962/1997《语法学习讲话》,见《张志公汉语语法教学论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
赵元任 1968/2004《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赵元任全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周家骥 顾海根 卢家楣 2002《情感目标和评价的研究》,《心理科学》第6期。
朱德熙 1981/2004《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邹韶华 2001《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商务印书馆。
Hunston,S.& G.Thompson 1999 Evaluation in Text: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bov,W. 1972a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72b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Martin J.R.& P.R.R.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Evaluation System
Liu Hu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Jinan University/National Center for Oversea HUAYU Research,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10,China)
Modern Chinese;Evaluation System;appraisal items;features of class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Modern Chinese Evaluation are mostly scattered,lacking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ies.By adopting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structuralism,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this paper initially generalizes five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Evaluation System systematically.In this system,the form and meaning are combined and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s made,including word,marked clause,sentence and text.This paper has done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s of those typical and atypical appraisal i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and syntax functions.
H146
A
1674-8174(2011)04-0072-07
2011-05-18
刘慧 (1982-),女,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应用。
广东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现代汉语评价系统研究”(wym090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10JYB2077)
①感谢《华文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给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②本文中的语料如无特别注明,均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责任编辑 胡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