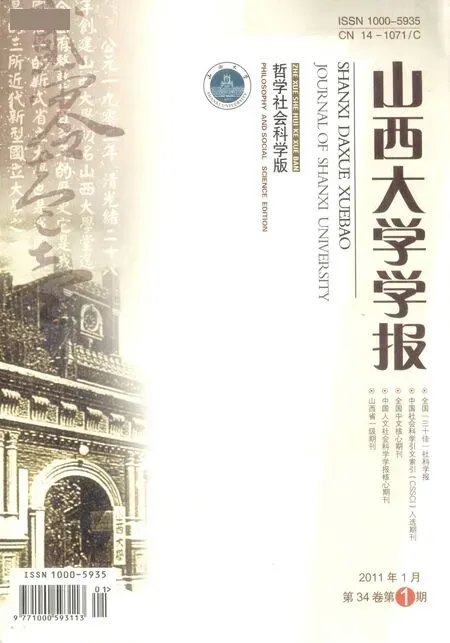论穆旦诗歌语言的隐喻性
叶琼琼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穆旦诗歌被推至经典地位,穆旦诗歌研究出现了大量优秀成果,但是关于穆旦诗歌语言的研究虽然起步早,却一直是个薄弱的区域,穆旦独特的诗歌思维方式与其诗歌语言之间的关系更是鲜有论者涉足。隐喻是人类最早最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可分割。本文试图运用语言学理论探讨穆旦诗歌隐喻思维方式与其诗歌语言之间的关系,以期弥补穆旦诗歌研究的空白。
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认知隐喻观”(CognitionView)与此前学说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类通过隐喻来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世界、想象世界,人类在隐喻中生存。认知隐喻观将隐喻研究进一步提升到了生命本体论的高度。正是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有的学者认为隐喻在语言世界的地位至高无上:隐喻可以解释一切语言现象,它赋予语言活力和生命,给予语言一个整体性的内核,构成语言内所有要素的约束力量,并贯穿于语言进化的始终。
当隐喻思维全面渗透进语言层面,它给穆旦诗歌语言带来三点特质:肉感、抽象、含混,三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一 肉感语言的隐喻
在语言最初的使用过程中,人们用身体来衡量万物命名万物。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当人们用身体去感知着客观世界时,身体以及身体感知便成为人类概念和语言的始源,也成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初的源泉。语言的意义源于人的主观认识,意义不能脱离身体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们是用身体以及与身体感觉有关的隐喻性语言来进行表达和思考的。
“用身体思考”正是穆旦诗歌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穆旦最擅长用身体感觉表达抽象的思考。王佐良首先在《一个中国诗人》中提出“用身体思考”这一为后来研究者广泛使用的著名论断。他这样评价穆旦“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所以存在是因为穆旦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就是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象里”,他还认为《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起来。他说《春》“出现了新的思辨,新的形象,总的效果是感性化,肉体化”,因此使得《春》“截然不同于千百首一般伤春咏怀之类的作品”。[1]无独有偶,袁可嘉也指出穆旦的诗的“肉感”特征,他对《诗八首》的评价是“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在穆旦那些最佳诗行里,形象和思想密不可分,比喻是大跨度的,富于暗示性,语言则锋利有力,这种现代化的程度确是新诗中少见的。”[2]
用肉体化的语言表达抽象思辨若追根溯源,其实正是现代派诗歌追求的一个诗歌理念。郑敏在《诗的魅力的来源》一文中指出“为抽象概念、哲学思维找到血肉之躯,将感性和理性有机地综合起来,是20世纪初英美现代派诗人和理论家庞德和艾略特都十分强调的一个诗的美学的革新运动。”[3]艾略特十分推崇17世纪初文艺复兴后期英国兴起的“玄学派”,“丁尼生和布朗宁都是诗人,他们思考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感觉他们的思想,像他们感觉一朵玫瑰花的香味那样,一个思想对于多恩来说就是一种感受,这个思想改变着他的情感。”[4]玄学诗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追求思想的知觉化和形象化,像感觉玫瑰花的香味那样感觉思想,也即是用身体思想。艾略特、奥登等诗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强调知性,即诗歌不是表达纯粹的抽象观念,而是要寻找观念的“客观对应物”,使观念物质化,使形象思想化。艾略特曾非常形象非常风趣地说:“写诗不仅要看进内心,还要看进大脑皮层、神经系统,还有消化道。”[5]无论是玄学派也好,现代派也好,他们的思想知觉化理念正是在隐喻的思维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这种用身体化、形象化的手法反映思想的做法正是一种隐喻思维。
穆旦身体的感觉十分敏锐,听觉的、视觉的、触觉的,种种最细微的感觉都能为穆旦捕捉。更绝的是穆旦常常能在身体体验和抽象玄思之间找到一般人很难以想象或察觉的类似点,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造出充满肉感的抽象化的语言。也就是说,身体感觉是隐喻的源域,抽象玄思是目标域,穆旦将身体感觉的特点、属性投射到目标域,从而使抽象、枯涩的思想变得具体形象、丰润饱满起来。
如《城市的舞》表现城市文明对现代人的挤压、阉割、异化。诗人采用身体语言将这个主题表现得十分新颖、形象、生动。第一节用“跳”“回旋”“动”等人体动词总写快节奏、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令人“昏眩”“郁热”,城市像一个钢筋铁骨的神,无所不能,掌控一切,而人,是渺小的,无力的,卑微的,小到如同一只寄生虫。第二节描写体制化生活对个性的压抑。作者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手部动词“切”,体制化生活就像一把刀,把人们“这样切,那样切”,切完以后还要“磨成统一颜色的细粉”,而不同意的个体呢,只有死去,而那些屈从的个体则在这一“切”一“磨”中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第三节对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进行反思。在城市庞大严密完备的体制前,普普通通的个体无可奈何、心有不甘但无可选择,唯一的选择是“服从”,在“服从”中“挣扎”,在“挣扎”中“服从”。虽然有时候还是会不甘心地高呼“为什么”,但是仍然只能把这“不正常的生活轨道”当做正常,并在这“正常”中追赶死亡,从精神到肉体的死亡。批判城市文明是现代主义诗歌中一个常见的抽象主题,但在穆旦的诗中,却是触手可及的、鲜明生动的身体感觉动词、形容词和感官形象,如“跳”“回旋”“鞠躬”“切”“磨”“挣扎”“追赶”“高呼”等。通过这些源于身体的感觉,诗人痛切地控诉了文明对人性的戕害,真切细腻地反映了作为个体的人欲反抗而不能、欲服从又不甘的心态。
最能体现穆旦诗歌语言“肉感”特色的莫过于他的爱情诗。穆旦创作爱情诗的时候正是20多岁的年龄,这个时候对身体和爱情的探索可谓同步进行。这个阶段的身体感受与心灵感受都是异常敏锐的,两种感受也很容易交织在一起互相印证对爱情的探索和体验。“新诗史上有过许多优秀的情诗,但似乎还没有过像穆旦这样用唯物主义态度对待多少世纪以来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的。徐志摩的情诗是浪漫派的,热烈而缠绵;卞之琳的情诗是象征派的,感情冲淡而外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穆旦的情诗是现代派的,它热情中多思辨,抽象中有肉感,同时还有冷酷的自嘲。”[2]
穆旦在爱情诗中大胆展示了充满原始欲望的肉体形象,这些肉体形象充满青春的激情,在强烈感染读者的同时引发读者的沉思。它们有的是展示现代爱情的混乱、焦虑、饥渴、躁动、不安,《春》中诸多意象如绿色、花朵、土地、光、影、声、色都染上了一层欲望的色彩,“摇曳”、“拥抱”、“反抗”、“紧闭的肉体”、“被点燃”、“赤裸”、“伸入新的组合”等词语也富有情欲意味。“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春天里满园都是欲望,绿茵吐出情欲的火焰,大地要与花朵拥抱,花朵反抗着大地,挣脱它的怀抱,暖暖的春风吹来的也是恼人的欲望。20岁的心和身体都无比地焦渴,等待着被点燃被重新组合。这首诗借助肉体感觉青春期特定的生命状态:“青春是痛苦与幸福的矛盾的结合。”青春的欲望是美丽的也是痛苦的,“在这个阶段强烈的肉体敏感是幸福也是痛苦,哭和笑在片刻间转化。穆旦的诗最直接地传达了这种感觉:爱的痛苦,爱的幸福。”[6]
为何穆旦如此痴迷于肉体?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源于一个年轻人的青春体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源于穆旦对肉体的认识。他认为肉体生存状态是对生命形态的一个隐喻,肉体是爱情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类追寻爱情的最根本的动机是为了寻求生命(肉体)的完整。
穆旦深受西方文明熏陶,他的诗中涉及的个体生命总是异常孤独,是残缺的、不完全的或变形的,就像被抽取了一根肋骨的亚当,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必须找到那根肋骨并与之相联结才能完成自己。他在《我》这首诗里表达了这个观点。穆旦诗中爱情的获得与自我生命的完成是相互关联的。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肉体是焦躁的、不安的;当爱情终于降临,相爱的人灵肉相融,外在的身体“完整”了,内在的生命形态也趋向完美。孤独、隔膜、死亡都是人在这个浩渺宇宙间生存的宿命,唯一能抵挡这一宿命的是心灵的沟通和交融,是灵肉合一的爱情。
通过身体以及身体感受的隐喻性表达,穆旦将自我身体官能、内在心灵感受、外在世界融为一体,人与世界、感性与理性、逻辑与感悟在隐喻中和解。
二 由具体到抽象的隐喻
穆旦采用身体语言,描述身体的种种感觉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的种种感受,其最终目的是欲“用彼类事物谈论、理解、体验、想象此类事物”,“彼类事物”指包括身体感觉和官能感受在内的感性形象,而“此类事物”则指种种抽象玄思。“概念只能触及人们的知性,它是思维的构成部分,只有当概念在诗人的灵感的催化下转化成有血肉,有声、色、味,有感性的魅力的一个意象,或甚至一幅幻景,它才能成为诗。”[2]这句话若是反过来理解也是成立的,那就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感性形象最终是为了表达“概念”,后者是隐喻的目标域,是营造各种意象的终极目标。若没有这个目标,那么所有的意象不过是小姑娘头上的花儿,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
穆旦隐喻思维的特点与过程在于他善于把看起来最不相关的事物捆绑到一起,制造出新颖、震撼的感觉,或是营造一个中心意象,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引申、延展。这两种思维方式都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判断、分析、比较、推理等理性思维活动。穆旦诗歌语言不仅仅诉诸人的感觉和经验,它的功能不是重在营造一种意境,掀起读者情感的波澜,而是诉诸人的头脑和理智,迫使、诱导读者去进行理性思考和评判,从而使诗歌的功能由抒情变为表达经验、哲理,在感性中织进抽象的理性。穆旦在《五月》中把至高无上的权力比作电力总枢纽,而读者在解读这首诗的过程中,不是被诗中的意象感染,而是惊讶于这个来自工业王国里的看似缺乏感情含量的意象,随之调动自己储备的物理知识,并进行逻辑分析和抽象思考,最后得出结论。同样,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也不是沉浸在情感的漩涡里,他动用自己的知识储备、生活经验,通过判断、分析、比较等一系列的理性思考,找到情感的客观对应物,行文成诗。如《裂纹》的下半首诗人没有直接进行呼告、抒情、祈求,没有直接倾泻自我的情感,而是通过“女人的裙角”“八小时劳作”“中心”“边沿”等具体意象的呈现,引导读者进行感知、理解、比较、分析、判断,从而领悟其中蕴含的思想。“中心”与“边沿”是二元对立式的富于政治色彩的意象,喻示着社会权利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中心和边沿,体现着中心与非中心的矛盾和抗争。这两个意象能够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八小时”最能体现穆旦营造意象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它喻示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和摧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意象在穆旦的诗中反复出现,已上升为一种象征,“八小时”象征着现代文明冲击下人类异化的存在方式。
如果说传统诗歌通过营造意境的方式,西方浪漫主义诗歌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把握世界,那么穆旦则是在隐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功能上,表现出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因此读者和作者的知识背景重合面愈大,那么读者对诗作的解读就越能接近作者的原意,就越容易“懂得”诗作的含意。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现代派诗歌妙不可言,有人却觉得晦涩枯燥,味如嚼蜡,不知所云。
穆旦独特的诗思体现在诗歌语言中则是大量抽象词、具象词与虚词水乳交融的并用,这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智性风格。
穆旦1963年为《丘特切夫诗选》写的“译后记”第五节关于丘特切夫的艺术手法的论述中开篇就提出:“丘特切夫有他自己独创的,特别为其他作家所喜爱的一种艺术手法——把自然现象和心灵状态完全对称或融合的写法。”“丘特切夫诗中,令人屡屡感到的,是他仿佛把这一事物和那一事物的界限消除了,他的描写无形中由一个对象过渡到另一个对象,好像它们之间已经没有区别。”[7]穆旦还举例说:“当普希金写出‘海浪’这个词时,他的意思是指自然间的海水;可是在丘特切夫笔下,‘大海的波浪’就不止是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人的心灵。请看他的《波浪和思想》:‘思想追逐着思想,波浪追逐着波浪,/这是同一元素形成的两种现象。’海浪和心灵仿佛都被剖解,被还原,变成彼此互通的物质。”[7]显然,穆旦这里分析的正是隐喻现象。穆旦所谓的消除事物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指的是打通不同事物(如“心灵”和“海浪”)之间的范畴界限,而这正是隐喻的重要特色,亦即语义学家们所说的“范畴错误”。
抽象词多来源于人的思维和心灵,具象词多描述外在于人的世界。这两类词在穆旦诗歌中之所以能够融合到一起,正是源于穆旦在“译后记”中所谓的消除事物之间的“界限”。穆旦诗中“把自然现象和心灵状态完全对称或融合”的诗句随处可见,例如:“让欢笑和哀愁洒向你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我看》)这里把“对实物使用的动词”(“洒”或者“燃起”)用于“空灵”的心灵状态和“抽象”的概念系统,使“欢笑”和“哀愁”成了可观可感的对象,使季节具有人的形象和情感。类似的不同范畴的动词的移用还有很多(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叫光明流洗你苦痛的心胸(《合唱二章》)
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穹/紧接着蔓绿的低矮的石墙/静静兜住了一个凉夏的清晨(《园》)
要从绝望的心里拔出花,拔出草(《从空虚到充实》)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赞美》)
灯下,有谁听见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童年》)
这些从别的范畴移用过来的隐喻性动词大大地增加了诗歌的感性,把一切经验都变成可感受的东西加以表现,但又不仅仅限于感性,而是在令读者新奇的同时,引发思考:为什么光明可以流洗心中的苦痛?光明具体指什么?苦痛又从何而来?
还有的“范畴移用”是把某一范畴的形容词用在另一个范畴之中。这种情况在穆旦诗歌中亦俯拾即是。例如:“它要求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诗八首》)以触觉上的形容词(“温暖”)形容视觉上的对象(“黑暗”);再如:“别了,那都市的霉烂的生活”(《给战士——欧战胜利日》),“霉烂”是形容外在世界的事物的,作者却用来形容生活。再如:
因为冬天已经使心灵枯瘦(《冬》)
它雇佣的是些美丽的谎(《爱情》)
给空洞的青春描绘五色的理想(《沉没》)
这些所谓的“范畴错误”现象打通了思维、心灵与自然事物之间的界限,语词意象相互渗透,语境相互转化,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相互呼应。万事万物都打上了人的思维与心灵的烙印。
穆旦晚年在一封信中告诫一位青年诗人:“暗喻不要太随便,应该在诗内有线索,读者自会解释出。如果作者不给线索,那就像读谜语了。”[8]这样的线索在穆旦的诗中是不难找的,那就是抽象词以及抽象词与具象词破格的搭配组合会提醒读者该诗的隐喻情境。如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第一节前几句几乎都是写景,乍一看,读者很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最后一句为读者寻找答案打开了一道门缝:“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这里有两处运用了隐喻手法:一是“亲切”,这显然是“范畴错误”,将形容人的词移用到自然界的事物上来;其次是“压死”一词会引发读者的思考:相互依赖的轮子和道路之间为何会有“压死”的情况呢?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在上述写景的诗句渲染的凄凉、寒冷的情境中陷入沉思。第二节依然是大段大段的写景,但“风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提醒读者这是一首关于“生命与时间”的诗。时间是无边无界的,无限的,而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明灭之间。第一节写到田间劳作的农人,第二节写到啼哭的儿郎,第三节写到祖先和祖先们的故事,然后再写门前的农具以及空中的雪花,作者在极短的篇幅里写到现在、将来、过去,再回到现在,使短短的诗篇极富有历史的纵深感。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诗激发的是情感,而穆旦的诗激起的是玄思。抽象词是穆旦诗歌中的灵魂,抽象词的存在使穆旦的诗歌摆脱了感性抒情方式,走向理性玄思。
其次,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穆旦诗歌中大量虚词的存在与隐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密集的虚词也正是穆旦诗歌智性诗风的根源之一。当诗人启动隐喻机制的时候,他要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进行选择、比较、分析、鉴别、判断,这些思维活动反映在诗句中,就是井然有序、逻辑鲜明的句群的出现。这一点与古典诗歌截然不同:古典诗歌是在一个空间环境里展开的,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六个意象是没有先后主次之分的,也不存在逻辑推理关系,它们之间没有层次感,包孕感,而是共同营造一个孤寂凄凉的意境。但穆旦诗歌中大量虚词的存在使句子内部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有主次先后之分,有不同的逻辑关系。这些虚词绝不是无意义的存在,而是记录着作者思维的轨迹。如《智慧的来临》一诗(部分虚词加了下划线):
成熟的葵花朝着阳光移转
太阳走去时他还有感情
在被遗留的地方忽然是黑夜
对着永恒的相片和来信
破产者回忆到可爱的债主
刹那的欢乐是他一生的偿付
然而渐渐看到了运行的星体
向自己微笑,为了旅行的兴趣
和他们一一握手自己是主人
从此便残酷地望着前面
送人上车,掉回头来背弃了
动人的忠诚,不断分裂的个体
稍一沉思会听见失去的生命
落在时间的激流里,向他呼救
这首诗每一节都采用了隐喻手法,虚词在诗思的延伸、句意的腾挪跌宕上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穆旦说,暗喻性的文字要给读者解读线索,这里,虚词就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这些虚词是思维转折、递进、变化的中转站和标记,把握了这些标记,就把握了作者的思维,进而就能迅速领悟诗的喻旨。
隐喻给了穆旦两把光闪闪的钥匙:抽象词和虚词,拿着这两把钥匙,我们就能打开穆旦诗歌的大门,走进一个智性语言的世界。
三 含混语言的隐喻
1930年,24岁的燕卜逊写出了《含混七型》(也有人译为《朦胧的七种类型》)一书,该书影响了整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界。燕卜逊在此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复杂意义是诗歌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他称这种现象为“含混”(ambiguity)。他对含混的定义是:“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9]燕卜逊根据造成含混的不同的语言机制把含混分为七型,但从读者的反应看,所有的含混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同一语境中,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含意,这些含意不但并存,而且可以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综合的、更富于表现力的复合意义”。[10]150这个理论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传统(布鲁克斯认为这个传统“缺少思想的灵活性,更谈不上反应的成熟性”[10]147),形成了“亦此亦彼”(布鲁克斯认为它有“‘细腻’的辨别力和微妙的含蓄”[10]147)的新的解读诗歌的范式。含混从此被承认是使诗歌有力量的因素之一。含混也被翻译成朦胧、歧义、多义、复义。含混七型第一型“说一物与另一物相似,但它们却有几种不同的性质都相似。”实质就是指隐喻带来的含混。燕卜逊说仅此一型“差不多把文字上有价值的东西全包括在内”,关于第一型的这一章是“篇幅最长,也是最有启发性的一章”,这足以说明“含混的机制存在于诗的根基之中。”隐喻与含混有必然的联系,隐喻机制运行的过程必然会带来含混。
现代派诗歌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含混多义,其根源之一就是因为现代派推崇隐喻。隐喻也给穆旦诗歌语言带来了复杂含混、蕴藉多义的特点。《诗八首》第一首第一句“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火灾”具有多重含意:火本是人类取暖之物,但是若火势过大,那就带来毁灭性后果,成为“灾难”。爱火在我的眼睛里燃烧,你心悸,惊喜,但是又恐惧莫名:是福?是祸?你宁静的心绪被我的爱火烧成灰烬!你亦惊亦喜,亦拒亦迎,亦嗔亦怒,亦悲亦欢。“火灾”这个隐喻就像一幅被无限放大的星云图,少女心绪的波澜起伏、瞬息万变被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火灾”一词同样也表现了“我”——爱的信息的发出者复杂的心绪和情境。突如其来、无法抑制的爱控制了我的心灵、身体,我振奋但又惶恐,我激动但又恐惧:该怎样向心爱的姑娘表白我的心意?她是欣然接受还是冷眼相向,出语讥讽,甚至拂袖而去?如果拒绝我,我还爱她,那将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如果接受我,我们会幸福吗?爱会在我和她之间勾勒出怎样的图景?“火灾”一词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我忐忑不安、辗转反侧、悲喜交集的矛盾心境。“火灾”一词还是对爱情本身的隐喻。一场爱情就是一场火灾,相识、相恋、相爱、相守或是分开;激情、冲突、和解、平淡。年轻的心灵和身体在爱情的烈焰中嘶嘶燃烧,在痛苦中感受快意,在愉悦中相互折磨,在无数个回合的冲突中相互博弈,在筋疲力尽中大彻大悟,最后在爱情战火的袅袅余烟中收获成熟。被爱情的“火灾”淬炼过的心灵就像佛家的舍利子一样尊贵、圣洁。这多重含意共同表达了爱情的复杂和矛盾:它能给人类带来新奇、快乐、活力,它也是烦恼、痛苦、灾难之源。它是爱的使者,也是死神的先锋。它是甜蜜的,令人沉醉的,也是残忍的,令人发狂到失去理智……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情在“火灾”这个隐喻中得到了多角度多层次深刻细致精细入微的阐释。
含混使穆旦诗歌语言“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然而这正是艺术的协调。”[6]含混赋予诗歌深刻的品质。含混就像一个三棱镜,从不同的侧面看,有不同的光辉,但是每一个侧面都是共存的,它们共同组成了迷人的镜像。这层层叠叠的视角像一个探索不尽的迷宫,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走进去,再走进去,永无尽头。
隐喻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语言现象,隐喻实际上就是语言本身,隐喻式语言因其自身特征必然呈现为感性与智性并存,抽象与具象相融,意义含混复杂,具有无穷的想象空间。正是隐喻这根魔杖使穆旦诗歌语言肉感、抽象、智性、多义。这将是一个广阔的说不尽的话题,本文只是从语义角度进行了粗浅的探讨,至于其他方面如语形、语感、语用等与隐喻的关系还有待方家进行深入探索。
[1]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M]//杜运燮,袁可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4.
[2]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M]//杜运燮,袁可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4.
[3]郑 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3.
[4]艾略特.玄学派诗人[M]//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22.
[5]艾略特.玄学派诗人(1921)[M]//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8.
[6]郑 敏.诗人与矛盾[M]//杜运燮,袁可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3.
[7]穆 旦.《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M]//曹元勇.蛇的诱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215-216.
[8]穆 旦.致郭保卫信(1977年1月28日)[M]//穆旦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29.
[9]燕卜逊.含混七型(选段)[M]//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44.
[10]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