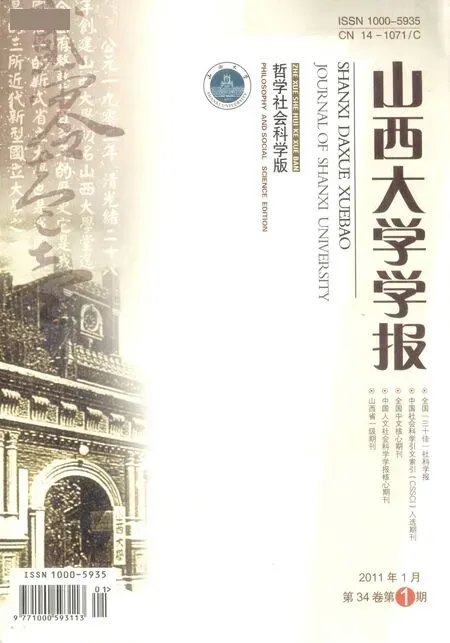《文镜秘府论》的二处原典考证
卢盛江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文镜秘府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原典考证。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几篇文章论及。本文想再就二处原典提出看法。主要涉及两个材料,一是西卷《文笔十病得失》,二是北卷《论对属》。
一 关于西卷《文笔十病得失》的原典
《文笔十病得失》后半出《文笔式》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后半开头即明确说“《文笔式》云”。[1]1238问题主要在《文笔十病得失》这一篇的前半,即自开头至“笔势纵横动合规矩”句之前一段[1]1189-1234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为前半原典也是《文笔式》①此一意见者最早由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提出,而罗根泽《文笔式甄微》作了详细考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前半与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引刘善经说多有相同之处,因此它们都出《四声指归》②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最早提出这一意见。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也说:“罗根泽所谓十病,本是刘氏引沈约说并加上自己的意见。”(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95页)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86年)表示了类似的意见。。笔者倾向于前一说,并以为还需作进一步的辨析。
(一)同一问题,《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八病”引刘善经说有不同
比如:同是笔之蜂腰,“八病”引刘说举例云:“阮瑀《止欲赋》云:‘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即‘体’与‘粉’、‘衣’与‘除’同声是也。”[1]956“体”与“粉”、“衣”与“除”,分为上下句的第三、第六字,是知刘氏所谓笔之蜂腰,是指三、六同声。刘氏又说:“又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此虽世无的目,而甚于蜂腰。如魏武帝《乐府歌》云:‘冬节南食稻,春日复北翔’是也。”[1]596以二、四字同声为蜂腰,他举的例诗魏武帝《乐府歌》,同声上句“节”“食”,后句“日”“北”均同入声,这是五言诗,是知刘氏所谓二、四同声,是指五言诗。就是说,“八病”引刘说,以三、六同声为笔之蜂腰之病,而亦以二、四同声为五言诗之蜂腰病。
再看《文笔十病得失》前半。《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论诗未说二、四同声为病,论笔,未说三、六同声为病。从举例看,四言:“笔得者:‘剌是佳人。’失者:‘扬雄甘泉。’”得者二、四不同声而失者同声。六言:“得者:‘云汉自可登临’,‘摩赤霄而理翰’,失者:‘美化行乎江汉’,‘袭元凯之轨高’”,[1]1208得者二、六不同声而失者同声。同样,七言为二七、八言为二八,得者不同声而失者同声。说法显然与“八病”引刘氏说有异。
再看关于“蜂腰”的定义。《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蜂腰:第一句中第二字、第五字不得同声。”[1]1208“八病”则说:“刘氏云:‘蜂腰者,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1]956稍加注意不难发现,两者看似一致而实有不同。所谓“第二字第五字不得同声”,《文笔十病得失》前半明确限定是“第一句”,而“八病”引刘说未加限定。刘氏举例:“古诗云:‘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是也。”他举的是两句之例,而这两句,上句“君”与“甘”,下句“独”与“饰”均同声,而元兢明确说“独与饰是病”,[1]954元兢实际承刘氏之说。就是说,刘氏所谓蜂腰,所谓“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实际是既指第一句,也指第二句。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举例:“诗得者:惆怅崔亭伯。失者:闻君爱我甘。”均只举了一句诗例,而且都是“第一句”。笔的举例也是这样。前已引述,刘氏引阮瑀《止欲赋》:“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1]956为上下两句。《文笔十病得失》前半所举之例均只一句。这说明,同是论蜂腰,《文笔十病得失》只就“第一句”言,而刘善经则兼论上下两句。两者显然有很大不同。
(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论蜂腰和《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一致
《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八病”引刘说的不同,恰恰也是它出自《文笔式》的证明。现在可以确知为《文笔式》的材料,除《文镜秘府论》正文及一些古钞本如三宝院本的夹注有说明的之外,还可从日本《本朝文粹》所载《省试诗论》找到。《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只就第一句论蜂腰恰和《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一致。
《省试诗论》记载的是日本长德七年(987年)因学生大江时栋的省试诗而引发的关于诗病问题的一场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也是五言诗第二句应不应该避蜂腰。讨论的双方,式部少辅兼东宫学士的大江匡衡,和大内记兼越中权守纪齐名,他们各自向天皇陈状。
纪齐名说:“件诗云:‘寰中唯守礼,海外都无怨。’今案:‘外’与‘怨’同去声,是蜂腰病也。”[2]233他说的正是下句第二字与第五字也不得同声。大江匡衡则认为:“蜂腰有每句之文,上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必避之;下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者,虽立每句之文,不避之”,[2]235因此纪齐名列举的这首省试诗并未犯蜂腰。他说:“近古之名儒,都良香奉试《听古乐诗》,以卧为韵,其诗云:‘明王尤好古,静听时临座。’如此,则‘听’与‘座’用去声,不为病累,已以及第。自余试用他声韵及第诗等,专无忌下句蜂腰。”[2]233他又举了题为《连理诗》,有名王、坂上斯文的及第诗,题为《听古乐》的都良香、藤原渊名、高阶令范的及第诗等许多例子,说,这些诗“下句不避蜂腰,皆预及第。”[2]233
他们都引有关诗学著作的论述为证,纪齐名引元兢《诗髓脑》和《文章仪式》,而大江匡衡则在引述《诗格》的同时,引述了《文笔式》。第一次陈状,他就说:“夫蜂腰病者,上句可避之由,见《文笔式》。因之,先儒古贤不避下句蜂腰。”[2]236第二次陈状,他引述更为具体,说:
《文笔式》云:“蜂腰者,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也。所为证诗,以上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为病云云。”又《诗格》所释:“初句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又是剧病云云。”然则依下句不可避蜂腰,《文笔式》、《诗格》下句已不载蜂腰之有无。[2]236
此处所引之《诗格》未详出自谁家。所引之《文笔式》,则显然和《文镜秘府论》所说的《文笔式》是同一书。《省试诗论》引述了《诗髓脑》,恰和《文镜秘府论》所引述的基本内容完全一致,说明《省试诗论》引述的材料是可靠的。从《省试诗论》可以知道,五言诗第二句是否须避蜂腰,当时人们的意见确不一致,而根源在于中国的诗文论典籍,元兢《诗髓脑》为一派意见,《文笔式》为又一派意见,正相对立。这又恰好可以和上面所分析过的《文镜秘府论》“八病”引刘说和《文笔十病得失》在蜂腰问题上的分歧相互对应。两相比较不难知道,刘善经《四声指归》和元兢《诗髓脑》一致,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无异。《文笔十病得失》和《文笔式》都只就第一句论蜂腰,都未论及第二句。《文笔十病得失》在这一问题上与《文笔式》同而与《四声指归》根本不同,这似可以作为一个有力证据,说明它的原典不太可能是《四声指归》,则更可能是《文笔式》。
(三)“‘文笔’十病得失”的标题和“文笔式云”
标题值得注意。为什么叫“‘文笔’十病得失”?可能因其所论之“十病”,既是“文”之病,也是“笔”之病,是“文”“笔”共有之病。也可能因为其原典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题为《文笔式》的书。换句话说,“文笔十病得失”就是《文笔式》的“十病得失”之意。也可能两种含义兼而有之,既指“文笔”共有之病,又指《文笔式》一书所载之病。
这样理解是有根据的。《文镜秘府论》的一些标题,常常就含有书名。天卷《调四声谱》即沈约的《四声谱》,《四声论》,即出刘善经《四声指归》,既是“四声”之论,又是《四声指归》之论,是《四声指归》关于“四声”之论。东卷《笔札七种言句例》,原典即上官仪《笔札华梁》,是《笔札华梁》一书所载之“七种言句例”。南卷《集论》,即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是《河岳英灵集》之论。北卷《帝德录》,则更直接是原典之名。因此,《文笔十病得失》之“文笔”,很可能就兼指《文笔式》之书名。
《文笔十病得失》中间有“文笔式云”,[1]1238也是一个根据。引述原文之后,再出现原典之名,《文镜秘府论》中不乏其例。西卷“八病”“第八正纽”,“元兢曰”三字就在所引元兢说之后出现,在它之后和之前,都为“元兢说”。“第十五龃龉病”以后诸病这类例子更多。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这一病目旁注“元氏云,兢于八病之别为八病,……八者何,一曰龃龉,二曰丛聚,三曰忌讳,四曰形迹,五曰傍突,六曰翻语,七曰长颉腰,八曰长解镫。”[1]1126说明龃龉、丛聚、忌讳、形迹、傍突、翻语、长颉腰、长解镫诸病原典均出元兢《诗髓脑》。“第一平头”元兢论平头病时,批评“今代文人李安平、上官仪皆所不能免也”[1]920,说明他论声病好引上官仪为例。“龃龉”等八病中,“第十三龃龉病”和“第十九长颉腰病”、“第二十长解镫病”的第一段,就都引了上官仪的例子,或引其论说以资佐证,或引其作品作为犯病诗的例证。这说明,这几病的第一段,原典都应为元兢《诗髓脑》。但这几病表明原典的“元兢曰”字样,却只出现在第一段之后,第二段之前。这是《文镜秘府论》中常见之例,特别在西卷。联系《文笔十病得失》的题名,结合前面分析的那些根据,《文笔十病得失》也当是前面已经引述了大段《文笔式》的原文之后,再出现“文笔式云”,在这个“文笔式云”之前和之后,都当为同一原典,即《文笔式》。
(四)关于和“八病”引刘氏说的相同之处
《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八病”引刘氏说确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仅此一点,并不足以证明其原典就一定是《四声指归》。空海反复说明他编撰《文镜秘府论》时处理繁复众多材料的基本思想是“削其重复,存其单号”(天卷序[1]24)、是“弃其同者,撰其异者”(东卷序[1]666)。既然是“弃其同者,撰其异者”,同一卷的紧相连接的两处,重复引述内容相同而原典又相同的材料,同一种原典的同一内容重复引述,才是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其内容相同,所以它们所据原典应该不同,这反而可能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两者的相同之处,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列数得比较全面,共列举了一十八例。[3]34-35这一十八例,情况各异,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形同而实不同,或者说,引例引言相同而实际观点相左。比如,同引“闻君爱我甘”[1]956的诗例,这是两句诗的上句,《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只引此一句,说明只第一句须避蜂腰,而第二句不须避之。[1]208“八病”刘氏说则同时还引了其下句即“窃独自雕饰”,[1]956用来说明五言诗每句都须避蜂腰。再比如论平头,都说过类似“疥癣微疾,非是巨害”[1]923,1189的话,但“八病”刘氏针对的是“铭诔之病”,虽不指诗,但仍属押韵之“文”的范围。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说的则是“文笔未足为尤”,[1]1189既指押韵之“文”,也指不押韵“笔”。
有些可能是两家均同引前人之说。如例诗“客从远方来”,据《诗人玉屑》卷十一,可能原出沈约。它可能是前人共同常引之诗例。“平声赊缓,有用最多,参彼三声,殆为大半”[1]956十六字,和“壮哉帝王居”一诗,同引刘滔说。“凡用声,用平声最多,五言内非两则三”[1]956一段,亦概括刘滔说。这些材料的原典,本来就非始出《四声指归》,刘善经可以引用,《文笔十病得失》应该也可以引用。隋至初唐诗文论共引前朝旧说,极为普遍。用《文镜秘府论》东卷空海注来说,是“古人同出斯例”。[1]678共引古人之说,不足以说明《文笔十病得失》原典为《四声指归》。
《文笔十病得失》所引材料,有的原典可能确始出于《四声指归》。但是,《文笔式》本来就好引刘善经之说,《文笔十病得失》之后半,引“文人刘善经云”[1]1247云云,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引用《四声指归》,不等于原典就是《四声指归》,这是有联系而有区别的两回事。
二 关于北卷《论对属》的原典
按照笔者在《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的看法,北卷“论对属”这一题名,既是北卷的大题,又是首篇文字的小题①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678页注①“盛江按”。。这里说的《论对属》,是指北卷《句端》之前的首篇文字。
《论对属》应该是初唐时的理论①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已指出:“(《论对属》)可能和《文笔式》《笔札华梁》一样同是初唐时的理论。”(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86年,第723页)但未说明更多理由。参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678页注①。。它讨论的还是上下尊卑,有无去来,东西南北,还有隔句、同类、异体、双声叠韵之类基本的对属,《诗人玉屑》引上官仪“六对”“八对”,就是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它还没有元兢《诗髓脑》奇对、字对、声对、侧对,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等这些东西,更没有后来皎然《诗议》邻近对、含境对、双虚实对、假对等东西。提出这些更为繁复的对属形式,应该是在提出基本的对属形式之后的事。而北卷《论对属》还提出还只是早期那些基本的对属形式,它还没有涉及后来提出的更为繁复对属形式。它说,像“寒云山际起,悲风动林外”那样的“上升下降”,像“日月扬光,庆云烂色”那样的“前复后单”,“语既非伦,事便不可”。[1]1680类似的情形,皎然《诗议》中也有。皎然《诗议》的“交络对”的“出入三代,五百余载”[1]784,“三代”和“五百”,同样是一升一降;“偏对”例句“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的古墓和松柏,日月和列宿,同样是一复一单。类似的情形,一则以为非伦不可,一则作为一种新的对属形式而加以肯定,这显然反映了对属形式认识的发展,而前者应该是更为早期的思想。从对属论的发展来看,是先提出基本的对属形式,尔后再提出更为繁复的对属形式。北卷《论对属》反映的应该还是初唐时的认识。它应该在皎然之前和王昌龄《诗格》之前②《考文篇》:“有人认为可能是王昌龄《诗格》。”盛江按:北卷《论对属》实应该在王昌龄《诗格》之前。,很可能在崔融、元兢之前,很可能与上官仪《笔札华梁》同时或稍后。
《论对属》正文的一些内容,可能出《文笔式》③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以为《论对属》均出《笔札华梁》。小西甚一以为出《笔札华梁》或《文笔式》(见其著《文镜秘府论考》之《考文篇》和《研究篇》。二家之说均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678页注①)但小西甚一未说明更多理由。。第一段就有可能出《文笔式》。
和东卷“第一的名对”所引《笔札华梁》和《文笔式》作一比较,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印象。从东卷“第一的名对”看,同一种对属形式,《笔札华梁》和《文笔式》名称并不一致。《笔札华梁》称之为“的名”的,实际是“同类对”④如:“持艳偶鲜,用光匹采,疏桐密柳之相酬:故受的名。”如果前面的分析可信,这一例当出《笔札华梁》,而这里的艳和鲜,光和采,疏桐和密柳,除“疏”“密”义相反之外,其余概念,其义并不相对,均属同类对。。而《笔札华梁》称之为“正名对”的,恰似多为“反对”⑤如说“天,地,日,月,好,恶,去,来,轻,重,浮,沉,长,短,进,退,方,圆,大,小,明,暗,老,少,凶,儜,俯,仰,壮,弱,往,还,清,浊,南,北,东,西。如此之类,名正名对。”[1]687-688又如:“又曰:‘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释曰:迎送词翻,去来义背,下言西北,上说东南:故曰正名也。”[1]688这些都出《笔札华梁》,这当中相对的语词概念,多属于“反对”。。《笔札华梁》所说的这两种对(“正名对”和“的名对”),在《文笔式》那里,统称为“的名对”⑥东卷“第一的名对”:“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东,下句安西;上句安南,下句安北;上句安正,下句安斜;上句安远;下句安近;上句安倾,下句安正:如此之类,名为的名对。”[1]687又以:“诗曰:‘东圃青梅发,西园绿草开;砌下花徐去,阶前絮缓来。’释曰:上二句中:东西是其对,园圃是其对,青绿是其对,梅草是其对,开发是其对。下二句中,阶砌是其对,前下是其对,花絮是其对,徐缓是其对,来去是其对。如此之类,名为的名对。”[1]688这两段论述都当出《文笔式》。若然,则前段中的山谷,后段中的园圃、青绿、梅草、开发、阶砌、花絮、徐缓相当于《笔札华梁》的“的名对”,前段中的正斜,远近,倾正,后段中的来去,相当于《笔札华梁》的“正名对”即“反对”,而《文笔式》统称之为“的名对”。。也就是说,《文笔式》的“的名对”,既包括了《笔札华梁》所说的“的名对”,也包括它说的“正名对”。
了解了这一情况,再和北卷《论对属》比较,就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北卷《论对属》第一段所论,除最后所说的重言、双声、叠韵各对之外,其余各种对,包括前面所说的“反对”,还有后面所说的“并须以类对之”[1]1675的各种对,恰恰与东卷“第一的名对”引《文笔式》称之为“的名对”的那些对属的类型相合。
二,如前所述,北卷《论对属》第一段来去、明暗、清浊、进退等称之为“反对”。[1]1675这个称呼,与《笔札华梁》是不相合的。因为这些对属形式,既称之为“反对”,就不应同时称之为“正对”或称“正名对”,而《笔札华梁》恰恰是将这类对属称之为“正对”或称“正名对”⑦东卷“正名对”,宫内厅本、高山寺甲本、乙本、醍醐寺甲本、仁和寺本、宝龟院本、松本文库本等作“正对”。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689页校记〔四〕。。但北卷《论对属》“反对”的名称,与《文笔式》却可以是相合的。因为《文笔式》的“的名对”,本来就包含“反对”。东卷“第一的名对”所引《文笔式》的远近、倾安、来去,按照北卷《论对属》的说法,都可以称之为“反对”。
从东卷“第一的名对”来看,《文笔式》虽然也说“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1]687但它毕竟只称“的名对”,而没有称“正名对”。它说“正也”,说“正正相对”,意思是说,构成对偶的一对语词概念名物,正相反或者正相对。而不论正相反还是正相对,都统摄在“的名”之下,它们之间关系密切明确的然,对应平衡恰切齐整,因此叫“的名对”。既然统称为“的名对”,在名称上,就和“反对”不冲突。“反对”不能同时称之为“正对”或称“正名对”,因为“反对”和“正对”的称呼是相冲突的、相矛盾的。却可以同时称为“的名对”。相对的两个概念意思相反(来去、清浊、明暗、进退等),可以称之为“反对”,构成一对语词概念名物的对偶关系明确的然,又可以同时称之为“的名对”。“反对”可以作为“的名对”大类下的一小类,《文笔式》的对属归类就是这样。北卷《论对属》第一段的对属称号,正可以与此相合。
还有一条材料。北卷《论对属》第一段说:“及于偶语重言,双声叠韵,事类甚众,不可备叙。”[1]1675这里说到重言、双声、叠韵,并且是把“重言”作为一种对属形式,和双声、叠韵并列。东卷《二十九种对》也论述到重言、双声、叠韵。从东卷《二十九种对》来看,《笔札华梁》是以重字属联绵对,它并没有将重言与双声、叠韵并列,作为一种对属形式。将重言、双声、叠韵并列的,有“赋体对”。我们前节曾分析过,“赋体对”很可能属《文笔式》。如果这一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北卷《论对属》第一段也很可能属《文笔式》,因为它和东卷“赋体对”一样,也是将重言和双声、叠韵并列。这种情形,与《笔札华梁》不合,而与《文笔式》较为相合。
这样看来,北卷《论对属》第一段,不太可能出《笔札华梁》,却有可能出《文笔式》。
但是,北卷《论对属》第二段起的正文,却可能出《笔札华梁》。
北卷《论对属》第二段起的正文,多骈俪体。如:
或上下相承,据文便合,……或前后悬绝,隔句始应,……或反义并陈,异体而属,……或同类连用,别事方成,……[1]1679
远近比次,若叙瑞云:……大小必均,若叙物云:……美丑当分,若叙妇人云:……强弱须异,若叙平贼云:……[1]1686
再看东卷《二十九种对》引《笔札华梁》。如“第一的名对”:“迎送词翻,去来义背。”[1]688如“第二隔句对”:“两相对于二空,隔以沾衣之句;朝朝偶于夜夜,越以空叹之言。”[1]701如“第三双拟对”:“既双结居初,亦两飞带末;宜昼宜时之句,可题可怜之论。”[1]707都是骈偶之句。再看下面二例。北卷《论对属》正文:
而有以日对景,将风偶吹,持素拟白,取鸟合禽,虽复异名,终是同体。[1]1686东卷《二十九种对》引《笔札华梁》:
持艳偶鲜,用光匹采。[1]688
不仅都是骈偶之体,而且一个是“将×偶×,持×拟×”,一个是“持×偶×,用×匹×”,句式完全一样。这应该是《笔札华梁》作者的惯用句式。如前面所分析的,《文笔式》多为质木少文的散文句式,而《笔札华梁》则为富于文采的骈偶句式。从文章风格看,北卷《论对属》第二段以下的正文,当出《笔札华梁》,可能为《文笔式》所引,却不可能为《文笔式》作者所作。
北卷《论对属》第二段以下正文之外,还有不少注文。注文出自谁人之手,也需要作出分析。
它是散文句式,与《笔札华梁》多骈俪体的文章风格不同。从注释内容看,可能有正文作者自注的成分,但很多则不太像是作者自注。注文的作者和正文作者像是两个人。比如正文说:“或上下相承,据文便合,若云:‘圆清著象,方浊成形’,‘七耀上临,五岳下镇。’”[1]1679-1680注文曰:“方、圆、清、浊、象、形、七、五、上、下,是其对。”[1]1680正文又说:“或前后悬绝,隔句始应,若云:‘轩辕握图,丹凤巢阁;唐尧秉历,玄龟跃渊。’”注文曰:“轩辕、唐尧、握图、秉历、丹凤、玄龟、巢阁、跃渊,是也。”[1]1680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是一些重复性的解释,本可不注而加注,这不像是正文作者自注,而是后来作者为把正文的理论更为通俗地介绍给普通读者而加的注。
这后来加注的作者,应该就是《文笔式》。注文质朴无华的散文风格与《文笔式》相同。注文习惯用“上……,下……”这样的句式。如:解释“比事属辞,不可违异。故言于上,必会于下;居于后,须应于前。使句字恰同,事义殷合”[1]1680句时,注文说:
若上有四言,下还须四言;上有五字,下还须五字。上句第一字用青,下句第一字即用白、黑、朱、黄等字;上句第三字用风,下句第三字即用云、烟、气、露等。上有双声、叠韵,下还即须用对之。
再看东卷《二十九种对》“第一的名对”引《文笔式》:
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东,下句安西;……[1]687
诗曰:“东圃青梅发,西园绿草开,……”释曰:上二句中:东西是其对,……下二句中,阶砌是其对,……[1]688
又曰:“手披黄卷尽,目送白云征。……”释曰:上有手披,下有目送,……。[1]688
都是“上”怎样,“下”怎样,都习惯用“上……,下……”这样的表达方式。这应该是同一作者的习惯句式。
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北卷《论对属》说到“不对者,必相因成义”时,有一段注文,说:
谓下句必因上句,止凭一事以成义也。假令叙家世云:“自兹以降,世有异人。”叙先代云:“布在方策,可得言焉。”叙任官云:“我之居此,物无异议。”叙能官云:“望之于君,固有惭色。”叙瑞物云:“委之三府,不可胜记。”叙帝德云:“魏魏荡荡,难得名焉。”皆下句接上句以成义也。[1]1686
这里重要的,是提出当不相对偶之时,上下句应该如何处理。这里提出的是下句要与上句相因说明事理以成其义。类似的思想和说法,东卷“第一的名对”引《文笔式》也有。如说:
又曰:“云光鬓里薄,月影扇中新;年华与妆面,共作一芳春。”释曰:上有云光,[1]688下有月影,落句虽无对,但结成上意而已。……
同样是有二个不对之句,同样是提出落句在无对的时候,要结成上意。这里所说的“结成上意”,和北卷《论对属》注文所说的“下句必因上句,止凭一事以成义”,“下句接上句以成义”[1]1686,应该是同一个意思。这是不是说明它们同一出典呢?
这和南卷《论体》、《定位》以及西卷《笔札七种言句例》的情形可能一样。正文出自《笔札华梁》,而注文出自《文笔式》。《文笔式》把《笔札华梁》的正文全部收入,然后自己给予注释,并加上第一段的论述,就成了现在的《论对属》。这是对北卷《论对属》原典的一些看法。
[1]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本朝文粹[M].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东京:岩波书店,1992.
[3]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M].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