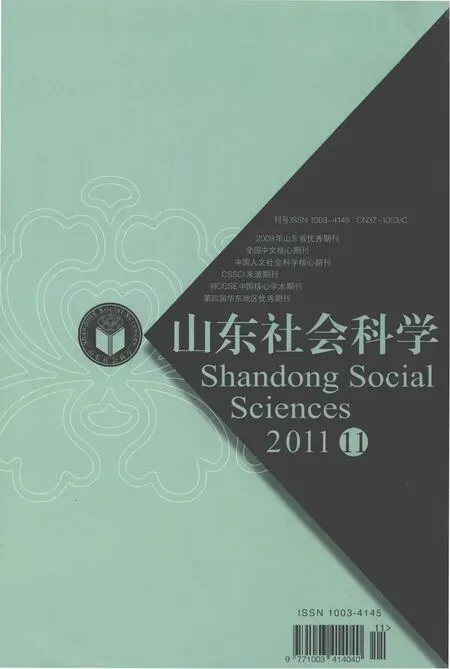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杨巧蓉
(山东省哲学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山东济南 250103)
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杨巧蓉
(山东省哲学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山东济南 250103)
以葛兰西、哈贝马斯、柯恩以及阿雷托为代表人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以独特的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转型。历史地辩证地对之加以研究有利于分析和促进了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丰富与创新,而且,其研究方法与关注的内容,对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建构及其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历史地位
在马克思之后的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成果的广泛运用,现代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以葛兰西、哈贝马斯、柯恩以及阿雷托为代表人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据西方社会与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元市民社会理论分析框架,发展为国家、市场与公共领域的三元架构。但就其实质上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与马克思的分析并不矛盾。作为私人活动领域,市民社会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生活领域。马克思也并未将其简单化约为经济关系,他只是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抓住了经济关系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是特别反对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而且他从来也没有这样理解市民社会。①何平、杨仁忠:《论市民生活观念的当代转换及其社会历史地位》,《求索》2007年第9期。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市民社会思想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转型。
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是葛兰西哲学体系中一个核心范畴,他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在他的国家学说中进行阐发的。在葛兰西看来,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靠强制力量来维持,而是主要通过取得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来实现,因而只有从经济的批判转向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才能切中这种不合法统治的要害。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例如危机、萧条等)入侵的灾难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好像是现代战争中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上去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其外部工事;而到发起总攻时,才发现自己仍然面临有效的防线”②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a,Ed.And trans.,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235.。而且,“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处于不断运动中的有机体而确立起来,他们能够吸收整个社会而把它提高到自己的文化和经济水平。因此国家的作用有所改变:国家成了‘教育者’等等。”③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这样,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就从经济交往转向了社会文化领域,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加以对待。他的这些主张表现出与黑格尔、马克思等近代市民社会论者的重大区别。
然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并非完全脱离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他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的社会中介组织以及伦理精神的论述进行了发挥。在黑格尔那里,同业公会作为中介组织是市民社会向国家过渡的桥梁,也可以说正是同业公会作为“中介”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葛兰西受此启发,但他不是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关系和需要的体系,而是规定为对经济关系和需要体系加以调控的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和道德规范。对此,博比奥指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所包含的“不是‘所有物质关系’,而是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关系生活’,而是整个精神和智识生活。”①Norberto Bibbio.Gramsci and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Chantal Mouffe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London,1979,30 -31.陈晏清、王新生:《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南开学报》2001年第6期。
葛兰西沿着这一思维路径,运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辩证的分析方法,加上自己对于黑格尔思想的发挥,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提出了上层建筑包含两个层面的思想,即“一个可以被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民间的社会组织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指挥的职能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②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990年版序言第29页。因此,葛兰西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应该有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③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990年版序言第1页。
葛兰西始终反对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强行分开的企图,他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不是完全独立的、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这只是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能成立。”④David Held.Political Theories and the Modern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16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990年版序言第2页。在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中,葛兰西批判了国家即“守夜者”的理论。他指出,这一理论“所标示的国家只能局限于维护公共秩序和保证守法,同时却没有提到在这种制度的形式下历史发展的领导属于私人的力量,属于市民社会。因此,我们看到“两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平面图’:一个平面图可以被称之为‘市民社会’即俗称‘部分’的有机体的总和;一个是‘政治或国家社会’平面图”⑤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5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990年版序言第2页。。葛兰西同时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虽同属于上层建筑,但是它们的职能是有所区别的,市民社会的活动不是绝对的、强制性的,只是通过产生集体影响达到客观的结果。
在对市民社会概念含义的新的认识基础上,葛兰西认为不能仅仅用经济事实来说明人类发展的历史,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于“从纯粹经济的(或感情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向道德——政治的因素的过渡,也就是向更高地改造基础为人们意识中的上层建筑过渡”⑥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与此同时,葛兰西并不完全否定政权更迭要以经济基础的变革为前提,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时候,政治都是基础中发展趋向的一种反映。但葛兰西同时强调指出,“这些趋向并不必定得到实现”,“并非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所直接决定的”,而且,“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每一个波动都可表述和理解成是基础的直接表现的主张,在理论上应当被当作原始的幼稚病来加以驳斥。”⑦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2-53页、第97-98页。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可见,在葛兰西看来,经济要素在作为基础性的东西作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时,其作用不是唯一的、直接的与绝对的。
基于对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的深刻认识,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须注意到市民社会领导权或文化领域领导权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革命不能走俄国的老路。因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形成的状态。所以,他坚决反对把国家职能仅仅简单地等同于强制性机器,也反对将国家职能仅仅规约为暴力职能。他指出,“必须把国家看成是‘教育者’,因为他致力于建立新型的文明或新水平的文明。”⑧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国家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统一体,有着极强的伦理的和文化的职能。“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体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型式)。在这个意义说来,在国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执行积极的教育职能的学校。”⑨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葛兰西的这一结论的得出源于他对西方社会现实运动的考察,与东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表现出一种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堡垒立即出现。
葛兰西还阐发了他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最终发展命运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结束自己”⑩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国家和法律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被市民社会所吸收而成了无用的东西。”⑪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他同时指出,国家的存在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辩证统一,是领导权与统治的辩证统一。国家的目标是自身的消亡,是政治社会再度并入市民社会。葛兰西把没有国家的社会称为“得到调整的社会”。认为这种社会是出自于市民社会的扩大,因而是出自领导权要素的扩大,直至市民社会占有原属政治生活的一切空间,一旦社会阶层使领导权普遍到强制成为多余的程度,向“得到调整社会”之过渡的条件就成熟了。显然,葛兰西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消亡乃是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的思想,而是认为国家消亡主要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运动结果,即在上层建筑内,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辩证运动的结果。
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沿着葛兰西开拓的方向继续市民社会问题的探讨,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虽然也强调文化领域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把市民社会归结为文化领域。他指出,文化领域是以经济交往的私人领域为基地的。而且,哈贝马斯已经认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
的统合,但他并不把市民社会定性为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认为它属于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私人自主领域。①陈晏清、王新生: 《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南开学报》2001 年第6 期。哈贝马斯宣称,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本身又由两个领域构成: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它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非官方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即公共领域,它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②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1990 年版序言第29 页。等。也就是说,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观念中的第一个领域,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念所指涉的范围重合;第二个领域则大致和葛兰西市民社会观念所指涉的范围重合。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领域,而哈贝马斯十分重视市民社会的第二个领域——社会文化生活领域。
我们不难看出,哈贝马斯除认同葛兰西的不在国家——社会两元框架下分析问题之外,并没有接受葛兰西的将上层建筑分化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观点,而是提出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的模式。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的推进与他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阐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③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1990 年版序言第1 页。
什么是公共的呢,即什么领域具有公共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如我们所说的公共场所或公共建筑,它们和封闭社会形成鲜明对比。”④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1990 年版序言第2 页。进一步说,“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⑤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 1990 年版序言第2 页。可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开放(性),“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封闭领域”相对的范畴;二是公共性,这也是“公共领域”概念最直接的性质,它与私人领域(空间)相对存在。
尽管哈贝马斯考察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历史变迁,但他所重点论述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他认为,只有出现了近代商业以来,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其在欧洲的确立,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出现了国家——公共领域——社会的三元结构,而这其中的公共领域不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共场所,正是现代资产阶级汇集力量与政治国家周旋而又不同于私人生活领域的“中间地带”。哈贝马斯十分看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他认为,公共领域通过其成员的活动有文化导向与政治干预的力量。
具体地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Lesegesellschaften)、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为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⑥哈贝马斯: 《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3 期。这样松散的、开放的谈论空间,是“公共领域”最为轻松的基本的形式,通过这种带着浓厚文学气质的“公共领域”,表达着“公共意见”。因为这样的公众场所的多种多样,参与讨论的人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其谈论的话题内容也会十分丰富。也许往往因为没有强制力的介入,这种情况下无法达成一致性的结果,但是这样的公共领域却为人们表达私人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随着这种谈论的深入扩展,其重心必然会发生转向,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再局限于市井、商业与文学,而会去关注与这些议题都有关联的政治生活,把一些生活中的情绪与反思传播开来形成影响广泛的“社会舆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公众表达影响甚至干预政治当局,从而找到政治国家与私人社会契合点的空间。哈贝马斯明确了公共领域的这一中心的转变,他指出,各种联系与交往网络最终成了处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之外”、但与两者“相关”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在这些系统中,每一种都满足特定而且有互补性的生产和分配功能,同时在另一方面对决策进行集体性约束。对我们来说有趣的是其政治功能,即自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这种新型的市民社会在宪政国家框架之内可以承担的功能。市民社会提供了在政治问题上多多少少是“自由的”舆论能够产生的土壤——一种通过民主参与的法律渠道转变为公民的交往权力的公共影响。⑦哈贝马斯: 《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3 期。
与此同时,哈贝马斯论证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解体的必然性。他指出:“宪法的核心条款指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然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宪法上得到确认却毋宁说是需要通过暴力才得以实现的漫长过程。相反,以公共领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声称自己是一个公共权力组织,能够确保公共权力服从独立和自由的私人的需要。这样看来,宪法规范所依据的是一种与现实根本不符的市民社会模式。”⑧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93 页。“公共领域本身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统治的,但是,在公共性原则的帮助下,却建立起了一种政治制度,其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统治”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那种完全平等、开放、理性的市民社会理想模式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于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其本质上具有私人性质。“随着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机制化,这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利益渐趋吻合。因此,公共权力在介入私人交往过程中也把私人领域中间接产生出来的各种冲突调和了起来。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以解决,于是,冲突向政治层面转移,干预主义便由此产生。”②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因此,“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趋势发展演变的结果便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土崩瓦解。因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前提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其中,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构成,他们将社会需要传达给国家,而本身就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重叠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就不再适用了。”③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全球公民社会思想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中继“公共领域”理论之外,又一个较有影响力的部分。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运动最终将从总体上使“民族国家”消亡,即“一个不断不对称地陷入有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动权、行动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哈贝马斯在华演讲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页。。从而导致国家对内主权的丧失,国家在决策过程中不断出现合法性危机;而人类将集合为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世界公民社会”。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康德世界公民社会的可欲可求的目标,“康德的世界公民观念,如果不想失去与已经发生彻底变革的世界局势之间的联系,就必须加以重新描述。”⑤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4页。他因此进一步指出,要使正处于萌芽之中的“世界社会”(Weltgeselllschaft)变为现实的三个方面条件:一是得到普遍公认的世界公民法;二是世界公民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三是该共同体所拥有的执行权力或执行暴力。
三、科恩、阿雷托的市民社会理论
在哈贝马斯之后,两位美国政治学家科恩与阿雷托以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们提出“重建市民社会”的响亮口号,将构建一种“能反映出新型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ies)的核心,并能表述出基于这种认同的计划赖以促进更加自由且更加民主社会的诞生的各种条件”⑥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的市民社会概念作为毕生的理论目标。在科恩和阿雷托看来,“无论二分法模型在描述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方面具有什么样的相对价值,它既不能描述隐藏于其转变背后的力量,也无法描述新的社会结构”。⑦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通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哈贝马斯关于体系和生活世界二分的市民社会理论框架,科恩与阿雷托得到了一个三元模式: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市民社会,从而将传统市民社会理论中的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三分模式下的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由私人的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尤其是自愿性的社团)、社会运动以及公共沟通形式所组成。现代市民社会是经由自我建构与自我动员的形式创造出来的。它是经由稳定化社会差异的法律与主体权利所有制度话语概念化的。”⑧J.L.Cohen and A.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2.IX.可见,他们所指称的市民社会是以交往为中心的,尽管它不直接具有权力,但通过自发的结社活动,型塑一定的公众舆论,并能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就这一层面上看,科恩和阿雷托赋予市民社会的特征与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民所构成的公共领域有一致性。
由此,在他们的论述中,就形成了市民社会概念的两种定义:一是指生活世界的机构,一是指基本权利的制度。这两种定义看似相互抵牾,其实并不矛盾。从概念之内涵来看,基本权利始终指向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需要通过主体权利加以确认;从科恩和阿雷托讨论的旨趣来看,两种界定都在于构造一种民主话语,以此捍卫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⑨李佃来:《生活世界之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建构:柯亨与阿拉托的努力》,《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科恩和阿雷托还就市民社会与民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从生活世界的制度与其现代化的语言文化基础的关系看,市民社会制度内部的变迁,是造成文化繁衍、社会整合与个性发展的原因。”⑩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可见,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契约的产物,其权利源于公民的托负与普遍认同,因此,民主权利的正当性蕴含于市民社会的自由沟通、交往之中。一方面,建构集体认同的途径使其成员自发地、自觉地参与交往过程,这意味着没有人被排斥在交往行为之外,人人都享有交往沟通的权利。另一方面,理性的交往程序也保证了互动过程的有效性。因此,市民社会提供了民主正当性的来源,一旦民主的集体认同建立起来,民主的各种经验形式都可以被接受,多元形式的民主是可达到的,因为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有其局限性,总是存在没有被纳入的群体。柯恩和阿雷托主张,主要符合公共性和参与性两个基本条件,任何形式民主实施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它们可以增强市民社会更深度地参与。⑪J.L.Cohen and A.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2.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地位
目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些人认为,以葛兰西、哈贝马斯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基本思想或者说主要观点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笔者认为,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思想有着相异趣的一面,但这主要是表现在所使用的概念的指代范围的不同上,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本本化、教条化的理解,而是着重于理论变迁上的分析,恐怕就不能说他们背离甚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以葛兰西、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对20世纪初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并对具体的一些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批判和将要如何发展进行了设想,就这一层面而言,他们的理论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当代形态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作为历史的范畴,要想科学地对之做出分析和认识,就必然要考察时代背景并结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进而从中加以清理得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知识判断。唯其如此,才能显示理论真正的时代价值。所以,针对不同时代进行思考的市民社会概念,其内涵必然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思想中有这样那样的偏颇就否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反之,应当充分地挖掘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
首先,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在理论上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变化做出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剥削本质没有变,只不过是剥削的方式更加隐蔽,这除了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及工人阶级自身斗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注重对工人意识形态的灌输。另一方面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启发我们要充分利用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通过教育宣传而不是灌输的方式,用科学、先进的文化思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机制观念,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①欧阳成:《浅析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但是,在强调思想、文化因素的同时,葛兰西虽然注意到了政治强制因素,却或多或少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没有从经济基础这个根本原因来考察现代西方社会,这就使他无法全面认识现代西方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治的历史优越性。
其次,哈贝马斯将“公共性”、“公共领域”和商讨引入其理论研究框架,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的“世界公民社会”思想,在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前景时提出了自己的路径、程序与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对于实践的审视。但从今天的现实社会、现实世界看来,哈贝马斯的“全球公民社会”理想无疑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即使有可能实现,那也必将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罗尔斯就曾揭示了哈贝马斯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一再地要摆脱他本人也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但是,他的理论所彰显的价值以及理念框架设计都与西方价值观连带在一起。②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最后,科恩和阿雷托等人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诠释与深化,推动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从宏观到微观的进一步拓展,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的现实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实践意义。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着眼于西方社会现实的变化,丰富并助推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转向。二者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一事实为出发点的话,那么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则是以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分离为基础的。”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这一当代转向,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新热潮,受到了学术界持续的强烈的关注,促使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在当代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格局。更进一步说,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家研究问题的方法、关注的内容及其对日常生活价值的深切思虑,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建构及其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B0-0
A
1003-4145[2011]11-0172-05
2011-09-10
杨巧蓉,山东省哲学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学术骨干,山东省委党校哲学部讲师、哲学博士。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0CZX001),本文系山东省党校系统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1040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陆影luyinga12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