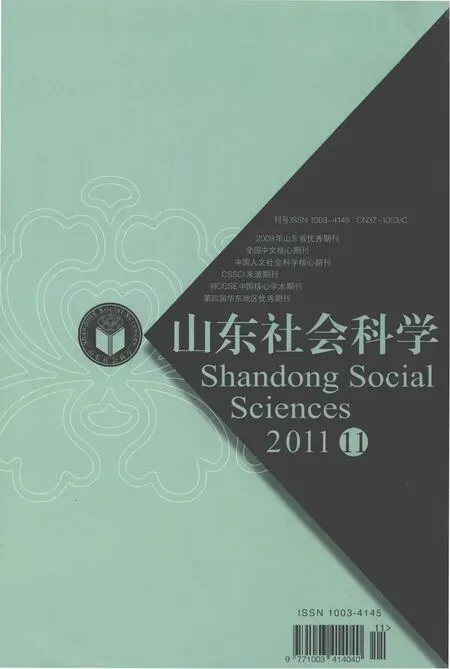民众对再造文化空间的认同和选择
——廿八都镇大王庙修缮后的文化传统变迁
冯 莉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 300072)
民众对再造文化空间的认同和选择
——廿八都镇大王庙修缮后的文化传统变迁
冯 莉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 300072)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是一个地缘性社会,其庙宇群落反映出不同于血缘社会的秩序世界。文章通过对廿八都镇大王庙文化变迁的案例调查,探讨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名村名镇保护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对“文化空间”概念和含义缺乏深刻认识和理解,造成保护行为同传承主体之认同的偏差或冲突。对古村落进行旅游化改造时,有必要对民众信仰规律进行了解和调查,尊重民众对信仰文化空间的认同和选择。
古村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传承主体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文化空间”一词出现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条例特别指出,“文化空间”的概念指的是“人类学”的概念。此后“文化空间”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形态。而文化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化场,有人在场的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的文化空间。①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当前随着城镇化速度在中国大地加快,我国的古村落正在急速消失。正如冯骥才所言:“古村落现在空前地进入一个消亡加速期。要不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②《温家宝同冯骥才对话古村落保护》,《中国艺术报》2011年9月9日第1版。从冯骥才先生的思考不难看出,对古村落的保护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修缮和维护,更重要的是古村落中传统文化空间的保护。古村落中的文化正因开发被肢解得面目全非,如何保护古村落和古村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2007年4月至2011年3月,由中国民协与日本神奈川大学组成的中日民俗联合调查组对中国历史名镇——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进行了为期4年的田野调查,旨在对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进行动态性研究。本文通过对廿八都镇大王庙文化变迁的案例调查,探讨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历史名村名镇保护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主管部门由于对“文化空间”概念和含义缺乏深刻认识和理解,造成保护行为同传承主体之认同发生了偏差或冲突;二、由于传承主体的被动性适应与主动性选择,导致了文化传统的变迁。
一、大王庙的历史变迁
廿八都镇,位于浙江省江山市西南端,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地处东经 118°26'~118°36'、北纬 28°14'~28°20'。东西长21公里,南北宽9.8公里,总面积183.3693平方公里。宋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行新法,以10户为保,5保为大保,10大保为都。江山县从县境东北(今一都江)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分设44个都,因廿八都排行第28位而得此名。2005年,全镇管辖16个行政村,147个村民小组,居民3574户,12614人。③蔡恭、祝龙光主编:《廿八都镇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5页。2007年6月,廿八都进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
与血缘同姓聚族而居的村落不同,廿八都是一个地缘性社会,兴起于驻军,兴盛于商业,镇内村落中主要人口都来自浙、闽、赣三省的江山、浦城和广丰。在这里,仙霞古道从全镇穿街而过,明清时期就已成为繁盛的商路。特殊的地理位置、商业地位和早年的经济实力,使得廿八都庙宇群落与一般乡镇相比,规模更大,建筑质量也更为上乘。廿八都曾建有二阁、三宫、三社、四祠、六寺、八庙,过去每一年,各宫阁庙社都要定期举办各种庙会活动。来自三省边界各乡镇的男女老少会云集镇内,从各地赶来的商号,则在大街两旁搭棚设摊展示商品,小商贩更是肩挑货品沿街叫卖。此时的廿八都几乎成为朝圣之地,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许愿,还愿,看戏,售买商品,交流生活物资。1949年后,镇内众多庙宇或改为民房或遭损毁,香火不存。目前镇内唯有东岳庙建筑完好,其庙会活动也在“文革”后得以恢复,迄今香火兴旺。
廿八都东岳庙又称大王庙,位于205国道以东灰山岭华坞口。大王庙是廿八都13座庙宇中面积和规模仅次于文昌宫的第二大公共庙宇建筑,始建于明万历甲戌年(1574年),清咸丰戊午年(1858年)被毁,重造于清同治乙丑年(1865年)。目前保留的建筑,是民国12年(1923年)由乡绅杨秀东根据原来建筑的结构和样式设计重建的,占地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25平方米,坐东北朝西南。院内建筑两进七开间,共一大四小五个天井。大王庙正殿内供奉东岳大帝,两旁为哼哈二将;两侧偏殿塑有四大公曹、十二司,两侧厢房有财神、五谷神、三圣、四社司殿。各殿内的神像均在“文革”期间被毁。东岳大帝是道教因袭民间信仰崇奉的泰山神。一般认为,泰山是人死后灵魂归宿之地,泰山之神是掌管阴间鬼魂的最高神灵。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农工商都十分重视对泰山神的祭拜。旧时各地皆有东岳庙,大多都以道士奉祀香火。传说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神诞辰日,当日各地都会在东岳宫内举行庆典活动。据《廿八都镇志》记载:旧时该镇东岳庙庙会每年三次,分别在正月初一、三月二十八和十一月初一。但从2005年以来,每年举办的庙会增加到了四次,具体时间也与以往有较大不同(详见下文)。
据当地的老人说,大王庙的原址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现址处向东北方向大概2公里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石灰山,过去村民长年以挖石灰为生,由于开挖的地方形成了许多坑,雨季时会发生塌方和泥石流,人们认为是有白马精①《廿八都镇志》中有关于“白马精”的民间故事。白马精原是宋朝大将韩世忠的座骑,浑身雪白无杂毛,人称“千里雪”,死后葬在廿八都东北的灰山脚下。多年过去,千里雪成了白马精,它伸伸腰,探探头,廿八都便地动山摇、山头开裂。“白马精”怕大王庙中的东岳大帝就没有作怪。后来,地方首脑请来阴阳先生,宰数条黑狗,将血滴入裂缝中,白马精被镇。至今,在廿八都灰山一带仍可见山头开裂、裂缝纵横。见《廿八都镇志》,第492页。作怪,因此在此修建了大王庙,以威震白马精保一方平安。后来庙被洪水冲毁,才复建于现在的位置。②罗德胤:《廿八都古镇》,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1页。
新中国成立后,在长达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大王庙失去了宗教功能,庙会活动全部停止,庙宇在不同时期先后被改为不同的公用场所。庙里管理人员T先生告诉我,1949后大王庙成为政府的公产,1952年被供销社用做收购和存放木炭的仓库,1958年改为酒厂,1963年改为木器厂,1967年人们用宁波运来的海水造盐,大王庙曾作为造盐的场所和盐仓,1970年作为竹篾生产车间,1975年改作酒厂,一直到2005年酒厂迁走。近年来,经过一批信徒集资重修神像,恢复祭祀和庙会活动,这里又逐渐重新成为香火兴旺的宗教庙宇。
二、大王庙作为“根庙”的角色与复兴
用桑高仁(Sangren,1987)的民间宗教理论③民 间宗教与区域制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民间小庙是大的区域的“根庙”的分化,民间小庙到大的“根庙”的朝圣行为是把地方庙与中心庙宇链接在一起的媒介。引自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看廿八都的土地庙、社公庙、大王庙之间的联系,大王庙的角色就相当于“根庙”。廿八都有浔里、花桥、枫溪三个村,这三个村各有一个社(黄坛社、隆兴社、新兴社)。各社均建有社庙,社庙的管理范围相当于一个自然村的村域,而在社下面每个村内的弄、巷中还设有土地庙,以保这一小区域家户平安。“社”既管阴间也管阳间,而大王庙的东岳大帝是管理阴间的总管,换句话说,大王庙相当于三个社之上管阴间的“根庙”。大王庙中碑文《东岳宫记》记载了1923年最后一次重修,对此进行记录的人正是“黄坛社”一个叫左谨的人。这一信息说明区域性的“社”对中心性质的“根庙”的复兴和重建责任在身。
大王庙庙会的复兴,同枫溪村新兴社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徐氏的口述,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经过:“当时庙里还是酒厂在里面,没有地方摆。那些人坏得很,我们刚摆了两个凳子他们就给踢开了,盘和碗都打掉了。从2001年开始我就给大王庙做佛龛了,做佛龛是我起的头儿,我们枫溪(村)人干的。后来庙会兴起后,每次有四五十桌呢。”④访谈时间:2008年8月27日;访谈人:徐氏;访谈地点: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枫溪村。
2009年,我们对大王庙管理者的访谈证实了徐氏所讲的情况,即大王庙的活动最初是由枫溪村新兴社管理者开始做的。他说,最初是一些信徒将大王庙内清扫干净,并在民间筹集一部分善款制作了神像,之后就有信徒(大多是老年妇女)轮流清扫维护。接着有更多的人开始陆续到大王庙进香,这几年香火逐渐旺盛起来。
廿八都镇三个社庙中,黄坛社、隆兴社在1950年土改后已经失去社庙功能,唯有新兴社香火仍在,正是由于枫溪村新兴社管理者发起组织信众筹款制作神像、神龛,大王庙信仰空间才得以复兴。在民间,这种规模较小的村庙对中心性的“大庙”有着周期性的进香义务,那么大王庙的复兴也是一些有组织的民间信徒向“大庙”寻找组织认同的一种行为。
“复兴”后的大王庙会都是依靠民间援助自发组织的,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东岳公寿诞日)、七月二十九(地藏王寿诞日)、八月十一(李老真君)、十月初一(东岳公会)都有活动。届时,廿八都附近的五佛村、花桥村、枫溪村、上峰村,甚至福建、江西、浙江都有人来祈愿祭拜。庙会时,组织者会请大约二三十人帮忙,有专门分工:管香火的,管火的,管香的,管纸钱的,管做饭的,管买菜的,管记账的。做庙会的钱是大家援助的,要登记,用毛笔在红纸上写出来贴到庙外公布具体金额。2008年我们来这里调查的那天,正好是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据大王庙当时的组织者介绍,庙里的主殿正中供奉的是东岳公,左边是地藏王菩萨、右边是李老真君。他们说,明天(农历七月二十九)是地藏王的生日,会有一个很大的庙会,可能要有21桌。我们看到主殿内有一些老人,正在主殿下的庙堂中准备庙会用的东西,有的在擦桌,有的在整理香烛、冥纸,场面很热闹。
从整个廿八都公共建筑使用情况来看,由于多数公共祭祀空间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宗教功能,民众不能从小的土地庙、社庙来完成更高层次的祭拜。而很多公共建筑功能的改变已造成民众祭拜行为和信仰心理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大王庙的复兴实际上填补了地方小庙所不能完成的公共仪式空白,整合了其他庙宇的公共祭祀活动。我在2008年调查时,发现庙堂四边塑了几尊小的神像,包括四大金刚、太阳神、观音菩萨和月亮神、财神、五谷神等,可以看出,这个空间中杂糅了许多祭祀内容。
由此可知,大王庙宗教活动的复兴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其历史感的一种延续和再创造,另一方面,从中也可以体会到信众对大王庙这样一种具有区域整合性质的信仰空间的认同。
三、再造文化空间的认同与选择
1.消失的庙会
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大王庙由政府出资进行修缮,庙会活动暂停了一段。修缮后的大王庙建筑外观变得整洁美观,倒塌的照壁不仅得到恢复,墙壁也粉刷一新,庙内神像也更换成了新的。但是仔细观察,却发现上一年还香火旺盛的大王庙,明显变得冷清了许多,与2008年筹备地藏王寿诞日庙会的热闹场景形成鲜明对比。已经复兴的庙会活动,在庙宇被修缮后却发生了改变:来烧香的信众少了,庙会期间也没有人来祭拜、敬香,庙会似乎突然消失了。据说,这可能与政府更换新的神像有关。原来的神像是民间筹集资金并找人用樟木雕刻、请宗教人士进行开光的神像,这些神像已经在庙里安放了几年,信众对它们已经有较多的认同。唐先生说:“新的神像是旅游局做的。现在老菩萨没有回来,这个庙会提不起,很冷清。老菩萨是2003年用樟木雕的,2006年从江西请来师公开光放在大王庙,开光花了好几千块。平常老百姓初一、十五都会来拜的,很多人的,现在没人了。”
从对徐氏的访谈中笔者获得了另一些信息:大王庙的庙会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神像的搬迁到了位于西边村的地母庙。以前地母庙庙会每年两次:三月初一日,十月十八日。去年七月、十月和十一月,原本在东岳庙的庙会在地母庙进行了:“大王庙每年庙会四五十桌呢,现在搬走了,没人去了。现在搬到地母庙了,今天八月十二、十月初一、七月二十九都是在地母庙做的庙会。菩萨搬到地母庙就有人拜了,大王庙就没有人来了。我们的菩萨去了哪里,大家就到哪里拜。”①访谈时间:2009年12月28日;访谈人:徐氏;访谈地点: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枫溪村。
2.地母庙纷争——老神像的争夺
2008年至2009年,政府对大王庙进行修缮,重塑神像不仅导致了该庙庙会主体的消失,还因此带来了一场争夺民间信仰资源的纷争。
东岳宫由政府进行修缮时,旅游局要重新雕塑菩萨,老的神像因地方不够不让放在殿内。原来管理庙的人想办法,到处去租房子,后来就跟西边村地母庙的人商量,暂时存放,以后假如租得到房子,想重新弄一个庙。地母庙的人同意了,旧神像搬过来的时候,都写有清单,双方签字。但一年后,当大王庙的人想要回神像时却与地母庙的人发生纷争。当时大王庙来取神像的人找了旱塘村的五六十人,骑着摩托,砸了地母庙的锁,损毁了3扇门。此事件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村民们认为这是双方利益之争,谁有老神像谁就能够把庙会的“人气”拉回来。但是当事人对此的说法却不一样。〛
A(地母庙的当事人):“当时来取佛像的人说好3天之后来拿,但是提前了,负责人没有在场,来取的人就误以为要和他们争神像。因为有清单,我们要求双方负责人都在场当面点清,也算有始有终。他们说不行的,今天非得把菩萨拿回去。随后,拿石头把锁磨开砸了,3扇门都砸了。他们都这样做了,我们肯定也不客气的。本来想义务让他放在这里一段时间,也没说要多少钱,但是既然这样,也没有什么必要客气了。我们也是农民,也不是很讲究那个的。后来,还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反正今天是他们的不对,不是说菩萨不让拉回去,他们砸了3扇门,还有钥匙钱,算起来可能是3000多块钱。所以,拖拉机当天没有把神像拉回去,我们说好了要罚款,罚多少钱说好了,下次来拉东西的时候把钱带上,我们把东西全部还给他。就是这样,我们那天就把条件谈妥了,他们也同意了。”②访谈时间:2010年8月24日;访谈人:饶氏;访谈地点: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花桥村地母庙。
B(存放神像的原大王庙管理人员):“地母庙那边说不可以弄回来,要给他们钱。本来是两个人准备讲和,准备把菩萨拿回来,他们去了跟地母庙的人好好商量,那边不同意。原来他们是要3000的功夫钱,搬来搬去也要钱的,反正你不同意,华坞口和旱塘头村的年轻人就开车去抢了,结果花了4500块钱。其实事情的起因是某人的女儿生病,病得很厉害。有人跟她讲,你要把这个弄回来,不弄回来你女儿的病不会好的,意思是把大王庙的菩萨请回来,这个毛病会好。她就想出办法,叫他们村庄的人把菩萨拿回来,摆起来,起头才会使用科学证据。所以,就证据使用顺序而言,科学证据是排在第二位的,是常识证据的补充。另外,科学证据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是,它有时会与效率、公正等诉讼价值目标产生冲突。聘请专业人员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进行检验、分析、判段,需要有时间、资金的保障,无疑会造成诉讼的拖延,会使贫穷的当事人无力承受。①二是,审查科学证据对事实认定者来讲是件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一方面,事实裁判者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被迫使用专家证言,而另一方面,他们还得对专家证人的证言进行批判性评价,甚至需要他们对专家证言之间的矛盾作出决断。但是,一个连该学科的基本概念都尚未掌握的人,又怎么能够洞悉其中的复杂性,或者对这些‘高级传教士’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呢?”②优先使用常识证据也是很多国家的做法,如澳大利亚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明确规定的普通知识规则:“只有在专门知识超出陪审团的知识和经验范围时,才有必要聘请专家提供专家证据。也就是说,如果证据所涉及的知识和经验,在陪审团完全有能力作出判断的范围之内,就没有必要聘请专家。”③《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条规定了专家证言的辅助规则:“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将辅助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裁判有争议的事实,因其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对此作证。”换言之,并非所有的主题都适于专家证言,“只有承审法官被说服,在一主题上提出专家证言对陪审员(或法官自己,在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中)有所帮助时,当事人才准许提出。”④与此类似,英国规定了专家证言的有用性规则,即只有专家证据能为法庭提供实质性帮助时,该专家证言才具备可采性。
汉斯·波塞尔先生在其名著《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引言”中写到:科学,“已以空前未有的程度与速度控制与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渗透与贯穿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铁面无私的法庭上,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圣经》中的上帝提出的律条,亦不是传统力量的约束,而是‘专家们’的一纸鉴定”。同时,他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又指出,“批判是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部分。批判即是对科学中所提出的每一个答案的批判,是围绕着科学所追求的每一个答案的客观性的批判,是科学中对其每一答案的解释与说明的批判,因而是在科学内部进行的批判”。⑤正是这种“内部批判”才保证了科学中的正确结果。⑥波塞尔先生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把握科学作用的基本原则: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有其发挥作用的边界。
今天,科学毫无疑问已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但它绝不是唯一方式,而是与神话、宗教、艺术、哲学等并存的一种方式。所以,达马斯卡教授的预言有所偏颇,科学证据不可能将常识证据从事实认定中完全排除,正如科学不能完全排除迷信一样,这与科学的普及、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不具有必然联系。
K890
A
1003-4145[2011]11-0069-04
2011-09-20
冯 莉(1977—),女,甘肃张掖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中国民协《民间文化论坛》杂志社编辑。
本课题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支持项目“关于中国民俗文化政策的动态性研究”的成果。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