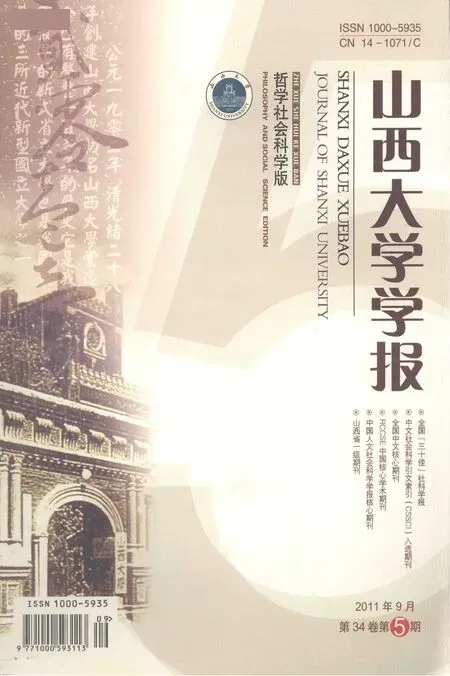宏观认识新探
王 前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宏观认识新探
王 前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宏观认识是以往认识论研究关注不多的领域,但对社会认识和决策有重大影响。宏观认识的对象不能靠逻辑分析完全加以把握,需要运用直觉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加以处理。在宏观认识过程中,视域的自觉扩展、意义的发掘和评价、认识路径的选择和调整起着关键作用。宏观认识规律的研究需要充分利用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开展跨文化的合作。
宏观认识;视域;意义;认识路径
宏观认识是指只适合在宏观层次上进行的认识活动,比如对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全面了解、对社会活动趋势的估计、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其特点是难以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往往需要运用直觉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思考。这类认识活动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对人们的观念、决策和行为有重大影响。可是,由于其中的直觉思维具有非逻辑性,一般认为不够严格,因而以往的认识论研究很少关注这一领域。人们对宏观认识活动大都习以为常,很少专门研究其对象、方法和规律。这种状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带来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 宏观认识对象的特点
人们在宏观世界里的认识活动,并不都是只适合在宏观层次上进行的。相当多的认识活动要由宏观层次向微观层次不断发展,并以微观层次的认识结果为基础来反观宏观层次的问题。这种思路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而且经过逻辑分析方法的长期影响,已经成为以往认识论认可的科学研究模式。按照这一模式,作为认识对象的整体被不断分解,越分越细,使物质结构研究逐渐深入到基本粒子层次,使技术应用逐渐深入到纳米、比特和基因的层次,然后以微观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解释各种宏观现象。逻辑分析的方法还广泛应用到数学、经济学以至哲学领域,成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典范。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的前言中写到:“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炼的技巧。”[1]
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要求认识对象的信息可以充分获得,认识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明确界定,认识对象的发展趋势可以准确预测,认识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可以确切判断。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逻辑分析的运用获益良多,有些经济现象、心理现象、语言现象也通过逻辑分析得到比较透彻的理解。然而,当宏观世界里的认识对象达不到逻辑分析要求的严格标准时,以往的认识论就暴露出局限性。基于逻辑分析的认识论模型是简单化、理想化的,而宏观认识活动是面向现实的、不断变化的、不能随意简化,也难以透彻解析和把握。
宏观认识活动之所以达不到逻辑分析要求的严格标准,是因为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宏观认识对象的相关信息难以充分掌握。宏观认识对象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物,关系复杂,变化多端,能够直接获取的信息有限,因而能够进入人们认识领域的信息可能是相当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宏观认识以及相应的决策,大都是立足于不完全的信息进行的,因而很难保证高度的精确性。历史上很多人和事曾经是存在的,但留下来的信息不仅很少,而且可能有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也不会展现其全部信息,这里除了刻意隐藏之外,还有人们获取信息途径和手段的条件限制。人们会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宏观认识对象的相关信息,但这种全面性远远达不到严格逻辑分析所要求的彻底程度。
其二,宏观认识对象的内涵和外延难以明确界定(或没必要明确界定)。由于宏观认识对象的相关信息不完全,而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其内涵和外延难以一次性地完全界定下来。对于某些宏观认识对象,诸如阶层、国家、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等等,人们的理解只能大体一致,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2]更多时候,人们关于同一宏观认识对象的讨论是从各自理解出发的,具有不同内涵和外延,但却没有明确意识到,所以讨论的结果难免众说纷纭。即使是人们的理解在某一时期基本一致的宏观认识对象,其内涵和外延也会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
其三,宏观认识对象的发展趋势难以准确预测。在信息不完全和定义不精确的情况下,准确预测宏观认识对象的发展趋势当然极为困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宏观认识对象的发展趋势,比如个人命运、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战场态势,只能做出大体上准确的预测。而且对未来发展趋势预测得越具体,其可信度就越差。过于自信或轻信他人对未来的过于具体的“准确”预测,会给当下的决策带来巨大风险。
其四,宏观认识对象的意义和价值难以确切判断。随着时代变迁和人们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同一宏观认识对象可能显现出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在特定条件下,相对于特定的人或人群,宏观认识对象的意义和价值是相对确定的,有些宏观认识对象的意义和价值还可能具有相当长时期的稳定性。但是人们理解和判断宏观认识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常常忽略了它们在何种条件下成立,或相对于哪些人成立,因而容易出现相互冲突的判断。
尽管宏观认识对象达不到逻辑分析的严格要求,宏观认识活动却不可能因而停顿下来。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每天都要面对个人、群体、国家、人类社会大量宏观认识问题,随时需要进行并不十分精确的思考和决策,甚至需要即时反应和迅速抉择。在这种情况下,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合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出现冲突也难以察觉。直觉思维的优点是方便、快捷,富有启发性,缺点是不够精确可靠,需要逻辑思维的补充和修正。人们通常的做法是:先从直觉角度提出原初的观念,然后从逻辑角度加以审查和修正,再回到直觉角度进行补充和完善,循环往复,不断发展。如果直觉的认识成果看上去不合逻辑,就会被舍弃或搁置。历史上很多看起来不符合逻辑分析要求的思想成果,往往只被看做文化遗产,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有效影响。按照逻辑分析方法建构起来的认识论,难以将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充分整合起来,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宏观认识活动的形态、方法和演变规律的研究来加以解决。
二 宏观认识中的直觉与逻辑
在宏观认识活动中,直觉和逻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有着特定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发现这种关系需要适当的途径。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直觉思维是非逻辑的、整体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然而直觉思维的结果并不是反逻辑的。尽管直觉思维本身难以进行透彻的逻辑分析,但直觉思维酝酿过程中仍然需要避免逻辑矛盾,尽管这是一个极迅速的过程。在宏观认识活动中,某些直觉思维成果看起来不合逻辑,甚至自相矛盾,这种缺陷有可能通过自觉扩大视域的方法加以消除。
“视域”是现代西方解释学强调的概念,表示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和理解的构架或视野。[3]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解释过程中会发生解释者的视域和文本的视域的融合。[4]视域除了用于在解释过程中发现事物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其认识论上的功能,就如同心灵的“窗口”一样,划定认识主体的思考范围和认识对象的存在背景,从而决定了对认识对象属性和功能的认知结果。视域的确定与认识对象的确定是同时生成的。当人们将某种对象事物纳入注意的视域时,同时也就相应的划出视域的边界,而视域之外的事物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就成为被遮蔽的东西。视域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对于对象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有所不同。在宏观认识活动中,直觉思维的视域常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只是考察了事物的某些方面、某些条件下的属性、某些时段的情形,这样就难免犯“以偏概全”的毛病。有些直觉思维的成果看起来不合逻辑甚至不合情理,无论如何讲不通,就是因为视域之外的某些隐蔽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进去,一旦考虑到这些因素就都讲得通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自觉地扩展视域,尝试发现各种相关的可能因素,以填补认识空白,消除逻辑缺陷。直觉与逻辑表面上的冲突,在这里成为扩展视域的动力,并能引导视域扩展的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宏观认识的思想成果中,直觉思维的成果占主流。由于历史上逻辑思维不够发达,古代很多思想成果并没有经过逻辑的追问。许多格言、寓言讲的道理至今仍富有深刻启发性,但人们很少追问这些道理在何种前提和条件下才能成立。比如老子讲的“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能争”等等,显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立的,这里的隐蔽前提条件有待揭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疑惑某些事情本不该发生却竟然发生了,或本该发生却竟然没有发生,也是因为有些隐蔽的因素没有考虑进去,表明人们的视域还有待扩展。直觉思维的认知结果看上去不合逻辑,大都是视域的局限性所致。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视域的确定会“遮蔽”很多相关要素,而视域的扩展就是一个“解蔽”的过程。视域的自觉扩展是认识主体的一种能力,相应的需要一些具体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
如果说逻辑分析是由宏观向微观不断深入的认识活动,那么宏观认识基本上是由眼前的宏观向更大的宏观不断扩展的认识活动,其视域也越来越大,尽管后者的变化给人的感觉可能并不明显。实际上,当后代人看待前人的宏观认识成果时,或者成年人看待自己以前的宏观认识成果时,其视域都是在不断扩大的。阅历的丰富、知识面的拓宽、思想境界的提升,都有助于视域的扩展。这种与逻辑分析相反的认识活动发展趋势,展现了以往认识论忽略了的另一种思想旨趣,值得认真关注。
三 宏观认识中的意义评价
在宏观认识活动中,通过自觉扩大视域,可以更深入发掘和评价对象事物的意义,这里同样需要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充分整合。
对事物的意义进行发掘和阐释,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主题。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意识、意义、意向性等范畴,已经触及“本质直观”、“生活直观”等与直觉思维相关的认知过程。从宏观认识角度看,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观念和方法富有启发性,对理解历史事件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意义以及培养生活情趣很有帮助,但难以用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具体实践活动。对宏观认识对象的意义的发掘,就是要把认识对象置于一个新的环境中,或者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察其性质和意义,当然这是以视域的自觉扩展为前提的。事物的属性都是在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有些隐蔽的属性必须置于特定环境中才能体现出来。事物的意义也是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事物与其环境和背景事物的新关系会展现其新的意义和价值。对事物意义的主动发掘和评价,需要主动变换其环境和背景。这种认知方法的动态机制,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研究很少注意的。
在宏观认识活动中,对于客观事物意义的评价更具相对性,更多地依赖于认识主体运用直觉思维的选择。对某一事件做出“意义重大”的评价,往往与认识主体的意向性有关,甚至受到潜在的利益因素的驱动。然而,被人们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很可能在当时或后来并未产生预期的实际影响,而一些当时看来意义不大的事件后来却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影响。这里存在着意义与实效性的关系问题。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成为行动的目标,但实现目标并产生实际效果还取决于其他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直觉思维适合对事物的意义做出判断,但对实效性并不敏感,因为直觉思维对于对象事物数量特征的变化缺少细致衡量,缺少实效性的量化指标,这一弱点需要逻辑思维的补充。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宏观认识的思想成果大都是意义视角的判断,上至天地人心,下至日常生活,如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由于忽视实效性方面的充分考虑,古代社会经常出现一些从政治或伦理角度看或许很有意义,但效益和效率却很低下的工程实践活动。单纯强调从社会意义角度进行技术和经济决策,实际上阻碍了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
有些看起来意义重大的事件却不具有实效性,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个人的判断可能具有认识局限性。自认为某一事件意义重大,未必真的如此,或未必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二是社会群体的判断具有历史局限性,有些事物刚出现时并不被普遍看好,其重大意义只是在后来的社会环境才充分体现出来。儒家学说和孔子的社会影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三是学科视角的判断具有专业局限性,基于直觉思维的人文学科视角的判断容易忽视事物发展的相关经济和技术条件,因而弄不清为何具有重大意义的某些事物却得不到切实地发展。通过逻辑的追问和自觉扩大视域,有助于发现意义判断与实效性反差的原因所在,使事物的意义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四 宏观认识活动的路径
宏观认识活动在认识路径的选择和调整上有其特殊性。由于宏观认识对象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宏观认识对象意义的确定具有相对性,所以宏观认识活动的认识路径选择需要靠直觉在摸索中进行,事先很难有完全准确可靠的方案。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意识到适中的认识路径是相对准确可靠的,于是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强调的是在具体情境中把握德性的能力。德性是“中道”,是适度的理性选择,既非不足,也不过分,这不能以规则或传统的节律来表达,只能通过实践智慧来达到。[5]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的追求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强调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儒家学说主张“允执厥中”,道家学说强调“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管子学派认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都是主张选择“中道”。这里的“中道”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是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可是,适中的要求在理论上容易理解,通过直觉思维也可以领悟,但在实践层面并不好把握。
宏观认识活动中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认识路径已经出现的偏差,一错再错,直到极端情形下才有所领悟,但却悔之晚矣。单靠逻辑分析难以发现和调整这种偏差,而直觉思维在这种情形下又很难保证可靠性。造成认识路径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心态因素造成的倾斜,二是短期利益需求的驱动,逻辑上的直线式推理也在不断为人们提供似乎可靠的“依据”。宏观认识活动中的心态因素直接影响对认识路径的把握,平和的心态有助于视域的自觉扩展和对事物意义的恰当把握,而极端的心态会使视域僵化,对事物意义做出极端的判断,使认识活动偏离适中的路径。短期利益的需求也会限制视域,夸大局部活动的意义,影响对事物整体意义和实效性的合理判断。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特别强调认识路径的自觉纠偏,给出了很多方法论的启示。
老庄哲学主张“悟道”要有清静无为的心态,不自以为是,不居功自傲,谨慎从事,抵抗住外界诱惑;儒家学说强调正心修身,反求诸已,做到“心统性情”,这些要求对于保持平和心态都是极有价值的。自觉纠偏还要注意事物发展“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趋势,从一些过度表现的显性特征中发现相反的隐性趋势,这就是老子指出的“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还应注意,追求短期利益一般采用的直线式思维,目的与手段完全一致,但很多时候会出现意料不到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事物发展的道路常常是曲折的,沿着直线行进的认识路径自然会脱离现实。中国古代的“太极图”描绘的阴阳分界曲线,体现了事物曲折发展的基本态势。按照这一图像的启示,当沿着曲折的阴阳分界线前进时,要在没有达到极端之前就适时纠偏,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不利的逆转。
以逻辑分析为基础的哲学方法论,尽管也关注到事物对立统一的变化,主张用辩证逻辑弥补孤立、静止、片面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弱点,但在宏观认识层面的应用仍有局限。因为日常生活中便捷的直觉思维往往取代细致冗长的辩证逻辑推理,人们的实践活动在急功近利驱动下往往难以控制,直到出现极端的后果才止住脚步。在这里,功利欲求和逻辑推断似乎是相互“诱发”的。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技术的直线式发展,是在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和社会文化冲突之后才进行反思和控制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宏观认识研究本身的薄弱。在一个需要应对全球化问题的时代,宏观认识活动的路径选择和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五 宏观认识研究的文化背景
对宏观认识活动的研究,需要充分利用东西方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开展跨文化的合作。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认识论范畴、模式和规律,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西方传统文化资源,但对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关注不够。由于逻辑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认识论研究提供的认知模式越来越精细,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却越来越受到限制。政治、经济、军事、工程技术、文艺创作、日常生活中的认识活动和相应的决策,都很少有时间、有条件、有必要上升到认识论高度,运用精细的认知模式。许多时候,人们可能面临不同甚至对立方案的选择,每一种似乎都有充足理由,看起来都说得通,这些时候只能依赖有丰富经验的人的直觉。而此时对直觉的信任,其实是以对以往经验的信任为前提的,这里仍然有很大的风险。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对研究宏观认识活动有益的思想资源,包括一些基于逻辑分析的认识论视域之外的范畴,如“心”、“象”、“意”、“道”、“气”等等,以及一些被认为未经严格论证的认识方法,如“取象比类”、“立象尽意”、“得意忘象”,还有“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之类规律性的总结。这些范畴、方法和规律性认识经过历史上长期的实效性检验,至今对现实的宏观认识活动仍有价值。可是,这些思想资源的意义和价值在自身体系内是不会充分展现的,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挖掘这些思想资源的意义和价值,同样需要自觉地扩展视域,融贯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开展深入探索。这方面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是对传统文化的直觉思维成果进行逻辑的追问,探求其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由此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很多对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解读,着眼于字面意义的准确,各种版本和前人注释的比照,很少注意逻辑上的追问。即使在逻辑上解释不通,也会归结为原意如此,不去考虑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要体现其现代价值,必须将其置于宏观认识活动的研究背景上,同源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论模式进行比照,用逻辑追问的方法进行现代意义的诠释。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宏观认识活动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发展,已经表现出对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关系的特别关注。现代认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使得个人隐性知识、体验性思维和创新机制的相关研究成为热点话题。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互动,加深了相互理解和解释能力。这些条件都为宏观认识活动研究的全面开展创造了难得机遇。而宏观认识活动研究提供的新的思想成果,又会促进哲学研究更有效地影响现实生活,促进人们思维和决策能力的提高,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更深入交流。
致谢:本文修改过程中,霍桂桓先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1]伊·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
[2]赵敦华.当代英美哲学举要[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92-97.
[3]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7.
[4]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2-194.
[5]唐热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J].哲学研究,2005(5):70-79.
(责任编辑 李雪枫)
A New Approach to Macro-cognition
WANG Q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116024,China)
Macro- cognition is a field which is not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e study of epistemology,but it has great effect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The macro- cognitive objects can not be grasped completely through logical analyses,Instead,they can be treated in the way of combining intuition and logic.In the macro -cognitive process,the conscious expansion of the field of vision,the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the selec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cognitive approach play a key role.The study of macro-cognitive laws need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nd to carry out cross-cultural cooperation.
macro-cognition;horizon;meaning;cognitive approach
B023
A
1000-5935(2011)05-0001-05
2011-04-16
王 前(1950-),男,辽宁沈阳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科学伦理、科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