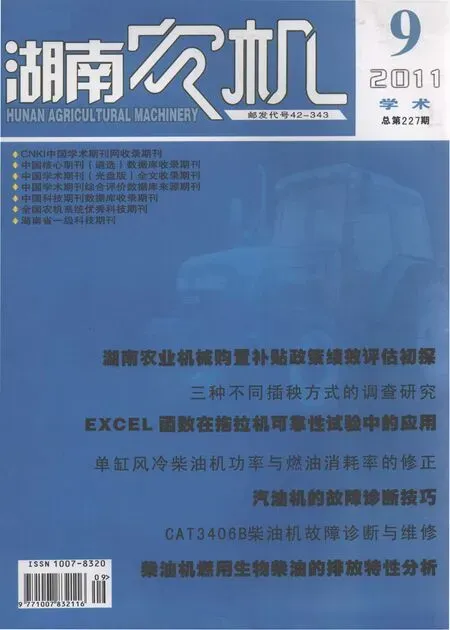以对话的视角浅析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
蒋一扉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法律系,四川 成都 610207)
1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
传统的国家法让我们通过法律去看社会,而民间法的提出可以让我们反过来通过社会去看法律,使我们深入到法律内部去洞察它的本质问题。当然,在这其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紧张关系,集中体现并主要爆发于各地各级法院法官的办案过程中,即民间法与国家法在不同区域间、不同民族间的调控力量的对比关系,主要通过各地各级法院法官在处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中对法律方法的运用而得以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二者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就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就是中西法律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冲突。国家的控制能力再强,甚至即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国家这架机器上的 “螺丝钉”,也不能彻底销蚀社会自治力量的客观实存。
《马背上的法庭》这部影片真实记录了我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处理方式以及当地极具特色的风俗习惯。笔者在这里就顺着影片的思路继续开始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的案例。
四川凉山彝族。在债权债务关系方面,由于当地彝族的社会契约观念不发达,租佃、借贷一般采用口头方式,即使是重大交易,也是多采取由第三人在场的方式,很少用书面形式。在婚姻家庭方面,根据彝族当地的习惯法,订婚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标志着婚约成立,对双方均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另外,彝族人对于没有明确证据或无法决断的疑难案件,如重大的偷盗案件未能当场抓住窃者或没有其他物证,或者纠纷通过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则交由毕摩(彝族掌管宗教事物的神职人员)主持,通过神明裁判解决。
云南布朗山布朗族。布朗族的村社头人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当许多家族聚在一起组成一个村社之后,为了便于管理公共事务,村社成员共同推选出几个头人作为村社内外事务的管理者和代表者,村社的日常事务都由头人管理,对内对外的重要事情由头人会议做出决定。大会所做的决定,村社成员都不得违抗。另外,当村社接受新迁入户或同意迁出户时,都必须通过村寨头人达曼和其他头人的同意方可生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布朗族各层次的头人之间以及他们与普通族人之间都初步形成了等级关系,并根据自身职权所确定的地位不同,产生一定的从属关系,这样会在某些方面造成特权主义以及利益冲突关系。
贵州苗族。苗族在历史上是没有文字的,传统的议榔规约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尽管这样,大量的习惯法还是长期存留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这些习惯法是依靠苗族特有的被称为“理词”的一种口传形式传承着。根据其传诵的内容,可以分为佳和理两部分。佳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以及处理人际关系、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依据;理是行为规范,是从一些公众认可的传统朴素的伦理道德、禁忌及生产和生活习惯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它通过寨老组织的强制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得以实施。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若出现了纠纷和矛盾,他们的解决方式往往是独到的,甚至有时是与国家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生活在“小传统”中的民间法,它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中逐渐形成,并在乡土社会中调整着乡民之间的关系和乡村之间的秩序。民间法常出于自然,人们在生活中甚至都没有认为那是一种来自“法”的约束,因为这些乡规民约已经慢化为人们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发生纠纷时,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些规则、范例。“山西之煤窑、四川之盐井、浙江之渔业、岭南之沙田、华北之平原、闽南之山地、两湖之丘陵、江南之水乡,各有其法。”究竟这其中的原因和解决对策分别是怎样的,笔者将试以建立二者对话的角度从生存土壤、发展脉络、形成传统、知识结构、主体需求、实施成本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和考察。
2 冲突发生的缘由:“对话”的缺乏
(1)生存土壤——“对话”产生的根本。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个定义在某种意义上仅指国家正式制定法这一领域,在人们的认识中甚至会将其归置于法律条文这一更加狭小的范畴之中。这就注定国家法的生存土壤是普适而具有权威性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表述,就极具威慑力和统一性。
与国家法不同,民间法的生存土壤显得更为复杂。我们同样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条文来举例,总纲中第四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从这里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是有其特殊性的,国家制定法在这些地区中实施时应考虑其相应的民族习惯和风俗,同时尊重当地民族自治的一些问题。
国家制定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一步一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代表着国家法治的动向,是对国家法治进程的表述。国家制定法往往都是进过严密论证后确切表述出来的,无论从书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具有其科学合理性。民间法产生于民间,发展于乡土,稳定于人心。民间法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它的生存空间更多的是在于乡土社会中,它是人们社会实践和生活秩序的客观需要,在特定区域对一定的人群和组织具有制约效力,同时,民间法主要依靠人们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取向来发挥效力,从而调节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孕育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土壤是不同的,它们带给我们对法律的理解角度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上说,这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产生冲突的根本之所在。
(2)发展脉络——“对话”的外在表现。国家法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来追溯是上个世纪法学精英们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是在西方法学家唇枪舌战中产生的,也是一种新的法学理念的表现形式。作为从传统法律秩序向现代法律秩序过渡中的我国来讲,国家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离不开国家强制力和政府系统的规制的。国家法是现代法治的重要体现,诚如我国法治十六字方针中所说的“有法可依”,国家法是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而作为民间法,它首先是源于民间,是民间习惯、风俗等的聚合体,它代表着某一地区乡规民约的方向,它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其不断发掘、整理以及继承的过程中的,不像国家法是在社会推进以及国家需要中建立和发展的。在这里,笔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国家法的修订工作,之所以会不断产生各部门法的修订草案,是因为国家法在不停地迎合社会需要,并且是尽力去保障整个法治进程的有效推进,而民间法并没有更多的修订工作,因为它是在长期积累中约定俗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将其印入脑海,并且将其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地区普遍认可的规范去遵守。
国家法与民间法不同的发展脉络,前者是在时代需求中发展,后者是在约定俗成中稳定,这可以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两者在其表现形式方面的冲突原因。
(3)形成传统——“对话”的渊源基础。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其著作 《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大小传统的概念,所谓大传统主要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由社会上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而小传统则是指存在于农村社会中,以农民为代表的文化,是一种具有地方社区和地域性特色的文化传统。谢晖先生将大小传统的概念带入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研究领域,将国家法引申为大传统,而把民间法比作为小传统,进而论述了大小传统间冲突的必然性:这种冲突的必然性取决于大小传统各自所依赖的主体——国家与社会、所代表的利益——权力与权利、所表达的人性——社会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对立。也许就是因为这大小传统的缘故,国家法与民间法从渊源上来讲就是有冲突的,国家法出于倡导一体、统一与权威的大传统,而民间法出于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小传统。国家法主要来自于各部门法的一个聚合,因而国家法的表述方式侧重于严格精准,而民间法主要来自于乡土民间的习惯、约定、风俗等,它则更偏向于通俗易懂。
传统不仅仅代表着过去,它更多地也指向了现在,传统在我们的脑海中是一种过去式的固化,然而它深刻的内涵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它是活在我们身边的,是在不断吸收与借鉴中发展的,从这一方面讲,民间法受此影响较之国家法会更大一些。民间法中很大一部分是一种对古代“礼”的新诠释,这就与民间法由来已久的“乡土本色”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大家从熟悉中得到了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一味去追逐国家法的脚步,似乎就很无情地抹煞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质朴的情感,从而也会让本不属于这片土地的“陌生感”生根发芽。
“礼”与“法”的传统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中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大小传统的各自呼吁下,国家法与民间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国家法彰显着一个国家“法治”的理念,而民间法多了一份“人性化”的魅力,可以说两者发生冲突的渊源基础就在于形成传统的不同。
(4)知识结构——“对话”的主观要求。“对法律的理解,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而不是对法律条文的熟悉程度。”“法律知识是通往认识法律之路,而非理解法律之桥。”尹伊君先生这两句话真切地道出了理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不同之处。国家法作为正式制定法出台,它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若要准确认识它的内涵与外延,要求认识主体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否则只会停留在对其法律条文表面的阅读,而无法洞察其本质所在。而作为认识民间法的主体,相应的条件要求则没有如此苛刻,因为民间法本是一种“民间记忆”,是一种地方性秩序的表征,这与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笔下的“活法”不谋而合,他要求人们不要把法律仅仅视为国家的官方机构发布的规则,应把法律看成是由社会团体创制,并从那里获得了相应的权威。埃利希的法社会学要求人们研究社会本身,“无论是现在或者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都不在立法、法律科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是在社会本身。”所以当真正要去认识和理解民间法时,认识主体应当具备更多的社会经验和更为扎实的社会阅历,而不单单是专业的法律知识。
基于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不同,有些人较为偏重于对专业法律知识的修养,有些人则重视社会经验的积累,他们在认识和理解法律时就会发生主观接受的侧重点不同,久而久之在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时就会有其不同的主观意识渗入,从而形成不尽相同的观点与态度,这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产生冲突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
(5)主体需求——“对话”的主体利益。国家法作为“国家之法”,民间法作为“民间之规”,它们在主体需求上也是不同的。国家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多的是侧重于对现代的需求,故而多了一分法律的理性;民间法因为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它较为偏向于对传统的保留,我们可以说它更多地是被赋予了一些感性,就像弗里德曼曾说过的:“违反大家感情和道德愿望的法律很难执行。”
国家法因其权威性的保证和形式严格性的要求,还有近来国际社会中全球一体化理念的冲击,它需要跟随时代的脚步,与其他国家的法律进行交流,然而在交流中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加之其自身的国际化要求,国家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发展状况。民间法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本土资源,基于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和尚有差异的经济发达程度,它在特殊的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的地区性和民族性并不能完全融入国家法这条“准绳”之中,使它只能“占一地之优”,而无“顾全大局之力”。尽管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过程中也对宇宙与自然有不断提高的认识水平,但仍然存在很多无法破解的东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农民的知识素养较为低下,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和熏陶相对有限,因而在认识和理解法律时会受此影响,同时对法律的需求也是仅仅围绕着自身的利益来谈论,这是与现代国家法日益发展的趋势不相吻合的。
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主体需求上发生冲突的另一方面是由其各自内部主体的需求冲突所引起的。举个例子来说明,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渴求日益增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周边的法律秩序也就耳濡目染,最现实的例子莫过于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他们通过正规的诉讼渠道有效保障了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当他们结束在城市打拼的生活之后回到农村时,若再发生类似的经济纠纷,他们脑海中会出现法律的印记,从而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权利,而抛弃了原本对其行之有效的乡规民约。这就是乡土民间中的规范在遭遇国家法时在其自身内部发生的冲突,也是源于其主体的需求发生转移这一现象发生的冲突。
(6)实施成本——“对话”的经济考究。“诉讼对于有钱人来说是高昂的奖券,对贫穷的人来说是权利的否定”,边沁这一论述似乎已经道出了诉讼成本的真谛,这也是世界各国诉讼存在的一个现实状况。严格而复杂的诉讼程序,高额的诉讼费用,较长的诉讼过程,这都是我们在诉讼之前要考虑的现实成本问题。
另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还有我国传统“厌讼”、“贱讼”观念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诉讼的心理和社会的成本。国家法的实施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威慑,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而且一旦没有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很可能会出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冤家”、“仇家”的后果。而民间法作为乡土民间生活的一种秩序维护,它是乡民们所了解和熟悉的地方知识,同时也是有着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优势,它的实施主要依靠民间权威以及民间舆论,可谓是近乎零成本的权益维护体,是乡民们所易于接受的习惯风俗。就民间法而言,它在国家法进入乡土民间之前就早已存在,并且一直有效地使乡村生活处于正常运行之中,这套制度对于正式法律制度来说是不太熟悉的,然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乡民却是耳熟能详的,是人们社会交往和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
权衡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实施成本,人们在纠纷发生时会有选择地偏向于低成本的民间法,而抑制了国家法的强制作用,久而久之就会在两者之间发生无法回避的冲突。
[1]孙伶伶.彝族法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晓琼.变迁与发展——云南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4][美]弗里德曼,李琼英等译.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