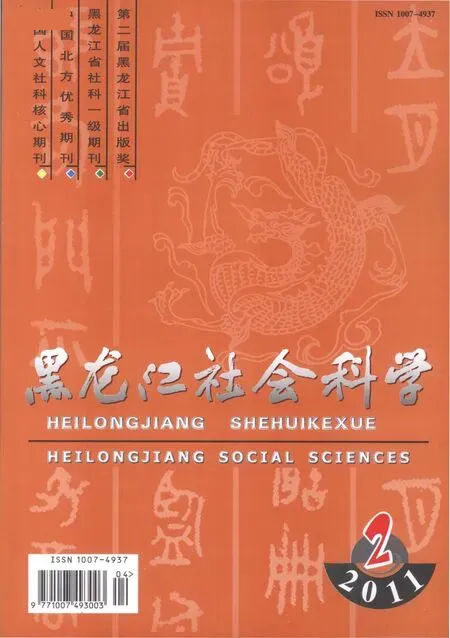不能为“红学”而“红学”
——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熊金星,熊元义
(1.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永州 425000;2.文艺报社理论部,北京 100125)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
——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熊金星1,熊元义2
(1.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永州 425000;2.文艺报社理论部,北京 100125)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姚雪垠;红学;《红楼梦》
在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作家姚雪垠可以说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姚雪垠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深入和发展。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姚雪垠多次总结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经验。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
推动红学界的思想解放和扭转“红学”的研究方向
为了纠正中国当代文学在人物刻画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不感人的倾向,姚雪垠总结了《红楼梦》创造典型人物的成功经验。1978年,姚雪垠认为《红楼梦》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创作典型性格的光辉典范。“曹雪芹如果考虑的不是写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而是考虑如何写出同一阶级的共性,便写不出那么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1]571。姚雪垠在总结《红楼梦》的创作经验时发现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亟待解放。接着,姚雪垠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
1980年,姚雪垠认为《红楼梦》研究要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竭力避免将我们现代人的政治感情、思想觉悟强加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人物身上,“彻底摆脱从政治出发给学术研究所定的调子或框框,也摆脱从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出发,对《红楼梦》做些不实事求是的比拟或解释”。姚雪垠反对迷信权威人物的结论,认为《红楼梦》研究是一门科学,任何权威人物,面对《红楼梦》都是一个读者——比较知音的或不知音的读者。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批驳了红学界的几个权威结论。一是反对称《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姚雪垠认为“历史小说”一词有它本来的含义,不应该将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一般优秀的小说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风貌,但不能都算作历史小说。许多写爱情的优秀小说往往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政治斗争,但不能就算作政治小说。其实,从前的索隐派的问题就是出在误将《红楼梦》当成了“政治历史小说”。二是驳斥了《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谬论。姚雪垠认为在《红楼梦》第四回中只不过抽象地写到金陵城中贾、史、王、薛四家。新中国成立以前揭露过国民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就说《红楼梦》也有“四大家族”,于是《红楼梦》就被说成是写“四大家族”。其实,《红楼梦》只着力写了贾家,薛家的财势并没有写多少,史家和王家都是影子。因此,《红楼梦》并没有写“四大家族”。三是反对用贾府衰败去比附封建社会的没落。姚雪垠认为在我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家族衰败,一些家族兴起,为什么说贾府的衰败反映封建社会的没落?在《红楼梦》中并没有出现将代替封建社会的新兴阶级,没有写出贾家的衰败是由于同资本主义社会力量斗争的失败,怎么能说贾府的衰败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中国封建社会在清朝进入没落阶段是一码事,贾府的衰败是另一码事,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四是反对将曹雪芹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过分夸张,将曹雪芹没有的东西加到他的身上。姚雪垠认为曹雪芹是他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人物,他的思想中有反封建的某些因素,但不能真正具有反封建的觉悟。那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思想家中,比曹雪芹早的李贽,差不多和曹雪芹同时代的戴震,也都没有达到那种境界[1]588-591。姚雪垠对权威结论的这种批判有力地冲击了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教条和框框。1993年,姚雪垠还批评了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新迷信。这种新迷信一是认为“从美学上(或艺术上)分析《红楼梦》的成败得失就不能算是学问。”二是将《红楼梦》看成十全十美、无法逾越的里程碑[2]510-511。姚雪垠深刻地批判了这些新迷信,认为有些红学家醉心于烦琐考证而不肯从小说美学上探讨《红楼梦》的成败得失,就是在对待伟大小说艺术作品上犯了研究方法的错误。而中国的长篇小说在继续发展,有些红学家将《红楼梦》看成十全十美和无法逾越的里程碑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可以说,姚雪垠对中国当代红学界新旧迷信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红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
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反对《红楼梦》研究轻视艺术研究的倾向,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
1980年 7月 19日,姚雪垠回顾了新中国三十年《红楼梦》研究,认为三十年来新中国学术界“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绩,人所共见。特别是在关于《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发现和考订,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更大”。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强调对《红楼梦》进行艺术研究。姚雪垠认为“除对曹雪芹的身世问题、《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脂批问题,等等,继续进行发现和深入研究之外,最好能分出相当力量从事这部伟大作品的艺术研究”[1]588。十年后,中国当代红学界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缺陷。1990年 7月 12日,姚雪垠指出:“几十年来,红学家们至今仍着眼于版本之学和关于曹氏身世的考证,尚欠缺深入的艺术分析。”[2]198因此,姚雪垠坚决反对把从小说美学上探讨《红楼梦》的成败得失置之脑后,认为《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课题应该是分析《红楼梦》在小说艺术上的成败得失。1993年 7月 20日,姚雪垠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红学界的偏向,认为“自胡、俞以来,红学家们利用传统的治学方法,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以及版本的考证研究,做出了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将《红楼梦》作为小说艺术,分析其成败得失,这应该是主要课题,却被置之脑后”。明确地提出了《红楼梦》研究应该在研究方法上“转轨”,认为“‘红学’虽然在过去数十年中做出了不小成绩,但早已进入牛角尖中,必须向新的研究方法‘转轨’,才能有新的发展”[2]510-512。
大家知道,1980年 5月 26日,俞平伯在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国际红学会上所写的书面发言中指出:“《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3]可见,姚雪垠和俞平伯同时指出了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中国当代红学界只提俞平伯的倡导,而遗忘了姚雪垠的独特贡献。
而姚雪垠在 20世纪 80年代初能够提出《红楼梦》研究方向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姚雪垠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从 1974年 7月到 1980年 2月,在这七年时间里,姚雪垠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和作家茅盾通信 88封 (《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收入了他们围绕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和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的通信 73封)。姚雪垠和茅盾在通信中不但有力地抵制了当时文艺批评不谈艺术的不良倾向,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简单化、公式化、表面化的现象。姚雪垠认为茅盾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探讨“正是我们文艺评论界多年来所忽略了的或回避不谈的”[4]67。而“许多年来,没有人能细谈艺术,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评论,只剩了几条筋,影响很坏”[4]91。姚雪垠尖锐地提出:“为什么我们读有的作品除得到思想教育之外同时也得到较多的美学享受,而读另外的作品,尽管它反映的内容很不错,却得不到美学享受?为什么《红楼梦》在艺术上那么感人,具有魅力?”[4]141在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同时,姚雪垠指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给读者积极的思想教育,也应该给读者丰富健康的美学享受。忽略了后者,小说就不能感人深刻,更不能使读者百看不厌。”[4]70姚雪垠在写《李自成》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探索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
姚雪垠高度肯定了茅盾的文艺评论,认为茅盾“具有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学力,总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小说作品,而不同于从干枯死板的条条框框出发。”[4]69茅盾的这些文字,是茅盾晚年留下的重要文献,会引起后代的重视。这不仅因为茅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很有贡献的老作家,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不少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精辟意见。姚雪垠认为茅盾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分析和评论“实为文艺评论的典范”[4]57。姚雪垠不仅是重视茅盾的文学批评,而且努力推动这种正确的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姚雪垠反对简单化的文学批评,认为“简单化是目前文艺批评与创作的大病”[4]84。提倡茅盾的文学批评。后来,姚雪垠从茅盾的信中将谈论小说艺术的部分抄出来发表,“推动重视艺术性的文艺风气”[4]91。1977年,《光明日报》发表了茅盾致姚雪垠的主要谈论小说艺术技巧的书信摘抄,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艺术的认识[4]106-115。姚雪垠和茅盾这些信中的美学思想曾经极大地推动了 20世纪 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
姚雪垠深入地挖掘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简单化这种偏向产生的历史根源,认为“解放区的文学也不是完美无缺……从苏区到解放区,文学直接参加战斗,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政治要求强调过多,对艺术强调不够,则是一种偏向。这个偏向一直带到解放后,成为一种指导思想,谈文艺光谈政治,不谈艺术,不谈美学”[5]108。可以说,姚雪垠推动《红楼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转轨”是他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深入和发展的有机部分。
提倡全面研究《红楼梦》和推动《红楼梦》古为今用
姚雪垠认为古典文学名著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最一般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引导读者正确地欣赏名著,使多数读者既得到美学享受,也提高他们的文学以及生活知识的修养;二是较高的研究目的,就是以自己对于小说美学修养 (包括思想修养)为基础,深入研究古典名著,准确地分析其成功与失误,代古人总结创作的经验教训,寻找出创作规律,借以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2]509-510。而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却始终没有超越古典文学名著研究最一般的目的。因此,姚雪垠大力促进“红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转轨”,认为《红楼梦》研究应有较高一层的研究目的。
《红楼梦》虽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伟大杰作,但是,它在艺术上也确实有不少毛病,绝非处处都好,高不可攀。姚雪垠深刻地指出,《红楼梦》是在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美学正在发育过程中的作品,而且也是作家不幸中年早逝、尚未完成的作品。姚雪垠所说的这个“未完成”,不仅指《红楼梦》只写了八十回,也指这已经写出的八十回也没有充分地推敲修改。前一个是历史的 (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客观条件。曹雪芹这位天才只能在一定的客观的历史条件中产生,不能超越一定的客观条件。后一个是作家的主观条件。假若曹雪芹不是中年早逝,有机会将全书写完,已经写成的稿子有机会再经过认真地推敲修改,留下的稿子应该大为完整。由于中国长篇小说史发育过程的客观条件和曹雪芹中年早逝的主观条件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前八十回《红楼梦》绝不是白璧无瑕的作品。毋宁说,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既有艺术辉煌的章节,也有黯然无色的章节,甚至败笔。只有如实地进行分析,才能将研究推进一步,也才能使《红楼梦》的遗产为发展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服务[2]510-511。但是,姚雪垠所指出的这个“红学”的较高目的却少人问津,进展不大。
姚雪垠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
首先,姚雪垠深刻地把握了《红楼梦》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源远流长,成就辉煌。概括它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宋朝是孕育和萌芽阶段,主要靠“说话人”创作和不断师承的口头文学。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一阶段。元末到明初是长篇小说孕育成熟和正式出世阶段,代表作品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二阶段,不仅奠定了长篇小说的章回体裁,而且开始将听讲的长篇故事变为阅读的长篇故事。说得更准确一点,这类新兴的长篇小说既可以听讲,也可以阅读,而以供阅读为写作的主要目的。第二阶段的长篇小说是属于“讲史”系统,写的人物和故事不脱离英雄传奇,不懂得或不重视写日常生活,还不善于细致地描写人物心理,也不重视描写风景。《水浒传》有写社会生活的部分,但着重在写英雄传奇。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三阶段开始于明朝中叶以后,以《金瓶梅》为嚆矢。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开始写社会生活,反映人情世态,而以常见的“社会人”代替了传奇英雄,同时作家所熟悉的带有乡土色彩的口语成为主要的文学语言。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才达到完成。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产生了《儒林外史》、《歧路灯》和《红楼梦》。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都是高峰[5]470-473。姚雪垠不但从小说艺术发展史上把握了《红楼梦》的地位,而且分别从小说描写的内容和从小说描写的艺术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从小说描写的内容来说,《红楼梦》是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最杰出的。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到元明之际,出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高峰。到了明朝中叶,出现了《金瓶梅》,形成了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二个高峰。尽管《金瓶梅》在思想上有严重缺点,被称为淫书,但是它开辟了写日常生活的道路,通过写日常生活塑造人物性格。到了清代的乾隆中叶,差不多同一时代出现了《儒林外史》、《歧路灯》和《红楼梦》三部长篇小说。虽然这三部长篇小说所写的社会生活迥异,文学风格不同,主题思想相距很远,但共同的一点是重视写日常生活,在描写生活中塑造人物。可见这是由各种历史因素形成的一种趋向。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最杰出的是《红楼梦》[2]511。第二,从小说描写的艺术来说,《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姚雪垠认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重要课题。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典型环境,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就没有典型的人物形象。有了许多光彩的细节描写,才有辉煌的小说艺术。”由叙述故事到细节描写的小说,是文学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从宋代的“说话”到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虽然开始有了细节描写,但仍然以叙述为主。经过《金瓶梅》,到了《儒林外史》、《歧路灯》、《红楼梦》等小说出现,中国长篇小说才完成从说故事到纯以描写为主要表现手法的漫长发展阶段。《红楼梦》丝毫不依靠惊险离奇的情节,纯以细节描写为胜,达到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5]133-134。因此,姚雪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沿着《红楼梦》已经取得的经验继续发展下去,而不是退回到叙述故事的阶段重新向前走。
其次,姚雪垠虽然高度肯定《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坚决反对盲目崇拜《红楼梦》,批评红学家很少指出这部巨著存在的缺陷。姚雪垠深刻地解剖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一是在人物描写上,“《红楼梦》中被着力描写的几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他们的学问修养同他们的年龄、学历都不相称”。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二是曹雪芹写贾赦及其周围的人物多是概念化的,一写到农村生活 (如刘姥姥女婿的村庄生活)就显不出杰出才华,这是什么道理?这些现象包含着什么值得思考的创作规律?”[1]590
因此,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这些规律既指出了历史经验,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启发和指导作用。这就是《红楼梦》研究要古为今用,即将研究与创作挂钩,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和研究提高中国文艺理论水平、文学史研究水平,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1]589。
21世纪初,红学家梅新林在中国当代红学界倡导“红学新批评”。所谓“红学新批评”,并非简单借用西方新批评派理论展开红学研究之意,而是标示着一种重在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概而言之,即三“还”、三“重”、三“新”的贯通、推进与超越。三“还”——意指还《红楼梦》于作者、还《红楼梦》于文本、还《红楼梦》于读者的相互贯通。三“重”——意指重估红学历史、重释《红楼梦》意义、重建文本世界的依次推进。三“新”——意指红学界新生代、新探索、新建树的代际超越[6]。但是,这种“红学新批评”仍然没有超出“红学”的范围。因此,姚雪垠对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的把握仍然是超前的。
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 80年代初,姚雪垠率先提出了“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就是姚雪垠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只论述“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另外有一种编写方法,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故名之曰“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而这种“大文学史”观就是对当时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1980年 9月 28日,姚雪垠提出了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两个原则,一是编写文学史,必须从具体作品出发,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二是编写现代和当代文学史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脚点进行工作,放眼各个流派,各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中国作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创造了什么精神财富。姚雪垠坚决反对文学史编写的“关门主义”倾向,即一部文学史成为宗派文学史,认为“文学派别不等于政治派别。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不断分化,不断重新组合。所以现代文学史应以分析作品为主要任务,不应该轻视作家的具体作品而偏重政治倾向。政治倾向应该注意,但对作家说,最应该重视的还是他们的作品。作品是作家的主要的社会实践。”[2]439-440姚雪垠提出的“大文学史”一方面要求尊重客观的文学事实,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兼容并收,即没有主次的分别。而姚雪垠提出的红学史观不过是这种“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部红学史既要反映“红学”的研究成就,也要反映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弯路[1]591-592。
可见,姚雪垠推动了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并在中国当代红学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是中国当代红学史不能遗忘的。
[1] 姚雪垠.姚雪垠书系:第 21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 姚雪垠.姚雪垠书系:第 20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3] 俞平伯.旧时月色[J].文学评论,1986,(2).
[4]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 姚雪垠.姚雪垠书系:第 18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6]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
W e Should Not Be"Hongloumeng Scholar ship"for"Hongloumeng Scholar sh ip"Sake—On Yao Xuey in’s Contribution to"Hongloumeng Scholar ship"
XIONG Jin-xing1,XIONG Yuan-yi2
(1.Yongzhou Vocational Industrial College,Yongzhou 425000,China;2.Department of Theory,Art and Literature Newspaper Agency,Beijing 100125,China)
Yao Xueyin not only promotes actively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in the circles of China’s"Hongloumeng Scholarship"of the present age but also devoteshimself to changing radicall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Hongloumeng Scholarship"of the p resent age and opposing the tendency towards stress of ideas and scorn of art in"Hongloumeng Scholarship"studies.On the basisof promoting the"retracking"in"Hongloumeng Scholarship"study app roach,Yao Xueyin grasp s dialecticall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a great novel,analysizing not only its art achievements but also its shortcomings.He thinks that we should not proceed on"Hongloumeng Scholarship"but should discover some laws of producing great writers and great works.He also puts forward grand conception of history on"Honglonmeng Scholarship",whick is an organic part of Yao Xuejin’s"big outlook of literary history".
Yao Xueyin;Hongloumeng Scholarship;A D ream of Red Mansions
J1
A
1007-4937(2011)02-0071-05
2011-01-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09BA013)
熊金星 (1964-),女,湖南永州人,副教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熊元义 (1964-),男,湖北仙桃人,主任,编审,从事文艺理论与文艺评论研究。
〔责任编辑: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