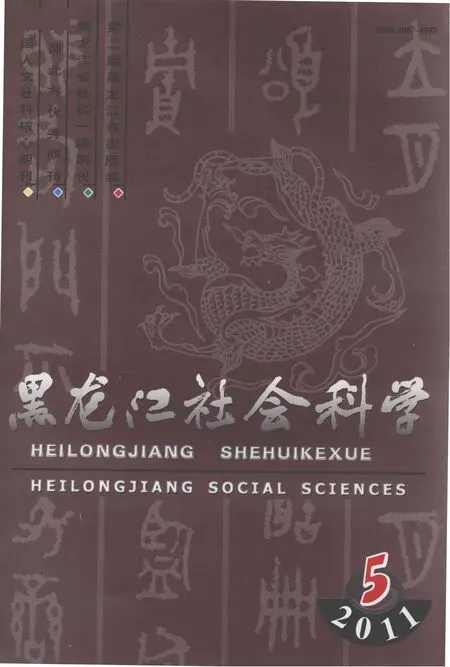论村民自治法律与物权法的衔接
——以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运行为研究视角
陈 杉
(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哈尔滨150030)
论村民自治法律与物权法的衔接
——以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运行为研究视角
陈 杉
(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哈尔滨150030)
《物权法》第五章关于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规定涉及村民自治的有第59条、第60条、第62条和第63条,这些规定涉及集体成员的表决权、知情权和撤销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与《物权法》衔接、配合,方能更好地发挥集体财产的效用,保护集体财产权利。
村民自治法律;物权法;农民集体所有权
部门法的适用各有其经度和纬度,形成各自的维度空间,不同的法律之间形成一定的交织地带。法律体系的理想化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在协调。在立法时新法一定要与旧法相衔接,精密配合,以保证法律公器的正常运转,发挥法治的最大效率。
《物权法》保护合法财产权利、促进财产流通的效益理念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推动力,作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庞大群体的农民也将受益于这一部民事基本法律[1]。《物权法》在土地征收、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浮动抵押等重要制度上的创新,都将对农业进步、农村发展、农民权利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村民自治是农村基本治理方式,中国正在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将来制定的村民自治法律,必须注意与《物权法》等现行法的相关制度及规范相衔接,避免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便利日后妥适法律。
物权法关于农民集体所有权规定的叙述路径,从权利运行的角度来看,为权利的归属—权利的行使—权利的保护;从集体成员权的角度来看,是表决权—知情权—撤销权;从村民自治的角度来,则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本文拟以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运行为研究视角,讨论村民自治法律与物权法的衔接问题。
一、村民自治法律与集体所有权的归属、行使规定的衔接
《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并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事项作了规定。对于土地承包方案、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为经(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第二种情况须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第三种情况须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这三部法律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同一位阶的法律文件发生冲突,当依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解决法律冲突。但笔者认为,在《村委会组织法》中明确以上重要事项采取绝对多数表决机制更为妥当,以便利法律之适用,但无需上级政府部门的批准,只需备案即可,因为这些毕竟是村民自治范畴的事务。
《物权法》第60条是对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规定。德国民法物权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作为权利之维的“所有权—他物权”和作为事实维度的“动产—不动产”这两种叙述进路间找寻平衡。但在中国物权立法除了权利之维与事实之维的取舍之外,还要考虑权利主体的问题[2]。在农村财产主体及行使主体这个问题上,物权法沿用不同的维度,农民集体、农业生产经营者、农民、村民、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表征权利主体的词语相安其中。中国《民法通则》、《村委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一系列法律谱系中对以土地为主的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发包等权利的行使主体作出了规定,尤其是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两个主体以有序位、并列、只择其一等不同的面貌出现。《物权法》第60条规定:第一,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第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也沿袭了该规定,在此不展开讨论。
二、村务公开与公布集体财产状况的衔接
《物权法》第62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村规民约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现行《村委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均对村务公开内容作了规定。
1.村民小组的村务公开。《村委会组织法》中没有关于村民小组村务公开的规定,无法保证本村民小组村民知情权的实现,可以说是一个法律漏洞。与《物权法》第62条关于村务公开的主体衔接,修订草案第26条第3款规定,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情况予以公布,符合《物权法》第60条第2款规定的由集体财产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情况,也与《土地管理法》第10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衔接妥当。因此,修订草案比现行法律规定得更为周到、科学、严密,也更能保护村民的利益。
2.对现行村务公开法律规定的疑问及解决办法。《物权法》规定了相关主体应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如果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或公布事项不真实,法律如何保障集体成员的知情权?目前的法律规定不够周全,急需完善。
第一,对《村委会组织法》第22条第4款的五点疑问。《村委会组织法》第22条第4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对此,笔者有五点疑问:其一,乡镇、县政府能做到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之间公正处理争议吗?乡村社会原本就是“熟人社会”,雷德弗尔德指出这就是乡村与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将合法性的判断权交给乡镇、县级人民政府显然不当。其二,“有关主管部门”语焉不详,徒增法律的理解与适用的困难。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立法语言表述不清,过于弹性化。法律语言不同于政治宣讲,这种模糊表述不符合立法语言明确、规范、严谨的要求,同时操作性不强也损害了法律自身的尊严和权威。其三,如何“调查核实”,乡镇、县政府往往缺少必要的调查手段去调取相关的经济合同、集体财务账目、集体资产登记文件和基本建设资料。其四,令人费解的是“责令公布”,而且针对的是村自治事务范围内村民委员会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这是乡镇人民政府在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吗?抑或在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镇一级政府是中国政权机关体系的最末端,村民委员会是中国农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执行机关。其五,再来看“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依法”中的“法”何所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规定有关人员如何承担责任,因此该条缺乏相应的明确法律依据。从本应“具象”走向抽象,幻化为概括力极强的“依法”二字,法律至此沦为摆设。
第二,解决的办法。总体来看,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村务公开的行政救济手段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有必要引入司法救济,同时法律应给予“村民委员会”恰当的地位。《村委会组织法》具有基本法的性质,宪法权利不具有普遍可诉性,在避免宪法司法化、没有宪法诉讼制度的背景下,此种责任的定性存在很难逾越的理论鸿沟,而没有救济的权利面临的尴尬犹如画饼充饥,权利难免会黯然失色。对此,可以创新村民自治权的救济途径。采取扩大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措施,将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公共行政范围的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如果确立村民委员会为行政主体将有利于村务公开救济问题的解决。
进一步讲,在村民自治领域亦可采取宪法性权利借用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的办法;再如《物权法》第63条规定的村民自治体的成员撤销权,这些途径和规定使得这些权利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获得司法救济。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针对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事项,“村民可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当然,这种诉讼的性质并不简单地类似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而应当是一种具有宪法诉讼性质的侵权诉讼,这种诉讼可以采取行政诉讼的程序。可以在一些地方先行试点,随着经验的成熟而逐步推广,最后通过立法手段加以肯定”[3]。
第三,修订草案对村务公开的完善。《物权法》第62条虽然赋予集体组织成员知情权,但对于违反该条的法律后果却没有规定;《村委会组织法》对于知情权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导致集体成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很难及时发现,将直接影响《物权法》第63条撤销权的行使。修订草案第29条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应当具备财会、管理知识,并由村民选举产生。该条规定了应设置专门机构、专业人员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对提高《物权法》第62条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的水平助益颇多。修订草案第30条对现行《村委会组织法》第22条第4款的修改有两处,只是在表达上更为准确,而总体未作改动。
三、在集体财产权保护方面的衔接
现实中,有的村委会违反法定程序或章程,擅自决定或者以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决定,低价处分、私分、侵占集体所有的财产,严重侵害村民的财产权益。《物权法》第63条第2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在村民自治的领域里赋予村民自治体成员在集体财产权受到侵害时撤销不当决定的权利,可以有效地矫正集体民主表决机制带来的弊端,以及修复在不进行任何民主议事程序下对村民自治权的侵害。与该撤销权立法旨趣类似的,一是《物权法》第78条规定的业主撤销权,二是《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股东撤销权。
但是,这种只有行为模式而无法律后果的条款,带有宣言式立法的痕迹,该条在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导向作用方面收效甚微。《村委会组织法》对此没有相关规定。修订草案第34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与《物权法》契合紧密。
1.村民小组成员也应享有撤销权。修订草案第26条规定,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同时《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均承认了村民小组可代为行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而《物权法》和修订草案却未提及当村民小组会议作出的决定侵害了村民小组成员利益时村民小组成员的撤销权,这同样构成了一个法律漏洞,但可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赋予村民小组成员撤销权。
2.关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责任承担。《村委会组织法》用“村民委员会”这一概念同时指称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广义的含义是指由广大村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中国现行《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村民委员会性质的定义“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在此种情形下使用的。只有广义的“村民委员会”才能谈及是否为法人的问题。另外,狭义的含义是指《宪法》第111条、《村委会组织法》第9条规定的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即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就是村民自治体中的执行机关。
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是采取多数决的民主决策机制,少数人的妥协和忍让是实现效率和维持秩序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村民委员会成员在不进行民主决策程序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作出决定。
村民委员会集体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一旦被撤销,必然涉及责任的承担,而修订草案仅规定“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该如何理解呢?既然是集体作出的决定,由于狭义的村民委员会是拟制广义的村民委员会的意思并代表其从事活动,是代表集体行使集体财产的所有权,无独立的财产无法承担责任,法律后果只能由村民自治共同体来承担,即该共同体内的全部成员。最后,形成维权者维权成功却要承担败诉者责任的逻辑悖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一种进路,村民委员会的决定侵害村民利益的,参与决议的村委会委员对村民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村委会委员可以免除责任。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未必违法、违反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情形下,依然有可能损害村民合法权益,因此,相比较《公司法》第113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承担的责任更为严格。该规定有利于规范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行为,使其民事责任规范化,有利于切实保护村民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共同体的债权人、村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更符合《物权法》立法本意、修订草案本意。
3.修订草案第22条第10款与其第34条的关系。第22条第1款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中第10款为撤销或者变更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村民会议是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暂且不论村民委员会自己召集会议撤销自己作出决定的不合逻辑性。该规定与第34条是什么关系呢?该“不适当的决定”虽然缺乏判断标准,但可能会有“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二者存在交叉。二者的区分在于前者是村民在行使涵盖“撤销”在内的自治权,即民主决策,而后者是在行使诉权。法院作出撤销决定的判决,其效力及于撤销权人、村民委员会以及第三人,即判决具有对世效力。而村民会议的撤销是无法达到该效果的,该规定在保护村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却有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内部的撤销决定是无法公示的,但对外部法律行为的效力施加影响,不利于交易安全及社会秩序,导致对第三人的不公平,同时村民委员会成员也逃避了责任的承担。撤销的虽然是某行为附丽的“决定”,但依附某“决定”的行为也有可能实施,如果通过诉的途径,村民委员会的行为一旦被撤销,即自始失去法律约束力,未给付的恢复原状。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讲,为避免第22条第10款对外部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同时也更好地与第34条衔接,可对其作限缩解释,即缩小至本村民自治体内部村委会成员的私分、侵占行为以及外部的还未给付的民事行为。
4.建议增加确认之诉。村民委员会成员擅自决定或者以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决定,低价处分、私分、侵占集体所有的财产等,而作出这些行为可能未经决定,或者决定是无效的、可撤销的,后者在意义、性质和效力上有很大差异,况且无效行为本身也无撤销的必要。因此,笔者建议增加决定无效确认之诉以及决定不存在确认之诉。法律应尽可能全面勾勒村民诉权的法律机制,并使其具可操作性,才能真正约束村民委员会的行为,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吉尔伯特·罗兹曼曾指出,“19世纪以来某些西方观察家提出:中国的村社是‘地方自治主义式的民主’或者是一种‘自由的、自我管理的社团’”[4]。中国正式的治理结构并没有延伸到农村,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自治状态。秦晖先生对此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中国的村民自治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完全没有域外经验可借鉴,农村治理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既要实现公平,又要保证效率。村民自治法律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应妥当与其他法律相衔接、配合,努力达致诸多部门法营造的“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和谐法秩序状态。
[1]申卫星.《物权法》与农民权益的保护[J].今日中国论坛,2007,(7):33.
[2]姜朋.中国内地物权法的主体维度问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5):58.
[3]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1,(3):139-140.
[4]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78.
D412
A
1007-4937(2011)05-0152-04
2011-06-06
黑龙江省教育厅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研究项目“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民自治法律问题研究”(11532008)
陈杉(1977-),女,黑龙江牡丹人,讲师,从事民商法、村民自治法研究。
〔责任编辑:杨大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