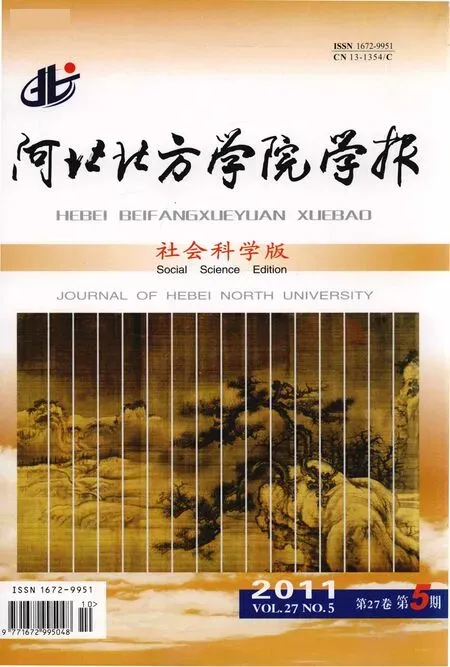科学与人文融会——论卡尔·波普的猜想理论及其社会价值
李 丽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于19、20世纪之交,逻辑实证主义可以说是第一个科学哲学的学派。在发展过程中逻辑分析方法遇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逻辑分析将经验事实还原成感觉材料,而他们只是个人的直接的主观感觉,并不能为科学概念和命题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提供基础。面对这样的现实,卡尔·波普创造性地提出关于科学知识的猜想理论,强调理论先于观察,科学的任务在解决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并且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知识即假说,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在不断的证伪过程中获得前进和发展,而证伪过程使用的是试错法,它是一种演绎的方法,因为它从一般原则推导到具体事例,因此在科学知识中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卡尔·波普的猜想理论虽然遭受到后来科学哲学的社会历史学派不同程度上的否定,但无可厚非的是,他为科学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向,使科学哲学重新观照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同时笔者以为卡尔·波普猜想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理论内容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其理论所引发的人们关于科学知识和社会的反思,这正是猜想理论的重要价值意义所在。
一、卡尔·波普的猜想理论
卡尔·波普认为随着基于经验主义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实证主义越来越盛行,先后经历了马赫主义、逻辑原子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然而实证主义在迅猛发展的同时,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刻和多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实证主义囿于经验主义,将归纳法作为获得科学知识的唯一手段出现了可怕的裂痕,因为休谟提出的著名的归纳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推崇者,使归纳原理的真实可靠性得到彻底的怀疑。休谟以为“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1](P60)。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过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1](P60)。“我要重复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条经验对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不属于以往事例的事情作出结论呢?”[1](P60)可见,休谟觉得企图靠诉诸经验为归纳法找根据,必然导致无穷倒退。因此,理论不能从观察陈述推演出,亦不能靠观察陈述为理论寻找理性论证,所以,归纳法不能成为获取科学知识的可靠手段。那么,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这也是卡尔·波普猜想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卡尔·波普接受休谟对归纳推理的驳难,但是不满意他将习惯作为因果关系的基础的结论。他独创性地提出了理论先于观察、知识即假说的猜想理论,在理性主义中自然地糅合进了非理性的因素,使得科学知识在获得有效性的同时又具有了创造性,使其思想理论中散发出浓浓的人文气息。以下笔者将系统阐述他的这一独特的猜想理论。
(一)理论先于观察
“我觉得,休谟的心理学也即流行的心理学至少在下述三个不同的问题上是错误的:(a)典型的重复结果;(b)习惯的产生;尤其是(c)可以说成是‘对规律的信仰’或‘对事件的类规律性序列的期望’的那些经验或行为模式的特点”[1](P61)。典型的重复活动是生理的、机械的,不会造成有意识地期望事件的类规律性序列或者对规律的信仰。另外,习惯并不产生重复,我们可以说,只是在重复起了其独特作用之后习惯才称得上是习惯,但并不能说这些习惯做法是大量重复所产生的结果。还有,我们只有先站在某一角度去观察,才会发现相似的重复,从而形成习惯。通过以上论述,卡尔·波普摒弃了科学知识是理性主义的说法,因为他认为归纳是一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和在理性上讲不通的程序,否则对科学知识的论证则会陷入无穷的循环论证,因而卡尔·波普提出理论先于观察的观点。“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它的描述必需有一种拥有专门语词的描述语言;它还需要以相似和分类为前提,分类又以兴趣、观点和问题为前提”[1](P66)。“我们可以补充说,只有同需要和兴趣相关联,对象才可加以分类,才会变成相似的或不相似的。这条规则不仅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科学家。对于动物来说,它的着眼点是由它的需要、当时的任务和它的期望所规定的;对于科学家来说,规定着他的着眼点的,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参照系、‘期望水平’来接受的那些理论”[1](P66)。因此任何观察都受一定的理论或理论上的倾向影响,观察不可能发生在理论之前,任何观察都是“期望”在先的。
(二)对规则的期望
卡尔·波普认为这些“期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期望找到规则性。他认为期望找到规则性不但在心理学上是先天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先天的。心理学上的先天性是因为期望找到规则性和指望规则性的天生的倾向,或者和寻找规则性的需要连在一起,这点可以从婴儿满足这种需要的快乐上看出来。而逻辑上是先天的,是因为他在逻辑上先于一切观察经验,因为如我们看到的,它先于任何对相似性的认识。但是尽管在这个意义上是逻辑上的先天的,但是这种“期望”并不一定是先天正确的。所以卡尔·波普赞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的说法:“当伽利略让他的球从一个斜面滚下来时(重量他自己选定);当托里拆利使空气支持一重物,其重量他事先计算等于一已知高度水柱的重量时……于是,所有自然科学家都茅塞顿开。他们懂得了,我们的理性只能理解它按照它的设计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强迫大自然答复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拖住大自然的围裙带,让她牵着我们走。因为未经事先周密计划作出的纯属偶然的观察,不可能由一条……规律相连结,而规律正是理性所探寻的东西”[1](P270)。但是这种动辄寻找规则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期望”会导致教条思维或行为,“我们期望规则性无所不在,试图甚至在子虚乌有的地方也找到他们;不服从这些企图的事件,我们很容易看做一种‘背景噪音’;我们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在这些期望并不恰当,我们应当承认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1](P69)。但是卡尔·波普又认为一定程度上的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可以使我们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表示一种坚定的信念,与之相对应我们还应具有一种审慎的、批判的态度。因为“教条态度显然关系到这样的倾向:通过试图应用和确证我们的规律和图式来证实他们,甚至达到漠视反驳的程度,而批判态度则是准备改变它们——检验它们,反驳它们,证伪他们(如果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做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做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1](P71)。并且批判态度必需以多少是作为教条的态度而保持的理论或信念为原材料。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批判的态度发生在教条的态度之后。既然任何观察都是“期望”在先的,那么这种“期望”具有的是非理性基础而不是理性基础,所以卡尔·波普得出结论: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仍如此。在一个理论被驳倒前,我们怎么也无法知道必须以哪种方式修正它,所以没有什么比试探——出错的方法更加理性的程序了。“‘我们怎样从一个观察陈述跳跃到一种好的理论?’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首先跳跃到任何一种理论,然后加以检验以发现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说,反复应用批判方法,取消许多坏的理论,发明许多新的理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舍此别无他途”[1](P79)。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卡尔·波普的猜想理论在讨论观察是“期望”在先时指向的是非理性主义,而在处理观察材料时指向的又是理性主义。
(三)科学知识是可错的
由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尔·波普认为科学知识是可错的了。因为观察是“期望”在先,“期望”则是人的“期望”,人是会犯错的,因此对科学的“期望”或假设也是可错的。这非但不会破坏科学追求真理的坚定性,相反,正因为科学是可错的,才使得科学具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出错中取得进步,并从科学的绝对权威中解放出来,使科学朝向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是探求真理,至少在塔尔斯基以后我们已不害怕这样说。的确,只有对于发现真理这一目标而言,我们才能说虽然我们难免有错误,我们却希望从错误中学习”[1](P327)。
(四)形而上学的重要性
卡尔·波普的猜想理论还强调形而上学的重要性。首先是因为“观察总是不精确的,而理论却作出绝对精确的断定”[1](P265)。其次是“观察总是具体的,而理论是抽象的”[1](P266)。因此,卡尔·波普认为科学理论并不在于观察材料的机械的积累,科学理论是创造性的,它是由严肃的批判和严格的检验支配的、自由、大胆和创造性地解释的结果。这里卡尔·波普虽强调的是理论的抽象性,其实更深一层次来理解,他强调的是人的创造性的抽象能力的发挥。在一个抽象的理论中,起作用的不只是理性,还有非理性的巨大功效。
笔者以为卡尔·波普强调科学知识是可错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重要性是其认识论走向乐观主义[2]而不是休谟的怀疑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正是归纳法求诸“纯理性”失败,无法为科学知识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础,因此非理性的转向为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新路向和新思路,让我们明白知识的可靠性和坚定性并非仅仅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验证实,它事实上是对一种人文思维的呼吁。
(五)知识增长的三个要求
卡尔·波普还认为知识增长应满足三个要求:一是“一种新的理论应当从某种简单的、新的、有力的统一观念出发,这种观念是迄今尚无联系的东西之间(如行星和苹果)或事实之间(如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之间)或新的‘理论实体’之间(如场合粒子)的某种联系和关系(如万有引力)”[1](P344)。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描述世界的结构特性要不陷入无穷的倒退。二是“我们要求新理论应当可以独立地受到检验”[1](P345)。也就是说除去所有那些新理论实现计划要解释的待阐释者的解释,新理论必须具有可加以检验的新结论(最好是一种新类型的结论),必须引出一种对迄今还不曾观察到的现象的预测。三是“我们要求这种理论应通过某些新的、严峻的检验”[1](P346)。总之,一种理论的猜想应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
二、科学与人文融会
卡尔·波普猜想理论的理论起点是非理性的,这是他的理论有别于之前科学哲学的重大区别所在,这不是他的一次偶然尝试,而是基于对科学理论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窘境和挑战的深刻反思,并蕴涵着一种新的科学理性的呼吁。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为制造的东西充斥着世界,人们也越来越依赖它们,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能否完全相信并依赖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科学技术能否像掌握自然一样来掌握社会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地出现,而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相反,在科学技术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的自由和灵活性正在逐渐丧失,我们的生活和行动越来越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和建议,这意味着我们的任何选择都要在别人的名义下活动,不能自主又有效地采取行动。同时技术化的思想渗透到社会领域可能会导致人们有目的地将公众舆论导向某个方向,并出于某些利益考虑对其施加影响。总之,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所依赖的工具理性将活生生的人奴役为工具,这大概是工具理性发展所始料未及的。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笔者认为卡尔·波普猜想理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具体内容本身。
首先,卡尔·波普认为理论先于观察的观点强调的是非理性因素在获取科学知识中的重大作用,他实际上已经敏锐地发觉出了科学的“纯理性”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从科学哲学之前的发展所遇到的悖论和在现代工业社会所引发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不仅科学知识的最初形成离不开一些诸如想象、灵感、感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在科学知识的具体应用中更离不开基于这些非理性因素的考虑。科学应用只有立足于对人类长远发展的思虑和人文关怀的融入,科学发展才是积极的、真正利于人类的。因此这些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是归纳推理所无法实现的,在科学发展中融入人文的关怀,才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新路向。
其次,基于对卡尔·波普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后来的科学哲学的社会历史学派逐渐否定了卡尔·波普的很多思想,但是这不能抹杀其思想的重大价值意义。卡尔·波普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同的,其猜想理论中“科学知识是可错的”以及“试错法”等思维方式渗透于其关于政治的思想理论中,他认为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控制社会整体,从而全盘改造社会,这样的想法是“乌托邦式”的。社会是一个整体,但是社会事实无法重复和复制,我们只能解决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强调政府政策的作用在于“消除痛苦”而非“增加幸福”,同时提出“最小政府原则”,认为国家的职能应限制在对个人自由的保
护上等等。这些积极又富有创造性的观点无一不是其猜想理论中思想的延伸。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探索蕴涵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心,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无形中承认了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离不开人文思维的作用,呼吁关注社会现实、关爱人类,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1]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陈安金.从“可证伪度”、“确认度”到“逼真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