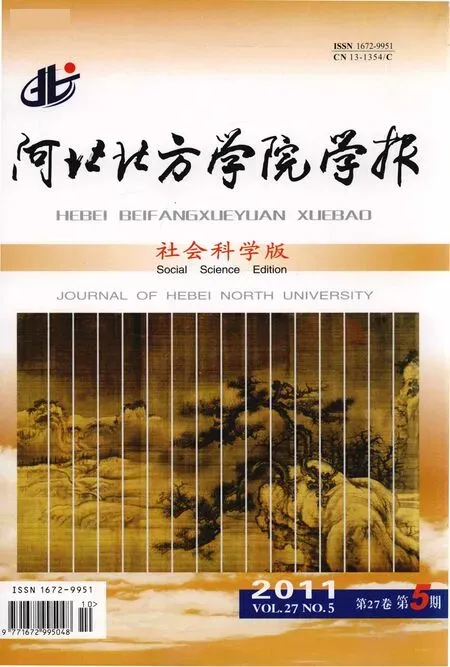近10年(2000-2010)词调研究论文综述
赵李娜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词调是词艺术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0-2010年这近10年中,对词调的研究依然保持了相当的热度,在词调的来源变化发展、类别研究、具体词调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也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本文试图从以上诸方面对这10年间词调研究的论文作一下梳理,清点词调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借以探讨词调研究的大致方向,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一、从宏观角度把握词调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并详细研究词调在具体历史时期的创制、运用情况是这10年词调研究的重点之一
曹辛华在《论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及其意义》中提出了建构中国分调词史的主张[1],作者从理论方面对中国分调词史的内涵外延、建构方法及其意义这3个方面进行了阐发,以期有利于各种分调词史的问世。作者所提倡的对中国分调词史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对词的本体研究、对作家作品的宏观研究、对词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和对词的“多元化”研究,希望能更客观更科学地揭示词学的现象、轨迹和规律。
在词体发展过程中,词调也在发展变化,并且出现了一调多名和同调异体的现象。王可喜在《略论一调多名现象与词调命名方式的关系》中统计[2],约1/3的词调为一调多名。一调多名现象的产生有很多途径,其中与词调命名方式有密切关系,如以词中之字句为调名,以词中所咏之事物或情意为调名,以人名、地名为调名,以篇章字数为调名等。他在《略论同调异体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中总结出同调异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4个方面[3],即字数句式的更动、用韵的变化、节拍快慢的差异、结构的改变等,并探讨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同词人对不同内容的需求,此外,也有知音度律者的创造及在别体基础上再创造等因素。
王叔新《词调功能嬗变之管窥》和黄静《依调填词与词体的完型化》这两篇文章都认为[4-5]:词最初以歌舞娱乐为主,人们开始作词时是依一定“曲调”填词的,而当广大文人参与歌词创作后,词体就兼备了音乐功能与文学功能。到宋代,词人音乐素质和词调曲谱自身的局限导致了词调音乐功能的弱化和缺失,词调最终被定格为文学性专用名词。
朱腾云《词调渐趋消亡的原因初探》一文主要讨论了词调的内在消亡即词的音乐性逐步丧失,词由音乐文学转变为纯文学的原因[6]。作者认为,南宋词人崇高雅、严音律,同民间新声断绝联系,堵塞了词调的新来源。再加上词调自身日益格律化,文人创作大多“不守规矩”,引起词体质素的变异。词体的文辞与音乐之间固有的矛盾不断深化,于是词调作为词体特有质素的自身独立意义消失,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金志仁《唐五代词创调史述要》认为[7],唐五代是词在创调领域的探索、形成、发展阶段,唐五代主要有3个创调词人群:花间词人群、南唐词人群、敦煌词人群。他们都对优化词体结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创制了大量的小令与一定数量的中长调,为形成满目琳琅的中国词调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玉琪老师有两篇文章详细研究了词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运用情况。《唐五代词调在两宋的运用》一文从词调发展史的角度对唐五代词调作了一番考察[8],结论是唐五代词调在两宋的运用大体可以分为4种情况:完全被淘汰消亡者、在旧调基础上产生新调者、成为流行词调而主导词坛者、词作数量很少而接近消亡者。虽然唐五代词调在两宋被运用者只有80调左右,但对两宋词调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运用唐五代词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呈现出多种风格。在《论金词的用调》一文中[9],作者根据《全金元词》做统计,金词从词调产生时代来看主要分三类:唐五代词调、北宋词调和本朝新调。金人使用唐五代词调,集中于流行词调,题材罕有言及恋情者,风格也较侧重于豪爽劲健一类。在题材取向上,赋“道情”是金人用唐五代词调的重要特点。使用北宋词调则深受柳永、苏轼影响。使用柳永词调,多赋“道情”,格调清快明丽;受苏轼影响,题材多写隐逸,风格豪放。本朝新调主要为道教词人创制,使用范围比较狭窄。这两篇文章从词调运用史的角度考察了唐五代词调在两宋运用的情况和金词用调的情况,所选角度新颖,从一个新的方面窥测出词调发展的脉络,对词调研究意义重大。
二、近10年对词调类别的研究也日趋细密,形成了词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洛地《词调三类:令、破、慢——释“均(韵断)”》以《词源·讴曲旨要》中“均”的概念为起点,认为均即韵(洛文特称为韵断),是一种介于“章”与“句”之间的以大韵为标志的结构单位[10]。洛地认为,从唐五代到宋末,词的发展主要是从上下两章各两韵断的“令”发展为上下两章各四韵断的“慢”,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介于“令”“慢”之间而又为人们所循用的词调,大多为上下两章各三韵断但并不完全对称 ,是“令”趋变为“慢”的摊破过程中凝固下来的词调,故洛地称之为“破”。词体的此种划分否定了按字数多寡划分类别的做法,提出了新的词类划分标准。
霍明宇《词中“小令”一体辨析》认为,词体中“令”的名称来源于唐代酒令[11]。受音乐形式的影响,令词往往调短而字少。在与音乐相结合的那段时间,文学作品中谈到的“小令”往往兼有文学和音乐的性质,但随着乐辞的分离,“小令”逐渐固定为词体的专称。今天,由于古乐的亡佚,人们再要对“小令”进行概念的辨析,已无法从音乐角度入手了。而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毛先舒以58字划分小令的说法符合大多数人对宋词的一般性认识,因而被延用至今。
李晓云《试辨慢词与长调之关系》认为,长调与慢词之间有以下两种关系[12]:第一,慢词多为长调。这是词中的普遍现象。第二,有些令词是长调。如柳永《采莲令》91字,欧阳修的《凉州令》105字等。如果就字数来说,这些令词都可归之于长调,但因为其乐曲是令曲而不是慢曲,故它们仍是令词。第三,存在一部分特例。作者根据《高丽史·乐志》里存录的40首宋词分析,发现有的注明“慢”的词反而短于“令”词。《瑞鹧鸪》一直被认为是令词,但其中的两首都标明为“慢”。更为奇特的是,两首《水龙吟》句式有异,字数都是101字,却被标为一令一慢。作者认为,“令”、“慢”等不应与词调名连称,它们不是词调类别,而是歌谱关于特殊歌法的符号或标志。令是一种急拍快唱的歌法,慢是缓拍慢唱的唱法。“急”与“慢”是相对举而言的,很可能宋代通称 “急”为“令”了,所以现在见到的是“令”与“慢”对举。因为急曲子大多字少短小,所以习惯误称之为小令。慢曲子因舒缓且句长字多,所以也就称之为长调了。书中作者做了一个假设,用以解释令慢与小令、长调之间不能一一对应的关系。假设大胆,但是没有足够的论证,因此只能说是他的猜测。
韩水仙《慢词风致与赋体手法》一文认为,将赋体手法用于慢词的创作,始于柳永,大成于周邦彦,后继以姜夔、王沂孙等,几乎贯穿了整个慢词的发展过程[13]。以赋为词适应了慢词的文体特征,契合并推进了词从小令到长调,从民间歌唱到文人创作的演变过程,莫定了慢词曲折蕴藉的审美特质。
三、从微观角度对具体词调的产生、发展、文体特征、文化意蕴等进行探索,也是近10年词调研究中的热点
彭国忠《论宋代〈调笑〉词》这篇文章分析了宋代《调笑》词与唐五代《调笑》词的不同,认为它是以女性为抒情主体,以男女之间相爱相悦、相思相别为主要内容的[14]。作为诗词文三结合的样式,它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它与曲接近,但又追求“雅”的风格。最后作者指出,宋代《调笑》词集中于北宋,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苏门文人集团的参与有关。
田玉琪《词调〈莺啼序〉探源》[15]、《词调〈莺啼序〉小考》[16]两篇文章对词调《莺啼序》的来源进行了探索。作者认为,此调非始于吴文英,而是始于高似孙,不过高似孙也不是《莺啼序》词调的制曲者。《莺啼序》曲谱(包括曲名)早已有之,高似孙只不过是最早为《莺啼序》曲谱配词的人,从此之后,《莺啼序》由单纯的曲调成为词调。随后,左洪涛在《〈莺啼序〉词调新考》一文中又对词调《莺啼序》始于何人的问题作了考证[17]。作者认为,从填词时间和内容上看,该词调应始于比高似孙早50年左右出生的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他填《莺啼序》的主要目的是传道布教的需要。
白静、刘尊明《唐宋词调之冠——〈浣溪沙〉初探》认为,《浣溪沙》一调在唐宋时代备受词人青睐,使用频率最高[18]。从曲调曲体来看,它具有轻灵与婉转之美;从形体结构来看,它具有整饬与变化之美;从对偶句式来看,它具有画龙点睛之美。这些共同构成了《浣溪沙》独特的体性特征和艺术魅力。
陈鑫、刘尊明《试论宋代〈渔家傲〉词的创作与嬗变》一文认为,《渔家傲》词调具有高扬清丽的音乐风格和声情特征[19]。北宋前期,《渔家傲》的歌词创作就呈现出异军突起的繁荣景象,尤以范仲淹、晏殊、欧阳修3人的成就最高。中期以后,则进一步朝着多元并存的格局发展演变,以苏轼、黄庭坚、周邦彦3人的贡献最大。
孙彦忠《词调〈采桑子〉从唐到元的传承流变情况》一文系统介绍了《采桑子》的名称来源、格律体式、从唐到元的思想内容及风格特征的传承流变情况[20]。《采桑子》一调源于乐府旧曲,在体式上有一正两变3种形式。在思想内容方面,唐五代时艳情词占统治地位;宋代词的题材迅速扩大,词人们开始用它写景状物,思索人生哲理,抒发性情怀抱;金元时期,又出现了大量宣传道教教义的劝世之作。在风格特征方面,《采桑子》以婉约柔美的风格为主,兼及欢快明丽,亦有深沉豁达。
李牧遥《〈菩萨蛮〉词牌探微——以温庭筠〈菩萨蛮〉为例》一文首先对《菩萨蛮》词调的由来、文体特性作了简要交代,然后对温庭筠的《菩萨蛮》创作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分析其在字词声律以及意境两方面的独特之处,总结出温庭筠《菩萨蛮》对后世的影响[21]。
杨黎明《论词调〈满江红〉在宋朝的创作流变》一文发现,两宋的《满江红》创作主要表达缠绵怨抑的情感,具有清新绵渺的声情特点[22]。其创作主题也经历了从一己悲欢到救国图存的转变。
李博昊《〈折杨柳〉源流嬗变及诗史价值考述》一文按照时代的变化,从音乐的角度分析了《折杨柳》由乐府古题变为声诗,进而演变为词调的过程,探讨了其内容题材和创作技巧等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23]。作者认为,《折杨柳》创作内容的变化说明了乐府与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体现了时代文学的特点。
刘栋《〈生查子〉词调探微》详细探讨了《生查子》词调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题材、意象和声情的特点,通过词调自身的演变,挖掘了此调所具有的文学内涵[24]。
张传刚《〈瑞鹧鸪〉词调浅论》一文介绍了《瑞鹧鸪》调的填制历程,尤其详细介绍了此调在字数和内容方面的发展变化[25]。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指出了此调的唱法技巧,即在演唱之前要有前奏,正式演唱时要“依字易歌”。此外,作者还考辨了《瑞鹧鸪》与七律、《舞春风》、《鹧鸪天》的关系。
付婧《试论〈江城子〉词调的演变》一文梳理了《江城子》词调的发展脉络,词调起源于唐五代,兴盛于北宋,在此苏轼起了关键的作用,衰落于金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此调表现出不同的内容风貌和感情体验[26]。
上述几篇文章,虽然都是以某个词调为研究对象,但是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彭国忠、陈鑫、杨黎明等的文章具有断代词调史研究的意义,而且在具体研究中考虑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孙彦忠、李博昊、刘栋、付婧是以史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阐述了《采桑子》、《折杨柳》、《生查子》和《江城子》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传承流变情况。李牧遥的文章从个别到一般进行了归纳总结。张传刚的文章则是以《瑞鹧鸪》的发展为线索,对《瑞鹧鸪》词调的演唱技巧和文体形式进行了探讨与考辨。
通过归纳总结可以发现,近10年来词调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一定的拓展,研究领域正逐步系统且向纵深方向发展,既有宏观综合研究,又有微观深入探讨。词调个案研究正在逐步成为研究者涉足的热点,一些致力于此的学者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些过去被人所忽略的问题,如辽金元三代词调发展情况、词调运用情况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对这些论文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第一,词体研究在总体上呈现不均衡的状态,令词调研究多,慢词调研究少;对词调的体式章法研究多,而对词调的音乐性质研究少;唐五代与宋是研究重点,其他朝代少有涉及;第二,在研究中存在选题重复、角度单一等问题,较少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创见,这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尽量避免的问题。
[1] 曹辛华.论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及其意义[J].中国韵文学刊,2009,(1):89-98.
[2] 王可喜.略论一调多名现象与词调命名方式的关系[J].咸宁学院学报,2005,(5):48-49.
[3] 王可喜.略论同调异体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J].咸宁学院学报,2006,(4):59-60.
[4] 王叔新.词调功能嬗变之管窥[J].台州学院学报,2009,(5):34-37.
[5] 黄静.依调填词与词体的完型化[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2):124-128.
[6] 朱腾云.词调渐趋消亡的原因初探[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12-15.
[7] 金志仁.唐五代词创调史述要[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4):63-69.
[8] 田玉琪.唐五代词调在两宋的运用[J].长江学术,2007,(4):55-61.
[9] 田玉琪.论金词的用调[J].江苏大学学报,2009,(6):27-31.
[10] 洛地.词调三类:令、破、慢——释“均(韵断)”[J].文艺研究,2000,(5):75-84.
[11] 霍明宇.词中“小令”一体辨析[J].福建论坛,2007,(12):14-17.
[12] 李晓云.试辨慢词与长调之关系[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3):64-66.
[13] 韩水仙.慢词风致与赋体手法[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6):64-66.
[14] 彭国忠.论宋代《调笑》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2):56-63.
[15] 田玉琪.词调《莺啼序》探源[J].南京社会科学,2002,(6):68-69.
[16] 田玉琪.词调《莺啼序》小考[J].文学遗产,2003,(4):110.
[17] 左洪涛.《莺啼序》词调新考[J].中国韵文学刊,2005,(4):66-68.
[18] 白静,刘尊明.唐宋词调之冠——《浣溪沙》初探 [J].湖北大学学报,2004,(2):200-202.
[19] 陈鑫,刘尊明.试论宋代《渔家傲》词的创作与嬗变[J].齐鲁学刊,2006,(1):130-134.
[20] 孙彦忠.词调《采桑子》从唐到元的传承流变情况[J].读与写杂志,2007,(5):5-6.
[21] 李牧遥.《菩萨蛮》词牌探微——以温庭筠《菩萨蛮》为例[J].西安社会科学,2009,(1):63-65.
[22] 杨黎明.论词调《满江红》在宋朝的创作流变[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7):79-82.
[23] 李博昊.《折杨柳》源流嬗变及诗史价值考述[J].作家杂志,2010,(11):92-93.
[24] 刘栋.《生查子》词调探微[J].邢台学院学报,2010,(4):30-32.
[25] 张传刚.《瑞鹧鸪》词调浅论[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4):16-19.
[26] 付婧.试论《江城子》词调的演变[J].鸡西大学学报,2010,(4):12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