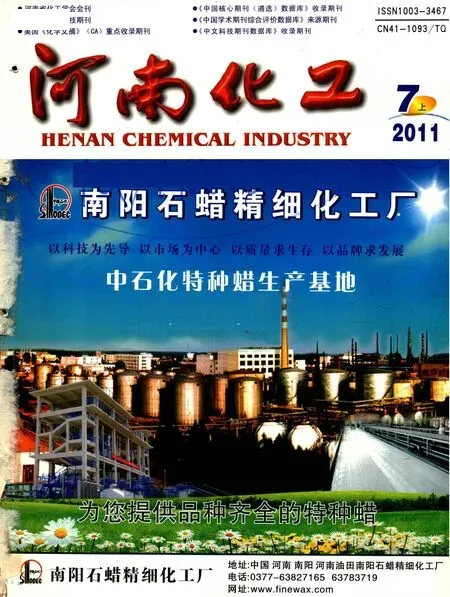土壤重金属Cr污染及其治理研究进展
吴泽鑫,邢文听,高青环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郑州 450052)
1 土壤中重金属Cr污染现状
铬是ⅥB族元素,它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为0.010%左右,分布广泛。近年来,伴随铬工业的发展,土壤铬污染的事件逐渐增多,对农业造成的危害也逐渐加大,随着食物链的扩大,对动植物和人的毒害也逐渐放大。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京曾因铬渣处理不当引起铬公害事件;我国的锦州等地排出的铬渣堆积如山,污染大片农田;北京、上海、河南等地也相继在土壤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铬污染[1],且危害已扩大到粮食作物。铬盐及皮革、印染、电镀等涉铬工业的发展、城市污水的非达标排放对农业土壤已造成一定的毒害,其危害由于生物放大作用也逐渐威胁人的健康。因此,铬被列为我国农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8个重金属控制指标之一。
2 土壤中Cr的来源及含量
土壤中的铬最初来源于岩石风化,在自然条件作用下转移到成土母质及土壤中[3];其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污水灌溉、污泥及城市垃圾正在成为土壤铬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上海农科院和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的研究表明[4],随着灌溉水中铬浓度的增加,土壤中的铬含量也相应增加,当灌溉水六价铬浓度为0.1 mg/L以下时,土壤中的铬积累不够明显,大于该浓度时积累则显著上升,北京等城市对灌溉农业环境调查后发现,灌溉区土壤比同类型的清灌土壤含铬量都高。另外,随着冶金、制革、电镀等涉及铬污染工业的发展,某些工厂和铬污染源所产生的含铬粉尘、铬渣及被铬污染的地下水也能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造成铬的累积,调查显示天津某区的原化工厂地域[5],由于其废铬矿渣的长期堆放,造成厂区附近严重铬污染,多年来该地域的树木、植物及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世界各地土壤中铬的含量悬殊甚大,美国土壤中含铬平均值为100×10-6,苏联为200×10-6,日本为20×10-6~200×10-6,我国为 82×10-6。铬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规律一般为土壤表层含量高,越往下铬的含量越少。说明外界进入土壤中的铬大部分被固定在耕层,很少向下渗透,铬在土壤中的水平分布主要受成土母质及人为因素的影响[6]。
3 Cr及其化合物的生态效应
3.1 Cr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铬是机体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正常代谢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调节人体内糖和胆固醇代谢的作用,铬含量太少时,会引起人体血管内壁脂肪的沉积,使本来具有弹性的正常血管逐渐硬化,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食物中的铬主要来源于谷类、水果和蔬菜,含量很低,因此需要外源性补充。铬在环境中最常见的价态是三价和六价,六价铬吸入后可能具有致癌性,而Cr3+在体外一般不具有遗传毒性,并且在动物或人体试验中均未显示致癌性[7]。Cr3+是铬最稳定的氧化态,在胃肠道不易吸收,在皮肤表层与蛋白质结合为稳定络合物,毒性不大,人体每天需要Cr3+的量为0.06~0.36 mg(铬在人体内半衰期为27 d)。如果过量摄入则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儿童过量摄入铬后肾小管过滤率呈明显降低,而且这种降低是不可逆的或者需要较长时期才能恢复;Cr6+的毒性比Cr3+大100倍,它能与核酸结合,对呼吸道、消化道有刺激、致癌和诱变作用。吸入含Cr6+化合物的粉尘或烟雾,可引起急性呼吸道刺激,能引起过敏性哮喘。人口服Cr6+化合物致死剂量为 1.5 ~1.6 g[8],口服时可刺激或腐蚀消化道,有频繁呕吐、血便、脱水等症状出现[9],人群调查实验表明,长期暴露于铬环境,特别是生产铬酸盐的工人的肿瘤发病率比常人高。
3.2 Cr污染对植物的危害
铬是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元素,在一般自然土壤中含一定量的铬,对植物生长是有利的。通常,低浓度铬对数种农作物的生长有刺激作用[10],如Cr3+浓度0.5 mg/L的培养液能刺激玉米生长,15~50 mg/L时则抑制此类植物的生长。石贵玉等[11]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低浓度(50 μmol·L-1)铬对烟草组培苗生长有促进作用,株高、鲜质量、叶绿素含量、蛋白质含量、SOD活性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土壤环境中铬的含量过高时,就会对植物及其他生物造成危害。徐加宽等[12人的研究表明,随着土壤铬含量的增加,水稻主茎总叶数变少、植株变矮、抽穗期延迟,水稻生物产量显著下降;另外,铬与其它重金属会复合污染,由于复合种类的不同,对植物造成危害的程度也不尽一样,例如:若铬与镍协同作用时,含铬仅2.0 mg/L即对作物产生危害,而铬与铅协同作用时[13]对水稻的伤害则由于二者的相互反应轻于单一的铅水铬污染。
3.3 影响Cr生物有效性的因素
重金属生物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土壤中重金属的有效态,土壤中铬的有效态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而重金属的有效态又与土壤中重金属的总量有极显著相关性。土壤中的铬形态直接影响它的活性和对植物的有效性,因此,研究土壤中的铬形态和迁移转化的影响因素对防治铬污染具有积极的意义。影响铬生物有效性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包括:土壤类型、pH值、有机质、氧化还原电位等。
3.3.1 土壤类型及有机质等
由于土壤类型孔隙率、含水率等对铬的形态和转化的影响,即使土壤中重金属总量相同,因不同土壤性质的差别较大,对植物的危害和吸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14]。研究结果表明[15],在同一施肥量下,铬含量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少,不同质地土壤铬的迁移能力不同,依次为:轻壤>中壤>重壤。另有研究显示[14],由于青紫泥有机质含量较高,容易把六价铬还原为Cr3+而降低其浓度,而黄筋泥由于有机质含量相对较低,但铁铝含量比较高,它对Cr6+的吸附又大于Cr3+,故而影响到土壤中铬的有效态,因此两种泥施入土壤后对植物的生长显著不同。
3.3.2 pH值
土壤pH值的高低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形态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土壤中重金属的有效性。土壤中Cr6+还原Cr3+,土壤对Cr6+的吸附及Cr3+在土壤中沉淀和吸附等都受到土壤pH值的影响,Cr6+在中性土壤和碱性土壤中的有效性和毒性要比酸性土壤高。李晶晶等[15]研究显示,在pH值2.0~6.5范围内,土壤对Cr6+的吸附量随pH值的升高而增加,但增加量很小,当pH值大于6.5时,吸附量随pH值升高而急剧下降,至pH值为8时,基本上不吸附Cr6+。而Cr3+的吸附和沉淀随pH值的升高而增大,在pH值小于4.0时,Cr3+不会生成氢氧化物沉淀,土壤对Cr3+主要是吸附作用;在pH值4~6范围内,溶液中Cr3+浓度随pH值升高而急剧下降。
3.3.3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影响着铬的价态变化[3],所以土壤中铬有效态的多少也将变化。当氧化还原电位较高时,土壤中的Cr3+在MnO2表面催化下可氧化成 Cr6+,有机质、Fe2+、S2-能使 Cr6+迅速还原为Cr3+,其还原能力是随着Fe2+、S2-及有机质含量的增高而变强。
4 Cr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措施
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不可逆和后果严重等特点,至今没有找到理想的治理方法;因此需要探索在不破坏土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治理重金属污染的新途径。铬污染土壤需要长期地努力,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才能缓慢地使其恢复。铬污染土壤的治理途径主要有两种:①改变铬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将Cr6+还原为Cr3+,降低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能力和生物可利用性;②将铬从被污染土壤中清除。根据以上两种思路发展出如下一系列治理方法:生物修复、工程修复、加入改良剂及农业措施。
4.1 生物修复
对于被铬污染的土壤也提倡采用生物修复法(Bioremediation),即应用微生物和植物来治理铬污染,现主要集中于微生物方面。
4.1.1 微生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修复就是利用原土壤中的土著微生物或向污染环境补充经过驯化的高效微生物,在优化的操作条件下通过生物还原反应,将 Cr6+还原为Cr3+,由于其活性较差,对植物毒性相对较小,从而修复被污染土壤。相比于化学还原和化学清洗法,生物修复的优势在于不会破坏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环境,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可原地处理,操作简单。Camargo等[16]已从被重铬酸盐污染的土壤中分离出Bacillussp和 ES29,Mclean 等[17]从一长期被制革废物污染土壤中分离出Arthrobacter sp;Francisco等[18]从活性污泥中分离出 genera Acinetobacter和Ochrobactrum;Amoroso[19]从河床淤泥中分离出Streptomyces spp;还有许多菌种是从工业污水中发现的。
4.1.2 植物修复技术
当前的植物修复技术方面,根据其作用过程和机理分为三类,即植物吸取、植物挥发和植物稳定。植物吸取是利用专性植物(通常指超积累植物),一般生长在矿山地区,其对重金属元素的积累达干质量的1%~5%,根系吸收土壤中有毒金属并将其转移、储存到植物茎叶,然后收割茎叶,离地处理[20];植物挥发是去除土壤中一些可挥发的污染物,向大气挥发的速度以不构成生态危险为限;植物稳定是一种原位降低污染物生物有效性的途径,而不是一种永久除去污染物的方法。相对而言,植物吸取是一种永久去除土壤中重金属的重要方法。目前报道的铬超积累植物仅有两种,即在津巴布韦发现的Dicoma niccolifera Wild和Suterafodina Wild,其铬的含量分别为 1 500 mg/kg 和 2 400 mg/kg[21],均高于铬的参考值;国内对铬超积累植物的报道,目前仅有张学洪,张学洪等[22]人在广西发现的湿生铬超积累植物——李氏禾(Leersia hexandra Swartz)。
4.2 工程修复
目前的工程修复铬污染方面,主要措施包括①换土、去表土、翻土;②隔离法;③清洗法;④热处理;⑤电化法等。这些技术有很多已成功应用于修复实践,尤其是对于污染面积较小、污染程度较重的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但这些技术存在很大缺点,如破坏场地结构,改变土壤原有理化性质使污染土壤修复后难以利用,容易带来二次污染以及实施方式难以为公众所接受等,而且对于污染面积较大的土壤,尤其是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农田土壤,或是因为技术上难以实施或是因为经济上难以承受而难以应用。
4.3 加入改良剂及农业措施
(1)选种适宜作物,实行水旱轮作是轻度Cr3+污染土壤的一项有效的生物改良措施。水旱轮作使土壤pH值升高、EH下降,这种变化有利于土壤对Cr3+的吸附固定,从而降低了土壤有效铬的含量。
(2)Cr3+污染的酸性土壤上施用石灰有一定的解毒效果。石灰的用量不同,对作物的产量、含铬量及土壤有效铬含量的影响也不同。李惠英等[1]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单独投加含Cr3+的物质,小白菜产量比对照下降,而地上部含铬量及土壤有效铬含量却增加,差异均为显著。施入石灰后,作物产量明显增加,地上部含铬量及土壤有效铬含量则下降,接近对照。
(3)施用有机肥能显著减轻Cr3+对植物的毒害。有研究表明[23],有机肥料的施用可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从而降低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是一种较理想的治理措施。李惠英等[1]在实验中,加入Cr3+20×10-6,小白菜减产57%,地上部含铬量增加13倍之多,土壤有效铬的含量也明显增加。施入有机肥后,小白菜产量显著上升,茎叶含铬量也大幅度下降,土壤有效铬的含量接近正常值。张亚丽等[24]研究结果也表明,在Cr污染黄泥土中施入猪粪和稻草等有机肥后,土壤有效态Cr含量降低,降幅约为30%,而微生物量C、N、P含量和脲酶、过氧化氢酶的活性增高,增幅为15% ~273%。
(4)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堆肥修复铬污染农田具有较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黄启飞等[25]通过模拟土培试验,研究垃圾堆肥对铬污染土壤中有效铬含量的影响的结果表明,垃圾堆肥可显著减少铬污染土壤中有效铬含量,垃圾堆肥主要是促进水溶态铬向结晶形沉淀态铬转化,垃圾堆肥用于修复铬污染土壤是安全的。
[1]李惠英,曾江海.土壤铬污染及其改良措施[J].环境导报,1990,(2):5-7.
[2]宋 波,高 定,陈同斌,等.北京市菜地土壤和蔬菜铬含量及其健康风险评估[J].环境科学学报,2006,26(10):1707-1714.
[3]刘晓潭,王 霞.新乡市灌溉用水与小麦中铬含量的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01,17(3):243-245.
[4]中国农业部环科所.农业环境保护研究资料[M].北京:农业出版社,2001.
[5]王 威.铬污染地区环境对植物吸收重金属的影响[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1(1):66-68.
[6]杨国治.重金属的土壤化学特征[J].环境质量,1980(1).
[7]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IARC monographs on the evaluation of carcinogenic risks to humans.chromium,nickel and welding[M].Lyon,France: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0,49:130-138.
[8]胡望均.常见有毒化学品环境事故应急处理技术与监测方法[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9]蔡宏道.环境污染与卫生检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10]周红卫,施国新,徐勤松.Cr3+和Cr6+对水花生几种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比较[J].农村生态环境,2002,18(4):35-40.
[11]石贵玉,秦丽凤,陈耕云.铬对烟草组培苗生长和某些生理指标的影响[J].广西植物,2007,27(6):899-902.
[12]徐加宽,王志强,杨连新,等.土壤铬含量对水稻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5,26(4):61-66.
[13]李 义,杨先科.铬的单一或复合污染及镧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4(1):39-42.
[14]陈英旭,朱祖祥,何增耀.土壤中铬的有效性与污染生态效应[J].生态学报,1995,15(1):79-84.
[15]李晶晶,彭恩泽.综述铬在土壤和植物中的赋存形式及迁移规律[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5,31(3):31-33.
[16]Camargo F A O,Okeke B C,Bento.In FM vitro reduction ofhexavalent chromium by a cell-free extract of Bacillussp.ES29 stimulated by Cu2+[J].Applied Microbiology & Biotechnology,2003,62:569-573.
[17]Mclean J S,Beveridge T J,Phipps D.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chromium-reducing bacterium from a chromated copper arsenate contaminated site[J].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0,2(6):611-619.
[18]Francisco R,Alpoim M C,Morais P V.Diversity of chromium resistant and reducing bacteria in a chromium contaminated activated sludge[J].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2002,92(5):837-843.
[19]Amoroso M J,Castro G R,Duran A.Chromium accumulation by two Streptomyces spp.isolated from riverine sediments[J].Journal of Industrial Microbiology& Biotechnology,2001,26(4):210-215.
[20]Caros G ,Itzia A.Phytoextraction:a cost-effective plant-based technology for the removal of metals from the environment[J].Bioresource Technology,2001,77:229-236.
[21]韦朝阳,陈同斌.重金属超富集植物及植物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1,21(7):1196-1203.
[22]张学洪,罗亚平,黄海涛.一种新发现的湿生铬超积累植物——李氏禾(Leersia hexandraSwartz)[J].生态学报,2006,26(3):950-953.
[23]张亚丽,沈其荣,姜 洋.有机肥料对镉污染土壤的改良效应[J].土壤学报,2001,38(2):212-218.
[24]张亚丽,沈其荣,王兴兵,等.猪粪和稻草对铬污染黄泥土生物活性的影响[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02,8(4):488-492.
[25]黄启飞,高 定,丁德蓉.垃圾堆肥对铬污染土壤的修复机理研究[J].土壤与环境,2001,10(3):17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