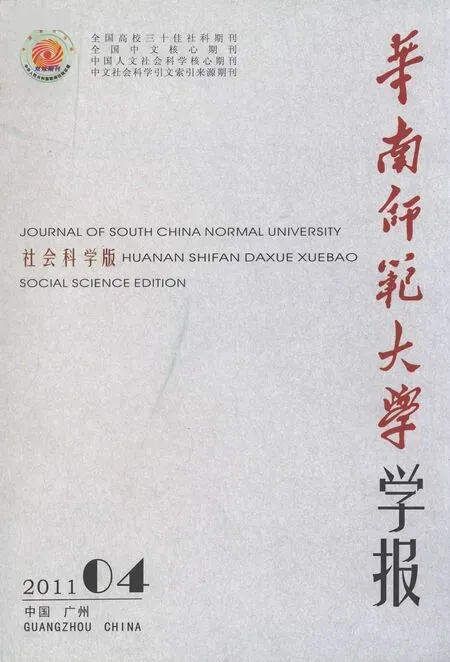胡先骕佚文《蜀雅序》考释——兼论胡先骕词学观念的文化守成主义倾向
闵定庆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胡先骕佚文《蜀雅序》考释
——兼论胡先骕词学观念的文化守成主义倾向
闵定庆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胡先骕《蜀雅序》一文,是为前辈词人周岸登《蜀雅》所作的序,刊于《蜀雅》卷首,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合编《胡先骕文存》失收。这篇佚文追述了周岸登的治词经历,真实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旧体诗人的创作情境,同时也通过回顾自己的学词经历,肯定了密切关注时局、心怀民瘼的创作观念,以此对五四新诗探索作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
胡先骕 《蜀雅》 词学 文化守成主义 五四
一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又曾两次留美,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植物学博士。1918年9月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东南大学)农科教授;1926年6月组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当选中国植物学会会长,次年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0年受命创办中正大学;1948年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三级研究员,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①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第16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他喜爱文学,旁及哲学,是知名的旧体诗词作家和评论家。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合编《胡先骕文存》,由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印行,有功于学术,但偶有遗漏。例如,前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岸登的词集《蜀雅》一书刊有胡先骕的《蜀雅序》,即可补《胡先骕文存》之遗。
现将胡先骕《蜀雅序》一文标点如下:
庚午岁暮得北梦翁书,以勘定词集《蜀雅》将竣,属为之序。余不文,何足序翁之词?然自丙辰邂逅于金陵舟次,有《大酺》之唱酬,忘年定交,忽忽十余载。关河阻隔,交谊弥挚,知翁之身世,嗜翁之词翰,环顾海内鲜有余若,则于翁以定稿问世之际,又乌能已于一言?翁,蜀人也。蜀本词邦,相如、子云导之先路,太白、东坡腾其来轸。自汉魏以还,迄于今世,言词赋者,必称蜀彦。而《花间》一集,岿然为词家星宿海。盖其名山大川,郁盘湍激,峰回峡转,亦秀亦雄,清奇瑰玮之气,毓为人灵,有以致之也。尝考风诗雅乐,本出一原,后世莫能兼擅,乐府与诗遂歧而为二。隋唐嬗衍,倚声代兴,宋贤从而发扬光大之,体洁韵美,陵铄百代。元明以降,此道浸衰。有清初叶,重振坠绪,而斠律铸辞,则光宣作家乃称最胜,半塘、彊邨久为盟主,樵风、蕙风赓相鼓吹,至异军突起、巍峙蜀中者,则香宋与翁也。香宋词人禀过人之资,运灵奇之笔,刻画山水,备极隽妙,追踪白石,而生新过之,余夙有文论之矣。翁词则沉酣梦窗,矞皇典丽,与香宋殊轨而异曲同工焉。居尝自谓古今作家之所成就系于天赋者半,系于其人之身世遭遇者亦半。翁少年蜚声太学,博闻强记,于学无所不窥,壮岁游宦粤西,屡宰剧邑。退食之余,寄情啸傲,穷桂海之奥区,辑赤雅之别乘,柳州、石湖以后,一人而已。迨辛亥国变,更宰会理,抚循夷猓,镇慑反侧,则蒐讨其异俗,网罗其旧闻,歌咏其昳丽瑰奇之山川风物,一如在桂。已而客居故都,落落寡合,黍离麦秀之慨,悲天悯人之怀,一寓于词,风格则祖述梦窗、草窗,而气度之弘远时或过之。盖翁之遍览西南,徼山水雄奇之胜,所遭世难,惝恍诪张之局,有非梦窗、草窗所能比也。丙辰参赣帅幕,武夫不足以言治,乃益肆志为词。征考其邦之文献,友其士君子,酬唱燕谈,几无虚日。所作气格益苍坚,笔力益闳肆,差同杜陵客蜀以后之作。乙丙而还,世乱弥剧,翁乃避地海疆,谢绝世事。讲学之暇,闲赓前操,命意渐窥清真,继轨元陆,以杜诗、韩文为词,槎枒浑朴,又非梦窗门户所能限矣。余少失学,束发就傅,专治自然科学,于吟事为浅尝。乙卯自美利坚归,闲与旧友王简斋、然父昆季学为倚声,于宋人夙宗梦窗,近贤则私淑彊邨,与翁所尚不谋而合。自识翁后益喜弄翰,篇什渐多,终以不习于倚声之束缚,中道舍去。十载以还,虽不时为五七言诗,而倚声久废,惟把卷遣日,尚时翻宋贤之遗编而已。视翁之老而益进、蔚为大宗者惭恧奚如。而翁不遗其僿陋,一篇脱手,千里写似,宁谓余知词无亦心神契合,有非形骸关塞所能外欤?余之叙翁之词,盖不仅述翁之所造,亦以志余与翁不谖之交云尔。民国二十年二月新建胡先骕。围绕这篇佚作,有一些问题必须先行廓清。其中,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第一,关于周岸登其人其书。周岸登(1878—1942),字癸叔,号二窗词客、北梦翁,清同治十一年清明日出生于成都郊外十里的白鹤湾。十六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历任广西阳朔、苍栝等县知县及全州知州。辛亥革命后任四川会理、蓬溪等县知事,1916年赴赣军幕,后任宁都、清江、吉安等县知事及庐陵道尹。20年代弃官,矢志作育人才。初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主讲词曲;1931年秋应安徽大学文学院聘讲授词曲;1932年秋重庆大学创文学院,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1935年重庆大学文学院并入川大,遂赴蓉主川大词曲学教席;1942年9月,因病辞世。传世有《唐五代词讲稿》、《北宋慢词讲稿》、《曲学讲稿》、《蜀雅》、《韩民血泪史》、《能登集》、《南征日记》、《贤女传讲稿》、《管子故训甄》、《楚辞训纂》、《金石学讲稿》、《手批宋七家词钞》等。1931年(辛未),门人包树棠等整理周岸登著作出版,名《二窗词客全集》。第一种即《蜀雅》,计十二卷别集二卷,分订二册,由王易、汪东题签,扉页有“重光协洽之岁择勘校印”字样,即辛未年,上海中华书局仿宋活字铸版代印;版权页上方贴“二窗”印记,上海南京路文明书局发售,实价三元;卷末署“门人上杭包树棠、玉环韩文潮校录”。其中,包树棠是周岸登执教厦门大学中文系时的得意弟子。周岸登序张秀民《宋椠经籍编年录》谈到了自己的几个弟子,略云:“岁丁卯,余教授厦门大学,诸生之潜心朴学者得二人焉,于文本科则嵊张秀民涤瞻,于国学专修科则上杭包树堂伯芾。二人者,日埋头于图书馆,暝晨写,矻矻不休,视其状若泰山于前而不知,震雷发于后而不觉,世间万事万物,举无足以当其一属目一萦心者然。呜呼,何其专也!伯芾兼工诗文词曲,涤瞻间一为考据之文,他则不甚措意,而皆好为目录之学。伯芾所为汀郡艺文志,余既序而传之矣。”可见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蜀雅》一书自然由门生任校勘印行之责。笔者所见《蜀雅》,为周岸登亲笔题赠“广东国民大学图书馆”者,钤“癸叔持赠”印。据此推测,周岸登当时曾将《蜀雅》赠给多个大学图书馆。
第二,关于周、胡二人的交往过程与此序写作的时间。胡先骕小周岸登十六岁,自然在行文之中以晚辈自谦。序文提到“丙辰邂逅于金陵舟次,有《大酺》之唱酬,忘年定交”一事,即1916年邂逅于南京,周胡二人的唱和作品均收入各自的集子:胡先骕《忏庵词》第四首即为《大酺》,题序为“舟中呈周癸叔先生”;而《蜀雅》卷七“南潜词一”的第一首就是《大酺》(金陵舟次酬胡步曾见赠),并附胡先骕原唱。从《蜀雅》按自然时序编排的体例看,胡先骕所提到的唱和,正好排在周岸登南下途径南京之时,“南潜词一”第二首则是次年中秋与胡先骕同作于南昌东湖的《莺啼序》,后面的作品按其游览江西各地的路线排序,相对集中反映了居赣期间的游踪和唱和。周岸登《蜀雅》录与胡先骕相唱和的作品计7首,而胡先骕《忏庵词》则达28首之多,如胡首倡《大酺》(舟中呈周癸叔先生),周作《大酺》(金陵舟次酬胡步曾见赠),胡先骕还在次年秋天作《忆旧游》(金风薄人缅怀江亭旧游和癸叔丙辰重九之作)追忆这次唱和;周、胡于中秋月夜同游南昌东湖,用梦窗韵填《莺啼序》;胡读周词有感作《惜秋华》(锦字银笺),周则作《惜秋华》(忏庵读余近稿有赋,依韵酬之,并示二湘)以和之;周登临滕王阁,赋《江城子慢》(滕王阁晚眺),胡亦赓和《江城子慢》(远鸿影明灭);胡得外祖父郑晓涵手稿,赋《齐天乐》(丁巳季秋于故纸中觅得先外王父郑晓涵先生手书自辑《晚翠轩词》残稿一卷,先外王父曾自刊《晚学斋集》,流传亦稀,仅存硕果,览物怆怀,赋此一解),周读手稿及胡词之后填《齐天乐》(得歙郑晓涵先生《由熙莲漪词》初刻及重刻二本,谂为忏庵外祖,举示之。他日,忏庵于故箧中蒐得先生手写自辑《晚翠轩词》残本一册,感而有作。余亦依韵成此,题《莲漪》卷后),并题在此卷之后。此外,胡先骕追和周词的作品更多,如《蓟门春柳词》三十首作《杨柳枝》(和癸叔蓟门春柳词仍借比竹余音均)、《渡江云三犯》(净社拈题得雨意限第八韵,赓癸叔作即寄)、《春从天上来》(和癸叔再叠祀灶叶赋立春均)、《扫花游》(吏事羁人,良人星散,重以风雨连夕,遂失三春花,时癸叔有宠瓶花之作,漫拈一解和之。用梦窗西湖寒食均)等,均可见出胡先骕对周岸登的景仰之情。正是在这两三年间,胡先骕填词近三十首,形成了平生仅有的一个词创作高峰期。随着周岸登离赣、胡家出现变故,胡先骕不得不为衣食奔走,渐渐疏远了词的创作,“倚声久废,惟把卷遣日,尚时翻宋贤之遗编而已”。平心而论,1931年的胡先骕,无论是作为自然科学家还是作为旧体词人,其声望均未达到巅峰,反倒是其为旧体文学“奔丧”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云:“这个‘古文死了两千年’的讣文出去之后,起初大家还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纷纷议论了;不久,就有人号啕痛哭了。那号啕痛哭的人,有些哭过一两场,也就止哀了;有些一头哭,一头痛骂那些发讣文的人,怪他们不应该做这种‘大伤孝子之心’的恶事;有些从外国奔丧回来,虽然素同死者没有太大交情,但他们听见哭声,也忍不住跟着哭一场,听见骂声,也忍不住跟着骂一场。所以这种骂声至今还不曾完全停止。”见《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第93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的名声更大一些。周岸登自然不必借晚辈的序言以自重,这里更多地流露出了对南昌词缘的留恋,对旧体文学创作复兴的一份努力,是引以为同道的心灵共鸣。胡先骕也一反连年来批驳胡适之文尖锐、犀利、嘲讽杂作的笔调,《蜀雅序》通篇文字平和、静穆而理性,充分体现了对于前辈学人的由衷敬意。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旁证材料,应予以注意。《蜀雅》由王易题耑,第二序也是由王易写的,接排在胡序之后,署“丁卯六月南昌王易”,其中有“今二窗将往教厦门,汇刊所谓倚声八稿,嘱余序端”的话。王易(1889-1956),南昌人,与胡先骕同时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为一生挚友。周岸登莅赣,王易、胡先骕与之唱和甚多,《蜀雅》卷七所录词就是1917年三人唱和的直接成果。1927年,王易执教于南昌心远大学,主词曲学教席,著《词曲史》,倩周作序。周序作于“丁卯六月”,亦即离开南昌前夕。略云:“南昌王子简庵,十年来倚声挚友也。去年教授心远大学,撰《词曲史》一编,用作教程。”②周岸登:《王易〈词曲史〉序》,见王易《词曲史》,第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是在周、王二人“闭门论著,数有切磋”的情形下写出来的,其中所表达的词学思想与胡先骕《蜀雅序》的词学倾向契合无间。1964年,胡先骕与词学家龙榆生通信,4月19日致龙榆生信言拟寄周癸叔之《蜀雅》、袁克定词及王易词望予采录,亦请录后原件寄还③胡先骕致龙榆生书手迹,转引自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第178页。,颇可见出胡先骕对于“南昌词缘”的眷恋。
从周岸登的赠书行为、行年经历、作品编排次序及胡、周、王三人的唱和作品等方面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确信《蜀雅序》必为胡先骕手笔无疑,可补《胡先骕文存》之遗。
二
胡先骕现存的最早词作,作于第一次留美期间。1916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中批评胡先骕那首由“一堆陈词滥调”组成的《齐天乐·听邻室弹曼陀铃》,就是发表在先前的《留美学生季刊》上的。胡先骕于1916年回国,与王易兄弟、周岸登唱和不绝,居于《忏庵词》之首的《莺啼序》(咏荷用梦窗韵)、第二首《喜迁莺》(题王简庵镂尘词),系题王易词集之作,而《大酺》(舟中呈周癸叔先生)则排在《忏庵词》第三的位置上。这三首词明确昭示了胡先骕渊源于梦窗词、盘桓于友朋之间的词学祈向。胡先骕一方面进行词创作,另一方面又撰写了数篇极具影响力的词学论文,如《评赵尧生〈香宋词〉》、《评朱古微〈彊邨乐府〉》(1922)、《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1924)等,皆“剖析精微,评骘得当”。经过多年沉潜与积淀,他对词创作的体认已相当深刻,词学观念更加成熟,至1931年作《蜀雅序》,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总结的具体成果。如果我们将这篇《蜀雅序》与其词作、词学论文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词学观念是一以贯之的。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从传统儒家诗学观念出发,推重词的尊体观念,因而在词体重新定位的过程中沾染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的色彩。胡先骕认为,旧体诗词由四言发展为五七言,最后出现词曲,乃是中国诗歌五千年探索的历史必然,“五言古诗实为吾国高格诗最佳之体裁”,而七言古、五七言律绝与词曲为其辅。无论是五七言诗还是词曲,都体现了汉字一字一顿、句法整齐、平仄押韵的特点,反映了汉字的“自然”和诗性的“本能”。更重要的是,词曲系从乐府中衍生而来,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尝考风诗雅乐,本出一原,后世莫能兼擅。乐府与诗,遂歧而为二。隋唐嬗衍,倚声代兴”;虽在形式上有所革新,“然不得谓为诗界之革命”,不能将其无限拔高,等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层次上的新诗革命。绝对不能误以为词曲长短句一如胡适所渲染的那样是“白话再现”。词曲一方面要继承“风诗雅乐”内在精神,另一方面还要严守音律,还原其音乐文体的基本属性,突出其音乐美。其《评朱古微〈彊邨乐府〉》一文推重朱祖谋一生潜研词学、四校梦窗词,精于词律为“有清一代之冠”,就是明证。从词的发展历史来看,词常遭“诗余”、“小道”之类的非议,胡先骕在《评赵尧生〈香宋词〉》中指出:“人每谓词为诗余、雕虫小技之流亚,然技宁有大小?要在人为耳。”因此,要极力提倡词创作主体的“高超卓越之理想、想象与情感”,使词的社会地位和文学表现力得到彻底改观和提升。词创作应继续发扬先秦诗歌“芳草美人”的寄托思致,“芳草美人之思,本为诗歌一要素”,如能将个人身世打入时代悲剧之中,“黍离麦秀之慨,悲天悯人之怀,一寓于词”,这样的词人方担当得起“词场屠龙手”之誉,这样的词作才能够真正体现“杜诗韩文”的真意。相对而言,周岸登《王易〈词曲史〉序》更将这一祈向作了更为“现代”的阐释。他指出,词曲能够在“群言混淆”的当今世界挺立“国学”的声音,引导后来者,臻于“高尚纯洁要眇”的境界,又能以“忠厚恻怛,闳约深美”的体性移人性灵,“涵濡德性,反之于诗教”①周岸登:《王易〈词曲史〉序》,见王易《词曲史》,第3页。。这是在传统文人对于词曲特性的普遍共识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认为可通过体悟旧体诗词触摸到传统文化血脉的悸动,进而涵养德性,体现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因此,“感于废学新潮,群言淆乱,深愍晚学无所折衷,将以祈向国学之光大,牖启来者,导之优美高尚纯洁要眇之域焉”的境界,正是胡先骕一生努力不懈的方向。而旧体诗词是他最拿手最擅长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之一,是他感觉到真正的文化归属感的“情感渊薮”,恰是达到优美高尚纯洁要眇境界的最佳途径,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再生的根本保证。
第二,天资与际遇的交错、地域性与时代性的融合,乃是词创作有所成就的关键。风云之气弥漫于词境,突出词创作的现实取向。胡先骕从词史的高度,提炼出了词创作之所以获得成功、词人之所以成就的关键要素:天赋、际遇、大文学传统、师承渊源、地域文学影响、时代风云的际会等等,并特别阐述了地域文学传统和个人遭遇的重要作用。在这里,他以浓笔重彩描绘了“蜀本词邦”的地域文学传统。自汉朝开始,“相如、子云导之先路”,司马相如、扬雄以赋名满天下;而唐宋时期“太白、东坡腾其来轸”,李白、苏轼天才踔厉,诗歌成就之高,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以致“迄于今世,言词赋者,必称蜀彦”。而在词创作的领域,《花间集》作为词体成熟的标志,作为中国词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词集,“岿然为词家星宿海”,垂范后世词家,影响深远。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纵轴还是在诗词文体嬗替的横轴上,蜀地文学内在精神贯穿其中,始终如一。究其原因,蜀地文人“得山川之助”是最主要最明显的原因。“盖其名山大川,郁盘湍激,峰回峡转,亦秀亦雄,清奇瑰玮之气,毓为人灵,有以致之也。”蜀地优美的自然条件无与伦比,是不可复制的,因而也营造了整个蜀地文学的特殊气质与精神氛围,最后凝定为文学遗传因子,产生了深层次的限定性影响。身为蜀人,周岸登被赋予了这种“亦秀亦雄”的先天禀赋,以此为其词创作的底色,故能开张犀利,对周遭的自然美景会然于心,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高度的敏感与共鸣。胡先骕在《蜀雅序》中提出了“古今作家之所成就系于天赋者半,系于其人之身世遭遇者亦半”这一极具兴味的命题,强调作者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他指出,周岸登以文学家“哀乐过人”的天性遭逢国变,时代风云之气奔来笔端,“客居故都,落落寡合,黍离麦秀之慨,悲天悯人之怀,一寓于词”,气度之弘远时或超越二窗;为西南小吏时一方面盘桓瑰丽山水,深得柳宗元、韦应物澹远醇厚的诗歌灵魂的熏染,另一方面“所遭世难,惝恍诪张之局,有非梦窗、草窗所能比也”;参赣帅幕时“乃益肆志为词”,“所作气格益苍坚,笔力益闳肆,差同杜陵客蜀以后之作”;退居海滨之后,发现国事难为、民生日艰、个人闷遁,一齐涌上心头,自觉继承了杜韩传统,“以凄悲为骨”,抒书了时代的悲哀与人生的凄凉,使其词作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都不是周邦彦、吴文英“门户所能限”的了。因此,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先天地注定了“时代之子”的命运。
第三,推尊二窗,扬榷晚清,标举“雅”、“悲”之美,凸现了密切关注时局、心怀民瘼的现实创作观念。众所周知,梦窗崇拜是在晚清才渐成气候的。“梦窗由平行的诸家数中的一家,而迥然拔于诸家之上,吸引了校勘家、注释家、谱牒家和鉴赏家的特别注意,由此导引一时词学潮流”①彭玉平:《朱祖谋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梦窗词研究》,见《词学》,第十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形成了清末民初词坛的一般认知与整体氛围,映射在胡先骕心灵深处,产生了极大的回响。而与周岸登、王易论词的经历,促使他更加认同梦窗词和晚清四大家词。这一词学环境便构成了胡先骕词学观念的“预设”性前提。所以,他在《蜀雅序》中回顾整个词史发展历程梳理出了“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于清真之浑化”的词学路向,将梦窗词设置为词史纵横两条轴线上的坐标,凸现其三重“角色”:一是遵循南宋雅词派的路线,既可视梦窗词为“词学高标”,学词、品词一以为准,又可将其提升为从王沂孙词入门、最后臻于周邦彦词的境界的过渡航梯和整合要素,从而表现词创作“矞皇典丽”、“隽妙”的美感,自能避免“花间之恶调”、“淫词之俗艳”;二是由于梦窗词与苏辛两派之间在表现对象、风格范型、音律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分别,可以将其与苏辛分隔开来,两峰并峙,双水分流,照顾到后学者的实际情况,不盲目追求两种风格的“整合”与“融合”,把词创作实践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和“迷茫心态”最大限度降低下来,走上一条相对“纯净”的创作道路;三是更为积极的态度,将梦窗词视为一个融合性的“平台”,熔王、吴、周、苏、辛于一炉,进而自成面目,使得词创作臻于“化境”。显而易见,他试图在这一词学传统下建构“摹仿与创造”的互动模式。也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明确表达了对晚清四大词人的服膺,认为晚清四大词人兼善王、吴、辛、苏、周之长,突破藩篱,达到了“杜诗韩文”的极致,如其《评文芸阁〈云起轩词〉王幼遐〈半塘定剩稿〉》评王鹏运“所治为两宋”,“自南追北,既得梦窗之研炼,复得稼轩之豪纵,工力、才华互相为用”,不屑为侧艳之语;又如《评朱古微〈彊邨乐府〉》评朱祖谋《金缕曲》《夜飞鹊》诸什“可见其蒿目时艰之忠忱”,《水龙吟》寓“易代之思,悲凄入骨”,“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也”。他以同样的口吻肯定了周岸登“感时伤世”的词创作,指出词人“于宋人夙宗梦窗,近贤则私淑彊邨”,迭经国变,“黍离麦秀之慨,悲天悯人之怀,一寓于词,风格则祖述梦窗、草窗,而气度之弘远时或过之”,最后超越梦窗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从梦窗词入而又自梦窗词出,将身世遭逢打入词创作,由此臻入杜诗韩文之境,才是他最坚信且最向往的了。
胡先骕在其《文学之标准》中列举了“文质之节制”、“情感之中正”、“文形之优美”和“议论之客观”四个标准。这四者互动关系的“度”的精确把握,是考验文学家的“试金石”,也是“欲创造新文学者所宜取法”的。在他看来,周岸登的词作完全符合这一复合型标准,理应得到充分肯定。我们发现,剔除个人情感不说,他坚持传统文学的美感特征来观察和评判研究对象,能从词史的宏观高度来对个体词家的创作进行定位,同时又能从西方文学中借鉴新理论新方法加以灵活运用,而不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体现了相当清醒的历史眼光和辩证方法。他始终未跳出传统的“藩篱”,未能往前再踏出一步。这也正体现了其理想“自限畛域”的文化姿态。
三
胡先骕是在浓郁的传统文化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倾向深深沁入了他的每一个毛孔,成为其人格心态的底色,内化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他以一种近乎严酷的方式将自己分割成了两个自我形象,一个是作为植物学家的自我,一个是作为旧体文学家的自我。前者以纯粹的技术服务社会,后者寄情于旧体诗词。就在他写作《蜀雅序》的1931年,新文化运动已经大获全胜,五四主将竞相欢呼“反对党已经破产了”。但是,他依然故我地延续着这个“过时”的论争,似乎早已预知自己必将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偏偏旗帜鲜明地表述了皈依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心态以及志在高扬旧体文学的祈向,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的坚持。这一文学姿态的形成,个中原因很复杂,既有内在的,也有外部的。这里,我们可先从以下三个内部条件来进行观察。
第一,旧式大家族的文化渊源。新建胡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封建官宦家族。胡先骕的曾祖父胡家玉于道光廿一年探花及第,官左都察御史;祖父胡庭风早逝,叔祖胡湘林中二甲第六十一名进士,授翰林编修,后两度署两广总督,辛亥之后寓上海,以遗老终;父亲胡承弼,举人出身,官内阁中书。胡先骕四岁入家塾,读四书五经,九岁时父亲亡故,母亲督教极严。他过早地尝尽了人间的辛酸,重复着许多传统文人忠孝传家的心路历程,因而对传统文化有着刻骨铭心的体认。他一辈子谨守传统纲常,没有根本的改变,晚年曾自述道:“我因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封建主义成为我的基本思想,无论如何发展,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①胡先骕晚年自述,转引自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第51页。因此,维系传统、光大国学,成为胡先骕一生努力不懈的方向。而旧体诗词作为他最拿手最擅长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之一,恰是达到优美高尚纯洁要眇境界的最佳途径,寄托着无限幽思,进而在这一弥漫着浓郁传统气息的氛围中孕育真正的文化归属感。
第二,教育经历的特殊性,烙上了深深的保守印记。胡先骕曾短暂入读家塾,但随着学制转型,他系统接受了新式教育,先后就读南昌中学、京师大学堂、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新式的科学教育反而使得他将科技与文化截然分隔开来,在情感层面无条件倾向于传统文化。终其一生,他都在感念几位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如启蒙教师熊子干先生授四书五经、诗词音韵,将他引入了古典文学的殿堂。他更受到时任南昌知府的“同光魁杰”沈曾植的关照,相继荐入南昌中学和京师大学堂。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时,几位桐城派末代大师,如林纾、柯劭忞等主文学教席,他在林、柯的指点下赋诗作文,以诗名列“太学十君”;又曾得到张之洞的接见,还获选列队为慈禧送葬。求学哈佛大学时,他接受了白璧德教授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他译述《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之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决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学,而提倡伪道德。若信功利主义过深,则中国所得于西方者,止不过打字机电话汽车等机器。或且因新式机器之精美,中国人亦以此眼光观察西方之文学,而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则见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谋而有合,可总称为邃古以来所积累之智慧也。”可以说,这是胡先骕文化史观的总纲,一生奉行不渝。这几位典型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既是他的文学引路人,更是他的精神导师,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三,交游网络的文化指向性。胡先骕交友,有两个圈子,一是科学界、教育界同人,一是旧式文人。前者多限于学科研究与教学领域,后者则深入到其精神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层面,进而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他对于这批旧式文人有着深刻的“同情之了解”,认同清末文人的政治作为与气节,在《评朱古微〈彊邨乐府〉》一文中指出:“清末文人与政局多有密切关系。甲午之役,一时号为清流者,如张佩纶、陈弢庵、文芸阁、张季直辈,皆拥常熟相国为魁,率纷纷主战。戊戌政变,参加者尤夥,谭复生、林墩谷辈至菜市之惨戮,陈伯严、文芸阁则降谪窜逐,郑太夷、严几道亦与之同声气。”这些人多半与胡家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又曾撰专文深入系统地评价了影响自己最深的几位前辈,于诗有沈曾植、陈三立、赵尧生、俞恪士、陈仁先等,于词则有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周岸登等。如赞沈曾植为“觥觥维新魁”,认为沈氏维护帝制是基于“爱国与忠君,国俗古如此”的传统,本无可厚非;又指出陈三立先后赞襄其父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施行新政,辛亥革命后“绝不以遗老自居”,乃是进步的表现。他还在《与吴宗慈论陈三立传略意见书》中深情地回忆起芦沟桥事变之后谒见陈三立的情景,“先生对于我国抗战,具莫大信心,盖先生平生负豪气,其忠于国家之枕至死不衰有如此者”。显而易见,这种充满温情的文化氛围,冶就了胡先骕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认同。守成主义情绪从家学领域漫延至政治、思想、学术、文学、人物品评等层面,由仰慕现实政治人物的风骨生发出弥漫历史天际的万千感慨。他终生都在感念这些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更多地看到了思想巨人的精神投影和人格感召力,更映射了对于传统文化日渐沦亡的焦虑与伤悼。他将旧体文学视为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传统的“根柢”,加以热情讴歌,以此张扬光大国学的“祈向”。
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从反方向刺激了胡先骕的道德情感。就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积极应对胡适的挑战,这就非常自然地建构了他所思考词学问题的时代主题,逐步形成并完善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观念,进而将这一观念渗透、落实到具体的词学活动之中,直接回应了五四新诗探索者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尖锐地批判胡适的词学观念的偏激与不足。这应视为理解《蜀雅序》的情感底色和理论倾向最关键的切入点。
胡适以“八不主义”和白话文学史观为前提,构拟了一个新的词学体系,其中有几点是专门与传统词学“唱反调”的,令胡先骕深感不安。首先,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或曰“活文学”、“平民文学”)古已有之,“白话的文学种子”伏于唐宋“小诗短词”之中,白话词便成了白话文学发展及白话文学史建构的重要资源。他的《留学日记》写道,李后主、黄庭坚、向镐、辛弃疾等人的近乎白话的词作恰是“活文学之样本”,代表了白话文学史第三期的成就;其次,胡适依据自己设计的文学新方式出自民间→文人参与→文人创作“匠人化”这个“逃不了”的运动模型,将整个词史的发展建构为“三步曲”:“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第三时期:自清初到今日(1650-19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创作主体亦随之划分为“歌者”、“诗人”和“词匠”,而对早期的民间词、白话词予以高度肯定;最后,胡适将苏辛词推尊为词的巅峰,认为苏辛词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创作范围的极度扩张与语言近乎白话的“自然”,这就使得他与当时词坛崇尚梦窗词的风气拉开了距离。他抨击南宋雅词“往往因音节而牺牲内容”,“至多不过是晦涩的灯谜,没有文学的价值”,以晚清四大词人为代表的“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派的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很少有价值的”,完全可以不予讨论。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第21页。
对此,胡先骕直斥胡适“于诗所造甚浅”,“本未升堂,不知名家精粹之所在”,只知拾掇“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唾余”,谈的都是“肤浅之改革”;“八不主义”、“白话文运动”仅触及“作诗之方法”,“不得谓为精神”;“但知诗面而不知诗骨”,因而“大有可讨论之处”。胡先骕撰《评〈尝试集〉》对胡适的《尝试集》进行了“肢解”式的剖析,以系统批判新诗尝试理论的缺失和实践的苍白。《尝试集》不过是一个172页的“小册子”,自序、他序和目录已占去四十四页,旧式诗词复占去50页,在所余78页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须复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新诗者,仅有十四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真正成为新诗的只有十三首”。集中“最佳”的《新婚杂诗》、《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在题目上“易于有真挚之语”,但“尚微嫌纤”、“尚微嫌不深切”;《送叔永回四川》“佳处在描写景物与运用词曲之声调”,短处则在“无真挚之语”。其余诗作都逃不了这样那样的讥讽,如《人力车夫》“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一颗遭劫的星》“肤浅之征象主义”、《蔚蓝的天上》“肉体之印象主义”、《一笑》“纤巧之浪漫主义”和《我的儿子》“无谓之理论”。如此微薄的成就怎能打倒黄鹤楼、踢翻鹦鹉洲呢?又怎能“上追李、杜,远拟莎士比亚、弥尔敦”呢?
在他看来,“文白之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活文学”与“死文学”之嬗替,都是伪命题。旧体诗词之不易被打到,自有其理由,那就是文学之美在于“以中正之态度,以平情之议论”,可为“人生之师法”,而非语言工具本身。他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中国的五七言诗比作西方的meter诗。关于此类诗体,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德莱登、德昆西、爱伦·坡等西方诗学巨擘都有“诗与文之别,即在整齐之句法与叶韵”、“整齐之句法,可辅助思想之表现”、“若使诗之媒介物,完全与普通言语之用法同,则不成为诗”一类论述。由此可见,“古往今来大诗人大批评家”“靡不以整齐之句法为诗所不能阙之性质”,与中国旧体诗词一样是起“增加诗之美感”的作用的。胡适仅以“俗话”、“明白如话”、“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这三点来界定白话文学,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汉字特征,更漠视汉语的特殊美感,漠视声调、音韵和格律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性。
胡先骕觉得,既然语言不是诗歌改良的根本问题,那么,讨论就应被拉回到文学的起点即“诗之精神”本身。他认为,文学可以表现闲情雅致,更应表现“高超卓越之理想、想象与情感”,以求“修养精神、增进人格之能力”,培养一种优美的、有自制力的、中庸的君子风范。反观“今日”文坛,却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一为“崇尚功利主义之习”,“近日之新文化运动者,虽自命提倡艺术哲学,骤视之,似为今日功利主义之针砭,实则同为鄙弃节制的道德之运动”,直接导致“吾国固有文化今日之濒于破产”,“将有最后灭于西方文化之恶果”;二为“卢梭以还之浪漫主义”,一味废弃文学规律,“全任感情之冲动”驱使文笔,以同情心取代道德尺度,“不求中庸节制之训练”,以致文坛弥漫着“人性之恶”。他认同白璧德的观念,“中国之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决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学,而提倡伪道德”,要杜绝功利主义,“勿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他指出,文学表现不能跨出这一步,要立足于古典诗词的抒情范式,“运灵奇之笔,刻画山水,备极隽妙”,“歌咏其昳丽瑰奇之山川风物”,“黍离麦秀之慨,悲天悯人之怀,一寓于词”,立象言志,修辞立诚。他批评胡适新诗“尚感情而轻智慧”,追求官觉上的美感,除与肉体有密切关系者外,都没有精神上的“独立之美感”。他在《蜀雅序》中重新把词创作纳入传统词学的范畴,提升到了杜诗韩文的高度,“取径少陵,发扬忠爱”,强调时代风云之气对于词创作的内在规范性影响,强调词创作的“词史”性质,集中体现了传统士大夫文人“民物胞与”的精神追求和“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
基于这一认识,胡先骕循着晚清民初词坛梦窗崇拜的习气,尊奉南宋雅词派及晚清四大词人,从继承与创造的辩证关系出发,强调了传统词学的线性传承谱系,建构以雅词为核心的中国词史的骨骼与脉络,极力反对胡适所建构的白话词史。他在《评〈尝试集〉》中系统论述了摹仿在个人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预设”作用,认为任何个人都是在前人所创造的思想、文化、文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则能培养相应的技巧,二则能接受其理论,三则能“领略其佳处”。这就像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摹仿艺术”那样,既摹仿天然景物,又摹仿“事实上之人情”,更摹仿“理想上可能之最高格之人情”,从而塑造出词人的人格模式和审美范式。但“摹仿既久,渐有独立之能力”,模仿有着“自异于古人”的创造力。这一能力的养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兼揽众长”,二是另辟意境,三是“发扬光大古人之一长”,四是将现代文人、科技知识导入诗作,虽然体裁摹仿古人,实质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只有正视基本史实,从文学现象入手,才能真正明白文学创作继承与超越的辩证关系,建构真正符合历史真貌的词史,穷尽“正变之理”。如此看来,胡适所构拟的白话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以及对梦窗词的攻击,反而显得缺乏生动活泼的成功例证和足够的历史依据了。
胡适与胡先骕在美国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都受到了欧美最新诗潮“意象主义”的熏染。胡适过于激进,注重“历史”的解析,导致了“诗性”的全面缺失;而胡先骕止步于传统诗教观,囿于“执古”的守望,未能把西方的新理论运用于文学的转型,五四诗歌建设与英美诗歌新潮擦肩而过,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二胡文学观念的不完备和文化情感的偏差,是那个时代极其典型的表征,也正是这一时代的局限性部分导致了五四先驱努力耕耘诗歌和小说却收获散文的尴尬。孙绍振在《“五四新诗”:胡适与胡先骕》中作了这样一个评价:“胡先骕反对五四新诗的立场,在根本方向上肯定是错误的,但是,他的错误,不是一般粗浅的谬误,而是一种深刻的错误,有时,深刻的错误比之肤浅的正确有价值得多。”①孙绍振:《“五四新诗”:胡适与胡先骕》,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显而易见,胡先骕对于传统的坚持、对于旧体诗词“神髓”的领悟、对于旧体诗词的生命力的深信不疑,正是其“深刻”且“有价值”的地方,却也不免流露出了些许“堂吉诃德”式的悲凉。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察,我们对沈卫威关于胡先骕1922年以后转向情绪化一途的论断②沈卫威说:“事实上,胡先骕的文学观念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脉络,即1922年前后的不同。1922年,他高举反对新文化的保守的旗帜,文学思想有意与《学衡》同人的整体倾向趋同,在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中,多了些有意识的偏至和情感上的成分……但1922年以后的言辞,便有了明显的偏颇和有意识的守旧,对欧美近代文学几乎全盘否定。”见《回眸“学衡派”》,第1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是有所保留的。
闵定庆(1964—),男,江西永修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1-03-05
I226.8
A
1000-5455(2011)04-0053-08
【责任编辑: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