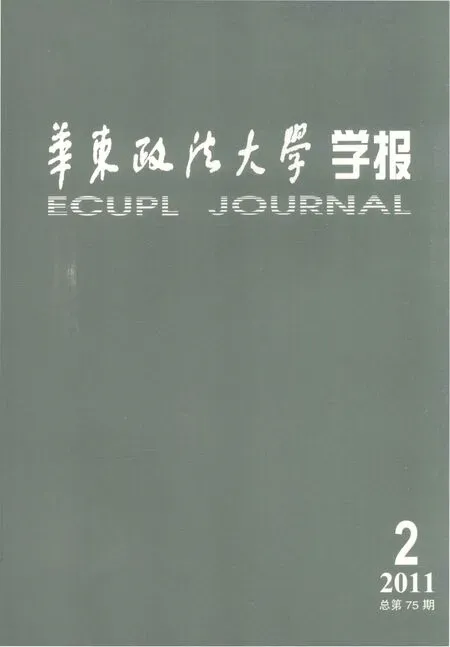民法典编纂的技术问题
魏磊杰
民法典编纂的技术问题
魏磊杰*
从晚近以来的法典重构运动观之,民法典的专业化与精细化乃是法典编纂的必然发展趋势,而民法典的编纂技术却是我国学界甚少关注的问题。当下,我国正在为编纂一部高质量的民法典而努力,因而在技术上借鉴他国的优良做法是有必要的。我国民法典编纂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在起草前期制定“立法原则”,在起草时注重条文用语的精确性,在条文编排上采用开放型编排方式,在条名设置上采用“系统排列”方式,这样就有望用先进的编纂技术确保法典编纂的速度与质量。
法典编纂 编纂技术 民法典
纵观民法典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晚近以来法典重构运动中所凸显的新规范和新做法,我们可以看出其未来大体是朝更为开放、更具弹性的方向发展的。〔1〕这一趋势主要体现为:在保持高度体系化规范架构的同时,在新法典中尽可能地设置诸多衡平性、开放性规范或原则(将法典视作并非自洽而是一种相对开放的动态体系),从而既能确保法典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又可为法官自由裁量营造充足空间,使得法律与现实保持必要的同步,回应法院对个案公正的追求及对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之强调。不可否认,除了具有文化的特质外,法典还有其技术性的一面。法典的文化性与其扎根的本土国情休戚相关,一般与异质的国情难以契合与融通,故而如何突破法典的文化性之阻力常常成为法律(典)移植成败之关键。但相对而言,法典的编纂技术则是价值中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普适的。有鉴于此,笔者仅从民法典的编纂技术(法典的技术性)这个角度对域外法典编纂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进行探究,以助益于我国“体系型、开放型”民法典体系之构建。
一、民法典前期起草程序中的技术问题
在集体起草法典的时代,如何协调众多起草人的思想以保证最终形成的法典草案具有内在精神的同一性?让我们先看一下拉美国家的做法。1999年8月4日至7日,在秘鲁的阿雷基巴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民法大会”。在此会议上,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和波多黎各的民法典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了一个《阿雷基巴纲领》,该纲领宣布,无论是制定新民法典还是已有民法典的签字国,都要遵守诸如保护弱者并尊重具有同等谈判权的主体间的意思自治、承认新形式的财产、保护家庭、尊重未成年人、承认土著民族的文化特性、通过内国立法促进区域一体化等11项原则。为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阿根廷的学者在起草该国新民法典草案前,首先确定了43项起草标准,然后又准备了341条“基础”(Fundamentos)以使这些起草标准更为具体化。就“基础”与草案条文的比例而言,条数比是341∶2627,页数比是144∶561。〔2〕详尽的描述,参见徐国栋:《从1871年〈阿根廷民法典〉到1998年〈阿根廷民法典草案〉》,载徐国栋:《认真地对待民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里的“基础”既可以是起草的操作指南,也可以是起草完成后的立法理由;在议会不完全讨论民法典草案的情况下,它们还可以成为议会讨论的对象。如果同意这些“基础”,民法典即可通过,因为民法典条文不过仅仅是“基础”的具体化和细化而已。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荷兰。1947年,莱顿大学法学教授梅耶斯受命起草《荷兰新民法典》。在起草之前以及起草过程中,梅耶斯采用了大体类同的方式。他首先拟定一系列涉及广泛的问题,发送给愿意提供答复的专家和利益相关人征求意见。这些对象包括法院、法律院校、银行、保险公司、市政委员会、律师事务所以及公证人等等。通过这种初始的“摸底”考察,梅耶斯获得了该国惯常做法与未来法律诉求的大量信息。当然,这些观点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相同的,甚至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于是梅耶斯采用了以下更为具体的策略:为重点凸显具体议题,他将政府委员会灵活分解成多个各自独立的小委员会并分别与其协同工作,每个委员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原有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而且还包括实业界和法律实务界(主要有银行、商会、工会、行政机构、出版商、旅馆营业者、旅游业者、建筑业者等)的代表。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意在解决以下问题:各种具体合同、知识产权、姓名权、监护、自由结社权(包括合作社与相互保险公司)、质押、抵押与不动产让与、人身保险与年金、公司设立、雇佣合同等等与社会体制架构关联甚密的问题。通过此种程序性操作,梅耶斯对于现行法、判例、实践性做法以及针对未来需要而提出的建议有了实质性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他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载有特别有争议的具有政治意涵的50个问题的清单。针对每个问题,他还提供了相应的说明性解答并给出理由。〔3〕See Joseph Dainow,Civil Code Revision in the Netherlands:the Fifty Ques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5,1956,pp.595-598;Arthur S.Hartkamp,Civil Code Revision in the Netherlands:A Survey of its System and Contents,and its Influence on Dutch Legal Practice,Louisiana Law Review,Vol.35,1975,pp.1061-1065.例如,问题十三:就国家公务人员的不法行为造成的责任,民法典是否应当进行规定?回答:至少从暂时来看,在民法典中规定此种责任既非可取也非常不合实际。再如,问题二十三:在缺乏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是否应当规定一项关于如何发现法律的条文?回答:在这种情形下,应当规定这样的一项条文。就如何发现法律,应当遵循以下顺序:(1)基本法律原则;(2)习惯;(3)衡平与理性。〔4〕See Joseph Dainnow,Civil Code Revision in the Netherlands:General Problems,Louisiana Law Review,Vol.12,1957,pp.273-293.可以说,如将编纂一部民法典比作构建一座建筑,那么,这些问题承载的制度考量可以说就是支撑整个建筑的基本架构,一旦基本架构稳妥地树立起来,接下来按图索骥式的增砖添瓦也就容易多了。通过这种方式,梅耶斯获得了必要的政治支持,并进而为《荷兰新民法典(草案)》的出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难看出,上述两类做法虽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却有共同之处,即在法典起草之前,都存在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中介”——原则问题(立法原则)与具体问题(具体条文)之间的中介。这样做的意义有二。一方面,在社会日趋多元的时代,法典编纂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立法机关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以及国家整体社会政策的调控力度。而在法典草案付诸表决前,就将关涉的社会、法律政策问题凸显出来进行评估,然后判断或径直确定、或采用折中方案弥合、或留待单行法规制等等,无疑可为事后法典草案整体之通过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在集体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特别在关涉原则性或政策性问题的时候,各起草委员会难免各自为政,起草出的各编条文相互间往往难以协调甚或彼此抵牾。因而在法典草案付诸表决之前,采用这种前置性程序设置,就某些原则问题或政策问题先行决定,以避免就同一问题在各种层次的会议上反复争论和博弈无疑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做法。
其实,这种先进的前置性程序设计在我国也并不新鲜,“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编纂就曾采用类似做法。当时依照“国民政府”制定重要法律的办法,先定“立法原则”,再定条文,然后讨论通过。即在起草各编条文之前,由“立法院”拟定该编的“立法原则”(又称先决问题)。例如“总则编”的立法原则共19条,“亲属编”的立法原则共9条。所谓立法原则问题皆为“立法上最有争议”之点,至于原则上的细节,则可在起草条文时讨论决定。具体而言,就是先行确定该编中的重大原则问题,并报“中央政治会议”批准,然后“立法院”根据这些问题拟具条文,再行讨论通过。〔5〕参见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这个办法在当时颇为有效。
具体到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纵观《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三部单行法的起草过程,不难看出,立法机关大体沿袭着传统“粗放型”的立法模式:首先根据全国人大的粗略立法规划,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知名学者准备法律草案,在此民间草案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初步草案,然后再结合循环往复的调研、征求意见等环节获得的必要反馈,对草案进行增删、修订以及必不可少的“政治化处理”,确定最终文本并提交全国人大批准通过。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几乎没有类似上述“中介”的程序性安排。当然,在这些法律的起草过程中,我国学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梁慧星教授1994年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方案》〔6〕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方案》,资料来源: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447,访问日期为2010年10月10日。和1998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建议草案)》〔7〕参见梁慧星主编:《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77页。就是践行这种做法的有益尝试。
诚然,考虑到当时的特定法制观念语境,这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很大的创新与进步,为系统性、综合性大规模编纂立法创制了极佳的范例。然而从今日眼光观之,这种尝试在精细化方面似乎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可以说,这些“立法方案”或“大纲”大体上仅是一种逐次列举说明应该规定什么而不应规定什么的“总体立法框架”,并未在实质意义上重点凸显和提炼出在编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原则问题或焦点问题。故而,如我国未来民法典起草旨在追求更为精致化、先进化之目标,那么在编纂过程中引入上述“中介”做法以使整个流程更为精细、更具效率,则确有必要。
具体而言,继《担保法》、《合同法》、《婚姻法》(修正案)、《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陆续出台之后,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总体步骤已然非常明确:分块出台,然后待时机成熟之时整合这些单行立法以求最终成就一部系统的综合民法典。在基本民事单行法出台后,如何对它们进行系统性整合将是决定未来民法典之总体水平和编纂质量的关键所在,其所需工程量甚至丝毫不亚于重新编纂一部民法典。考虑到当前我国法律起草的既有制度性设置,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和做法,笔者认为,无论是通过“系统整合法”还是“重起炉灶法”成就一部民法典,都需首先对现有的涉及民事关系的单行法律、相对成熟的司法判例与法律学说进行总体“摸底”与系统梳理。与此同时,在这些预备性工作基础上,延续以往的做法,拟定民法典立法方案或起草大纲之类的“总体框架”,然后以其为参考蓝本,就未来民法典所可能涉及的基本价值或社会、法律政策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炼出比较成熟且更为中肯的“立法原则”(类同于上文所述的“基础”)。即使对其暂时无法达成统一意见(这是一种通常形态),亦可通过将不同方案分别列举的方式(可分为甲案、乙案以供选择)予以提交。法案纲要中应该附有间接的理由书。理由书应该有法案与现行民法的比较、与以往判例和学说的链接、引用及参考的域外法以及国际条约等内容。“立法原则”确立之后,接下来便可通过程序性设置逐步将此原则性方案细化并最终具体到一个个的法律条文,从而确保民法典之编纂理念能够融贯始终。
二、民法典条文用语的技术问题
作为法律特有的思考手段和传递方式,法律概念的确定性和概括性,不仅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安全价值,也担负着法律的效率价值。“如果试图完全摒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将化为灰烬。”〔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
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法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导致法律技术概念与日常生活概念的分野。由于现代权利义务纠纷原则上都要经法院的审判,立法中的用语最好采用便于法院适用的概念,即必须十分准确。而采用通俗的词语去表现法律命题则存在局限,因此高度技术性的法律术语自然不可避免。《法国民法典》虽以文风简约和词语通俗而著称,但事实上,在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更为严密的技术概念和逻辑又不得不借助判例和学说来进行补充,其结果使所有的普通人读了条文就可理解的赞誉,只剩下了《法国民法典》的轮廓,在审判中使用的仍然是那些具有高度技术性的、非日常生活性的逻辑和概念。因此,有时不使用特殊的技术概念和逻辑去构筑法律命题,就无法在现实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9〕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具体到民法而言,该法的规范对象与其说是广大交易民众,毋宁说是裁判者本身,而这与公法不同。除组织法和诉讼法之外,公法基本上皆为行为规范,以引导人们的行为为其目的,从而规范内容必须充分考量人们的理解能力,高度逻辑化、体系化的法典反而造成认知障碍,妨害规范目的之达成。〔10〕参见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而反观规范私领域的民法,从内容构成角度而言,其财产法主要内容只是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模拟正常交易活动而作的规定,身份法基本上也是建立在普遍的人伦和习惯上,不必“使知之”,即可“使由之”;〔11〕参见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承载的功能角度而言,私法规范的作用主要在于当私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欠缺或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时,为裁判者提供一种裁判准据。而作为裁判准据的任意规范亦可以说是在理性的社会成员通常采用的行为模式之上抽象出来的,事实上它依然依附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说,所谓的法典编纂,“只不过是立法者在对民众自发形成的交往规则和交往秩序予以必要尊重的基础上,将某些旨在解决纠纷的规则加以系统化表述的活动而已”。〔12〕朱庆育:《民法典编纂中的两个观念问题》,载《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既然规则源自社会生活和交易之常态,那么民众无需了解法典内容即可知道怎样生活和交易。由此似乎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民法典编纂的规范意义主要在于为裁判者立法,无论法典如何难以理解,都与行为人没有太大关系,而这就意味着,以民法典的专业性会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阻碍为由来反对法典编纂或主张法典规定应“通俗易懂”,难以自圆其说;其二,既然民法典是以法官为主要规范对象(Normadressat),那么在法典编纂时,在概念选择、句型使用乃至文体调适上,宁可牺牲自然与通俗,必要时吸纳比较法之经验多做创新与突破以求精确与严谨,反而更易达致规范适用之统一,进而最大限度地契合此类规范的终极目的。〔13〕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者的角色》,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从晚近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重构运动观之,法典条文抽象化与立法语言精准化乃是民法典编纂的总体发展态势。肇端于1994年《秘鲁民法典》的改革,立法者就特别注重纠正既有民法典概念上的错误。例如修订委员会认为,“合同的解除”这一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合同本为法律行为的一种,是旨在设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合同一经成立,本身是不可解除的,可解除的应该是因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委员会将法典中所有此等表述都变更为“合同所生法律关系的解除”。在修法过程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14〕徐涤宇:《〈秘鲁民法典〉的改革》,载张礼洪、高富平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997年开始的《波多黎各民法典》重订秉持的方针也是如此。为确保法典重订工作朝着正确方向持续前进,该国立法者事先起草了一个名为《〈波多黎各民法典〉重订工作指导标准》的文件,其中第3条最后一项明确规定:“应特别注意语言的正确使用,并应避免表述模糊或文风缺陷。对于所保留的规范中的那些歧视性、蔑视性或不合时代潮流的语言,亦应替换之。”〔15〕[波多黎各]马尔塔·菲桂罗阿·托勒斯:《〈波多黎各民法典〉的重订进程》,徐涤宇译,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01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改革中,德国法学家认为,消灭时效的中断(Unterbrechung)——指消灭时效重新开始计算——这一表达,从立法语言的角度来看并不成功,为求概念的准确和易于理解,在新法中将这个沿用甚久的概念改称为消灭时效的“重新开始”(Neubeginn),并限制在两种情形下,即只有当债务人承认对于债权人的请求权或债权人采取或申请法院、政府机关强制执行时,时效期间方重新开始。〔16〕[德]米夏埃尔·马丁内克:《200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几点批评性的评述》,许兰译,载米健主编:《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编纂2002年《巴西新民法典》的过程中,巴西立法者尽量取消可能导致疑问或歧视的一些概念,例如“sociedade”(社团)这个术语曾经被用来指所有的私法人,现在新民法典第44条用“associaçao”(社团)这个术语来指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取代了原来的“sociedade”的用法。〔17〕[意]阿尔多·贝特鲁奇:《在传承与革新之间的巴西新民法典》,薛军译,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鉴于在葡萄牙文中,“filhos ilegitimos”(非婚生子女)直译为“非法子女”,具有很强的侮辱性,立法者遂径直取消了这一表达,而改采“O filho havido fora do casamento”(婚外所生的子女)这一更为中性的表达。〔18〕参见徐国栋:《从〈巴西民法汇编〉到〈新巴西民法典〉》,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在2003年日本法律现代语化改革过程中,日本立法者着重将《日本民法典》中一些混淆的概念进行了处理。例如将第132条中的“不法行为”修改为“不法的行为”,这样修改主要是为了避免与“侵权行为”(日语表述为“不法行为”)的概念相混淆;将“解除的请求”修改为“解除权的行使”(第420条第2项)等。〔19〕参见周江洪:《日本民法的历史发展及最新动向简介》,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在民法典重构过程中的共同做法就是:尽最大可能地确保法典术语的精准和统一,为此,有些国家甚至力图达到精益求精的程度。
我国的法典编纂实践虽然维持一般立法的白话语体,但并未特别标榜通俗,《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单行立法基本上沿袭了德国法律体系的通用概念。而且,伴随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深入发展,我国大陆整体立法水平愈发呈现技术化与精细化之态势。但在诸多新近的单行立法中仍有很多地方似乎有待更为精准之设计。一个经常为学者援引的例子是《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20〕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者的角色》,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卉:《德国劳动法中的解雇保护制度》,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1期。在德国法中,能够导致合同关系消灭的单方意思表示,可分为“Rücktritt”和“Kündigung”两种。前者主要针对买卖、借贷、承揽等为一次性给付的合同关系,此种意思表示导致溯及性的消灭合同债务关系的法律效力,所谓合同自始无效。与之相反,“Kündigung”适用于包括劳动合同在内的租赁、合伙、银行结算等继续性合同关系,此种意思表示导致非溯及性的消灭合同债务关系之法律效力。而且,“Kündigung”的原因也不限于违约,当事人基于自己的需要提出,一般也被允许。显然,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制度。我国早期法律学者照搬了德国的这种制度设计,将“Rücktritt”和“Kündigung”分别译为“(合同)解除”和“(合同)终止”,以作区分。1999年《合同法》虽继受了这种制度,但却并未进行区分,合同关系的消灭情况一律采用“解除”,并将第六章标题定为“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而没有使用“合同关系消灭”或者“合同关系结束”的概念。故而,有学者断定,这种做法将“致使术语的不精确及其引致的学理混乱被高位阶立法所固化,学界之后的术语厘清工作定会更加困难”。〔21〕参见黄卉:《德国劳动法中的解雇保护制度》,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1期。此外,肇端于1986年《民法通则》并为2010年《侵权责任法》承继的“赔礼道歉”这一民事责任形式也屡为学者所诟病。魏振瀛教授曾指出,在基本法中规定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形式,是我国的首创。其实,可以说,在基本法中规定这一民事责任形式,乃是我国当时的立法者闭门造车的“独创性”成果。在绝大多数大陆法国家皆将“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作为基本的民事责任形式的情形下,我国这种过于具体化的粗糙规定似乎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同时,立法者将《侵权责任法》第十一章的标题定为“物件损害责任”,且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包括在物件之中。然而,无论从大陆法系的通常界定还是中文的通常表述习惯研判,似乎都无法做出如此宽泛之诠释。诚然,针对此类不一而足的立法概念不准确、不规范、含糊甚至根本不正确之缺陷,通过系统性法律解释可适度补充,似乎倒不至于造成太大之适用问题,然如在立法之时刻意留心采取某些未雨绸缪之举措,既可铸就法典自身的精准体系,亦可收到避免事后不必要之理论困惑或错误解读之功效。
为此,笔者提出三项建议权作参考。其一,综合吸纳各国立法经验,乃是后进法治国家寻求法律现代化的共同进路。然而,每项规则甚至每个术语,皆有其存在和生长的特定制度环境。这就要求在描述、理解以及翻译诸国制度或规则之时,务求厘清其间所涉的关键概念或术语的特定内涵,切忌望文生义,在进一步将它们引入法律草案之时,力求确保术语或概念自身的精准性及其含义在整个文本中的融贯性。其二,不妨效法加拿大魁北克立法者的做法,在法典起草的最后阶段,由负责起草法典的机关设立一个法典审读委员会(Reading Committee),〔22〕参见徐国栋:《〈魁北克民法典〉的世界》,载徐国栋著译:《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编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成员可由法律语言专家、汉语语言专家、法学教授以及实务部门的法官、律师共同组成,专门对法典术语、行文进行技术性的润色处理。其三,在准备法典草案之前,不妨效法《德国民法典》或《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编纂者的做法,制作“法典词目索引”〔23〕[法]弗朗索瓦·惹尼:《现代民法典编纂的立法技术(民法典百年)》,钟继军译,徐国栋校,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或“以字母顺序排列的术语表”〔24〕See RenéDavid,A Civil Code for Ethiopia:Considera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s of the Civil Law in African Countries,Tulane Law Review,Vol.37,1962-1963,pp.196-197.以确保法典概念的精准性、统一性,尽量避免在整部法典中就同样的概念使用不同表述,或就不同概念使用相同表述。
三、民法典条文编排的技术问题
法典编纂并不能像理性主义者和概念法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够获得一劳永逸和毋庸置疑的绝对确定。编纂法典的意义只能是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确定,使人们拥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行为指引。一方面,法典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必要的立法技术处理和立法完善工作,如在法典中引入大量的一般性基本原则、及时对法典进行修改补充和加强立法解释等方式,来获得某种程度的缓解和弱化。但另一方面,法典具体条文不确定性的有效消除,法典从“书面之法”(law in book)上升为“行动之法”(law in action),法典真正得以确定性适用,还必须通过法官的斟酌判断、自由裁量和创造性的法律续造来实现。因为法典不可能绝对确定,所以,适时的法典修改也是必然的。法典的修改,无论是修正、增删还是调整条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法典的相对完美的逻辑化、体系化格局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无疑会波及人们依照旧有法典之规定而建立起来的某种确定和预期(如公民的法律认知、学术研究及法院判决等),进而可能给相对稳定的正常私法秩序带来或大或小的干扰。由此,如何在法典编纂过程中灵活安排法典条文以使适时的法典修改不至于影响正常私法秩序自然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现今绝大多数民法典的编排方式皆为“条文累加式”,也即从第一条一直逐一排列到最后一条。在自然法法典编纂时代,这种方式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以此表明法典乃为在逻辑秩序意义上的一部完整的作品。〔25〕See Pierre Legrand,Antiqui Juris Civilis Fabulas,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45,1995,pp.322-323.在对法典进行修订的情况下,为保证原有的条文体系布局不致因此被打乱,通常的做法是:当需要增加条文时,增加的条文被放在原条文后,但不另外增添法典总条文数,增加的条文仍按原条文的后续编码计;需要删除过时或无用条文时,则保留该条文的位置,相邻的条文不自动升位。例如在对1932年《墨西哥联邦民法典》进行修订时,需要补充有关房屋租赁合同的新规定,该国立法者就直接在第2448条(房屋租赁合同)之后,补充了第2448A条直到第2448K条的规定。在2001年对《德国民法典》债法部分进行修正时,在原法典第312条之后直接增补了第312a条到第312f条作为调整《远程销售法》的规定。
然而,伴随法典(法律)起草技术的日趋精细化,特别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条文编排方式:“单独编码式”,即法典(法律)条文并不统一编码,而是各编条文单独编码的编排方式。这种编码一般由两种码数组成,前一种码数一般依次由条文所处的编、题、章的号码构成,而后一种码数则就是条文所处的序数码,两者中间常常以点号“.”、冒号“:”或英文分节号“-”加以区隔。如Art.2:270IIBW即指《荷兰新民法典》第二编第270条第2款。这种做法的最大益处就是确保各编的相对自治,在形式上彰显整部法典的开放性。因为条文排列的无限弹性,各编如往后增加的条文将不至于影响其他各编既有的条次,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整部法典成为了一个“开放型”的文本,随时吸纳或变更其本身涵盖的条文内容。通过比较“条文累加式”与“单独编码式”两种不同的条文编排技术,不难看出,前一种虽然也能发挥“减震器”的作用——将因法典修改造成的波动减少到最小,但这种在原有条文基础上增补或保留无用条文的方法,将不可避免地使每个条文承载的信息量大小不等,这无疑将对法典整体的外在美观造成冲击;而后一种做法,则以其自身“开合自如”的机制从根本上了避免上述弊病的发生,同时也可有效维持法典外在相对完美的体系架构。因此,两者相较,各编条文单独编码的编排方式自然稍胜一筹。
这种方式,最初可能被用于1952年美国《统一商法典》以及“二战”后法国陆续颁行的诸多“行政性法典”(如《法国消费法典》、《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国不动产转让法典》等)等汇编类法律的条文编排中。〔26〕所谓“行政性法典”(administrative codification),大体是指“二战”后法国立法者为便于公民法律检索等因素考量,将调整某类法律关系的所有相关条文(包括立法、行政规章甚至条例)按照一定的逻辑性、系统性顺序加以编排而成就的所谓“法典”。因为汇编这类法律的目的就着眼于其实用性(它们往往被称为“功能性法典”)且其自身的增删修改相对频繁,采用此种方式,便于更新而不至于影响法律整体框架。这种编排技术正式在民法典中获得应用大概发端于1947年开始编纂的《荷兰新民法典》。〔27〕See Drion,Introduction to“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Book 6”,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el.17,1970,pp.231-232.在1947年接受受托起草该法典时,梅耶斯考虑到通过整部民法典将异常困难,而只能分编起草、逐次通过。在此种情况下,针对草案内容而引发的反复协商与频繁修改将不可避免。由此,一者为使增加或删除条文更为容易而不至于对所有条文重新排序,二者为使对有待理顺和整合的草案的具体条文之定位更为明确,在其主持起草的草案中,在稍作修改的基础上,梅耶斯采用了这种条文编排方式。例如,在《荷兰新民法典》草案中,第6.1.9.7条是指第六编第一题第九章第7条。然而,这种编排方式仅在草案中使用,在草案成为法律之后,鉴于每编连续排序,上述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而转采一种简洁的排序方式(省略到其间的题号和章号)似乎更为经济,以至于草案中第6.1.9.7条在生效的法典中直接被标记为第6:7条便能足尽其功。〔28〕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教授Jan Smits指出,荷兰立法者分别在法典草案和法典中采用了形式上不同的条文排序方法,由此纠正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既有误解,谨此特表谢忱。就这样,1992年问世的《荷兰新民法典》(主体部分)在民法法典编纂史上率先采用了此种条文编排技术,并在事后为2000年《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29〕《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英文版,可参见该国司法部官方网站,资料来源:http://www3.lrs.lt/pls/inter3/dokpaieska.showdoc_l?p_id=245495,访问日期为2010年10月15日。关于2000年《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的详尽介绍,参见 Valentinas Mikelenas,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New Lithuanian Contract Law System Based on the Civil Code of 2000,Juridica International,Vel.5,2005,pp.42-50。2001年《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民法典》、2002年《荷属阿鲁巴民法典》、〔30〕[荷]扬·斯密茨:《法律模式的进口与出口:荷兰的经验》,魏磊杰译,载吴汉东、陈小君主编:《私法研究》(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007《柬埔寨王国民法典》〔31〕《柬埔寨王国民法典草案》(2002年)英文版,可参见柬埔寨王国商务部官方网站,资料来源:http://www.moc.gov.kh/,访问日期为2010年10月20日;《柬埔寨王国民法典草案》(2003年)日文版,可参见ICD NEWS(法務省法務総合研究所国際協力部報)第11号(2003)。该法典草案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协作起草,共分总则、人、物权、债、各种合同和侵权行为、债务担保、亲属、继承以及最终条项等编。以该草案为基础的《柬埔寨王国民法典》于2007年生效。以及2009年《日本民法(债权法)修改草案》所继受。〔32〕由渠涛等学者共同翻译的2009年《日本民法(债权法)修改草案》的全文,参见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9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595页。同时,2003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法典〉基准法》第5条明文规定,正在编纂的《加泰罗尼亚民法典》也将大体采用这种开放型的条文编排方式。〔33〕参见[西班牙]埃斯特·阿罗伊奥·伊·阿麦耶拉斯:《西班牙民事法律之多元化——西班牙国内解法典化与加泰罗尼亚地区法典化之争》,叶微娜、张礼洪译,载张礼洪、高富平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由Ole Lando与Hugh Beale组织起草的《欧洲合同法通则》、由“欧洲侵权法小组”组织起草的《欧洲侵权法通则》、由David J.Hayton与S.C.J.J.Kortmann主持起草的《欧洲信托法通则》以及由William W.McBryde、Axel Flessner和S.C.J.J.Kortmann共同起草的《欧洲破产法通则》等意在为欧洲私法一体化提供范本的软法类法律,〔34〕See Ole Lando& Hugh Beale(eds),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The Hague,Kluwer,2000;European Grope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Texts and Commentary,Springer,2005;D.J.Hayton et al(eds),Principles of European Trust Law,Deventer,Kluwer,1999;William W.McBryde etal(eds),Principlesof European Insolvency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5.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起草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由冯·巴尔领衔的“欧洲民法典研究组”起草的堪作未来“欧洲民法典”编纂蓝本的《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CFR)等皆采此种条文编排模式。〔35〕See 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Full Edition),Edited by Study Group on a European Civil Code/Research Group on EC Private Law(Acquis Group),Sellier 2009.
从《大清民律草案》直至今天,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几乎所有的法律条文之编排大体都是采用传统的“条文累加式”的编排方式。更为糟糕的是,在解放后的民事立法过程中,或许是继受苏联法律传统的既有做法,在删去或修改某一或某些条文之时,我国并未像大陆法系传统做法那样保持原有条文架构或位置不变,而是将后续条文径直抬升占据原条文的位置,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近乎崭新的条文排列秩序,进而影响甚至干扰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律秩序既有的认知与预期。例如我国1980年《婚姻法》原有条文共计37条,但在2001年修改后,条文扩充到了51条,原有的条文排列秩序完全被颠覆,这种近乎彻底革新的变更不仅增加了法律工作者的学习成本,而且也会大大冲击着已然形成的内在法律秩序。有鉴于此,在未来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采用上述全新的条文编排方式实有必要。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变革速度很快,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法学可能都将处于注释法学和实证法学的发展阶段。由此,在这双重语境下,似乎更需要这种技术,既能因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灵活修改、调整或增删法律条文,同时又能以此确保法律人以及普通民众对法律文本所持之法律认知和法律预期的相对稳定。
当然,提出一种全新的编排方式无疑会给历史铸就的传统立法观念造成冲击进而可能使得这种制度变迁成本大幅升高。但是笔者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既然要制定领先于21世纪域外诸国的不朽民法典,那么就要敢于突破前人、敢于充分借鉴域外先进做法,就要勇于改革,既然要改革,那么必要的转化成本应不可避免。同时,较之新做法可能促发之实益,或许成就这种技术层面的制度变迁所付出的成本可能是微乎其微。有必要提到的是,此种条文编排方式已为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所采用,这就为我国民法典条文编排模式之选择做出了甚为有益的大胆尝试。
四、民法典条文题目设置的技术问题
一般而言,民法典的内部结构建立在某种位阶排列的分类和亚分类基础之上,也即大体可被分为编(book)、题(title)、章(chapter)、节(section)、条(article)、款(paragraph)等逐次递进的系统层次。18世纪以降,自然法法典以来的几乎所有民法典皆具有一个标题,各编、题、章以及节也皆有其本身的标题。然而,节以下的分类单位条是否具有标题(也即所谓的“条名”)则有不同做法,大体可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初始缺乏型”,也即法典从颁布之日起一直都没有条名的设置。以法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拉丁法系国家皆是如此。例如1804年《比利时民法典》、1838年《荷兰民法典》、1864年《罗马尼亚民法典》、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1867年《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1949年《埃及民法典》、1950年《菲律宾民法典》、1971年《阿尔及利亚民法典》、1992年《荷兰新民法典》、1994年《魁北克民法典》以及以1857年《智利民法典》、1869年《阿根廷民法典》、2003年《巴西新民法典》为代表的几乎所有中南美洲的民法典。
第二种可称为“事后补充型”,即民法典最初也没有条名设置,但随着时代演进,专门出版“六法全书”的出版商(如德国的Beck出版公司、日本的有斐阁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三民书局等),为便利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的检索和阅读,在编辑法典条文之前,往往依条文的具体内容而配以适当标题,同时特意将这些“标题”置于小括号或中括号中以标明它们乃是外人添加,并非法典的构成部分。伴随这种做法渐趋普及并为阅读者所普遍接受,一些国家的立法者开始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实际价值,遂在修订或重构法典的过程中将这种民间技术融入其中,从而使得条名开始出现在官方法律文本中或径直被认可为法律文本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主要出现在日耳曼法系国家以及深受德国法学影响的国家。例如,在1949年之前,《日本民法典》并没有官方认同的条名,大约在此之后,日本立法者开始进行如下区分设置:被置于小括号中的条名乃是法典的组成部分;而被置于中括号中的条名则是法律编辑者添加,本身并非法典组成部分。〔36〕「昭和24年以降の法令(及ぶ昭和22年、同23年の法令の一部)には条文見出しがついているので、()を用いて条文の右肩にそのままを表示した。もっと古い法令で見出しが付いていないものについては、編集委員が見出しを付し、[]に入れて条文番号の下の収めた。」参见青山善充、菅野和夫:《判例六法》,有斐閣2009年版,凡例7頁。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在2001年之前的德国,与这一阵营中的其他多数国家一样,《德国民法典》的条名皆被置于中括号之中,意为并非法典的组成部分;在2001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改革中,意在谋求对不同编辑者添加的条名加以统一和规范之考量,德国立法者遂将中括号去掉,使得每一个法律条文皆被冠以官方的(amtlich)标题,从而使得它们正式成为德国民法典文本的组成部分。〔37〕参见[德]米夏埃尔·马丁内克:《200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几点批评性的评述》,许兰译,载米健主编:《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而其他国家的做法,大体介于这两者之间,多数仍将条名置于小括号或中括号中,不承认它是法典的组成部分,例如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1958年《韩国民法典》、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1984年《秘鲁民法典》等,皆是如此。
第三种为“初始拥有型”,指立法者原本就为法典设有条名,条名从法典生效之时即为法典的组成部分。这一“阵营”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直接标注型”与“系统排列型”。前者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以数字为顺序的编排方式,每个条文对应一个条名。这种做法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前苏联国家新近编纂的民法典所采。其实,不难看出,如果不考虑条名是否作为法典的组成部分,似乎绝大多数日耳曼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皆属此类。而所谓的“系统编排型”是指按照标题提示的内容重新对以数字为序的法条进行了体系编排,从而使得整个外在安排更显体系性与逻辑性。虽然这种做法表面上与前者似乎差别不大,但技术考量上却明显更胜一筹。根据笔者对80多部民法典的综合考察,迄今为止,正式采用这种新颖方式的民法典仅仅只有两部,即1907年由著名法律史学家欧根·胡贝尔主持编纂的《瑞士民法典》以及1960年由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主持编纂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与多数民法典一样,1960年《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的每个条文皆有条名,但差别在于在该法典中调整多数同一主题的条文除了共享条名之外,各自还附有更为具体提示条文内容的次级条名。例如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第30条皆调整“自然人的肖像”这一主题,由此共享同一个条名,但这些条文本身还分别附有次级条名,依次为“原则”、“例外”、“制裁”、“家庭成员的权利”。1907年《瑞士民法典》则更为特殊,因为该法典拥有学界称之为“边题”的设置方式:立法者独辟蹊径地在每页文本左边都设有这样的标题(条名)用以揭示某条或某数条的内容。在实质意义上,它的功能与《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的做法相同,只不过这部法典将统辖数个条文的主条名和条文各自的次级条名置于文本的左边,意在与条文内容区隔开来,而且也将这种做法贯彻得更为彻底(遍及每一个条文),从而显得整个法典文本更具条理性,也更为赏心悦目。
那么,设置条名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笔者认为,首先,其最基本的作用在于提示法条主旨内容,同时与编、章、节的标题功能大体类似,条名便利于立法者的整体规划,并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于对篇幅不等的不同条文的整体布局,特别是在依同一条名提示数个条文的情形下,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区隔和辨别的效用,从而显得整个文本布局更为清晰、更为明确。其次,条名的意义还在于为法律解释提供便利。法典颁布后需要对其进行可能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大量的学理解释。对某个法律条文的解释包括解释该条文的文意以及解释其与其他条文的相互关系,而从该条名入手进行整体性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毕竟条名的设置与条文主旨、条文间的内在关系密切相连。最后,不可否认,条名的存在对于司法者找法、法律的讲授与学习、法律的宣传与传播等活动也具有减少熟悉成本、学习成本之功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于1956年、1964年和1982年三次起草民法典,出台的草案皆未采用条名设置。1980年《婚姻法》、1985年《继承法》、1986年《民法通则》、1995年《担保法》、1999年《合同法》、2007年《物权法》和2010年《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重要民事单行法也未采用条名设置。
笔者认为这大体是历史传统的影响使然。清末《大清民律草案》(“一草”)、1925年《中华民国民律草案》(“二草”)以及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皆未设置条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深受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传统的影响。根据学者整理出来的文献披露,建国之后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主要的参考蓝本大体是:1922年《苏俄民法典》、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民法典》、1950年《保加利亚债与合同法典》、1951年《保加利亚财产法》等。〔38〕一般来说,立法者在编纂民法典时,几乎很少在草案上标注借鉴的法律规定的来源。但在何勤华、李秀清、陈颐三位教授整理出版的两份1956年民法典草案起草的草稿中,起草人列举了所拟条文的来源,由此得以让笔者归结出上述论断。参见何勤华等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4页、第232-242页。而所有这些民法典或民事单行法皆没有条名的立法设置。〔39〕参见《苏俄民法典》,郑华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民法典》,郑民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保加利亚债与合同法典》与《保加利亚财产法》的英译本,皆可参见保加利亚法律发展研究所的官方网站,资料来源:http://archive.bild.net/legislation/,访问日期为2010年10月20日。或许是由于路径依赖,这种“传统”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在统一合同法起草时,学者就曾注意到条名的重要意义并进行了初步尝试,但立法部门最终并未采纳学者的意见。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以及徐国栋教授分别主持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包含的条文均有条名。而且,不难看出,民法学者对法律条文设置条名基本上形成了共识,甚至对一些条名的具体名称也做出了大同小异的规定。然而,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除了贯彻汇编民法典的指导思想之外,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沿袭过去的传统,各条文不设条名。考虑到此种“制度变迁”之完成几乎不会耗费什么成本但却无法实现,这不能不说明立法主导者总体所持的比较保守的立法态度。当然,这种严重的“路径依赖综合症”可能仅是计划经济时代陈旧立法思维的遗留,伴随立法主导者观念的更新以及知名学者在立法过程中话语权比重的日趋提升,相信在不久之将来,这个似乎并非问题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可能,借助此种机遇,更新观念,放弃传统的“直接标注型”而改采更为先进的“系统排列型”条名设置方式,则有望大大推动未来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精细程度。
五、余论
法典编纂成就的最经典的作品或许就是民法典。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再到《德国民法典》,以至于晚近以来的《意大利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荷兰新民法典》以及《巴西新民法典》,每一个法典似乎都比前一个法典更精细,更加专业化,理性化、抽象化程度也更高。专业化和精细化无疑是法典编纂的总体发展趋势。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同时基于特定国情、民情和政情之考量,我国民法典编纂,在具体制度选择和规范导向方面,虽然为避免消化不良或水土不服,而可能不会或不能引入过于前卫的实体规范,但采用某些技术层面上的先进做法,却不失为一种较为经济同时亦无需通盘考虑过多配套设置的明智选择。
上述论述皆是从理想法典编纂需达到的“应然”程度来阐发的,至于“实然”的制度语境似乎并未进行太多系统考量。然而,普适的“应然”状态转变为“实然”的具体践行往往取决于特定的制度运作环境。具体而言,诸多法制先进国家的立法决策模式大体为“专家主导型”,也即法律专家直接参与立法决策或他们的意见能对立法进程产生实质影响。以此,他们有理由期待将先进的做法或规范融入草案并最终贯彻到生效的法律之中。而我国当前立法制度仍远未达致如此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学者们的“宏大理想”往往不能不寄望于或借助于甚至受制于立法决策者这一“中介渠道”来实现。鉴于上述四点技术层面的改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或多或少已为国内主流学者所关注并积极倡导,或许现在所需解决的瓶颈问题已不再是没有太多实益的反复理论论证,而是尽可能地赋予和增强学者更多的立法参与权与话语主导权,以此将真正业已获得普遍认可的优良技术和做法融入立法之中,而非仅仅停留在纸上或口中。当然,最为乐观的期待是,在学者的游说、推助甚至直接参与下,立法机关能效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同仁们的做法,〔40〕2002年,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了《加泰罗尼亚民法典基准法》,该法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确立正在进行的加泰罗尼亚民法典的结构、基本内容以及编纂程序。该法共计7个条文,依次为编纂目的、法典结构、编章划分、内部结构分配、条文编号、编纂程序以及第一编的通过等。根据该法规划,《加泰罗尼亚民法典》分为六编:第一编一般规定(包括预备规定、时效与期间)、第二编自然人法与家庭法、第三编团体人法、第四编继承法、第五编物权法、第六编债法。资料来源:www20.gencat.cat/docs/Justicia/Documents/Lleis/doc_30924256_1.pdf,访问日期为2010 年10 月25 日。在系统编纂民法典之前,也能颁行一部名为《民法典基准法》之类的法律,将未来法典结构、基本内容、起草程序以及本文所涉的法典用语、条文编排以及条名设置等议题统统加以明确规定,以期在实质意义上确保和提升未来我国民法典编纂的速度与质量。
(责任编辑:李秀清)
*魏磊杰,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