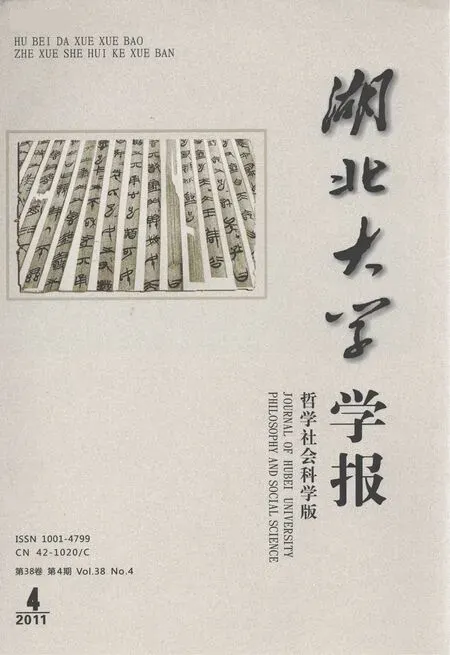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
范小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国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3)
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
范小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国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3)
陈独秀等人1925年底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国民党人孙科等在上海进行了一次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这次谈判多年来被认为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大让步。实际上上海谈判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大让步,而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谈判有它的必要性,从谈判的内容上看,并无什么大的让步,有些方面还有对过去既定目标的前进;其次,上海谈判中的某些消极方面,显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处理国共关系中陈独秀既作过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也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再次,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和政策来看,孙科等人应属国民党中派,陈独秀在上海谈判中争取他们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以团结中派,也就不是什么让步问题了;最后,从谈判的结果来看,通过上海谈判,团结了大多数,维护了国共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来了大革命运动浪潮的蓬勃兴起。
陈独秀;上海谈判;共产国际;让步问题
1925年12月,陈独秀在上海与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国民党人孙科等进行谈判,并将他们请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作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大让步,是陈独秀对国民党三次大让步中的第一次大让步,是政治大让步。
比较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蔡和森,他在1931年写的《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认为:陈独秀“改变只要左派国民党的方针(坚决打击右派,削弱中派和强大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左派)号召与国民党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领回广东,这是三月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1]811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作的报告明确提出,陈独秀上海谈判是对国民党政治上的大让步。此后,让步这一说法成为定论。
本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事实与理论的阐述,旨在辨析,陈独秀赴上海谈判,是否是他个人所为,而应由他负个人责任?所谓的让步是否都是消极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一、历史背景与上海谈判的主要内容
客观地说,陈独秀等与国民党人的上海谈判,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谈判的内容来看,谈不上是消极的让步。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内新老右派遥相呼应,兴风作浪,力图把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治舞台上排挤下去。1925年4月至7月,国民党新右派代表人物戴季陶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演讲、文章和小册子,形成“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鼓吹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充分发挥国民党的“支配性”,排斥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鼓吹团体的“排拒性”,反对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新右派反共的理论纲领。
与戴季陶主义遥相呼应,邹鲁、谢持等国民党老右派,打出“反共清党”的旗号,主张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掌握于国民党之手,这些老右派于1925年11月在北京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议案,结成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小集团。这样,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危险。
对于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5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揭露他们分裂的行径[2]452。同时,中共中央利用各种机会,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接触和谈判,以促进国共两党的继续团结。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与帮助,国民党中央于11月27日发出谴责西山会议派的“感电”,并决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国共间出现的矛盾。这一决定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但西山会议派却悍然决定在上海或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二大”,以与广州即将召开的“二大”分庭抗礼。一时,国民党内妥协气氛占了上风,一些中间派也徘徊于“广州会议”与“上海会议”之间。
很显然,要顺利地召开国民党“二大”,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就必须争取中间派,即使是对国民党的新老右派,也应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这在当时情况下是需要的。
当时的形势一方面对共产党十分有利。首先,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共产党的规模与影响日益扩大。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继发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使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农民运动也有了恢复和发展,广东农会组织扩散到20多个县,会员达20多万人,并逐步向湖南、江西等地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2000多人,而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3]112~113。其次,国共两党合作不断加强。自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并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南征邓本殷等战争,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民党在各省的地方党部,两党联合在南方发动省港大罢工,在北方组织大规模的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共两党并肩作战,合作关系进一步密切。
但必须看到,形势对共产党也有不利的一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规模和影响虽有相当扩大,但与近10万党员的国民党相比,实在只是个小党,与当时的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党不相上下。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共产党影响虽大,党的组织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党内涌出了很多活动分子,但是来不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4]578其次,工农运动虽然兴起,还只是局限在部分地区;再次,国共合作仅只一年多时间,其宗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最后,国共关系虽较前密切,但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进一步分化,一些右派人物公开反对国共合作,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使统一战线内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可能壮大自己,消灭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策略。列宁曾经非常明确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5]225
毛泽东是制定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最好典范,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必须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反帝反封建大军,无产阶级在与合作者建立同盟时,应该使合作者得到好处,甚至可以做出积极的让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向国民党作了让步,如改编红军,改制边区,取消暴动政策等。抗战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不仅争取国民党左派,也做国民党中派的工作,甚至国民党右派人物如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毛泽东都亲自登门拜访,争取他们支持国共继续合作,共建新中国。这些,都是正确的,都被认为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最好范例。然而,当我们面对陈独秀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呢?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创建初期,为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陈独秀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批判戴季陶的反动理论的前提下,去上海与动摇于广州和上海的孙科等人谈判,争取他们回广州开会,为什么竟成了政治上的大让步呢?
上海谈判的过程比较简单,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也不多,据张国焘的回忆,1925年12月,中共代表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与国民党人孙科、叶楚伦、邵元冲等人在上海外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就国民党“二大”及国共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谈判中,陈独秀表明:“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从来都反对这种企图。”他还澄清了一些谣言,说:“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负责。”[6]66
陈独秀温和的发言,多少消除了孙科等人的一些疑虑,于是他们相继作了简短的声明,主旨是说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并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回广东参加大会。
双方通过反复交涉,在国共关系一些问题上,逐步形成一致意见,最后达成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上海一些领导人回广州时召开;两党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解决等[6]6。
纵观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一般来说,是看不出什么政治让步的,大多论者抓住的是第三条,即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认为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权。而事实是,早在1925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二大”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人数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就坚持不能超过“一大”人数,即只能有3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执委,陈独秀力争,才达到了4名。而上海谈判提出的三分之一,显然大大超过了5月会议确定的4名,这不是对国民党的让步,而是对自己既定目标的前进。
二、共产国际对上海谈判的影响
陈独秀与国民党人的上海谈判并非完全没有消极的东西,但消极的东西显然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总体思想是要求维护国共合作的,而这一总体思想又与斯大林的战略思想不无关系。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庆祝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庆四周年大会上,作了《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报告,他说:“在埃及和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而执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个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象国民党这样的工农党的形式。”[7]124
斯大林要求维护国共合作固然有加强控制影响国民党的一面,同时,也基于中国革命两个基本特点,即:首先,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其次,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农民以至整个革命。因此,中共必须同国民党合作[8]374~379。正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1925年,《共产国际》杂志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之前的东方革命问题》的社论,指出:“在长期的政治交往中,共产党应该通过经常性的影响把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同盟者引到民族自决道路上来。”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及其领导机关,必须在各个方面支持国民党的行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在中国指导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都主张中共对国民党实行让步,以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鲍罗廷要求中共在发展时,“不要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9]613~615维经斯基则要求:“当我们对中派进行批评和论战时,应当考虑到合作”[2]488。不久,维经期基又提出对右派也不要过于激烈,他说:对国民党右派“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10]101。
成立时间不长,尤其是刚刚与国民党合作,便面临如此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理解和执行上是矛盾的。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认为对国民党让步过多,将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便提出:“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控制。”[11]对陈独秀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主张,共产国际坚决反对,认为退出国民党是极大的错误,陈独秀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意见,但他仍坚持在国民党内要与右派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陈独秀写了一些文章,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右派言论,认为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不能停止阶级斗争,他在给戴季陶的信中明确写道:“在民族斗争中实有阶级斗争之必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年9月11日),《向导》周报,第129、130期。)陈独秀一方面亲自写文章批评右派言论,另一方面,他主持的中共中央也一再做出决议发出通知,要求反对向国民党投降的右倾错误,指出:“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并提醒全党:“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12]77~78
然而陈独秀的主张不断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和批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陈作为中共领袖,必须考虑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陈独秀还考虑到实行激烈政策是否会有不良后果,于是他开始放弃自己的主张。后来,陈独秀回忆说:“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11]这时,陈独秀的内心是矛盾的,他的尴尬并不是个人尴尬,反映出当时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过多干预下的整体尴尬。
由于中共中央服从共产国际留在国民党内的意见,便开始寻求新的策略,即“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而“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化右派这些措施的”[6]60。此后,陈独秀的激烈态度开始缓和下来,并逐步向共产国际的政策靠拢。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做出决议,认为:“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应当继续合作的政策,竭力推行这一党进行革命运动。……假设认为这种现象(指戴季陶主义的出现——笔者)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3册,第183页。)
中国共产党勉力使自己与共产国际政策趋于一致,而现实斗争又不断向中共提出挑战,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行为再次敲响了警钟,亦引起陈独秀的高度重视,他主持的中共中央一再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对国民党中的反共派进行坚决斗争。
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66号通知,指出:“此时,国民党新右派已和从前的右派相等了,他们在北京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共派,实际上是要推翻广州的国民政府。”[2]451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知指出:“民校的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谢持、居正、覃政[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在北京西山开会,其所决议之开除共派中央(委)及候补委员党籍及惩戒汪精卫二案,最为荒谬,望各地民校党部一致发电痛驳。”[2]452
中国共产党的激烈态度当时不会为共产国际所容,他们不同意采取整个打击西山会议派的政策,陈独秀不得不再次服从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正如德国学者郭恒玉在其著作中所说的那样:“西山会议造成了可能导致广州彻底分裂甚致崩溃的严重局势。中共在上海的领导又重新和维经斯基商谈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维经斯基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中共党接着决定,通过策略上的妥协政策争取一部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中间派,以孤立右派。”[13]148这一政策即打击右派,团结中派,扩大左派,为了扩大左派,团结中派,共产党要作某些让步。
既然要和国民党合作,就要团结国民党人中的大多数,特别是那些思想上还处于犹豫徘徊的国民党人,要对他们做争取工作,这就是陈独秀到上海与孙科等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到上海谈判确非他个人的行为,而是执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总体策略。这一点,在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就说的十分清楚了,该文件说:“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做出让步。……这就是在最近国民党中央举行改选取时,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与右派领袖进行了谈判。”[14]153陈独秀自己也说:“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15]136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对鲍罗廷说过:“如果说中国党是犯了机会主义,那末根本这机会主义就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教我们的,国际教我们加入国民党教我们帮蒋介石。”[1]817
虽然在共产国际说了算的处境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组织纪律上讲,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执行其在中国代表的命令。但是,陈独秀并没完全放弃自己的意见,在他起草的一些有关国共关系问题决议案中仍然强调坚持斗争,如四届一中全会决议案就认为:“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2]489就在上海谈判前后的一段时间,陈独秀仍在发表一系列激烈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政论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右派的言论。如1925年10月30日发表于《向导》的《戴季陶之道不孤矣》、11月发表于《向导》的《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12月3日发表于《向导》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12月20日发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等,这就说明,陈独秀到上海与孙科等人谈判,并非自己真心所愿,谈判中一些有消极倾向的条款,也并非陈独秀一人主张。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及政策
要说明陈独秀在上海谈判中是否向国民党右派投降的问题,必须弄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各派的政治状况及中国共产党对各派的认识与政策。
比较早提出国民党内存在派别的是共产国际,周恩来曾经回忆说:“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看作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3]165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刚刚合作时,认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从维护两党合作目的出发,所采取的政策也是十分宽松的。1924年2月底颁布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指出:“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面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统认为他们是所谓‘右派’,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这样,必致惹起他们的反感,促成他们的实际联合。这将不但使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些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力量,而使国民党不能免左右之分歧。我们应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躯(驱)左为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团刊》第7期。)
到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共才接受了共产国际左、中、右三派的判断,大会认为国民党已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并确定了“扩大左派,反对右派,批判中派之游移态度”的方针,后又改为“扩大左派,分化右派,联络中派”的方针。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分析了国民党内实际情况后,又回到过去的认识上,认为:“以前在我们的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分析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把国民党的领袖都列到中派,这不但在理论上不正确,而且在策略上也不适当。……并且在事实上从前的右派已公然反动。已公然离开国民党了。从前的所谓中派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2]417~418。毛泽东当时也指出:“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毛泽东:《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主置》,《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这说明中间派不可能长期存在,通过做工作,就可以在反帝反封建大旗下,存大同弃小异,最大限度团结中间派,使他们向左跑入革命派。
事实上,国民党内一些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在当时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确实在发生变化,一个时期是中派,一个时期会变为左派或者右派。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这就不能固定哪一个人物就是哪一派的代表。
国共合作初期,中国共产党只是将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视为顽固派即右派,如冯自由,谢持,邓泽如等,而将不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视为左派,陈独秀当时就这样说:“胡汉民,谢持,汪精卫,张继这4人几乎可以代表国民党全体,除谢持一个外,其余3人都不能说是右派,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的。”[16]333
后来,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五卅运动发生后,国民党内的分化也日趋明显,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领导人的看法也发生变化,将原来支持国民党改组的一批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中间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张继,邹鲁,戴季陶,徐苏中,邵元冲等……”,一类是孙中山的亲信干部,“他们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矛盾,后来发展的方向各不同,但在当时他们对国民党的改组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表示拥护的。这一类人物主要是: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蒋介石等”[17]597。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将戴季陶,张继,邵元冲等是列为中派而不是右派。一直到陈独秀上海谈判后的1926年,中共中央仍是如此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随处可以看到。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在谈到戴季陶,蒋介石时,虽然用了“新右派”的概念,但仍认为新右派即中派,而且认为他们代表的是第四种社会势力即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一派别“在客观上是有倾向革命之可能的”[18]115,116。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谈到叶楚伧时,认为他是中派,说:“国民党中央党部自我们同志退出后,大权握于中派张静江,叶楚伧之手,除与我们为难外,并无其他工作……”[18]244,谈到孙科时,甚至认为他是左派,说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的文章传到广东后,“李济深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18]247。
从以上罗列的材料可以看出,孙科等人当时确实不能算在右派之列,他们政治上变化,向右转是在以后发生的,叶楚伧、邵元冲是在“3.20”、“4.12”后发生变化的,而孙科则是在1927年6月郑州会议后变化的。既然孙科等人当时不是右派,那么中共的政策也不能打击、斗争,而是团结、争取。这一点,周恩来当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对左、中、右三派的政策,应该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与右派斗争;对中间派必须打破他们的妥协心理,要求他们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孙中山的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对右派必须实行孤立和打击的政策。”(周恩来:《孙中山北上后之广州》,《向导》第2辑,第92期。)要打破中间派的妥协心理,要中间派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就必须团结他们,必须做他们的工作。那么陈独秀到上海与孙科等人谈判,争取这些中间派回广州开国民党“二大”,就是为了打破他们的妥协心理,要他们与革命派联成一气所做的工作,也就不是什么向国民党右派让步的问题了。
四、谈判的后果分析
陈独秀与孙科等国民党人的上海谈判,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陈独秀在政治上的软弱,但从谈判的后果来看,消极作用不是主要的,总的说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促成了国民党“二大”的召开。上海谈判前,由于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二大”筹备工作不能很好展开。当时,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汪精卫优柔寡断,害怕中间分子都倒向西山会议派一边,“二大”不能代表多数,因此不想开会了。据吴玉章回忆,1925年12月,当吴率参加会议的四川代表团到达广州,去拜访汪时,汪精卫愁眉苦脸地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吴玉章问为什么,汪说:“邹鲁、谢持等人闹得很厉害,如果我们召开‘二大’,形态将会更严重。”[19]131不仅汪精卫忧心忡忡,在广州的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有类似的担心,这种情况使得“二大”的召开遇到了危机,而如果“二大”不能召开,则国民党内分裂加剧,国共合作也将面临分裂的危险。“二大”能否召开,关键是争取孙科等徘徊于“广州会议”与“上海会议”之间的中间派,这样,使“广州会议”能占绝对多数。本来孙科、邵元冲等人跑到上海,只是想对广东方面造成一些威胁,以抬高他们的身价。现在陈独秀主动到上海找他们谈判,邀请他们回粤开会,孙科等人正好借梯下台,表示在所达到7点协议的前提下,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并表示要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上海谈判后,中共中央认真履行协议,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基层党员报告,为了将协议精神贯彻到国民党“二大”上去,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去广州出席“二大”,并担任中共党团书记。这样,终于使国民党“二大”于1926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召开。
其次,上海谈判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积极意义是主要的。会议对分裂行为的国民党右派作了严厉处置,不仅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将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邹鲁、谢持开除党,即使是对回粤参加会议的叶楚伧、邵元冲等人,也提出了警告,对戴季陶,也“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另外,会议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虽没有大量增加,但还是有所进步,如中央执行委员36人中,共产党员7人,约占五分之一,而国民党“一大”时,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5有中,共产党员只占3人,仅占八分之一弱。总之,国民党“二大”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坚持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坚持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些成功又是与陈独秀等人的上海谈判密不可分的。
再次,陈独秀等人的上海谈判,在一定程度孤立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争取了多数,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当时,邹鲁等西山会议派分子就对孙科等人回广州开会十分恼火,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6]67。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扩大左派,分化右派,联络中派的策略方针总的说来还是正确的,不扩大左派,就无法联络中派,也就不能同右派作有力的斗争以至分化他们;如果不联络中派,也就不能壮大左派的声威,也就不能更好地孤立右派,分化右派,维护国共合作。张国焘后来总结说:“从上海谈判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多数国民党人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包办等等论调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的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阻滞了”[6]67。这段话多少反映了当时一些国民党人消除对共产党人误解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毛泽东后来与斯诺谈话时也说:“在国共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20]45至少,毛泽东认为陈独秀的上海谈判使国共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43年春天,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中对陈独秀上海谈判持否定态度,他说:“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完全让步的政策。……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3]119如何看待周恩来的这一论述呢?我们认为,周恩来的谈话发表于1943年春天,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由于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由于共产国际将面临解散,这都使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党内报告中,总结过去的历史,要求我们党与国民党斗争中不能采取让步政策,吸取陈独秀上海谈判中让步的教训,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这主要是从政治斗争出发,而不是从学术研究出发,因此,二者不能等同起来。同时,我们评价历史事件,应放在当时历史中考察,而不是放在后来的现实中发挥,否则就会失去真实性,因为当时历史要求人们所做的与后来现实要求人们所做的,总是会发生极大不同,人们的观点、办法也会有很大差异。如蔡和森,后来批评陈独秀,但在当年,他也是尽量维护国共合作的,在陈独秀上海谈判刚刚结束,他在工人大会上就指出:“工人阶级很明白自己历史的使命。……决不因国民党中那位先生破坏国民革命的说话,而减少他对国民党之同情与帮助。工人阶级态度是很鲜明的,只要国民党是革命的,他必须同情到底和帮助到底。”(蔡和森:《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答词》(1926年1月3日),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99、200期。)
当我们以冷静的态度来看待陈独秀1925年底在上海同国民党人谈判这一历史事实,认真地分析当年的历史背景,“分析它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21]112,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所谓上海谈判中陈独秀的右倾让步并非是陈独秀一人所为,而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旨意,执行中共中央的总体战略进行的。上海谈判本身也并非全是消极的,而是有着许多积极意义,通过谈判,团结了大多数,维护了国共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迎来了大革命运动浪潮的蓬勃兴起。
[1]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M].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7]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8]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0]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J].近代史研究,1999,(2).
[1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郭恒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M].李逵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4]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15]陈独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M]//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17]包慧僧.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M]//“二大”和“三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9]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20]斯诺.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D23
A
1001-4799(2011)04-0007-07
2010-06-26
范小方(1950-),男,湖北天门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国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