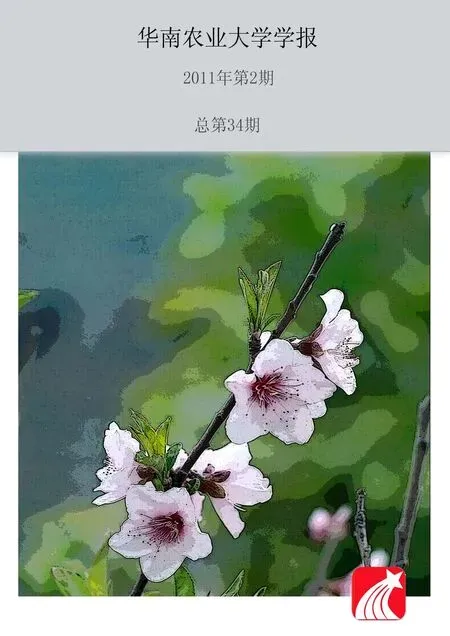集权、分权与治理:行政派出组织的缘起、特点与影响
董 娟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行政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
国家行政体制从其一开始,就包含着行政集权的萌芽[1]62。这一点,在中国国家行政体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从秦始皇统一开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统治便成为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特点。通过层层设置严密的国家机器,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控制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力图实现的目标。然而,政府权力在不同维度的配置势必会引起权力的分散,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央集权。因此,如何既不影响政府权力的分散配置又能实现中央集权统治一直是我国国家治理者力图实现的目标之一。行政派出组织作为政府管理的有效组织形式,通过在外设置行政派出机构、行政派出机关、行政派出人员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延伸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管辖与治理,从而有助于强化中央权力的集中、控制,一定意义上与中国国家治理者强化中央集权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成为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行政派出组织的源起
行政派出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汉时期。从秦代的监到汉武帝时期的十三州刺史部、魏晋隋唐时期的行台再到唐贞观时期的道、宋代的路、金元时期的行尚书省、元中统四年的行枢密院、行御史台、明代的都察院乃至清代的道等等,数目繁多,不胜枚举。仅任何一个朝代就可以罗列出许多该时期政府的派出机关或是派遣使。可见,通过行政派出的方式进行国家控制从秦汉时期起便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模式。总体而言,行政派出组织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
一般而言,“在行政集权体制下,不是由立法机构,而是由被委以最重要的行政功能的机关,即主要执行机构来行使中央对地方政治共同体的控制。”[1]30派出组织便是为了实现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控制而设置的行政机构。具体来讲,中国作为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从秦始皇统一开始,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一直是各朝代统治者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通过设置派出组织、人员的方式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便成为中国政府行政派出的首要目的。首先,通过设置派出组织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诸如秦汉时期的“监”便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派出的监察机构。而汉代的“十三州刺史部”作为中央派出监察地方的监察机构则是为了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此外,为了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控制而设置的派出组织还包括汉代的司隶校尉,唐代贞观元年的“道”,宋代的“路”等等。其次,通过派出负责专项事务的派遣官吏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力监控。诸如西汉时期每郡对其辖县分二、三、四或五部,每部设一督邮分部进行督察。督察对象主要是所属县的长吏[2],可见,“督邮”作为郡一级派出负责监察县级官员的官吏,主要职责在于对属县的长吏进行督察并报告郡府。最后,通过临时派遣官吏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管,诸如明清时期的巡按御史等等。
(二)强化特定区域的治理
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加强权力与控制,在不增加行政层级的同时通过行政派出,可以强化中央政府对特定区域的治理。首先,通过设置中央政府部门在地方的派出机关,实现对特定区域的治理。诸如金元时期的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关,就是为了集中管理某一地区而设置的。而元代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行御史台则是为了“掌察一方诸路州县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之事”[3]179,都水监派往山东、河南等地的派出机关行都水监是为了“掌治一处水利之事”[3]179,宣政院的派出机关行宣政院则是为了“掌一方诸路州县僧、道教事务”[3]179。其次,为地方政府为了辅助、强化特定区域的治理设置的派出机关。以清代的同知、通判为例,同知、通判作为省一级政府的派出机关,除了作为协助知府办事的辅佐官吏外,“兼理民事,直隶于各省者,其职如各府、各道、直隶州之制,而品级则同。”[4]
(三)为了完成特定任务
中国政府设置了诸多派出组织、派遣官吏以完成特定任务,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中央政府通过设置派出机关,派驻地方以完成特定任务。以汉代的部为例,汉代县尉由中央任命,秩二百石以上,治所与县令、长异处,掌缉捕盗贼及更卒番上[5]。县尉以部相称,而且多分部而治[6],因此,部是中央派往县主要承担缉捕盗贼职能的派出机关。其次,地方一级政府设置各类派出机构,目的在于协助地方政府完成特定任务。诸如,秦汉时期的乡不是一级政权机构,而是县延伸至乡的行政组织……乡级行政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征税、司法、教化、治安[7]。此外,亭作为县派出的治安机构,设亭长,以禁盗贼[8]1534。可见,亭长的职责主要在于“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8]1534,即协助都尉管理治安,并负责接待往来官吏,监管官府文书,物资承传转递等事[9]319。因此,乡、亭均是秦汉时期为了完成特定领域的治理任务而设置的派出机构。此外还包括清代省一级政府的派出机关 “道”等等。此外,因事临时派遣官吏以完成特定任务也是派出管理的重要目的之一。诸如秦汉时期的啬夫、游徼、盐官、铁官、水官、工官等。汉武帝时期的诸仓令长、都水、搜粟都尉、榷酤、都农尉、农都尉、户田校尉、渠梨田官、北假田官、骍马田官、侯农令、守农令、劝农掾等。唐初的封禅使、九鼎使、册礼使、卤簿使、道桥使、知顿使、顿递使、礼仪使、山陵使、按行使、陵下使、应接使、节度使、观察使为中心的使职系统、市泊使、度支使、户部使、盐铁使、税盐使等。明代的盐司、茶司、茶马司、钞关、市舶司、铁冶所、金银铜诸矿及行太仆寺、苑马司等。清代的巡按御史、巡漕御史、巡视屯田、巡视江南上下两江御史、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巡盐御史、督理陕甘洮宣等处茶马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
总之,对于追求高度中央集权统一的中国政府而言,行政派出组织适应了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与统治,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适时实现国家权力的“上收”与“下放”的统治需要,从而成为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之一,并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我国国家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二、行政派出组织的特点
强化中央集权历来是中国历代政府所努力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如何能够进一步地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控制便成为中国历代政府治理的最高理念,从而也是行政派出组织的主要目标。中国历代政府的行政派出在这一过程中进行活动,并在管理活动中呈现出这一时期政府行政派出组织的特点。
(一)性质的虚位性
由于派出组织是根据上级派出政府的委派授权而产生,因此,行政派出组织不论形式如何,都不具有一级政府的“实”位性质,仅具有“虚位”。诸如形式各异的派出组织仅仅作为上级派出单位的代表,只能在上级派出政府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因事差遣在外的派出官吏,不论师出何名,同样也只能在上级派出机关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纵观中国古代政府的派出组织,无论是秦汉时期的监、游徼、亭,还是汉武帝时期的十三州刺史部、郡邸还是东汉魏晋隋唐时期的行台尚书省、唐代的“道”、宋代的“路”、金元时期的行中书省、元代的行枢密院、行御史台、行都水监、行宣政院、“道”、明代的督抚、巡按以及清代的“道”、同知、通判,无一例外,均只具有虚设的代表席位,代表上级派出单位进行活动。
(二)设置的权益性
派出组织的代表身份导致了其废立均无需对原有行政体制进行变革,较之于其他政府组织的变更更加容易,从而使得政府对于派出组织的设置抑或废除都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行政派出在中国政府的管理实践中往往被当作没有办法的办法,由此形成的派出组织大都具有临时性、过渡性、权益性的特点。诸如秦代的亭作为县派出的治安机构,除了负责地方治安之外还协助都尉负责物资承转工作,发展到东汉后便逐渐被废除。东汉时期的行台尚书省作为尚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行使尚书省的职权。唐代的“道”作为中央政府的临时派遣机关完成其考察地方政治、纠察政纪、兴办管理农垦事业、催办赋税、督理财政等任务,还有元代的行台尚书省等派出机关。此外,还有大量因事临时派出在外履行政府某项职能的官员。仅以秦汉时期为例,秦汉时期各地特设的主管盐铁、水、工等事务的官吏,汉武帝时期出于逐捕盗贼,治理大狱的目的而临时派出的绣衣御史,大司农派往各地的大司农部丞等等。
(三)管理的灵活性
政府机构也需要有灵活性来对复杂的迅速变化的情况作出反应[10]。中国古代政府行政派出过程中派出组织性质的虚位性以及组织设置的权益性,造成了行政派出不同于中国古代其他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大特色——灵活性。派出组织不属于一级政府,对于派出组织的设立与变更较之于普通政府机构更加容易,不需要变更原有的行政典章制度,不需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更具有效率。因此,事出则设,事毕则罢,成为我国行政派出组织的生动写照,同时,也为新的政府组织形式的产生提供了试验与最终成型的机会与可能性。如汉武帝时期的十三州刺史部、东汉时期的行台、唐代的“道”等均由最初的行政派出机构演变为一级政府。
三、行政派出组织产生的影响
(一)对行政区划的影响
纵观中国行政区划的发展历史,地方行政区划中“县”作为稳定的一级始终存在。“在中华帝国的晚期,最基层的一级地方政府是县衙门。许多县2000年来始终沿用同一个名称,并保持了大致不变的疆界……县是地方政府组织当中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基本单位。”[11]72而“省”、“市”、“乡”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其产生、演变均与行政派出组织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省为例,“省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和这个字在欧洲历史上的含义大不相同。在中国,省级政府是政治结构中最反复易变的一个部分。13世纪以前,所谓‘省’并不存在。介于中央和县衙之间的是巡府,这类行政机构名称在各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像宋代所设的12—15个‘监司’即属于这一类机构。这类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其主要职能就是对属下各个县实行监督,”[11]69即行政派出机构。可见,行政派出组织与中国行政区划的形成具有密切关联。中国历代政府利用自身虚位性、权益性、灵活性等特点以行政派出组织的形式在“虚”“实”之间变动,并对行政区划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中国的行政区划从最初秦始皇统一后开始的郡、县两级制、汉魏南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唐朝的镇、州、县三级制、宋朝的路、府、县三级制、元代的省、路、府、县四级制到明清的省、府、县三级,无一不是政府行政派出影响的结果。
(二)对监察制度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监察制度脱胎于行政派出组织。作为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为了监察组织在地方运行中既具独立性又具权威性,行政派出组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行政派出组织形成了中国历代监察机构组织性质的“虚位性”以及存在方式的“临时性”。为了及时发现、检举、纠察、惩戒地方官吏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利用行政派出组织灵活性的特点,在不增加行政层级的同时,通过派出的方式,设置结构精简的监察组织,成为历代中国政府控制地方的重要举措。诸如秦代的“监”、汉代的“十三州刺史部”、隋唐时期的“巡按郡县”等都是由中央临时派遣到地方执行监察职能的行政派出组织。其次,行政派出组织形成了中国历代监察机构的单线型垂直领导体制,即在领导体制上奉行“谁派出对谁负责”的原则。为了保证监察权的独立行使,监察机构大都采用“派驻”的组织形式,派驻在地方的监察机构既不属于地方行政机构,也没有固定于某一驻地,因此不受所在地地方政府的管理,有助于监察权的独立、有效行使。最后,行政派出组织形成了中国历代“以下制上”、“以卑察尊”的特殊的监察方式。由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机构直接受命于皇权,行使包括弹劾、纠正、审计、视察等在内的广泛的权力,因此往往官阶品秩低而权力、权限大,譬如明代的巡按御史最终由皇帝差点,而秦代的监郡御史,尽管官秩仅六百石,但有权监察郡守和郡内的所有官吏,在一郡之内具有最高监察权。
(三)对职官制度的影响
行政派出组织对于中国历代职官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派出这一组织形式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灵活性与易操作性导致了临时派遣官吏完成某项职能的活动层出不穷,对原有僵化的职官制度带来了活力,使得有才能者可以获得任用与升迁,重组了职官队伍,提高了行政效率;其次,派出这一组织形式的灵活性与较少受限性导致了诸使差遣的盛行,并对原有国家机构的职官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随着派遣官员的增多,不适应政务的机构,不予调整裁的官员撤造成了官吏队伍的膨胀,“各种名号的诸使也就遍布政府各个部门,完全侵夺甚至取代原有国家机构的职权。”[9]210仅以唐代为例,临时派遣使数量庞大并对国家正式职官制度产生影响,及至宋代诸使差遣制的普遍实行导致临时派出的官吏任命方式甚至一度凌驾于国家正式职官之上的现象。“正式组织表明了在集团内部存在着的主要的价值或态度,至少在集团初创时期是如此。这些态度塑造了集团的正式结构,集团的正式结构反过来为集团活动提供了渠道,也限制了其活动。”[12]可见,派出组织作为正式职官组织结构形式之外的补充形式,反映了中国历代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中皇权至上以及人治的鲜明特色,而这一特色又反过来对正式的职官制度造成一定的影响,形成了中国职官制度的一大特点。
总之,任何一种组织形式也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行政派出组织在具有其自身特色以及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该种管理模式自身的弊病与缺点,而它的缺点正是基于其自身的优点而产生的伴生物。代表性与权益性性造就了行政派出组织形式灵活的特点,同时,正是由于虚位性、权益性及灵活性使得派出组织较之于其他组织形式较为随意、缺乏规范,带有明显的人治特点,而这一点又与中国历代政府的家国同构的治理理念是分不开的。由于行政派出的权益性,使得国家在原有国家机构设置之外增加了众多仅具有代表身份的行政组织及人员,容易造成行政组织机构数量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病。此外,由于组织的存废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的制约,完全出于个人意愿,尤其在君主集权的人治色彩浓厚的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临时差遣官吏对中国官制的影响表现更为直接和突出。尽管临时差遣的官吏不在正规官制之列,然而其所拥有的权力却远远超出其所具有的正规官阶。由此,差遣制发展到宋代甚至成为任官的主要方法,“使典章规定的国家机构名存实亡,行政管理结构也就发生变化,国家机构职能处在不稳定的状况中。”[9]210-211然而,行政派出组织之所以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各种形式的演变均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随着政府治理的不同需要进行的,尽管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作为政府治理的有益尝试与方式,对于政府治理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并为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派出组织的设置、管理、变革等诸多方面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王 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 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5.
[3] 王俊良.中国历代国家管理辞典[K].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4] 高宗敕.清朝通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2210.
[5] 季德源.中华军事职官大典[K].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369.
[6] 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4.
[7] 徐 勇,吴理财.走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困境——县乡村治理体制反思与改革[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90.
[8] 范 晔.后汉书(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4.
[9] 韦庆远,柏 桦.中国管制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10]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
[11]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 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M].陈 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38.